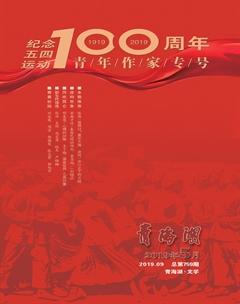石火敲光,虚舟长任风(外一篇)
马越
闲居自题
[唐] 白居易
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
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
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
时逢过客爱,问是谁家住。此是白家翁,闭门终老处。
我从云南带来的小青柑早已喝完了,所剩不多的,还有普洱,普洱味道浓烈、颜色奔放,从小饼上撕下一块儿来,喝一下午都能看见杯中跳动的棕黄色。这次去买茶时,相中了白茶和太平猴魁。在悠闲的午后,给家中花草浇完水,习惯泡一杯太平猴魁。这茶与自己妖冶张扬的长相一点儿也不相符,放入好几根也是清甜的味道,通常喝了几杯才会回过神来,齿间留的竟是它的香味。
喝太平猴魁,我一定会挑个特别安静的时期,手里乱翻的也会是文风比较平和的书。西北的宁静各有各的特点,拉萨的佛神情凝重,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和信仰不曾打破这座城市的神圣;敦煌的风一眼飘过,于阗的金银玉饰发出丁零丁零的响声;兰州的黄河依旧朝着固定的方向流走;而青海,在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居住的久了,甚至能背下来每条街道的广告牌、清楚夜晚的霓虹从何时替代夕陽,因为工作的缘由,每当在凌晨和这座城市碰面的时候,总觉得故乡在我眼前飘飘荡荡、摇摇晃晃,一种索求内心安宁的想法也会戛然而止。所以,我喜欢关注长安的一切,那里“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也或许白雪教人白头。
在长安的时候,志趣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诗人,可我们极少提白居易,大家都不说破。读过白居易野史的人,心里都看不起他“招妓买马”的勾当,故而每回读他的诗,总是下意识地去寻求一些“风花雪月”的证据。直到今天,我耐着性子想再了解他一番,几乎要被这位“老可爱”所打动了,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竟写下了15首自题诗。
据说唐朝官方认可的诗仙,就是白居易。后人却把这个名号冠给了李白。李白喜欢直言,痛苦、浪漫、奢靡、繁华这些极端的意象总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任意发挥、拿捏,后人读着他的诗,往往会有一种直击穴位的快感。李白一生的心事都在自己的诗里,没什么秘密,爱什么不爱什么、想要怎么过他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大部分作品,是掩盖了自我情绪的、低调的、含蓄的。抛开《长恨歌》《琵琶行》不谈,这位诗人,居然也有诗只写给自己、留给自己。
“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热月无堆案,寒天不趁朝。”从翰林学士到江州司马,再到刑部侍郎,宦海沉浮,这条路上的风霜雪雨和酸甜苦辣,都是他的冷暖自知。有多少个夜晚里,他都是徒对盈樽酒,无堆案、不趁朝这样的事,在旁人看来“应寂寞”,自己却觉得逍遥自在。
“野鹤一辞笼,虚舟长任风。送愁还闹处,移老入闲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让人感到幸福,老天将富我这个老头,我这个老头何处富有呢?——酒库不曾空。幸福的人总是唠叨又可爱的,微风深树里,斜日小楼前,诗人总爱携酒出游,坐着小船、脱下官服,摒除身外物,畅快地做自己。甚至把“渠口添新石,篱根写乱泉”也要当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记录下来。在某种程度上,白居易也和李白一样,在不断地寻找入仕和出仕的平衡点。
他审视自己风雨飘零的一生:“功名宿昔人多许,宠辱斯须自不知。”努力地劝慰自己,笑对得意失意。“马头觅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几时。”写出最经典的一句来识破人生虚妄,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句句触目惊心,读来甚是心疼这位“战战兢兢”的老人。许是觉得他代表了很多“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人,这类人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甩开所有痛快归隐,只能用一生的时光寻找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平衡点。当时的人们这才尊称他为“诗仙”,这种与浓烈繁华的长安格格不入的“清新”文风,让人觉得舒适又接地气。
由此看来,白居易并不是只有“招妓买马”、写写《长恨歌》的功夫,他可以坐下来,勇敢地面对自我、看见自我,加在身上的年龄筹码,只是时光的分量,自己依旧是想在平淡中过自己真正的生活。脱去官服后的诗酒人生,闲适中看清局势的他,早已勘破、自在。
“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
千年之前,白居易在长安农耕,自由自在,我一觉醒转,他一定在彼岸喝一壶茶,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
抬眼向窗外望去,山上的灰尘又落了些,这座小镇依旧在夜以继日地运转,清洁工一遍遍扫去烟火炮仗抖落的空壳,仿佛在扫掉某种虚无的热闹。雪也不再下,茶早就喝败了。在这世俗中陷得最深的人,却也是最早惊觉的人。
万顷风涛不记苏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写过的诗不多,除了记住他笔下“为有暗香来”的梅花,我深深记着这句他写给孟子的诗。
除了他,每个人面对穿越千年的知己,见诗如已晤面,在他留下的故事、字迹里,早已写着你想要的某些答案,早已经历过感同身受的事情,相似的灵魂隔空互相渲染,这才使自己有了一种勇敢继续的勇气和动力。人生不同的阶段,会和不同的古人成为知己,读词的心情也骤然不同。
吾亦有旧友,名叫苏东坡。
那年苏21岁,他的文章震惊世人,独步天下。世界比想象中的温柔美好,皇宫的阳光刺眼又温暖,苏在朝堂上刚睁开眼,如同千万意气风发的少年,对官场的阴暗和君臣之间各自拥有的难处一无所知,他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笔杆子就能把生活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哪怕周围有个“天命不足畏”、一心想要变法的王安石,他的内心从没有迎合过背道而驰的人或事。
当自己的政见、立场跟不合时宜的朝廷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自请出京,调任湖州知州。一句“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锒铛入狱,被贬黄州。这年,苏43岁。在那片荒凉无人的土地上,名震四海的文豪放下了最后一丝的清高骄傲,食不果腹,整天为薪米发愁,却还要劝自己“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门前能向西的流水,陡然变成了生活的鼓励和安慰,给予自己“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勇气。日子平淡失意却又被他过得有滋有味,不久,曾在“乌台诗案”中被自己牵连的好友王巩,被贬后北归过黄州,携柔奴前来看他。苏欢喜地迎接二人走进自己不大的房子,看着眉目娟丽的柔奴,肤莹玉,鬓梳蝉,明眸皓齿,一开口唱歌,没有绣阁幽恨,只有雪飞炎海变清凉的镇定气场,这个世住京师,没有去过任何地方的娇女子,以此动人的歌喉和美貌,定能在京师寻得更好的归宿,居然那么有魄力地在陌生的远方,陪伴着被贬谪的王巩,细心呵护着这个失意的男人。她究竟有没有怨过,有没有后悔过呢?
苏若有所思地盯着眼前“万里归来年愈少”的柔奴,柔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顿时感觉她微笑时都带有大庚岭梅花的香气。苏再也忍不住疑惑,从她的歌声中回神,清了清嗓子,试探道:“远方的岭南,偏僻荒凉,地处赣、粤交界处,跟随定国在赣生活的这几年,应该很辛苦吧?岭南应不好吧?”
苏给予了柔奴充分思考的时间,柔奴却看了王巩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苏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好像被击中了一般,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答案。俩人走后,苏一夜难眠,抬头看去,黄州的黑夜崭新得就像从未见过,从前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心境不再有,如今这苍茫夜色是那么的完整、宁静。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被贬北归的王巩还能如今日一样站在自己的面前,柔奴亦不虚此行,实在是“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白天到底是在问柔奴,还是在问自己呢?苏一直在试着跟自己和解、敞开心扉。
旧欢新怨,君臣一梦,今古空名。
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官场,乌台凄惨的鸦声已经在记忆中逐渐远去了,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曾恨命运: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想来还是浪费了时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柔奴之岭南,苏之黄州,不过就是一场随时会醒的梦。重要的是,需要自己心安,心安才能豁达。与其把生命浪费在抱怨和悔恨上,与其“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倒不如早些“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于是苏真的做到了,他安于清粥小菜、与高僧下棋悟道的生活,写文章练字,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不再患得患失。有了黄州的被贬生涯,哪怕早已人到中年,他才在真正意义上焕然新生,迅速成长为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他甚至像柔奴一样,从未把黄州当做自己一生的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永远在任何记忆和成就之前。
这个暑假每次读苏,我总能想起令我心安的长安,生活了四年的长安。从长安出发,又回到原点的距离是多少丈?究竟需要多長时间才能逐渐化解这种离开长安的不适感?当我每次投稿,都忍不住在个人简介里,像往常一样写一句: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那一刻,感觉自己仿佛还没有从这句话中醒过来,更不想删掉它,不想让它从此就这样轻飘飘成为一段人生阅历,那座诗意万分的城市,总是把我重重敲醒。
是的,我离开了。
长安,长安。但长久离开,吾心难安。
我怀念终南山余脉对面不大凌乱的506室,每日烹茶看宋词,面对窗外绿景从未觉得居室逼仄。怀念在白鹿原吃过的油泼面,带着那份厚实迅速走过兆鹏、白灵的一生,望着不大的县城、黄土、朴实的当地人民,感慨自己珍贵的闲暇人生,亦怀念在曲江散步、看画展、喝咖啡的安宁。
毕业不久前,我跟友人穿过不夜城,看着这座城市在黑夜中顾不得我的视线,逐渐在灯火中模糊的那一刻,竟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像小时候走丢了,晚上见到远处妈妈的身影。已经找到了,所以心安,所以幸福,所以,它早已是我灵魂的故乡。
现如今,当我无比抗拒着这座我已离开七年的小城,心心念念地想着长安,不禁害怕起来:我是不是正在与理想背道而驰,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转念想起老苏,逐渐与这种执念和解。不知是谁跟我说过,眼下的人生,才是如梦初醒。阻碍个人理想的,始终也是自己一人。
与其在30岁的年纪里恍然大悟,不如提前懂得,提前明白,乐观积极地取悦自己的生活。
那就不要老是回头看那些经历、故事了罢。
秋天来了,合上苏词,想起老苏“更须携被留僧榻,待听催檐泻竹声”的那场雪,便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回长安终南山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