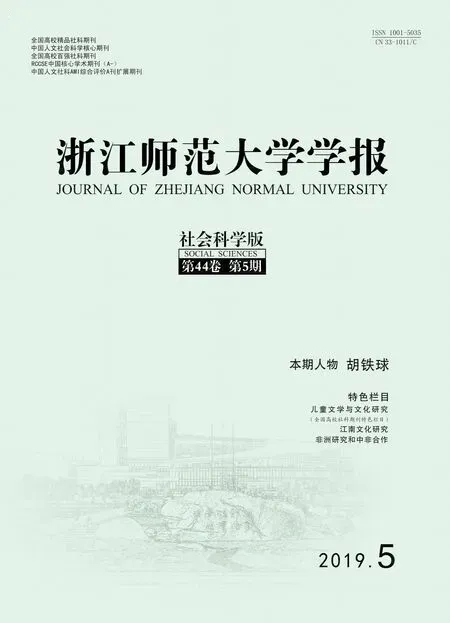吕叔湘先生“语体”观述略
张家合,殷晓杰
(1.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近年来,随着语法学者的介入,语体研究突破修辞学、语用学等研究领域,重新成为汉语研究的热点。语体视角在发现语言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语体因素对语法规律概括的影响、语体机制及其理论基础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功能语法学者更是把语体对语法研究的意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认为:“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1]
其实汉语的语体问题一直伴随汉语研究的始终,特别是语体影响汉语语法的问题,前辈学者已多有揭示和阐发,吕叔湘先生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吕先生当时的一些远见卓识、真知灼见,可谓当今汉语语体理论特别是语体语法理论的源头活水,而体现这些精粹思想的经典之作均集中收录于《吕叔湘文集》第4卷。①对这些经典论作进行重温和深读,体味吕先生的思想精髓,对当今汉语语体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是极为必需和有益的。
一、“语法”应与“语体”结合起来
何为“语体”?唐松波提出:“语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运用语言特点所形成的体系。”[2]近年来冯胜利又对“语体”作了最新的定义,认为是“指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而所谓“语体语法”,“指的是‘为表达某一语体的需要而生成的语法’。就是说,语法为语体服务,语体促生语法(或格式),于是形成语法和语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3]虽然吕叔湘先生并未对“语体”这一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却较早地指出当时研究不曾措意的一类语言问题,即“某些句式,某些虚词,用在某种环境很合适,用在另一种环境就不合适”,[4]164并提出可以将这类问题译为“语域”。吕先生所提的“语域(register)”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体”。之所以不主张“语体”这一说法,并非吕先生绝对排斥,而是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即当时距“管白话文叫语体文”的时代还很近,为避免概念表述上的混乱,吕先生启用“语域”的说法。换言之,吕先生已深刻认识到:语法研究应与“语体”结合起来,“语体”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围,这是以往探索得很不够的一个领域。
吕先生在30多年前学界不少人尚不知“register”为何物时就已首揭其谛,实在难能可贵。吕先生所谈的“我们”和“咱们”、表被动的介词、“和”类连词等语法现象与语体的关系,也已成为目前汉语语体语法研究的重要问题,且随着语体分类的不断细化,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语体”的语言解释力也越来越得到凸显。这个吕先生认为以往探索得很不够的领域,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潘文调查了不同书面语体中被动结构的使用情况,发现戏剧作品中“被”字句的出现频率比小说、散文、诗歌及政论文要低很多;“叫”“让”“给”字句只出现在文艺语体中,且主要分布于小说和戏剧作品中;[5]郭圣林统计了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不同文体里被字句的使用情况,结果表明这四种文体里散文中的被字句使用频率最高;[6]陶红印、刘娅琼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将一般认为的口语体又细分为自然对话(电话)、电视、电影三类,并调查发现,被字句的使用跟书面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然对话中的被字句远远低于其他语体,情景剧对话比较接近戏剧剧本语言,电影对白更接近散文和小说,进而说明(口语)语体细分对语法研究的重大意义。[7]
正因如此,语体语法的研究者们不止一次地呼吁:“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1]“要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在合适的语体里合适地解释实例”,[8]“如果语体语法是客观的存在,如果语体不同则语法也因之而异,那么现实中就没有不带语体的语法,就没有不关语体的合法性(grammaticality)”。“句法研究若不分语体,就如同方言研究不分文白异读一样,所遇到的现象必将一团乱麻。”[9]
吕叔湘先生在更早时候曾说过:“语法研究包括结构的分析和用法的说明两方面。句子的组织,词语的类别,这是语法分析的事情;某种语法格式,包括虚词,表示什么意义,什么情况之下用得着,什么情况之下用不上,这是用法的说明。”并指出,相对语法结构分析而言,用法的研究还很欠缺。[4]33
拿目前的实践来看,“语体”理论在发现语言事实和解释语言事实方面已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是目前推进“用法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二、语体功能与范畴、量级
对于语体对语言形式的决定作用,在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的解释。陶红印、刘娅琼提出:“不同的语言服务于不同的交际场合和目的,也可以说,不同的交际场合和目的决定了不同的语言形式,亦即修辞选择。”[10]冯胜利举过一个实例:
a.*昨天他买和炒了一只龙虾。
b.昨天他购买和烹炒了一只龙虾。
他认为在a这种非正式的口语说法中单音节的“买”和“炒”并列是不合法的,而b这种正式场合的句子中“购买”和“烹炒”的并列则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与之相适应,语法不同,则代表的语体性质和表达的语体功能也不一样。冯先生进而提出“语体语法”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形式—功能对应律”,该定律是语体研究的终极目标和鉴别标准。而“语体功能”指的就是“人们在说话时,根据交际对象、场合、内容以及听说者态度所选取的、决定交际关系(亲疏、远近或[±正式]/[±庄典])的语言形式的表意能力”。[11]对上述问题的认识,30多年前吕先生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将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比作穿衣服,什么身材就要穿相应尺寸的衣服,什么季节就要穿当季的服装,性别年龄不同也应选择材料花色不同的衣服,总之要适宜。[4]148
这个比方寓深奥的语体理论于穿衣这样的日常事务中,现在读来仍然如此地活泼、生动与贴切。冯胜利也举过类似的比喻,[12]二者所折射出的思想内核保持着高度的统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谈内容均属语言学上的语体得体和语体错位问题。具体而言,吕先生的“各有所宜”即当今之语言形式和语体功能相对应的“形式—功能对应律”,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和谁说话,说什么,怎么说,这些又恰好揭示了决定语言形式选择的四要素,即场合、对象、内容、态度。对四要素的提取,冯胜利引用拉波夫的阐释进行了说明,即人都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交际的产物,人类进行交际的基本方式就是运用语言来确定和调节彼此的关系,而场合、对象、内容和态度就是影响彼此关系的重要的交际要素,决定着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的搭配,即语体的结构体系。[11]关于语体的结构构成,按照冯胜利的新近研究,大致有三大范畴,即[±]正式、[±]庄典、[±]俗常:

图1 语体结构图
冯胜利认为:“语体范畴中的两个方面不仅是相反的,而且是相对的。……没有正式就没有非正式,没有通俗就没有古雅。”并据此提出“等级”的概念:正式有程度的高低,典雅也有量度的大小,且语体各范畴中的两个方面(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通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9]
其实,关于语体的范畴及其层级关系,2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就已言简意赅地指出:“使用语言随着不同场合而变化。这种变化从极其严肃到十分随便,是一种渐变,如果要分别,可以大体上分成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4]8虽是寥寥数语,却是一语中的,即语体是一个系统,且是一个渐变的系统;系统内是可以大体分级的。在吕先生的阐述中,“语体”的基本范畴和彼此关系已呼之欲出。随着今天研究的不断深入,“语体”量级的分别和测量,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实现,比如冯胜利、王洁、黄梅等研究者已经尝试给出了汉语书面语体庄雅度的量化方法和自动测量的方法,[13]其基本公式为:
庄雅度=(嵌偶词比例+合偶词比例+书面语句型比例+HSK丁级词比例+古汉语功能词比例)×20%
三、“语体”观照下的汉语史研究
吕先生在1940年代已指出语体和语言发展的密切关系,认为笔语(书面语)和口语是相对的,随着语言不断的变化,原先的口语也可能变作笔语。[4]74也就是说,词汇的替换、演变可能先在口语中发生,慢慢体现在书面语中。“怕”取代“畏”,“冷”取代“寒”,原因即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口语,这是词汇“口语度”的“历时替换”。可见,词汇的竞争与替换极有可能就是口语语体发展的结果。这种将语体与汉语词汇演变实例相结合的做法,直到60多年后才有学者重新谈起,比如冯胜利所举的“种/树”例和“合/应”例。[9]
从常用词历时演变来看,新词总是先在口语度上得到语言社团的认可传播开来,取代旧词在俗常语体中的固有地位,然后寻找一些突破口,慢慢出现在文人的笔下。一开始,这些太“白”的词总是很难进入高雅的文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地得到文人的默许,特别是能够在有影响的文人笔下用开之后,可能会迅速地在高雅文体中扩展开来,并在正式语体中与旧词“和平共处”,这种情况在口语中是无法想象的。之后,一些旧词又逐渐带上了庄典体的特征,如古为今用的词。旧词之所以继续存在而没退出历史舞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满足了人们或正式、或典雅的语体表达需要。文言在现代汉语里之所以仍有活力,是语体作用的结果。另外,汉语词汇中有些词异常稳固,千年未有更替,如“山”“水”等,意味着这些词的语体选择面广,属庄、正、口三体通用。如果把没变化也看作是语体演变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些词也应成为语体研究的对象,“不变”及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典雅和正式都是“交际定距机制”中的语体手段,但二者使用的语言材料及表现手段很不同:典雅往往采用古代的语词(如古语今用的“嵌偶词”)来实现,而正式则常常通过宾动倒置及泛时空化等正式化手段来实现,前者是历时的,后者是现时的。可见,古汉语词汇的语体演变是语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为汉语语体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素材,特别是对典雅这一语体范畴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如果说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研究还不够的话,那么把历时因素考虑进来的话,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在历时竞争中会有变动,且这种变动会有多次。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诸多个案即是很好的说明,如表“应该”义的“合”始见于西汉,而“应”始见于东汉;中古时期“应”在口语中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合”;然而到了唐代,“合”的使用频率明显提高,已跟“应”大体持平或略为超过,所以李善注引《世说》改“应”为“合” ;[14]直到元代,这个唐代的口语词“合”还在元杂剧中频繁使用,但已经受到“该”的强势挤压,口语度逐渐下降,慢慢退居书面语;“合”在今天又变成了文言词汇,同时“应”“应该”的语体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只有把这些演变的脉络描写清楚,才能更好地解释现代汉语同义单音节词(如“合—应—该”)语体不同或含同一语素的同义单音节词(如“应”)比双音节词(如“应该”)更具书面色彩的原因。
导致词汇演变的原因,不外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目前有关内部原因,又有词汇系统自我调节机制、内部更新机制等解释。“语体”也是促发语言演变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词汇演变特别是新旧词替换的原因,或许可以从语体角度找到新的突破口。
以往的汉语史及汉语词汇史研究,均较少考虑到“语体”这个视角,吕先生和冯先生的做法为汉语词汇的语体演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另外,仿古作品之所以定性为“仿”,伪造古书之终究被发现,最根本的原因即超语体文中必然透露出后时代的语言信息,这些蛛丝马迹足以被有心人按图索骥,破解伪造的谜团。
探讨汉语史上的语体及其演变问题,很重要的一样条件便是语言材料的选取,一方面是传统研究一直所认同的口语色彩浓厚的语料,另一方面亦应关注与口语相对的书面语体及典雅语体材料,因为口语语料在证实词汇或语法现象的口语度的同时,也需要书面语体或典雅语体语料来反证语言现象的正式度或庄典度——多出现于口语语体中说明该语言现象口语度强,反之则弱——继而通过考察书面语体或典雅语体来加强说明。吕先生对历史上口语和笔语的区别多有辨析。区分文言和白话,实在是件难事,但吕先生以“听得懂和听不懂”这一看似模糊的标准为这个连续统划出了一道界线,不得不让人佩服。而对历时文献的语体类别,吕先生也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对我们进行语体视角下的汉语史研究多有助益。比如他指出《论语》《孟子》大体上是语体,《荀子》《庄子》有超语体的嫌疑,《左传》《国策》里对话部分是语体,而议论部分应该归入超语体,另外,后世的《史记》《汉书》《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等都是语体的代表。[4]76
对历时文献的语体进行鉴别和探析,在吕先生之前是比较少见的,而这一工作在今天看来却是无比重要的,因为无法想象口语、书面语一锅煮的情况下,将如何展开科学的汉语史研究。在吕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之下,②语体的鉴别与划分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③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汉语史的发展。
余 论
经过最近十几年的努力和发展,“语体(register)”这个在吕先生看来探索得很不够的领域,如今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出路”,成为“打破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之间的界限、开拓整合型汉语研究的一个有希望的路子”。[10]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尤以陶红印、冯胜利、方梅、张伯江等国内外学者为代表。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用语体理论来观照古今汉语的不同,即语体对汉语史研究的启发性,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一些可贵的探索。如方梅从历时角度发现,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带宾语、“VP的”作定语修饰人称代词等现象最初都产生于特定语体,语法是在运用中逐渐成型、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塑造了语法;[15]张伯江通过考察《水浒传》中的无定主语句,提出“只见”一类词语的“兴盛”并不是属于某个时代的语言特征,而是属于讲说性语体的语言特征;有没有这样的标示主观视角的形式出现,不是语言年代的差异,而是语体风格的差异,这对传统的观察视角和研究结论本身都是一种突破和颠覆;[16]冯胜利更是颇具创见地指出:“汉语史上的双音化(如赵岐《孟子章句》),在新的语体理论的诠释下,就不仅仅是韵律系统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口语语体发展的产物。如果说语言演变无时不在,那么长期困扰语言学家的‘演变之源’的奥秘,也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语体或许就是直接导致语言演变的策源地。”[9]
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语体研究不单单要努力植根于现代汉语(语法),也要努力将种子播撒到广阔的古代汉语即汉语史研究中,只有打通古今、地域④的汉语语体研究,才能真正成为汉语研究的一条新路子。
注释:
①《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②主要有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56年1期)、胡明扬《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研究》1957年2期)、俞敏《白话文的兴起、过去和将来》(《中国语文》1979年3期)、任学良《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古书中口语和文言同时并存》(《杭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1期)、郭绍虞《再论文言白话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4期)、雅洪托夫《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语文研究》1986年4期)、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③主要有梅祖麟《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中国书目季刊》1980年14(2)期)、《从语言史看几种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汪维辉、[14]辛嶋静志《《道行般若经》和“异译”的对比研究——《道行般若经》中的难词》(《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五辑))、孟昭连《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南开学报(社科版)》2009年3期)、梅思《汉朝汉语文言中的口语成分——《史记》与《汉书》对应卷的语言学比较研究》、胡敕瑞《汉译佛典所反映的汉魏时期的文言与白话——兼论中古汉语口语语料的鉴定》、张美兰《元至明初白话口语——以明初《训世评话》文白新旧常用词为对象》(《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④冯胜利曾指出北京话的被动标志有“被、教、让”。第一个是正式的,后两个是非正式的。然而,对说南方方言的人来说,“教/让”听起来却比“被”显得正式。显然,这是地域不同或北京话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