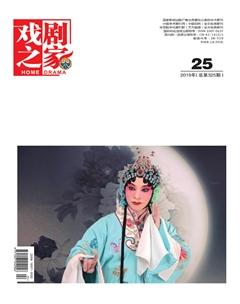由朱晓玫《哥德堡变奏曲》浅谈老子音乐美学思想
张轩卿 马向芬
【摘 要】本文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为基础,从著名演奏家朱晓玫所演奏的版本中浅析其中所传递出的音乐审美思想,并结合老子道家音乐美学观念,探究这位中国音乐家在演奏这首巴洛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作品时所追求的宁静致远、以柔克刚的至高音乐境界。
【关键词】老子;音乐美学;朱晓玫;《哥德堡变奏曲》
中图分类号:J6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5-0041-02
一、主要探究思想概述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尤其是其晚期身处莱比锡所创作的《哥德堡变奏曲》,更是因其规模之宏大,结构之恢宏的特点而永世流传。从巴洛克时期一直到现代,历史上不断涌现出各类非常优秀的钢琴家来弹奏这首作品,他们每一个人的演奏风格都各具特色,就在这些不同的风格之中,朱晓玫这位“钢琴隐者”在这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其中所体现出的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更值得国人去深入研究和探索。
老子,笔者认为他应该是中华民族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位思想家,就算到今天为止,也依然没有人能够完全地搞清楚他的生卒之年,甚至连他的姓名究竟是什么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有人说他首创了道家学派,可实际上据史料的记载,“道家”一词最早是在东汉早期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出现的。换而言之,在东汉之前的春秋时期应当是没有“道家”这一说法的,所以道家究竟是为何人所创这一问题,仍然是如同老子一样,充满了神秘与未知。当代的人们对于老子思想的发现与研究主要是从其最后所留的《道德经》中而来,而且老子本身其实并未对音乐美学思想有过专门的论述,我们现在对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解只是限于《道德经》中对于“音”的一些片段,如其中所提到的“音声相和”,“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而这里面对于音乐的理解早已不再局限于人耳的范畴,他将音乐上升到了人类的思想境界之外,进而直接从宇宙观的角度来阐述,即:万事万物本唯一。所以无论美与丑,好与坏,最终都是同一种本源,所以事物的本质并不在于复杂,一切都应顺其自然。而这种思想具象到审美上,就演变成了今天道家独特的“淡和”的审美观。笔者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也甚是浅薄,不敢随意妄谈,本文旨在就朱晓玫所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中所对应的“淡和”的美学元素进行简单论述,尝试从老子的美学思想角度来欣赏巴赫的音乐作品。
二、朱晓玫关于道家音乐思想探究
时光倒回到2014年的莱比锡音乐节,安静肃穆的莱比锡圣多玛教堂,当一位身着淡雅的玄色中式服装,干净利落的七分袖,褐色袖口,褐色衣领的中年女士,缓缓地侧身踱步到教堂一侧的钢琴旁时,掌声便此起彼伏地不断响起。没错,她就是朱晓玫,这样一位从出场便带着浓厚的中国元素的一位“钢琴隐者”。且先不论朱先生在这首乐曲中所展现的钢琴技巧之高超,单讲先生的妆容,笔者认为其中就蕴含着老子“淡和”的审美思想。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大体是在说,世界的本源都是“道”,所以万事万物又何须刻意追求那些所谓的华丽,那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一切从简,是为“淡”;相融于自然,相和于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又生于无,包容一切,是为“和”。而朱晓玫在圣多玛教堂演奏时的素衣素容正是将“淡和”的审美观体现得恰到好处。或许也是为了表达对历史上巴赫的尊敬,能够看得出来,当时教堂内的观众大多都是黑色的西服与长裙,然而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庄严与肃穆,那是一种西方贵族绅士风格所独有的肃穆,而朱先生身上所体现的“淡”与“和”,那是一种与自然相统一的协和,不温不火,不露锋芒,看似平平无奇,毫无个性,可实际上却是居后而争,以无而生有。正如老子的认识论中所提到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我们现在常讲的“和光同尘”,就是由此而出。归根结底,这还是在表达一种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万物同源,自然相融的崇高境界。所以笔者认为,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深植于心中“淡和”的思想,才能让这样一位淡雅无争的中国女性历经无数的艰辛练习与磨砺,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之上。
三、朱晓玫演奏《哥德堡变奏曲》风格简析
历史上选择演奏《哥德堡变奏曲》的钢琴名家数不胜数,但每一位演奏者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亦不甚相同。而谈到朱晓玫对于巴赫的理解,或许从她的演奏上就可以见得。在这里笔者认为,朱晓玫或许是找寻到了中国的老子与西方的巴赫之间的某种共性。其实无论是巴赫也好,老子也罢,这两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已经成为某个观念的代名词。如果说中国人对于宇宙的观念最早来自老子,那么乐界对于巴洛克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巴赫无疑。人常道:“一千位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算所有中国人对于宇宙和自然的认知都曾在无形中受到了老子思想观念的影响,可如今众人对于自然之道和宇宙依然有太多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又怎么能轻易地评价出对与错呢?所以由此看来,西方的巴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老子,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时代,留给了后人以无限的想象。万物都有两面性,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只不过是人们理解不尽相同,而更愿意见己所欲见而已。所以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不恰恰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吗?只是朱晓玫将她所理解的中国道家“淡和”的审美元素融合进了这样一首规模宏大,结构恢宏的巴洛克作品之中,使这样一首富丽堂皇的巨作收敛了棱角,更增添了几许圆润与柔和。
朱晓玫对本乐曲的处理处处都是那样的低调与温柔。譬如乐曲中第三变奏曲的一度卡农,此时乐曲情绪开始变得活泼,与主题沉思的心境做出对比。然而朱晓玫在演奏这一组时并没有像其他的钢琴家们那样处理得十分欢快,而是在快慢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仿若翩翩起舞一般稍快速中带着优雅,在乐风巨大的转变面前带给听众以足够的缓冲时间。在演奏到第四变奏曲时,开篇的三个单音在模仿间不断地跳动,与切分形成了一个情绪高昂的灿烂托卡塔,此时朱晓玫演奏时的触键也开始变得愈發的轻盈和干净。第十一变奏出现了大量的双手重叠演奏,音阶的交错、琶音的变幻和颤音的出现让听者不禁沉迷进了一个飘荡迷幻的世界。变奏十三又给听众们造成了一种画风突变的感觉,仿佛是心灵的升华,让听者由物质的感知上升到了一个缥缈而又崇高的心灵感知境界之中。此时朱晓玫对节奏的处理轻柔而节制,在自然而然之中表露出了一丝神秘与庄严。尤其在第十三变奏接入第十四变奏时,音乐情感的急剧变化似乎要把人从梦幻迷离的世界之中剥离,然而朱晓玫并没有把那种尖锐的下行音乐行进强烈地凸现出来,依然是缓缓地控制着,再次给予听众一个转变的时间。所以笔者认为,这些无一不是朱晓玫“淡和”的音乐审美思想的体现。
道家常讲“道法自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在论述一种“道”的存在方式,道就是自然,自然又是万事万物,万物有同源,本源又为“道”。所以由此来看,老子的道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规律,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自然而然。而想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其实是需要人们对道的把握上排除感性的经验,一切遵循本心,所以老子才会提出“涤除玄览”的修心之法,唯有“涤除”,才能在心中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上境界。因为从老子道学角度来讲,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所表现的一切都是虚无的,又何须劳神而费力呢?无即是有,有即是无,只需遵守本心,遵循自然即可。所以“涤除玄览”,其实就是要让人们把心放下,放平内心的一切杂念,转而用“道”来做判断,即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守静而制动,顺其规律而行。
所以,由此来看,朱晓玫的演奏风格不正是如此吗?这样一首80多分钟的乐曲,加上主题和变奏以及主题再现一共有32段,而朱晓玫从中间体验到的不仅是她的人生,她的性格,更是从其中找到了一种平和、舒畅与安宁。人们常说巴洛克风格是追求极致的华丽与辉煌,然而巴赫难道不像是中国的老子吗?他们都有两面性,就像佛教的众人总是在描摹着佛陀的微笑,道家的人们总是在追求三清之道,然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这个东西,哪有什么清楚的固定实体,但是它虽然恍恍惚惚,令人难以捉摸,可它本身却又可以具有形象,含有实物。每一个人所理解的“道”都不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敢放言自己能够完全地读懂老子,不是因为他所留下的《道德经》有多么晦涩难懂,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状态不同,每个人的理解和感悟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又何必去刻意追求。朱晓玫或许正是因为自身对于自然的把握与感受已经达到了化繁为简的境界,所以她才能够从这样一首宏大的乐曲之中把握住那一种安静祥和和宁静致远的美。她演奏时的状态,镜头数次切换到她平静的面孔,她的身体轻轻地伴随着音乐而摆动,她的触键轻柔之中暗藏着刚劲,急速跳跃的音符在她手里变成了一颗颗圆润的珍珠,就那么不慌不忙、本本分分地流出,这不正如同当今的道家所追求的守静而制动的“道”吗?当今的道家常常讲阴阳相合,其实就是在说万物都是两面性的,哪有什么绝对的极致,与其不断地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倒不如守柔静心,涤除玄览,在最自然的状态之中,去把握住真正的自然的“道”。
四、结语
老子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宇宙之外的东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老子究竟是谁,他究竟从何处而来?最终又去往何处?他就像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内的一个幻化,超越了自然而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人,留下了一卷《道德经》,骑青牛出函谷关,至此不知所踪,留给了世界一个又一个谜团。而巴赫,他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的追求,他的向往,如今早已随时代而隐藏,我们又何必要完全搞明白呢?阴阳相生,万物都有两面性,朱晓玫从《哥德堡变奏曲》中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巴赫,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巴赫”,一个满含着中国道家守静制动,以柔克剛,宁静致远的“巴赫”。
参考文献:
[1]修海林 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1
[2]苏琳.寻求内心宁静与平和的至高音乐境界——聆听朱晓玫《哥德堡变奏曲》随想 [J]. 北方音乐,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