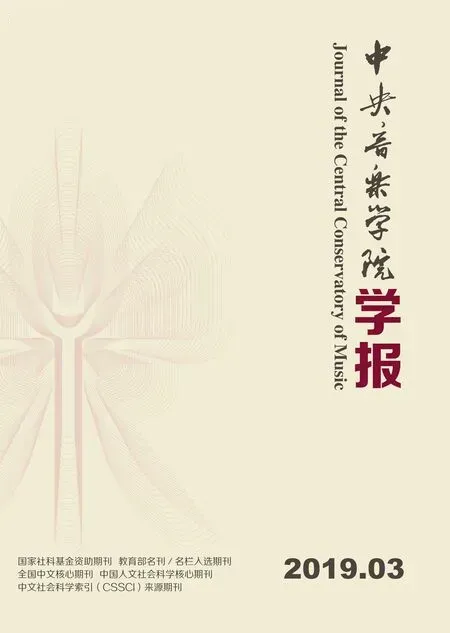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告别”叙事
张 晨
构建于文本之外的体验:思考死亡
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充满了哲思,包含复杂的内涵。他的作品从时代的洪流中脱颖而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是受到热烈追捧。深刻的写作特质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马勒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他的人生观决定了作品的基调。早期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的葬礼音乐类型是他孕育的雏形,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思索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他的作品充满了朝圣般的情感,但并非纯宗教性质,这点与布鲁克纳音乐中的虔诚相异。比如,《第二交响曲“复活”》中的“上帝”只是一种理想境地的代名词;建立于“圣灵降临节赞美诗”之上的《第八交响曲》也是以宗教为依托,但最终的出口是世俗精神——对人生意义的思索。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各具特色,其内涵随着作曲家思想的不断变化而愈加深刻。
如果说马勒早期作品中对生死的辩证思考是建立在兄弟早亡、父母去世之上,那么1907年这个转折则使他离死亡更近。中年丧女、自己由于疾病而如同新生儿般重新学习生活中的基础琐事,对于马勒的精神和肉体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双重打击。他意识到,死亡距离自己也许只有一步。也就是说,如果死亡真的降临了,他应该如何应对。他表示,“我对生的渴望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我还发现生命的特性比先前更为甘甜。”(1)孙国忠:《马勒交响曲的哲理内涵》,《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83页。马勒坚信复活和不朽,并完全同意哲人费希纳(2)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研究从“自上而下”的传统哲学思辨方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经验方式起着关键性作用。和诗人吕克特(3)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德国浪漫主义后期诗人。他是德国东方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将《古兰经》翻译成德语。马勒为其5首诗谱曲,集合为歌曲集《吕克特之歌》。对于生命的认知。费希纳的《死后生命手册》(BüchleinvomLebennachdemTode,1836)在当时流传甚广,在他更为著名的《阿维斯陀经》(Zend-Avesta,1851)中努力勾勒出一种超越的哲学并科学地证明“不朽学说”;吕克特是一位虔诚的抒情诗人。(4)Constantin Floros, Gustav Mahler,Visionary and Despot Portrait of A Personality,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GmbH,2012,pp.67-68.在马勒的思想中这二者的思维和气质同时存在,并间接地反映在作品中。
马勒的思想在20世纪初仿佛经历了轮回,早期音乐的反讽气质依然存在,但不再是主流。在病痛和丧女后,他必须重新思考生命,这促使他将早年的哲思做进一步提升。无法想象,对于马勒这样一个嗜工作如命的人来说,被病痛纠缠无法脱身是多么剧烈的折磨。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他真的准备好面对死亡了吗?可以说,马勒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现实。正如1908年7月18日,他在给瓦尔特的信中满含刺痛地写道:
灵魂的实质是什么?它的瑕疵是什么?我在哪里才能找到救赎?
……只有在这里,在孤独中,我才能恢复理智,重获知觉。自从我被恐慌和恐惧压倒,就一直在试图转移视线、不再倾听。如果没有找回自己的路,我必须向孤独的恐惧投降。但基本上我还是在谜中讲话,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会进入到我的内心并持续;但它就像你说的那样,肯定不是忧郁症患者对死亡忧伤的恐惧。我知道我一定会死。但是,我不想去解释或描述一些也许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我只想说,我一下子失去了我曾经努力想要达到的一切清晰和平静。在生命的尽头,我就像一个初学者,必须学会走路和站立。至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学一遍,这显然有些令人沮丧。我不能在我的座位上工作。内在的活动必须伴随着外在的活动。(5)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554.
信件的基调是悲凉的。瓦尔特认为:“他知道自己会死。但马勒随即会否认自己有对死亡的忧郁和恐惧,我们应该相信他。”(6)Herta Blaukopf ed., Gustav Mahler: Briefe (Vienna 1996); partial Engl.trans,Eithne Wilkins,Ernst Kaiser and Bill Hopkins as Selected Letters of Gustav Mahler,ed.,Kurt Martner(London 1979)376;Engl.trans.375(letters from Gustav Mahler to Bruno Walter,18 July 1908).转引自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69。“如何面对死亡”的想法从1907年夏天就萦绕着他,并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以往的状态。直至1908年5月,马勒依然沉迷于对来世的思考——关注歌德和《浮士德》,并认真研读歌德和埃克曼(7)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诗人和作家,因作品《歌德谈话录》而闻名于世,他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晚年生活的见证者。的交谈副本。这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书中的神秘主义气息吸引着马勒,他注意到歌德和埃克曼在1830年1月10日的谈话,那时的歌德大声读出了《浮士德》中的场景。(8)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87.可以说,“浮士德精神”开启了《第八交响曲》及之后作品的大门,包括面向天堂和救赎。马勒作品中大量关于爱、悔恨、愤怒及反抗的描述并未有详细的说明。“带着愤怒”“以最大的力量”是他演绎内心表达的谱面标记,它们在音乐中显示的不只是等待上帝召见而发出的叹息。他一方面试图直视死亡,另一方面选择逃避,乐曲在勇敢与恐惧中交替,希望与绝望相互平衡。(9)〔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庄加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97页。
马勒浓厚的哲思气质和对“下一个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哲学思考,他对哈特曼(10)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是叔本华哲学的继承人,意志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写有《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1869),他把意志作为世界的本源,把表象作为意志的向导。有关生命的继续与死亡意义的思索有着和谐的共鸣。1911年,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哈特曼的《生命的问题》(DasProblemdesLebens,1906)。哈特曼在最后一部分论述死亡,那些段落吸引着马勒。(11)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86.作者用如下思考开启他的章节:“在所有生命的背后,死亡像幽灵一样潜伏。为什么?凡是生下来的为什么一定会死?因为生命本身不死,乃是在新世代继续存在。”(12)Eduard von Hartmann,Das Problem des Lebens(Bad Sachs aim Harz 1906),s.289.转引自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86-687。在这章的末尾,哈特曼基本回答了困扰马勒的问题。哈特曼注意到,如果生命必须要经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转变,其结果是新一代取代旧一代,那么,“世界总是需要新的一代人以新的和公正的意识来适应新的条件,以便把进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13)Eduard von Hartmann,Das Problem des Lebens(note 38),p.309.转引自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87。生命必须以接力来延续,人类的精神需要信仰作为依托。马勒信仰更深层次的宗教,天堂和上帝的王国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更是一种需要,就像他的艺术是对这个信仰的呼喊。但普福尔(14)普福尔(Ferdinand Pfohl,1862-1949),音乐评论家,与马勒在汉堡时交往甚密。确定,在马勒内心仍旧有一种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在“啃噬”马勒,“折磨和质问他”。(15)Pfohl,Gustav Mahler,Eindrücke 58f.转引自Constantin Floros,Gustav Mahler,Visionary and Despot Portrait of A Personality,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GmbH,2012,p.141。
1907年以后,马勒愈发深入地思考生命与死亡。他的音乐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否能够吻合,音乐文本是否能体现他对世界的认知,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猜想需要大量的音乐分析来证明。也就是说,这些哲思究竟如何体现于他的音乐中,他的作品中究竟有没有这些观念的索引。如果说,《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中歌德诗剧、仿唐诗和人声的加入将音乐作为一种纯粹聆听体验的文本复杂化了,那么,在《第九交响曲》这部纯器乐作品中,马勒将人生最后的呐喊写入进去,在乐章的安排上设置了一个迷局。
《第九交响曲》的形式与结构:叙事进程解析
马勒于1908年冬天再次返回美国,1909年夏天完成了《第九交响曲》(1908—1909)的草稿,作品于1912年6月26日在维也纳首演(瓦尔特指挥),钢琴四手联弹曲谱出版于1912年,总谱出版于1913年。这是马勒再次回归到第五至第七号纯器乐交响曲形式的最后一部完整作品。浪漫主义晚期,对交响曲中奏鸣原则的坚守在逐渐失去真正的要义。虽然作曲家们依然使用奏鸣曲式,但是二元对立的本质已经淡化,四个乐章的构成框架也产生了松动,交响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6)孙国忠:《论马勒的交响思维》,《音乐艺术》,1988年,第3期,第83页。马勒的交响曲顺势而行,乐章的安排经常会突破规则。比如,《第二交响曲》有五个乐章,《第三交响曲》有六个乐章,《第八交响曲》有两个乐章。快慢乐章的安排顺序彰显出作曲家的独特设想,乐章的规模有时也不成比例。比如,《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非常庞大,等于后面五个乐章的总合。(17)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第329页。
《第九交响曲》虽然保持了四个乐章的形式,但其内涵和乐章间的关联模式已经悄然改变。它延伸了马勒早期作品对音色、结构和表达的关注,但在整体上不再受调性约束,每个乐章有单独的调式,在顺序的安排上也区别于一般的交响曲——它以“自在的行板”开始,随后用变形的连德勒舞曲作为谐谑曲,第三乐章是“回旋曲—滑稽曲”,最后以“柔板”乐章结束。(18)〔德〕沃尔夫冈·施雷伯著:《马勒》(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高中甫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四个乐章的形态貌似回到传统四乐章构架,但乐章的奏鸣性安排却已经完全不同,马勒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异化。中间两个乐章的安排非常独特,第四乐章以“柔板”替代了快板作为终曲。阿多诺认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可能建立于《大地之歌》的经验基础之上,放弃了奏鸣原则,他只是想通过他的整部作品来表现出潜在的准备好了的东西。(19)Theodor W.Adorno,Mahler: A Musical Physiognomy,trans.Edmund Jephcot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95.
《第九交响曲》的语言表述很有特点,这导致音乐效果极具个性。勋伯格在《古斯塔夫·马勒》一文中认为,“他的《第九》极其诡异。在其中,作者不再以他个人的身份发言,好像有一位隐藏在他体内的代表,用马勒作为他的发言人,他的喉舌。这部交响曲不再以个人的口气说话。我们可以说,它表达的是客观的——几乎是无激情的——对美的描绘。只有精神淡漠,不识肉体温存的人才能与这种宁静与豁达为伍。”(20)〔奥〕阿诺德·勋伯格著:《风格与创意》,茅于润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马勒的音乐语汇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音乐完全是心灵的悲泣。乐曲带来的聆听体验有一个核心的内容,但他并没有用标题的方式指出。格劳特和帕里斯卡认为,“音乐完全可以表现哲理性的标题,它很可能存在于许多没有被承认为标题音乐的作品之中。例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舒曼的《第三交响曲》、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以及马勒的纯器乐交响曲。相反,描绘性标题更难以同音乐本质上的抽象性相调和。当被描绘的事物是明确的和确定的,或设计自然音响的模仿时,产生一部仅仅是新奇的作品的危险就是最大的。”(21)〔美〕帕里斯卡、格劳特著:《西方音乐史》(第六版),余志刚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543页。对于马勒来说,文字或许是他构筑交响曲的基础,他的灵感会基于特定的文本之上,但绝不能反过来用文字解释音乐,因为他的音乐高于文字而建立了一个世界。
《第九交响曲》以纯器乐形式叙述了一个“死亡和与生命告别”的故事,马勒通过对记忆中经历的转变将四个乐章定义为不同的角色,形成叙事过程中必要的信息链条。从第一乐章开始处“告别”动机作为引入的“告别”赞美诗开始,到最后的“柔板”,角色变化的过程附加其上。“告别”动机的下行级进三音列像一声叹息,故也被称为“叹息”音调。整个第一乐章围绕该动机展开,低沉悲泣的情绪昭然若揭。在最后的乐章中,“告别”动机消失了,在嘲笑了一切皆为徒劳之后,“柔板”以一个高尚的、赞美诗式的主题为主导。末乐章以“告别”动机的缺席、用另一种方式讲述了“告别赞美诗”,“告别”也因此改变,从根本上转变了第一乐章的形式。从表面上看,两个乐章是矛盾的。(22)David B.Greene,Mahler,Consciousness and Temporality,Gordon and Breach,Science Publishers,Inc.1984,p.276.然而,音乐在不断发展变异中行进,从而达到最终异化的过程。
有关第一乐章的聆听体验,新时代的引导者阿尔班·贝尔格很有发言权。1912年秋,贝尔格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回忆《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整个乐章基于一种死亡的预兆,不断地重现。所有尘世的梦想都指向它,这是纤柔的乐段后跟从惊人的高潮的原因,像新的火山爆发。当死亡的预感变成特定的认知之时,在意义深远的、极度痛苦的生命之爱中,死亡以最极限的力量宣示……”(23)Alban Berg,Letters to his Wife,p.147.转引自Donald Mitchell, Discovering Mahler:Writings on Mahler 1955-2005,The Boydell Press,2007,p.498.这是乐章叙述的核心,沉思、哲理、慨叹引导整个生命进程。马勒以反讽的语汇展开中间两个乐章,但它们最终抵不过死亡的终点,相比冥思又显得那么浅薄。
第二、三乐章是整个叙事链条的中间环节,尽管不那么高贵,却必不可少。谐谑曲、滑稽曲的反讽特质让人想起了马勒早年的风格。舒伯特去世前半年写下了《a小调钢琴二重奏》快板乐章,它很简短,通常被视为一首未完成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他生命中这个时期创作的最令人不安的作品之一。舒伯特和他的出版商称其为“生命的风暴”。相比之下,马勒《第九交响曲》第三乐章像生命中的龙卷风,在空虚的喧嚣中描述了世界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敏锐洞察力。这个“生命的漩涡”是第三乐章的中心,它采取了怀疑的、讽刺的音调,音乐试图从中突破并获得自由。(24)Jens Malte Fischer,Gustav Mahler,trans.Stewart Spenc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16-617.“回旋曲—滑稽曲”追寻着a小调,与第二乐章的C大调是关系调。在第四乐章的结尾,马勒是否会将第一乐章的D大调确立为最终目标,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以对“生命”的肯定作为结束呢? 马勒向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创造者:简单的选择并不适合他。根据第一乐章强有力地阐述二元性的方式来看,选择D大调就意味着选择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因此,降D(比第一乐章低半音的调)进入视野。它不是一种普通的解决方案,而是马勒对艺术和生活的真实认识。马勒的艺术和生活就是如此——D大调不再可能。
如果说《第九交响曲》四个乐章表述了一个行进的过程,那么这个进程是极富戏剧性的。弗洛罗斯赞同门格尔贝格(Willem Mengelberg)对这首乐曲的描述:第一乐章的“告别”是与深爱的人告别;第二乐章“死之舞”是“必须进入墓穴”,因为你活着就会面临死亡,是残忍的幽默;第三乐章,绞刑的幽默,努力、斗争,但均不能逃离死亡,三声中部(trio)中的原始动机衍变为一个扭曲的理想;第四乐章是生命的颂歌,发自内心的歌唱,他的灵魂在唱着最后的告别歌:“再见!”他的生活是那么充实,那么丰富,但不久就要结束了!(25)Constantin Floros,Gustav Mahler: The Symphonies,trans.Vernon Wicker,Amadeus Press,1993,pp.273-274.在马勒的观念中,第四乐章“柔板”代表一个更高的形式。早在1896年的夏天,他就开始思考各乐章的顺序安排了。他认为,慢板相对小快板来说是一种“更高的形式”。他在那时已经决定以慢板作为《第三交响曲》的结尾。(26)Natalie Bauer-Lechner,Gustav Mahler in den Erinnerungen von Natalie Bauer-Lechner,Diary entries,Herbert Killian,ed.Hamburg,1984.s.68.《第九交响曲》的叙事方式直接反映出马勒的人生观。正如戴瑞克·库克所说,《第九交响曲》乃是“马勒的心灵暗夜;更令人感佩的是,他绝不轻向绝望低头。在终乐章痛彻心扉的感怀中,虽然历经了前三个乐章的种种惊恐和无助,马勒对于生命无法割舍的爱仍然破茧而出,而这必须归功于伟大的音乐能将相互冲突的不同情感同时并呈的特质。这首交响曲是诗人里尔克所称的‘终无所怨的生命礼赞’的音乐诗篇。”(27)〔英〕爱德华·谢克森著:《马勒》,白裕承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第四乐章“柔板”:无言的告别
在历史的过往中,众多音乐理论家尝试过理解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他们的阐释基本离不开“死亡”话题。比如,规多·阿德勒早在1913年认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在对生命的想象之后与其告别”,作品接近“死亡”;马勒的热情崇拜者威廉·里特尔(William Ritter)认为,《第九交响曲》的第一和终曲乐章可以用格言“死与变形”来概括;门格尔贝格认为,离别和死亡是乐曲的中心。(28)Constantin Floros,Gustav Mahler: The Symphonies,trans.Vernon Wicker,Amadeus Press,1993,p.273.但马勒究竟如何在音乐中思考死亡,如何用音符书写与世告别,直到现在仍旧是个谜题。这或许印证了音乐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言语。在马勒作曲的过程中,《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整部交响曲的感情出口,它以简洁的结构调节了复杂的材料来源。思辨式的音调和对死亡的高层次反思并不需要一个具有对比性的或者复杂的曲式来承担,它需要的是一个空间和过程。在塑造与第一乐章不同的死亡思考方式中,不稳定和声围绕主调的游离、和声与旋律半音化造成的矛盾是音乐进行的特质,它以自身的累积不断地凝结与推进。
在第四乐章“柔板”的开头,弦乐组以“很慢速且更加节制”(Sehrlangsamundnochzurückhaltend)的基调演奏了前10小节,这是纯粹的冥思音响,音乐上的悬置和凝固展现了更高的表达境界。主题来源于两个材料——回音音型和一个下行的音调。马勒早在《第四交响曲》中就使用过回音音型,他运用过去的材料制造了一个新的主题,但与此处回音音型更密切相关的音调应当追溯到《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四乐章新的回音动机引导下的下行哀伤音调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情怀,这与旋转的华尔兹塑造的形象完全不同(对比谱例1a和谱例1b)。
谱例1a.《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第261-272小节(29)Christopher Orlo Lewis, Tonal Coherence in Mahler’s Ninth Symphony,UMI Research Press,1983,p.55.(华尔兹)


谱例1b.《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柔板”第1—6小节

第四乐章“柔板”开头的两个材料均来自于第二乐章(见谱例1a和谱例1b中标注的两种不同形状的对应标记)。第一小提琴极慢速演奏的回音音型并不是装饰,迂回的旋律特质奠定了整个乐章的基调。第二乐章的华尔兹以回音音型塑造出动态的舞姿,它随着节奏的律动飞驰狂奔。第四乐章的开头两小节(见谱例1b),小提琴在无任何乐器共鸣的情况下独自奏响,声音略显干涩。上跳八度后的回音音型接继续上行小三度,不给人丝毫的喘息机会;降C长音带来的悬置紧接下行音阶,这个旋律大调带给人痛苦的体验。“柔板”的主题是复杂的,它在第3小节运用了弦乐组合唱一般的配置,并将第二乐章舞曲般旋转的回音音型完全转变为沉重的凝思。在如此慢速、凝固的进行中,回音音型的回转原形几乎认不出来了。
终曲乐章以毫不畏缩的情感奏出了第3小节的下行音列,它是哀伤的。下行的音调暗示了下沉的情绪,含混地表明了降D大调。以这个动机为起点,马勒编织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第3—11小节)。第二个阶段(第17—25小节)回答了音乐在开头提出的问题。“告别赞美诗”另外两次出现于该乐章第49—87小节和第126—147小节,它们是第一主题复杂化的新阐释。第28小节起的升c小调主题作为一个对比的因素在情绪和调性上体现出不一样的温度。升c小调的乐段比起开头赞美诗般主题的稀薄和麻木是更丰富和热情的。格林认为,开头的降D大调首先建立起一个目标,使音乐一直向终点的降D大调移动并保持一种持续的力量,音乐暗示着最后的告别语,丰富的内涵建立起动机与意义的联系。半音和声的出现使音乐的色彩更丰富了。尽管生命之流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并充满了漩涡,但这个过程是有趣且有价值的。半音进行对调性和音乐进程有些干扰,但从未削弱降D调。(30)David B.Greene,Mahler,Consciousness and Temporality,Gordon and Breach,Science Publishers,Inc.1984,p.276.
乐章中埋下的伏笔令人惊讶,超出了一般的写作模式。在第一主题中的第11小节,马勒以大管独奏插入了一个由两个拱形的小乐句组成的材料,它打断了第一主题悬浮的、飘忽的模式。在第28小节的第二主题出现时,这个材料成为主题的开端。由于降D与升C的等音关系,这两个音调的音响竟然是相同的,这次由低音大管演奏。但是它们的调性性质却迥异。这个音调演绎了第二主题的重要因素并被发展。它如同固定旋律,一直持续在主题形象的塑造中。
第49—87小节是第一主题的不断复杂化,依旧保持了降D大调,回音音型是一个重要因素。第88小节,调性直接并置进入四个升号的调,与E大调天堂的梦想相关,这里的情绪明显与之前不同。第89小节英国号奏响了温和的旋律。它的开头延续了第二主题的升c小调,并发展了其材料。第107—125小节的第三部分发展第一主题的材料,以其建立了高潮。第126—158小节的第四部分是第一主题复杂化的新阐述。第159—185小节构成的尾声来自第一主题并摘引《亡儿之歌》第四首,它以逐渐消失的死亡意象作为结束,成为全曲最终的答案。
对于“柔板”的独特设计,作曲家有自己的构想。它与之前的作品构思有些许联系,但完全从属于新的叙述对象,服务于新的叙述内容。关于《第九交响曲》的写作方式,马勒认为:“这部交响曲用最长时间说了一些我的预言。作为一个整体,它最接近《第四交响曲》,但完全不同。”《第四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和《第九交响曲》的“柔板”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回旋曲般的主题复合体的交替和对比,它们都接近“逐渐消失”(morendo),但有细微的区别。在《第四交响曲》的“慢板”乐章中,“逐渐消失”是在结尾部分,这与“天上的情绪”相对。在《第九交响曲》的“柔板”中,“逐渐消失”成为整个乐章的线索,至少出现了八次。(31)Constantin Floros,Gustav Mahler: The Symphonies,trans.Vernon Wicker,Amadeus Press,1993,p.295.
《第九交响曲》终曲乐章展现出与第一乐章完全不同的意识转化过程,包括在最后的告别语中对“界限”的暗示,引导意识进入一个新的存在空间。中间两个乐章清晰而戏剧化地促成转化,它们的加入引导第四乐章得以进一步阐述。在结尾,转换在“逐渐消失”的找寻过程中实现。可以说,第一乐章引领听者进入对超然冷漠世界的想象,听上去比第四乐章更加激进,甚至包含了与未来的相关联系,即使未来是不可实现的。它书写了斗争和渴望的过程。第四乐章以意识上的根本转变回答了中间虚无的乐章,强调了没有希望的行为之后的意义,并用“完全—不完全”的结束勾画了对未来的空想。(32)David B.Greene,Mahler,Consciousness and Temporality,Gordon and Breach,Science Publishers,Inc.1984,p.294.结尾在现在和未来的矛盾中延展。
通往天堂之路:进入未知领域
马勒通往天堂之路的设想在终曲乐章完成,第四乐章“柔板”的结尾展现出一个独特的叙事过程。在《亡儿之歌》的引导后,乐曲于第171小节进入了最后一个旋律音——第一小提琴的降A音。这个长音从持续到逐渐变短,展示了消逝在远方的断续存在,并以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演奏的回音音型作为另外一个因素引导“逐渐消失”的进行。这里的“消失”是意味深长的,它蕴含了“涅槃”的观念。首先,高声部的第一小提琴是主和弦五音旋律位置,并没有做出肯定的完结回答,音符时值的不断缩短与空拍的介入造成了渐行渐远、逐渐消失的体验。此处音乐陈述的意境作为引导的因素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其次,回音音型在第172小节和第179小节的第二小提琴声部制造出“逐渐消失”的体验,因为第179小节再次出现的回音音型已经是不完整的了,它在下方的辅助音上停留,并在空拍后才出现中心音。随后的两个长音进行代表着这个音型的消逝。中提琴用回音音型的节奏拉伸暗示远行,并在最后一次拉长的回音音型中运用倒影方式给人意外之感。它代表一些可变的因素,或暗示在“逐渐消失”之后孕育着更多可能。在《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回音音型虽然与前两个乐章有相似的外表,但材料存在新意。终曲乐章“柔板”的告别,通过回音音型完成了自由变异的进程。这里的结束不是通过自我肯定的方式来完成。在这个乐章结束之时,变异的回音再次指向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来实现自身意义。最后,力度上的“逐渐消失”(pp-ppp-pppp)和速度上的“逐渐消失”(rit.)都经历了很长的渐变过程。节奏的拉伸形成“未完成”之感并带来一个开放的结尾,暗示对“美好”的畅想和寻求(见谱例2)。
谱例2.《第九交响曲》“柔板”第171—185小节(33)Gustav Mahler,Symphony NO.9 in Full Score,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3.


第171小节降A音到达,它在延续至下一小节弦乐组奏响之时形成了三个层次:低音的下属框架、六级上的回音进行、主和弦的五音到达,这是完全不协和的,强调的是“自我”的横向进行,而非纵向带来的音响,表达出复杂的意境。随着第173小节主和弦的到达,乐曲更明确地出现了终止。高音的降A音是真正的目标,它不是一个暂时的替代品,对它的延长和重复寓意走向平静。但是,降A的平稳和音乐的建立并不是完全稳定的。基于感官上的完整性和降A音作为一个自身完满的音,听者会感到这个结尾有些复杂,是基于一种不完满的完满。它的指向是未来,提示了预兆与从未实现,在平静中包含着欢乐和悲伤。降A音建立了一个目标,进而取代主音降D作为终结,此处非主音的结束指向了之后还未发生的事。
基于回音音型动机来创造是马勒源于古典浪漫之根并富于创造性的写作模式。此处的音乐不仅令人想起了美,也预知了一个乌托邦的领域——传统动机的遗迹和回音的死去,从而暗示一种在阳光下继续行进的步伐。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页用旋律的碎片作曲,不仅唤起了这个乐章中更早的瞬间,还有他更早的作品。提取出的短句为马勒专有,它从过去事件的记忆中制造当下的经验观念。阿多诺对马勒作品的这一写作方式特别敏感,这是他用来比较马勒的交响曲写作和小说技巧的基础。阿多诺认为:“当他出于正式的理由重复过去的材料时,他没有赞颂那些过去的碎片本身,而是力图在疏远中忘记它们。已存在音乐的变体宣布了过去不可能再复原。”(34)Robert Samuels,"Narrative Form and Mahler’s Musical Thinking",Nineteenth-century Music Review,8(20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53.旧材料在新时代、新语境中生发出新意义。马勒此时寻找创意的途径已经改变,他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
随着《第九交响曲》单薄的、断续的、无人间气息的、“逐渐消失”的结束,温暖的音响再一次表明马勒的信念——死后生命的永远存在。(35)李秀军:《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61页。马勒用这个结尾叙述对美好天堂生活的期许,即将告别的此生孕育着温暖的来世,他运用虚无朦胧的配器将听者引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对重生的美好理想。马勒对人生与下一个世界的思考可以通过《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体现出来,结构上的寓意似乎比他对“永恒”与“告别”动机的摘引更有意义。马勒晚期交响曲开放的结尾点燃之后作曲家对非闭合结构的认同,这是新的音乐形式和理念诞生的萌芽。《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结束调比第一乐章开始调低了半个音(D大调——C大调——a小调——降D大调),该手法在《大地之歌》中曾出现过。这种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表现痛苦的艺术手法被马勒借鉴。而在第五、第七号交响曲结束乐章中调性移高半音的手法,与马勒表现肯定的内涵情绪有着内在的象征联系。(36)同注,第251页。同时,前进的调性原则是将调性溶解进入泛调性的第一阶段,预示着十二音系统的可能性。(37)Dika Newlin,Bruckner·Mahler·Schoenberg,Norton Company,1978,p.201.
马勒对调性的安排是为了获得表达螺旋式上升内容的途径之一。调性的“前进”动摇了中心调性的地位。这是调性松动、不断突破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与《第九交响曲》的“告别”故事息息相关。格林认为,相似的类比可以提及勋伯格《钢琴曲六首》(op.19)中的那些开放终止,它不仅寓言了最后音符的可能性结果,还让人感觉到其它音符最终将脱离作品而不完全发声。像马勒的终止一样,勋伯格最后的音符不是通过调和调性被建立;与马勒不同的是,勋伯格的作品都未建立在调性基础上,包括它的结尾。(38)David B.Greene,Mahler,Consciousness and Temporality,Gordon and Breach,Science Publishers,Inc.1984,p.279.新音乐的诞生离不开传统的土壤。作曲家的技术手法与其欲表达的想法有关,做法体现于技术上的设置,进而形成隐喻。
结 语
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形成了一个叙事过程,乐章的安排可看作从“思考尘世的死亡”“丑陋的魔鬼狂舞”到“对天堂的憧憬和到达”一系列进程。第四乐章“柔板”是一切观念的提升,是最高层次的思考。《第九交响曲》与《第三交响曲》有着微妙的联系,不仅仅是因为“柔板”都延续了布鲁克纳式的传统,情绪的相似远比表面形式的相似更加深刻。这两部作品都起始于提出上帝之爱,但《第三交响曲》的结束是狂欢式的,《第九交响曲》则是在一种温和的顺从情绪中结束。
对死亡的思索和与人世告别是《第九交响曲》的叙事主题。这与作者的经历、想象相关。马勒通过音乐——一种区别于外在说明的形式——表达了在生命尽头的思考。这种表述方式其实已经萦绕了他多年。在创作《第二交响曲》时,他的“标题观”便已经确立。1901年12月18日,他在德累斯顿写给阿尔玛的信中指出,《第二交响曲》的节目单是“写给一个肤浅的、头脑简单的人读的,那里面涉及的仅仅是这部作品中最为外部的、完全表面化的东西”。他认为,即使是“启示录”也是最多揭示小部分真理,“直到最后,作品本身和它的创作者为一般认知所曲解。”(39)〔奥〕古斯塔夫·马勒著:《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曹立群、庄加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80页。马勒的交响曲放弃了风靡一时的标题音乐形式,试图在纯音乐的叙事中达到文学无法企及的生命力。
马勒对标题的观念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是一致的——“更多地表现感情,胜过表现图画。”他在谈到《第二交响曲》的诞生时写道:“在孕育这部作品时,我从未想到这一个过程的细节,我关心的是一个过程的感情。”(40)〔德〕沃尔夫冈·施雷伯著:《马勒》(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高中甫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并升华,他用纯音乐叙述了一个隐秘的“告别”故事。纯音乐写作在摒弃说明文字的同时提升了自身魅力,更加引人深思。在对马勒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中,对音乐文本的分析应首当其冲,这符合他拒绝标题的初衷。用音符来说话,是马勒延续贝多芬、瓦格纳作曲理念的精华,《第九交响曲》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作曲是一个设密的过程,分析是一个解密的过程。作曲家的音乐符号形成了密码,等待后人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