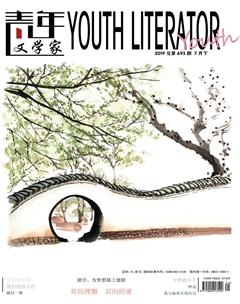消失的父亲
作者简介:蒋文娟(1998.1-),女,江苏泰州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03
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基本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早逝,二是出轨。她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风格相近却不雷同的父亲,《白围脖》与《墙上的父亲》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通过讲述父亲的故事,讲述自己;通过审视父亲,进行自我审视;通过分析父亲,进行自我的精神分析。”[1]
一、父亲形象原型
“消失的父亲”是鲁敏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人物形象,《戒指》、《白围脖》、《墙上的父亲》、《逝者的恩泽》等多篇小说中均有一位正值壮年却猝然离世的父亲,他们的早逝往往与出轨经历密不可分。诺斯罗普.弗莱曾说:“我所说到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整合起来。”[2] “不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稳定性的象征、神话、意象等,它根源于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之中,将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并体现出文学传统的力量……文化传统通过原型而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体现,文学批评可以通过作品中的原型追溯历史渊源。”[3]鲁敏在散文《以父之名》中坦言,自己的父亲正是小说中众多父亲形象的现实原型。
《以父之名》是鲁敏对于父亲的回忆:鲁敏的父亲出生于苏北农村,但他天资聪慧考取了南京的大学,毕业后顺利留在南京工作,成了村子里响当当的人物。虽然父亲已经在南京工作,但他的婚姻大事仍然由父母做主,他的妻子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这就注定他与妻子在精神层面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不光是妻子,甚至整个家乡都与父亲有着莫大的隔阂,所以父亲只在春节回家,并且与妻女鲜有交流。在南京时的父亲邂逅了一位能够与他心灵契合的女性,并不顾一切地沉溺其中。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父亲显然犯了“生活腐化”罪,两次劳改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鲁敏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失怙者”,父亲的消失给她的青春期抹上了一层黯色。她理所当然地将出轨的父亲视作自己痛苦经历的始作俑者,并加之以道德层面的讨伐。可当她真正开始知晓爱情为何物时,却选择了理解父亲,甚至同情父亲,因为她明白“生而为人,完全的不落灰,或许也是不真实的吧”。[4]她在散文中详细描绘了一件小事:父亲曾因鲁敏想吐掉一块难以嚼烂的油渣而发怒,先是责骂,继而用皮鞋踢她的腿。虽然她知道父亲并不一定是真踢,但她已经“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5] “油渣”事件给鲁敏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6]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墙上的父亲》,就会发现有这么一段文字“她记得,饭桌上,妹妹夹起一块猪油渣,不小心掉到桌上,她捡起来放到嘴里重新吃,但嚼不烂,再次吐到桌面,父亲瞥了一眼那烂糟糟的油渣,突然放下碗筷,离桌而去。”[7]由此可见,早年生活经历对鲁敏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父亲形象的塑造,还是小说细节的刻画,都有她早年生活经历的影子。
二、父亲:勇士抑或神明
“缺席的‘父亲成了想象的诠释之地,欲望的寄托之所。父亲这个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是联接家庭与外界的纽带,在鲁敏的小说中同样一般地表现为纽带的断裂,于是生活窘困、不安,精神乃至心理、生理的跳动不安都成了叙事中盘旋不去的支撑。”[8]《白围脖》与《墙上的父亲》虽然都是描述父亲消失后对女儿的影响,但两篇小说各有其侧重点。
《白围脖》讲述了女主人公忆宁突然得知父亲的死讯,与母亲从家乡奔赴南京处理父亲的后事,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日记与围脖。父亲留下了两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忆宁对性对情感的全部启蒙和引领”[9],第二本日记则成为了“父亲偷情史的备忘录”[10]。由于少女时代的忆宁固守着是非分明的道德观,因此第二本日记显然让忆宁难以接受。等到忆宁结婚时的1997年,整个社会对于婚外恋显得格外宽容,三年后忆宁也陷入了父亲当年的困境:是选择枯燥乏味的婚姻,还是选择新鲜刺激的出轨?怀着深深的好奇忆宁打开了父亲的第二本日记,随着阅读的深入,她逐渐发现原来父亲在为世人所不齿的“婚外情”中获得了纯洁无瑕的爱情,而这种纯真的爱情正是此时的她极度缺乏的。至此父亲的形象从令人唾弃的“背信弃义”者转向令人崇拜的“追逐真爱”者,忆宁也渴望能够像父亲一样在出轨中寻找到真挚的爱情。前文中提到的“白围脖”正是父亲与“小白兔”纯真爱情的证物,“小白兔”为了能够得到这条白围脖不惜以离婚为代价“离就离吧,离婚算什么,婚姻对我从来就没有一点意义……但我一定要去看看你爸爸,我们前后有十年没有见过面呢,这最后一面我不能不见,哪怕全世界上的人都来指责我嘲笑我,我也会拼死去见见你爸爸的,对你爸的死,我相信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绝望:我们不在一个天空下了……”[11]作为一个被惯认为虚情假意的“第三者”,“小白兔”却在父亲死后依旧如此痴情,这不得不让忆宁感叹父亲这段婚外戀的真挚纯粹。父亲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来了一段真诚的爱恋,就算他的肉体已然消亡,可他的灵魂依旧是饱满充沛的。忆宁开始效仿父亲,“精神既然已经没人能够顾及,肉体的忠贞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与崔波牵强附会一次吧,就当是真的有爱情在婚外翩然降临吧。”[12]她接受了崔波的求爱。在与崔波的婚外恋中,“忆宁觉得自己跨越了少年时期对父亲的那种单纯的怨恨,相反,忆宁觉得自己现在已与父亲处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战壕,忆宁正在不顾一切地用行动试着为父亲诠释并平反。”[13]她在心中不断地追问着“父亲,我们谁更有破坏力呀,谁更有创造性呀,谁更能够战胜虚无赢得永恒呀。”[14]父亲对此时的她而言就是一位追逐真爱的勇士,她效仿父亲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像父亲那样用一种充满破坏性的方式——出轨来寻得真爱,并在真爱中赢得永恒。现实很快给了她迎头一击,崔波之所以会与她婚外恋纯粹是为了报复自己的妻子,“人家崔波是在跟老婆赌气呢,没你什么事儿,最多拿你当枚子儿在跟老婆下战棋呢……”[15]原来忆宁渴望的真爱只是一段虚假的情谊,她以为自己在愚弄别人,殊不知自己才是被愚弄的那一个。小说以忆宁哭着喊出“爸爸,我想你”作结,忆宁想的并非是早逝的父亲,她想的她渴望的其实是父亲与“小白兔”间的真挚爱情。
如果说《白围脖》中的父亲是一位追寻真爱的勇士,而女儿也正是受了父亲的感召才会去寻找真爱,小说的焦点在于爱情是否真挚。那么《墙上的父亲》则更进一步,父亲的形象从平易近人的“勇者”上升为遥不可及的“神明”,在现实与回忆的交错并行中,读者得以一窥女儿丧父后的成长历程,也更能理解女儿一系列异于常人的选择。《墙上的父亲》中的王蔷有着与其他待嫁女青年卓然不同的婚姻观:“婚姻的本质,就是一桩精心算计的事务,得‘划算、‘超值,像在汪洋中搭乘一去不返的舟楫,尽可能装上母亲、妹妹,以及更多的东西……”[16]她喜欢比自己年长的男性,排斥浪漫与纯洁的爱情,甚至认为“任何与爱情有关的念头都是天真的罪行。”[17]为什么王蔷对爱情会有这样病态的认知呢?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父亲的早逝。父亲的早逝使得母亲及两个女儿过早地认识到生存之残酷。母亲身上的端庄与柔弱随着父亲的去世一并消失,她不得不忍背恶名与各种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借此获得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尽管这一举动给女儿们带来了对劣质情感的粗浅感知,她们以为“人与人的关系,天生就是相互利用的,就是‘恶的,就是靠不住的……”[18]没有了父亲的家庭,生活注定是贫困窘迫的。母亲为了节省支出,想尽各种办法去占厂里的便宜。无论是用工厂的食堂来蒸自家的饭还是母女三人集体长途跋涉去厂里灌热水,都给王蔷带来一种“讨生活”的卑下感。困窘的生活使王蔷对待婚姻的态度变得十分功利,她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得结婚,得带一个腰缠万贯、顶天立地的男人进入这个家庭,改变一切……”[19]终于她找到了老温,虽然老温比她大得多,但她毫不介意,甚至甘之如饴。她随身携带着父亲的小照,并不是为了怀恋,而是以此为道具增强自身的神秘感,从而成功吸引男人的注意。老温就是因为父亲的小照才注意到她,他与王蔷“以父亲的小照为起点,在爱情的幌子下,定下某种基调:失怙者与年长者、渴求着与施予者。”[20]王蔷与老温并不是因为爱情才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是纯粹的交易,老温以物质为筹码换取了王蔷的陪伴,王蔷则以青春为筹码换取了老温提供的优渥生活。嫁给老温,等于是将自己一家三口从生活的泥淖中拯救出来,尽管她并没有得到爱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王蔷极端厌恶与父亲关系融洽的女生,但她却热衷于偷窥別的女生与父亲撒娇玩闹的亲昵场面,哪怕她要在潮湿污秽的厕所里待上很久。后来当她去看心理医生时,心理医生犀利地指出“你情感高度营养不良,你总想知道更多的情感内核,你不得不偷窥……对家庭情感模式,你存有深深的怀疑和拒绝,你患上了情感洁癖症。”[21]在读者看来,心理医生的这番话不无道理,甚至十分准确,可是王蔷却对此大为恼火“去他妈的精神分析,谁能贴近所谓的心灵深处,什么前因后果,什么无意识下意识,见鬼去吧,我们姐妹俩的往事,我们的悲欢,我们的灵魂,从来就不是复述的能够分析的!”[22]心理医生透彻的分析在王蔷看来是对自己及家人的嘲笑与侮辱,她们之所以在旁人眼中如此怪异,还不是因为这该死的生活,谁让它是那么的拮据贫乏,她们只能挣扎着去过日子,这其中有多少辛酸,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对于王蔷而言,父亲离开后,生活的基调就是苦难与悲伤,母女三日省吃俭用,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因为她们已经形成了心理定势“在没有父亲的屋檐下,就得紧紧贴着地面……”[23]《墙上的父亲》中的父亲虽然也是因为出轨而早逝,但他却无法像《白围脖》中的父亲那样在死后成为女儿精神上的引路人。他以“遗像”的形式存在于家庭生活中,最大的功能无非是让母亲对着遗像排遣她心中的愤懑之情。他被挂在冰箱上方,整日注视着家中的一举一动,可他与这个家之间却有着巨大的隔膜,王蔷甚至都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关父亲的记忆。成年后的王蔷甚至当着母亲的面询问父亲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的女儿,母亲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他这个人,从我跟他结婚,就一直很淡的……所以,我想,在他心里,对你们,肯定也是好的。这个你要信。”[24]父亲好像高高在上的神明一般,冷眼旁观着他的至亲在俗世里挣扎求生。母亲经过多年岁月的摧残,曾经的风华已消磨殆尽,可墙上的父亲却几十年如一日的眉清目秀。相框将父亲与母女三人隔开,母亲与王蔷姐妹的生活愈是困窘不堪,相框中的父亲就愈发显得自在潇洒,这巨大的反差使王蔷感慨万分“父亲啊,你是不幸之身,亦是冷酷之人。我们生下来就已经失怙。我们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父亲,父亲是一辈子的生字。”[25]王蔷不知爱情为何物,而且她也不需要爱情,她以无爱婚姻为代价换来与猥琐现实的媾和。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墙上的父亲》将视角聚焦于“爱情是否必要”。
无论是《白围脖》中的勇者,还是《墙上的父亲》中的神明,父亲的形象始终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消失的父亲”给女儿带来了程度不等的情感创伤。爱得虚伪也好爱得无能也罢,这都是情感创伤的不同表征。女儿始终无法正常去爱,这将是她终生不愈的“暗疾”。
三、审父背后的意义
鲁敏在一系列小说中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审视,揭示了丧父对于女儿精神世界的残酷影响:她们永远无法真正去爱。曾有批评家认为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模式化”的,“他们虽然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但在小说结构方式上却如出一辙。”[26]不过鲁敏自己认为这并非“模式化”,因为这些父亲形象是“在同一母题下的多角度书写,或者在同一系列下的,群像式的分部展示,跨时空角度的呼应与书写。”[27]应该说鲁敏的审父是成功的,她在审父的同时也发现了当代人情感世界的空虚与贫乏。《白围脖》中的崔波对忆宁有关爱情的讨论态度冷淡,反复用“爱情不需要语言”来搪塞,不禁使忆宁发出感慨“完了,这是人类的共同退化:大家都不会爱了,只会做爱。”[28]现代社会物质资源的丰富使人们逐渐忽略了内心对真挚情感的渴求,拜金主义的盛行暗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现代社会金钱对人的吸引力远大于爱情。大家都不会爱了,真挚的爱情成了遥不可及的幻影,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粗劣情感里虚与委蛇,精神世界一篇荒芜。这无疑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暗疾”,鲁敏在作品中直截了当地撕开它,“夸张地变异地呈献给大家看,但不负责‘解说或‘解决。”[29]高明的小说家从来只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鲁敏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现代人的“暗疾”所在,并将其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这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也为她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增添了一层独特的社会意义。
注释:
[1]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说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99.
[2][加]诺斯罗普.弗莱著.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42.
[3][法]丹纳著.艺术哲学[M].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0.
[4]鲁敏.以父之名[J].人民文学,2010(3):196.
[5]鲁敏.以父之名[J].人民文学,2010(3):194.
[6]鲁敏.以父之名[J].人民文学,2010(3):194.
[7]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82.
[8]程德培.距离与欲望的“关系学”——鲁敏小说的叙事支撑[J].上海文学,2008(10):88.
[9]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65.
[10]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65.
[11]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1.
[12]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73.
[13]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75.
[14]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75.
[15]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5.
[16]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71.
[17]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86.
[18]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79.
[19]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70.
[20]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85.
[21]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207.
[22]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208.
[23]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92.
[24]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212.
[25]鲁敏.取景器[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212.
[26]孟繁华.历史、主体性与局限的魅力——评鲁敏的小说创作[J].扬子江评论,2008(1):80.
[27]鲁敏,姜广平.“我所求的恰恰就是‘不像”[J].西湖,2009(3):100.
[28]鲁敏.纸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77.
[29]何平,鲁敏.“把虚妄定作这一生的基调”[J].东方文化周刊,2017(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