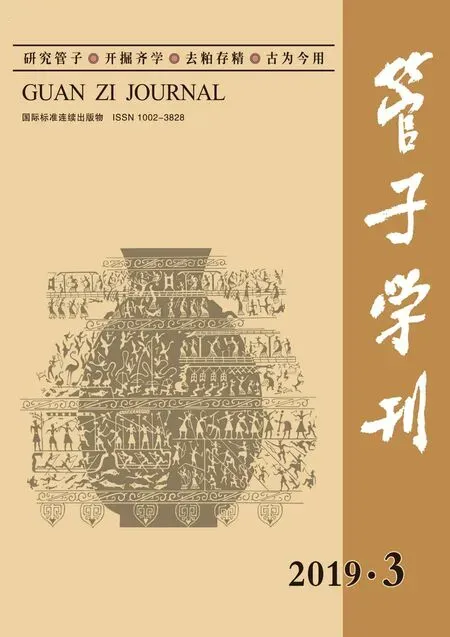历史与当下的合理对接
——读《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藏 明
(邢台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西哲的“形质论”,重形而轻质,而中哲的“文质论”,文质相佐,孔子的“君子之论”(《论语·雍也》)即为力证。儒家肇于先秦,其说立足于自然而然的人情现实,注重礼对于人类生活的提升而使人以区别于禽兽,但并不是使人区别和超越于自然,而只是以有序的自然之质,区别于无序而混乱的自然之质(1)吴飞:《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国家焦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97-198页。。但儒学之质具有“和而不同”的属性(2)张岂之:《论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从血缘到地缘,从家庭到国家,儒家在不断建构、更新着自身的秩序蓝图,虽然批驳之声也不绝于耳。如《商君书·开塞》将古代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了上世、中世、下世,其中,上世被亲情主宰、中世被道德主宰、下世被法政主宰,与法政相比,亲情与道德正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儒家学说是否真如道、法等家所说得那样,其弊在爱私、无制、怠事,并修饰以蛊世?
一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儒家——原则上是指那些与汉和汉代后历代王朝的官僚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特性是介于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之间起平衡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儒教的这种‘中庸’特性使它特别地适合于长期存在,亦即在漫长的官僚社会中充满了活力。”(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61页。儒家的这种“中庸”特性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演化的?这些都可以在由李友广、王晓洁合著的《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4)以下简称《传道与出仕》。一书中找到答案。此外,儒者在传道与出仕之间不断地困惑着、调适着,但却使质与文之间始终尽量保持着平衡,对于这一历程进行诠释,能够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与难题的合理化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帮助。
《传道与出仕》一书以西方社会学的共同体理论为视角,在避免“文化简化主义”“夸大差异性”“追求趋同性”等中西比较弊病的前提下,立足于文献分析,从儒者在成为儒者之前所经历的生活场域以及礼仪传统入手,不仅描绘了早期儒家鲜活多彩的形象,又探寻出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的伦理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考量先秦儒家的价值立场、思想主张、行为方式、政治游说等,揭示了儒家试图以德性方式介入政治的艰辛历程以及在构建政治文化秩序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儒家学说虽因无法见用于世而屡遭碰壁,但在求学问道的过程中,儒者逐渐突破了血缘共同体(家)的限制,进入了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形成了“道德共同体”。王道政治既成为了先秦儒家最鲜明的政治理论特色,又成为了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特性。
作者在书的封面内折页上写有言简意赅的内容简介,其内容如下:
相同的早年经历,道德学识产生的威严和志同道合的性质让儒家群体呈现出共同体的结构特点,而儒家群体在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又始终贯穿着传道的历史使命与出仕的政治诉求。传道是对王道理想的维系与弘扬,出仕则是为了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儒家共同体的形成借势于先秦社会的宗法伦理性特点,但其传道与出仕又具有公义的应然诉求,这在客观上便对共同体本身的结构特点造成一定冲击。当中国历史由王权社会进入皇权社会,汉代儒生在治经与面对中央集权时因立场、态度所发生的分化而使儒家于先秦时期所具有的共同体特征在此时逐渐被弱化乃至被消解,则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命运。
本书正是以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为视角,以传道与出仕之间的张力为线索,对先秦儒家共同体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层解析。
短短的两段文字,其实已经简明扼要地梳理与交代了先秦儒家共同体的形成背景、特点及其变化。正如内容简介所言,儒家学派之所以在先秦会形成共同体式的群体,是与先秦社会的宗法伦理性特点,弟子们相同的早年经历,孔子道德学识产生的威严,以及在学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志同道合性质(始终贯穿着传道的历史使命与出仕的政治诉求)。可以说,儒家所传之道既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与思想渊源,又有着对于现实社会的深沉人文关怀。与此同时,儒家的出仕也不是随意的,而往往是以有德有位的舜、周公等历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为出仕为政的范型的,同样也充分彰显了儒家在政治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历史性维度。
在此基础之上,该书进一步指出,先秦儒家的政治追求是建立在对三代政治秩序及文化推崇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损益的前提下,儒家对于三代文化究竟了解多少?“真正的儒家不是要毁坏儒学,而是要揭示出儒学更早期、更真正的层面。在此过程中真正有趣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儒学之源却越来越支离破碎。由此,任意诠释的几率大大增加了。”(5)[德]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吴德祖、韩雪临、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271页。尽管先秦儒家对于三代政治进行了重新诠释,并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施政能力,甚至还预设了政治制度,但在面对“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面时,儒家却凸显了意志力上的漠然与无力,以及社会地位的尴尬(6)[美]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索》,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然而,在先秦儒家看来,干政行为无论成功与否都不会减损道的绝对真理性。成功的干政行为自会不断地验证理想的正当性和不可置疑性;而于干政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挫折、失败则正突显了道的可贵性和超越性(7)李友广、王晓洁:《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可见,儒家传道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出仕的挫折而受损,而是坚守着“从道不从势”的底线。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书伊始的《导论》中,作者结合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先秦儒家的研究走向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学界对于先秦儒家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社会学的路径日益受重视,这是作者针对以往儒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作出的考量。作者认为,以往的儒学研究,存在着过分模式化的思维倾向,如此则导致了儒家价值、身份、地位、情怀等多面向的弱化、模糊甚或丧失。作者主张,要从历史情境与元典精神入手,试图发掘或者说恢复先秦儒家在其时的社会生活中所本有的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生动之形象。二是,注重比较性的思维与方法,这是作者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时代特点的积极回应。作者认为,“比较”的理想状态是具备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大的比较范围(可称之为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若果真拥有这样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的理论思考与学术成果便在思想的纵深性与视野的广阔性上非常值得期待。三是,借重出土文献进行研究,这是作者对于学界新近出土文献材料研究前沿的把握与肯定。《传道与出仕》一书,是作者在之前郭店楚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对于出土文献的价值与作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作者结合学界的研究现状,并对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归纳,得出结论说:“郭店简的发掘的确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但就目前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状况而言,其不足以改写相关学术体系的发展历程。”(8)韦政通:《董仲舒》,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作者对于郭店简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定位还是比较谨慎的,并主张需要对出土文献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整理、清理与研究过程,方能真正发挥出土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作用。可见,具有全书总览性质的《导论》对于先秦儒学的研究现状是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的,它对于学界研究动态的梳理与归纳,相信对于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学人会有一定的启示与帮助。
二
当然,《传道与出仕》一书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先秦,而是将儒家共同体政治挫败的痛楚、群体的焦虑延续到了汉代,借以阐述在大一统政权下,儒家所做的自我调节,以及在传道与出仕关系上有别于先秦的特点。该书以中央集权政治权力作为着力点,来论述汉代儒学悄然发生的变化。首先,作者将汉代的儒者分为了三类:“第一类儒生,面对即将到来的出仕机会,他们选择了坚守王道理想与道德立场,对于治世者他们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以此来维护儒家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主要发生于中央集权体制确立的初期,尤以鲁地的那两位儒生为典型代表;第二类儒生,诸如叔孙通、公孙弘辈,要么因为经历过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而调整了对于自身的定位与角色期待,以急于干政、急于获取当权者赏识的心态去拥抱政治权力(以叔孙通及其儒生弟子、所征鲁诸生等人为代表),要么由于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威严深有体会而选择了以明经、解经作为通往仕途的工具与手段(尤以公孙弘为代表);第三类儒生,既感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与皇权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同时又不愿放弃儒家一贯的王道理想、道德立场和尊严气节,在这种情形下,这一类儒生往往通过明经、解经这种较为缓和、含蓄的方式来隐晦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主张和王道理想,以尽可能地回避与皇权发生直接的冲突和交锋,这就包括辕固生、赵绾、王臧、董仲舒、鲍宣、眭弘、夏侯胜、卢植、赵岐等人。”(9)李友广、王晓洁:《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第186-187页。于此,叔孙通等儒者看到了体制正在发生的变革以及为他们所带来的可能性的调整机遇,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们在文化秩序需要重建的时代成功地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对于自身身份、定位的调整,成为了汉帝国官方哲学的首席代表,在文化秩序的重构中占据了优先的地位,使得先秦百家争鸣、互诘互融的文化大繁荣局面,逐渐变得趋于稳定,归于一统(10)李友广、王晓洁:《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第167页。。其次,汉代儒学的伦理法则由先秦的双向转变为了单向,并出现了“移孝作忠”的倾向,部分儒者为了实现王道政治而妥协。最后,出现了政治反转伦理的现象,家庭等私人领域也被权力所笼罩,儒家缺乏制度建设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强悍的汉帝国面前发生了质变,政治开始归化王道,王道也浸染着现实政治。大一统政权的确左右着儒学的发展,但这一影响却是双向的。在汉代,如何使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相结合成为了儒者们首要解决的问题(11)韦政通:《董仲舒》,第145页。。而治世者同样需要一种学说来维护帝国的稳定。“汉帝国建立,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儒者必须持续证明儒学对帝国的贡献,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国的过程。在‘以秦为鉴’,寻找替代严刑峻罚的治国方略成为共同的思维模式下,儒学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稳定体制的功能,确实很容易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12)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但是,儒学独尊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动荡的政治秩序中,作为传统官僚政体的中国,“君王在治政过程中总是起着积极的、有效的、政治的作用”(13)[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164页。。武帝、章帝的确成为儒学发展节点上的关键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与帝国不断改变、不断磨合、不断渗透。吕后废除挟书令后,典籍复兴,经学始昌。叔孙通制礼,才使得儒学与帝国政治初步结合。而韩婴试图构建既独立又从势的士人集团,未果。直到董仲舒注释经典,明微言大义,构建起了内容广博、鸿富的,天人互动哲学体系,才使得儒学的相关批判功能得以恢复。到了东汉,《白虎通》则将师友等非血缘关系纳入到了儒家的伦理范畴,从而使得儒学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术界往往以汉代儒学丧失先秦儒学之道德性、杂糅谶纬之学、心性成德之学衰落等理由来否定汉代的儒学。但《传道与出仕》一书并没因“枉道而从势”对汉代儒学进行批判,而是以“传道”与“出仕”作为判断标准,对汉代儒家共同体中的儒者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分别论述了三类儒者在“道”与“君”之间的彷徨与游离,以及他们在儒学理论发展、大一统政权构建等方面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向我们展现了汉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形态。
“在谈论儒学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应该由儒学的性格、儒者进入体制后带来的影响,以及统治思想发展的需要去解释,而不应局限在道德理想的角度去看待。”(14)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第11页。即便西汉出现了叔孙通、公孙弘等突破“从道不从君”限制的儒者,但是,儒学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公孙弘以丞相之尊,将儒学水平的高低作为了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吏、师的角色也发生了互换,学者和官僚二种身份兼采,开始成为士大夫们最重要的特征。”(15)袁德良:《思想史视野中的公孙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儒学经过不同儒者从不同方面(文献、经义、制度)的创建,逐渐成为汉帝国的官方哲学。但是,“通观古今中外,学术与现实政治,必有一相当距离,使其能在社会上生根,学术乃有发展可言,政治乃能真得学术之益”(1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所以,两汉开创的儒学发展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儒学在获得政治权力支持的同时,政治的锋刃势必也会侵蚀到儒学的独立性价值与尊严。
三
《传道与出仕》一书深度挖掘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从儒者群体的整体属性出发,来探讨环境与儒家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借以阐述儒家对于实现王道政治所做之努力。“人的本质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取决于他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传统中的自由创造。”(17)[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序》,阎嘉译、冯川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儒家共同体在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完善着儒学,创造着理想中的王道政治。
首先,人是社会的存在,“人首先是一个社会存在,才能达到文化的存在”(18)[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序》,阎嘉译、冯川校,第13页。。乡村生活、礼俗传统塑造了先秦儒家共同体的本初性格特征,而先秦的社会环境又为此种性格平添了些许政治意蕴,儒者由礼俗的践行者演变为政治的参与者。其次,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作为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是年轻的,作为过去文化的产物,他是古老的。”(19)[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序》,阎嘉译、冯川校,第14页。先秦的儒者既崇信三代的政治文化,又期许能够将其运用到当时的社会当中去,古今的矛盾碰撞并没有让他们丧失信心,反而使其结成了牢固而又持久的共同体性质的学派团体。
再次,人是传统的存在,“传统对人的制约力量是强大的,但传统又是可变化的。传统的保守性和人的创造性是一对矛盾,创造力最伟大的兴盛时期是在一种文化的中间发展阶段。”(20)[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序》,阎嘉译、冯川校,第13页。对于王道传统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共同体内部的分化,正是由于儒者对于王道政治的不断修正,才有儒学在汉代的一统。最后,人是历史的存在,“人的一切繁衍生息、社会活动、文化创造都是历史的,但人作为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却是永恒的,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自我救赎与解放、自我教育与突破同样是永恒的”(21)[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序》,阎嘉译、冯川校,第12页。。社会变迁、政权更迭,但儒者修、齐、治、平的目标却并没有改变,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在追寻王道梦想的历程中,使儒学更加得多样化,更加得色彩斑斓。
《传道与出仕》一书虽极为重视儒学传统性与连续性之间的裂变,并试图探寻儒者在这种裂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裂变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但该书并没有放弃对于儒学能群特质的探寻与考索,“孔子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道德论者,而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者则不太注意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他们极为重视个人价值的独立实现,并认为超越原则需建立在自我实现的巅峰基础之上,被创造的世界也与他们相异。”(22)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戈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始终以共同体作为视域来探究儒学的发展,进而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贯穿于儒者的传道与出仕,该书未对其进行二分式的解读(23)李友广、王晓洁:《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第102-103页。,更加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从先秦至两汉,道德律令在家与国之间的流动,以及儒者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将道家道教的新近研究成果附录于后。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有着作者对于“道”“德”等理论范畴的考察,有着对于这些范畴在先秦时期发生变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不仅如此,作者还希望读者在阅读完附录于后的研究成果以后,能够从道家的视角或者说“由道(家)入儒”“由道(家)观儒”来发现一个更为立体、丰满与多元的先秦儒家群体和儒者形象。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用心,而且还反映出了作者的治学范围与理论视野在逐渐走向拓展与深化。
结语
在传道与出仕之间不停游走的儒者,促成了“中庸”特质的形成,其发端于先秦,初定于汉代,成为了儒家适应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政权的重要法则。当然,儒者的这种徘徊不定并非割裂了价值理想与日常行为之间的联系(24)李友广、王晓洁:《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第196-197页。。东汉末年,“政权崩析,当时社会上最具势力之士大夫既不复以国家社会为重,而各自发展与扩大其私生活之领域”(2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1页。。即便国家不复存在,儒者同样可以通过礼玄双修,将价值理想践行到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当中去(2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33页。,进而确保了质、文的相胜相合。即便爆发了安史之乱,李华在《质文论》一文中仍极力避免质与文的失衡,希望通过道德的生活方式,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秩序的重建。而《传道与出仕》一书,正是通过还原儒者形象演变的历史,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中华文化中“质”与“文”的互损、互补,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古之文化源远流长的内因,力图做到有益于当下社会发展与民众文化生活的提升。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