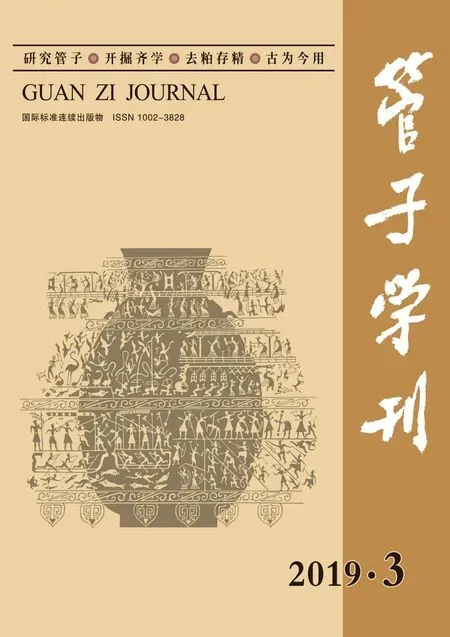略论中国传统“义”观念的当代意义
——以荀子“义分”思想为例的批判与反思
王成峰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一、正义与义:中西观念的差异
“正义”(justice)是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讨论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中国学术界谈论的“正义”范式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挖掘资源,试图通过一些中国文化思想内的、与西方现代“正义”(justice)相对等的观念,来阐释中国本土的“正义”理论。“义”与“正义”(justice)在语词表征上的相似性,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对应性(1)黄玉顺曾指出:“不同民族语言系统的语义之间,既存在着非等同性,也存在着可对应性。”这既是不同语言概念之间比较之为必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沟通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用“正义”来翻译“justice”,多少也表明了其与中国文化中“义”在某些内涵上的对应关系。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因而中国传统中的“义”观念作为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在“正义”话题趋热的过程中,也越发的受到重视。且不说中国传统中的“义”观念与西方现代“正义”(justice)观念之间的对等性或对应性能否成立,只要我们还因循着现代西方“正义”(justice)的框架,那我们在本土传统思想中寻找到的资源也只是在谈论现代西方“正义”(justice)而已,而且这种谈论的方式充斥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因而也极易受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指责。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核心旨在构建一套公正的制度,正如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的:“当代政治哲学关于正义的各种主流理论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沿袭了一个共同的方法——‘社会契约’方法。……这种方法的突出特征是将对某个社会的‘公正的制度’的描绘作为正义理论的主要使命。”“当代政治哲学中基本的正义理论——不仅来自罗尔斯,还来自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ck)、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戴维·高蒂尔(David Gauthier)以及其他学者(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契约的内容上看法各异)——都将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社会契约作为其核心。……但他们都将正义理论视为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2)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现代西方正义理论是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谈论正义的,其基础是人人自由平等的观念,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即使直面现代生活,现代西方在正义的诸概念之间还经常相互冲突、对峙(3)麦金太尔在《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就详细论述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正义概念的诸种观点,并且一开始就指出:“在当代各社会内部,互相争论的各个个体和群体对此(正义)都提出了种种选择性的、互不相容的回答。……有些正义概念把应得概念作为中心概念,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则根本否认应得概念与正义概念有任何相关性;有些正义概念求助于不可转让的人权,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却求助于某种社会契约概念,还有一些正义概念则求助于功利标准。”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吴海针、王今一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那通过描述一个观念世界与意义世界都和现代社会相距甚远的古代社会的正义观,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呢?因循着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框架,或许可以阐释清楚中国传统的“正义”或“义”究竟是什么,但这种阐释的意义更多地可能是对文化理论的廓清或丰富,而作为面向现代生活实践的伦理反思,这样的阐释是不够的,而后者恰恰是伦理学最重要的任务。
这不是要否定阐释传统中“义”或“正义”理论的价值,而是意在思考如何推进传统研究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联。如果因循着“正义”而谈“义”,那我们现在讲“义”,到底是在谈什么?单就“义”观念而言,它并没有从我们现代生活观念中消失,我们生活里经常会有“有情有义”“义气”“仗义”这样的表达,但这些表达中的“义”在多大程度上等同于传统的“义”观念呢?就传统中“义”的解释看,儒、墨、道、法各家的“义”内涵都有所不同,更何况笼统的比较现代话语中的“义”与传统“义”观念的异同。现代生活中的“义”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义”观念的内涵,通过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有效存留而追溯其在传统中的源流与意义,或许更有利于我们直观地把握传统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也能更好地发挥出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活力。本文尝试以荀子为例,通过对荀子以“分”释“义”的传统的说明、批判与反思,来阐明传统“义”观念在当代生活世界的某种可能的意义,以及其对现代正义理论的启示。
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话语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达,“为人应该有情有义”“应该讲义气”“应该仗义”等等,但究竟什么才是“有义”?怎样才算讲“义气”?怎样才是“仗义”?简而言之,什么是“义”?笼统的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可能,一个或可以回答的问题应该这样问:某个具体的学派或思想家的“义”指什么?儒家传统中的“义”的影响或许是最大的,但是“义”的起源远在儒家“义”思想占据正统地位之前,仅是先秦诸子对“义”的解释和说明都十分的不同,老庄以“自然”释“义”,墨子以“兼爱”释“义”,孔孟开创了儒家以“仁”释“义”的传统,荀子则以“分”释“义”,法家则强调以“法”释“义”。
有研究认为,从殷周开始,“义”观念就已经突显出来,并逐渐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不断下移与扩展,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具有共识性认识的社会观念,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准则,并称之为是“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也正是“义”的观念存在,才使得现实的社会分裂得以弥合,华夏族群能历经战国纷争而依然能保持完整一体(4)桓占伟:《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义观念在战国时代的下移及其社会组织作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战国时代,一如墨子所言,“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5)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9页。。“天下失义”并非是“义”观念的没落,更准确地应该被理解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政治层面,“义”作为社会准则难以落实,对“义”的内涵的把握出现混乱,但“义”依然是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战国时代“天下失义”而“诸侯力正”以及诸子争相释“义”都从侧面反映了“义”观念在当时的重要性。只不过战国时代是一个只知有“义”却很难在“义”的内涵上达成一致的时代,我们当代谈“义”的局面与当时诸子争相释“义”的局面似乎有几分类似。而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剧烈程度相比于战国时代而言,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旨在通过阐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义”的观念来说明当代“义”的内涵,这当中将要面对争议几乎是必然的。下面尝试以荀子以“分”释“义”的理论为例,来看一下传统中某些“义”观念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二、以分释义:荀子的“义分”观念
在先秦儒家传统中,荀子不同于孟子以“仁义”并举的传统,而多强调“礼义”并举,而在“礼义”关系上,“义”无疑有着更基础性的地位,因为“义”规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正如荀子讲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6)本文引用《荀子》文献,均出自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而荀子称“义”则强调“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其“义”经常是相对“分”而言的,其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分”由于“义”的规约而得以可能,而实际上“义”则意味着按照“分”来行动,“敬分安制”之“义”可谓是治理国家之要,荀子讲“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礼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荀子·王霸》)。
在荀子那里,“分”的基本含义是“区分”。“区分”首先是基于自然的差异,然后经由“义”而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秩序。“水火、草木、禽兽、人”这种分别一开始只表现为物类之间的差异,但这并没有引出物类之间的平等,而是经由“义”规定出了物类之间价值上的差异,只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而“最为天下贵”。不仅在物类之间存在价值上的贵贱差等,在人类社会秩序上荀子更强调有差等性的“分”,其“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差等性的“区分”,没有这种“区分”则“义”不存。这也即是荀子批判墨子之非“义”的重要原因,他批判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荀子·非十二子》)。在荀子看来,君臣贵贱差等之“分”是“义”之关键,由此“分义”才有人类社会之和谐秩序。荀子以“分”释“义”的重要理由就是,没有贵贱差等之“分义”人类社会就不能够维持,就会导致纷争,曰“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王制》)。而只有以义分,人类社会才能避免纷争,发展壮大,曰“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
荀子是在两种向度上讲“明分”的:一个是在纵向上强调上下尊卑贵贱差等的区分,一个是在横向上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两者都是“兼足天下之道”(《荀子·王霸》),然而只有前者之区分才指向“义”。当然,上下尊卑贵贱差等之区分,也可以说是社会分工上的不平等,因为君、臣、百姓都承载了职业上的意涵,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金银铜铁”为喻来说明统治者、护卫者、农民和工商业者之间的尊卑贵贱之分一样。然而通过“义”,荀子之“分”规定出了身份的纵向不平等而非强调横向上的差异,从而使得“义”与人的“职分”相联系,并最终与依“职分”而定的“名分”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荀子混淆了“社会分工”与“区分上下贵贱差等”,他在论证上经常通过“社会分工”而导致的身份地位的差异来说明“区分上下贵贱差等”之必要(7)崔宜明在《论荀子的“礼义”与“分”》一文中曾指出,荀子将这种基于身份差异的“区分”称为“义”,而极力维护一个身份不平等的社会,其原因在于荀子混淆了“社会分工”与“区分上下贵贱等级”。。不过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荀子的确存在通过“社会分工”导致的人身份地位的自然差异直接过渡到人在身份权利上的不平等的问题,但是由分工引起的自然差异到人身份权利的不平等的规定,恰恰是产生“义”的巨大飞跃,只有从自然的层面上升为规范的层面才可以称“义”(8)综合荀子的表述看,他实际上也是支持一种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的,其“社会分工”基于的是事实,“区分上下贵贱等级”则是包含了价值判断,故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义”。。
荀子所谓“先王制礼义”,根本上表明了“义”的人为性,自然的差异或许是先王“制礼义”的根据,但只有上升为“不平等”才成其为“义”。故荀子所谓“义”就是根据自己之“名分”而安守自己之“职分”。荀子之“以礼定伦”实际上就是这种“义”的制度化的显现,所谓“礼”本身即在于规定了“名分”、“职分”之“分”,所以荀子在解释礼的起源时给出的是与释“义”相似的解释:“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根据以上的分析,从荀子之“分”大概可以得出荀子之“义”有三个含义:一是相应于“名分”,指对逾制之行、非分之言给予惩罚;二是相应于“职分”,指上下贵贱各等级“皆内自省,以谨于分”;三是相应于“区分’,指以“区分”为本质的“礼”(9)崔宜明:《论荀子的“礼义”与“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三、对荀子“义分”观的当代批判
如果以荀子的“义”的内涵为参照来理解当代生活话语中的“义”的话,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挑战,即我们与荀子在信念上的差异,而这又根源于社会结构事实上的不同。历史地看,荀子把分工导致的差异强化为身份权利上的不平等的做法在全球来看都是普遍的事实。这可能是在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身份不平等区分的强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社会分工的稳固与发展,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在某些历史时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10)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解释了的这种以身份的不平等来推动社会分工的历史现象,他说:“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然而,在当代社会分工已经细分到极致的情况下,这种以人为造就的不平等强化社会分工的做法还有多大意义?就“职分”而言,现代社会并不由于分工不同而产生身份上的不平等,现代社会分工也会导致身份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横向的而非纵向的,就像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虽然事实上,当代社会中不同的工作在声望上有高下,但这远不能跟荀子“职分”的贵贱差等相比。“职分”的贵贱差等是绝对的,它直接决定了人身份上的贵贱差等;而当代社会生活中职业声望的高下是相对的,它只取决于一系列参考指标(收入、受尊重程度、工作性质等)的不同,不会对个体身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而更根本的是人人自由平等是现代人所坚定不移的基本信念,而荀子基于“名分”称“义”的内涵则坚持身份不平等的合法性。其“义”在内容实质上看,是旨在构建一个依于身份的贵贱差等的社会,非差等化不能有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就意味着差等化,社会秩序与这种差等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而现代平等观念几乎扩展到一切领域,职业赋予的身份差异已经构不成行动的任何障碍,依于职业区分的各行其已经不能称“义”了,坚持职业操守,完成本职工作,这早已经在“义”的规定性要求之下了。人们极少会说正常地完成本职工作就是讲“义”,即使荀子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安分守己”可以称“义”的关键在于身份的不可逾越性,僭越身份必为“不义”,而只有“安分”可能也还不足以称“义”,称“义”有更高的要求。只有那些在种种诱惑或不可想象的困难面前,依然能够坚持“安分”,或可以称“义”。
荀子之“义”对我们思考当代之“义”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尤其是将之引入到现代正义问题的讨论中时?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信念的巨大历史差异,都构成了古今观念沟通上的巨大障碍,更何况是古代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即使荀子之“义”中有些方面契合当代正义的观念,但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在这样的讨论中非得引入古代的话语呢?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荀子之“义”的内涵与现代观念是如此格格不入,那谈荀子之“义”对我们当今的生活实践还有多大意义?我们该如何透过传统把握和理解当代话语中的“义”呢?其实不单是荀子,对传统中各个思想学派或具体思想家“义”观念回顾后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传统学说与当代社会结构性巨变之间的落差是所有学说都要面临的问题。跟传统相比当代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观念方面的,这使得“义”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地改变;而且跟“诸子争义”的时代相比,我们当代跟传统的距离更遥远,当代同样在“何为义”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就“义”而言我们却面临两个传统,一个是“诸子争义”之前的传统,一个是“诸子争义”及其以后的传统,只有厘清这两个传统对“义”的影响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当代生活话语中的“义”。不管怎样,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即在“义”的内涵同样存在争议的当代,试图通过古代某些思想家对“义”内涵的主张来完整证成“义”的当代内涵的做法,是无法达成的。某些古代思想家对“义”内涵的主张或许有可取之处,但对当代来说,古代“义”在形式方面的意义可能比某些思想家具体可取的对“义”内涵的主张更重要。
就荀子以“分”释“义”的内涵来看,基于职分、名分的“义”实际上在当代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身份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像父母与孩子、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些在具体范围内的身份不平等也是存在的,像上下级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都有一些不可逾越的方面,这些关系中基于身份的“义”还是有的,也会要求不同的义德,孝父母是“义”、敬师长是“义”、忠于上级是“义”。而且还有一些没有差等的特定身份也讲“义”,如朋友之间的信义。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基于身份的“义”几乎已经从社会身份领域完全退出,而更多地在个体身份关系中得以延展。这也正反映了现代社会与古代共同体之间的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陌生个体之间追求的是身份的平等性,社会结构就决定了平等观念不断扩张的事实,依于身份不平等的“义”观念就失去了建构的条件;而在古代共同体中,共同体身份的不平等更多地由是血缘宗亲关系决定的,因而具有依于身份差等而建构“义”观念的条件和可能性。因而,当代社会生活中由身份决定的“义”从社会领域退缩到私人领域是必然的。而且尽管在私人领域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荀子“义”的内涵依然保持了生命力,但也要看到即使是在私人领域,“各安其分”的“义”的具体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当代社会很多人推崇父母与子女关系平等的理念,所谓“孝”义表现在行为规范上,古代完全不可忤逆父母之命的孝在当今社会几乎没有市场。在更为广阔的当代社会生活领域,当代“义”观念从荀子以“分”释“义”中得到的可能是一片空白。当然,通过寄希望于某个思想家对“义”内涵的阐释而完全把握当代的“义”的想法本就是不现实的。正如前文提到的,要理解和把握“义”的当代内涵,需要对“义”的两个传统做深入而细致的考察,而且还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生活,而这些都这不是本文所能企及的。本文最后将通过一些比较简单地考察,并结合荀子“分义”的思想,粗略地谈一谈“义”在当代的某些可能意义。
四、“义”在当代的可能意义

“义”在古代文本中的另一个重要解释是通“宜”。《中庸》中讲:“义者,宜也。”把“义”解释为适宜、合宜。以往研究中多强调儒家以“宜”释“义”的传统,其实先秦诸子争“义”很多都以“宜”来释“义”。《管子·心术上》也有讲:“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尸子·处道》也云:“义者,天地万物宜也。”《吕氏春秋·孝行》云:“义者,宜此者。”《韩非子·解老》则云:“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这就使得诸子从不同的内涵释“义”具备了合理性,这也为我们如今质疑传统“义”的诸多理念在当今社会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说明直面当代生活来理解“义”的必要。而“宜”最早其实也和古代祭祀活动有关,甲骨卜辞中常见“宜于义京, 羌三人, 卯十牛”的说法,意即在义京这个地方进行“宜”的祭祀活动。《尚书·泰誓上》云:“类于上帝,宜于冢土。”《孔传》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19)胡奇光、方环海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页。《尔雅·释天》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20)胡奇光、方环海撰:《尔雅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而在古代,“祭祀之礼因对象不同而异名,天神为祀,地祇为祭,人鬼为享”(2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3页。,故可称“宜祭”。从甲骨卜辞中就可以看出,宜祭在商代已经是重要且具有比较严格规制的祭祀活动。后世以“宜”释“义”很有可能就是“义”与“宜”在祭祀活动中建立了某种联系(22)详参桓占伟的《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一文,文中引用了关于“义”与“宜”关系的诸多研究成果,认为“义”是宜祭中最重要和最具象征意义的程序。。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将“义”引申为威仪、仪表之意,曰:“古者威仪字作义,……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威仪出于己,故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2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结合“义”与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之间的这种关联性,不难理解段玉裁对“义”的这种引申性解释。祭祀活动在先民生活世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在先民生活世界里,宗教祭祀活动都是庄严且神圣的活动,可以想象个体在祭祀仪式中的所有行为都会是有严格要求,且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的。个体在祭祀活动中对自我行为仪态的约束在实际意义上表达着对祭祀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认同。祭祀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在更深刻意义上构成了观念认同的基础。“义”观念的生成很有可能就是凭借着对宗教祭祀活动的这种认同才得以实现,并逐步下沉而达到一种普遍化认同的地位。
相较而言,从在人们现实生活世界所起的作用的角度来考察“观念”可能更有意义。那么对“义”观念而言,且不管诸子争“义”而赋予“义”的诸多内涵是什么,就诸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而言,“义”观念极有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即“义”只在观念形式上得以社会化地保持延续,而在内容实质上出现认同上的混乱。这个时候,“义”作为一种“名”在社会上保持了较高的认同性,而其“实”则出现了争议,这种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从什么是“义”转向了什么是“义的”。当代在“义”观念上面临的争议,实际上问题也不是什么是“义”,而是什么是“合于义的”。在这种意义上,“义”观念在诸子争相释“义”的时代以及当代的最深刻的意义可能在于,“义”成为了中国人最高的道德认同,或者说“义”构成中国人最基础的道德心理。这种最高的或者最基础的认同性之所以能形成,极有可能就源于对祭祀活动神圣性和权威性的认同,这种在民族幼年时的神圣认同在民族精神和文化形成中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对“义”的认同是传统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
对“义”的这种最高的道德认同,或者说最基础的道德心理认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对人作为道德属性的存在的认同。荀子最好的说明了“义”代表了人作为道德属性的存在的本质特征,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跟水火、草木、禽兽的最大不同就是人有“义”。而这一点正是旨在建立“公正的制度”的当代“正义”讨论所不能替代“义”的方面,至少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义”具有一种“正义”所不能取代或达致的作用。作为一种观念社会化的力量,“义”在当代生活实践中能给予人们一种极易被唤起的且根深蒂固的关于自我的道德意识。当然,这种意识并不一定能保证我们行为的正确性,这有待于充实“义”的具体内容,但却能促进个体对道德行为的积极性以及非道德行为的审慎性。
——论庄子之“物无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