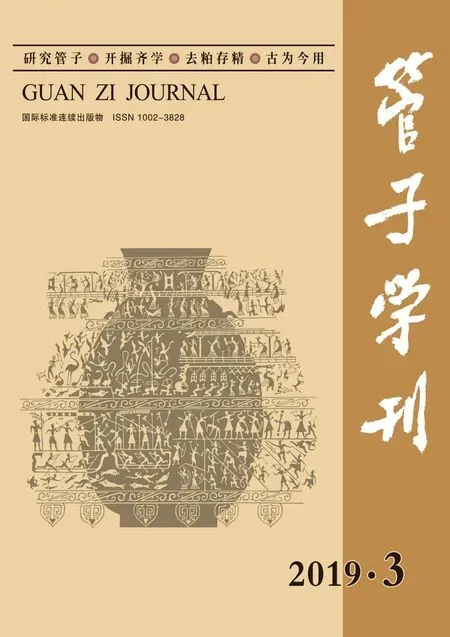帛书《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的思想联系
赵 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帛书《易传》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世以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纷纷对其中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解读,其中就包含对“五行”的讨论。“五行”是《周易》中的重要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见司马迁将“五行”概念归入《易》之义中。但“五行”不见于今本《易传》,而历代学者在解《易》时却往往用五行说,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所幸帛书《易传》中频繁出现“五行”,《二三子问》篇更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这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可供参照的研究材料。
关于“理顺五行”,学界多有讨论,如邓球柏先生曰:“理顺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的关系。”(1)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赵建伟先生则根据《要》篇“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指出“五行”谓地道(2)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2页。,丁四新先生赞同此说(3)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但二人均未对“理顺”做出解读。连劭名先生进一步对“理顺”有所解读,其曰:“理顺五行同于《周易·说卦》所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4)连劭名:《帛书〈周易〉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8页。此说引用《说卦》思想来解释“理顺五行”,从道德、理义、性命层面进行理解,恐不符合帛书的原意。不过连先生在解释“必顺五行”时,指出:“五行金木水火土,布于四时。”(5)连劭名:《帛书〈周易〉疏证》,第223页。这一点很重要,所谓“必顺五行”便是将五行与四时相配,但对于五行如何布于四时,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直到金春峰先生将“理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进行联系,才对如何理顺做出回答,其曰:“这样的‘五行’,无疑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什么叫‘理顺’,如何理顺?按《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管子》之《五行篇》的说法,是君主的立政和时令五行相顺应,如春(木)不行夏政秋政,夏(火)不行秋冬之政。”(6)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此说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刘彬先生按照此思路,把“理顺五行”进一步阐释为“时令”思想,其曰:“‘理顺五行’,即圣人施政,要顺从木火土金水运行之理,此涉及古代‘时令’思想。所谓‘时令’思想,是一种重视天时,强调顺天时以行政令的观念,认为顺时行政则有祥瑞出现,而如果违背时令,则会发生灾异。”(7)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刘说指出“理顺五行”的关键在于顺从木火土金水运行之理,并对五行如何与四时相配进一步做出解释:“其‘五行’内涵,是以春为木,以夏为火,以秋为金,以冬为水,以土分布于四时,佐助木、火、金、水,以化育成就万物。”(8)刘彬:《帛书〈二三子〉“理顺五行”“必顺五行”解》,《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第40页。刘先生的解决之法,是将土分布于四时,以克服五行与四时不相配的难题。
综上可知,学界对“理顺五行”“必顺五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如何顺应五行这个问题上面,帛书《易传》对此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而《管子》一书有“顺五行”的详细行政方案,即春行木政,夏行火政,秋行金政,冬行水政。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借助《管子》中的“时令”思想来理解“理顺五行”的思想含义。经过笔者考察,《管子》一书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时令模式,君主行政既可以与四时相配,也可以与五行相配,内容十分丰富。所以,本文试图对帛书《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书中的“时令”思想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不周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顺五行”与其时令含义
帛书《易传》提及“五行”主要在《二三子问》和《要》这两篇解《易》文献中,《衷》篇也提及“五行”,但因文义断裂不明,故可忽略不计。
《二三子问》篇有两处地方提及“五行”,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第一处在第八章,孔子释《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时,其曰:
《易》曰:“康矦(侯)用锡(赐)马番(蕃)庶,昼日三接。”孔子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圣人之正(政),牛参(犙)弗服,马恒(极)弗驾,不夏乘牝马,□□□□□□□□粟时至,刍稾不重,故曰‘锡(赐)马’。圣人之立(莅)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菑(灾),民□不伤,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民悤(总)相(惕)以寿,故曰‘番(蕃)庶’。”(9)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第29页。
第二处在第十四章,孔子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时,其曰:
《要》篇提及五行一次,其曰:
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
以上有三处地方提及“五行”,可见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五行”。其中《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必顺五行”言及天道,重视天时渐变之理,而且与君主行政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其中具有时令含义,涉及圣王安世莅政,并与《管子》思想多有契合,故是本文所论的重点所在。而《要》篇以三才之道言及“五行”,以“五行”配以地道,与《说卦》的记载相似,因其不涉及时令含义,故暂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那么在《二三子问》篇中,孔子为什么能从中阐释出“理顺五行”“必顺五行”的时令含义呢?这与其本身的卦爻辞有关,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理顺五行”之语由《晋》卦卦辞阐释而来,其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关于康侯,一说泛指安康的侯爵,一说为周武王的弟弟卫康叔,以前者为是。《周易本义》云:“康侯,安国之侯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程传》云:“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顺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宠数,锡之马众多也。”赵建伟先生曰:“虞翻训‘康’为‘安’,盖与此‘安世’相关。”(11)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第211页。此处讲的是康侯被赏赐的马很多,一日之内被三次接见,这就涉及到圣王安世的主题。统治者具体要怎样安世呢?《二三子问》篇对此提出“理顺五行”的行政措施,认为统治者要顺从五行运行之理,尊重四时之代序,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这样百姓就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会有灾祸降临,故孔子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

需要注意的是,《二三子问》篇“五行”所指并不明确,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金、木、水、火、土,学界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其与《要》篇“五行”的含义应是一致的,即水、火、金、土、木。但《要》篇“五行”属于地道范围,而此处“五行”显然更接近于天时的内容。邢文先生即认为:“这里所谓‘五行’与‘水火金土木’并非一事。”(12)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此说有理。所谓“理顺五行”“必顺五行”,就是要君主在行政的过程中顺应天时,即四季之时,强调顺时而动,尊天而敬众。
以上可见,《二三子问》篇认为统治者在行政过程中要尊重天时,按时而动。而这种对春夏秋冬之四时的重视由来已久,于先秦古书常见。《逸周书·周月》最早有记载,其云:“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13)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9页。可知古人十分重视四时之序,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不仅影响万物的生长,而且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其他先秦典籍对天道和四时也有充分的记载,如《国语·越语下》云:“(范蠡)对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谓之始。’”《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管子·形势解》云:“天生四时,地生万材,以养万物。”又云:“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孔子家语·问玉》云:“天有四时者,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以上文献都体现出古人对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寒暑冷暖的关注,均属于圣人之教的内容。
传世本《易传》亦十分重视四季之时,《观·彖》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程颐云:“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14)程颐:《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3页。又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中既有对天文之日月星辰的观察,也有对四时循环运行的关注,并以此贯通天道与人道。再如《说卦》“帝出乎震”章,以震、离、兑、艮四卦对应春夏秋冬之四时,震卦代表东方和春天,象征万物萌生;离卦代表南方和夏天,象征万物长高而相见;兑卦代表西方和秋天,象征谷物丰收;坎卦代表北方和冬天,象征万物休息。可见传世本《易传》对自然界万物,特别是植物的生长过程,以及四季气候的变化,都有特别的关注。
这种对四时的重视,最终发展出“时令”思想。所谓“时令”思想,核心在于“顺天”,即顺应天时,以为民生日用之资,具体内容是顺应五行、四时以及寒暑之代序。这种“时令”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历政文化,梁韦弦先生认为:“历政文化,是指自尧时的观象授时之‘政’形成的一种管理社会生产的治道,及其中包含的人们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15)梁韦弦:《汉易卦气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18页。可以说,这种“时令”思想或历政文化是先秦最重要的文化之一,由此形成的政治模式强调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如何处理好天人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正是此意。
二、“顺五行”与早期灾异思想
《二三子问》篇孔子提及“理顺五行”时,有“天地无菑(灾),民□不伤,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之语,这是圣人莅政之后的治理效果。此要求圣人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尊重天时,敬爱百姓,且理顺五行,这样天地之间便不会有灾祸降下,不会出现如飘风淫雨等异常天象,百姓也不会因此受到损伤。不仅如此,若是“理顺五行”,还会有春天应时之雨降落,滋润正在生长的秧苗,可见此处展现为一幅良善的政治图景。
笔者认为,以上这段话含有古代灾异思想,此是我们所说“时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早期灾异思想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有降灾和不降灾两种情况,目的均为警示统治者要顺应天时,不能妄为。以上引文即属于不降灾的情况,原因是圣人做到了顺应天时,敬重民众,且理顺五行。此常见于先秦文献,属于当时共同的思想背景,如《礼记·乐记》云:“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管子·四时》云:“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正是此意。反之,如果不能理顺五行,甚至是违背天时而动,天地则降下灾祸,飘风苦雨等异常天象纷纷出现,农业收成得不到保障,百姓遂无法安居乐业。
这种早期灾异思想由来已久,《国语·楚语》即载:“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将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此言民有忠信,神能明德,故“民神异业”。对神要“敬而不渎”,因为神既能降下“嘉生”,也能不降下“嘉生”。所谓“嘉生”,即茂盛的谷物,古人认为这是祥瑞的象征。“嘉生”降落的表现首先是四时有序,风调雨顺,《国语·周语》即云:“阴阳次序,风雨时至,嘉生繁祉。”神若降下“嘉生”,谷物即得以茂盛的生长,百姓得以永久享用而不匮乏,灾祸也不会到来。神若不再降下“嘉生”,则几乎没有谷物可以收获,百姓没有东西可以享用,灾祸也随之而来。可见,古人认为神可以通过谷物的丰欠,影响百姓的生活,这是早期灾异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
《诗经·十月之交》中也有记载,其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这是一首政治讽怨诗,抒写了对周幽王时期朝政混乱的讽刺和怨恨,《毛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中,此诗的创作者将日食现象与国无善政、不用贤良联系起来,反映出西周末年的自然灾异和政治情况。
而以“飘风苦雨”为特征的灾异思想最早见于《尚书·金縢》,孔颖达正义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此介绍《金縢》篇的由来,乃源于周公告神请求代武王死。但是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由周公辅佐,管叔等人忌恨周公,遂在邦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成王听信谣言,于是疏远了周公,周公遂主动请求去东方征伐叛乱。而在成王疏远周公之后,天降异象,这是上天对成王的警示,《金縢》详细记载了这次异常情况,其云:“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此言周公被成王疏远后的这年秋天,百谷已经成熟,但尚未收获,天空突然雷电大作,狂风肆虐,把庄稼都吹倒了,大树也都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慌。随后,成王发现周公告神的册书,感动于周公的为人,心生愧疚,遂将周公接了回来。此时天象亦有所表现,《金縢》云:“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此言成王出郊外迎接周公归来,天仍然下着雨,但风却反向而吹,倒伏的庄稼又全都立起来了。太公、召公遂命令国人把大树压倒的庄稼扶起来,重新把根培植好,于是这一年的庄稼收成特别好。可见,这种灾异思想其实是将人事与天象结合起来,目的是警示君主及下民。
这样的灾异现象在《墨子·尚同中》中也有记载,其云:“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其中有“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之语,此言若不能尚同乎天,天则降下灾祸,譬如寒暑、雪霜、雨露不能按时出现,五谷不能按时收获,牲畜不能按时生长,以致出现疾病、灾害和疠疫,旋风淫雨也伴随而至。这是属于降灾的情况,《二三子问》篇“飘风苦雨不至”则属于不降灾的情况,很明显,二者有相同的语境。关于天不降灾的和谐图景,《墨子·天志中》有记载,其云:“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因此我们可以说,《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的含义应该就是“节四时调阴阳雨露”,即顺应时节的运行规律。
以上早期灾异思想体现的是人与天(或神灵)的相互感应和相互作用,有时可能感应的很好,有时也可能感应的不好,感应的不好上天便会出现“灾异”以警示之。灾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四时错乱,即在春天出现夏天的景象,在夏天出现秋天的景象,在秋天出现冬天的景象,在冬天出现春天的景象。譬如“六月飞雪”,最早说的是邹衍的故事,后来民间将此情节演绎到《窦娥冤》中。《后汉书·刘瑜传》引《淮南子》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此言燕王请齐国的邹衍等贤人来帮助治理国家,燕国有一部分人对邹衍不满,在燕王面前进谗言,让邹衍蒙冤入狱,当时正值盛夏六月,天降大风雪。燕王意识到邹衍的冤屈,就释放了他。这是一桩冤案,后来终得昭雪,遂后世用来形容莫大的冤情。关汉卿《窦娥冤》所写窦娥含冤被斩之后,“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与此一致。其实“六月飞雪”的真正原因是由自然的变异引起的,产生这种现象多半是由夏季高空较强的冷平流造成的,并不神秘。
总得来说,这种早期灾异思想来源于对时节的观察,这在《逸周书·时训》里有充分的体现,其中记载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时令物候及其反常所导致的灾祸,即是将“时令”与“五行”“灾异”结合起来。譬如:“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逸周书》认为,在雨水这一天,獭如果不祭鱼,国家就会有盗贼;鸿雁如果不归来,远方就会不归服;草木如果不萌动,果蔬就不成熟。如“獭不祭鱼”“鸿雁不来”“草木不萌动”之类,均为不合时节的异常现象,古人认为这是灾祸之兆,预示着人事的反常。《武顺解》云:“天有四时,不时曰凶。”又云:“天道曰祥……知祥则寿。”可见顺时则吉,逆时则凶。《时训解》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都是同一模式书写,所表达的意思即是,若不按照时令节气行事,必有灾祸发生。笔者认为,这种早期灾异思想是我们所说“时令”思想的一部分,与《管子》中的“时令”思想十分贴合。
三、《管子》中的“时令”思想
《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的前提是“圣王安世”,此涉及君道思想,关注的是君主行政的措施,即“圣人之立(莅)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之意,与《管子·四时》所云“圣王务时而寄政”含义一致。其中反映出“时令”思想,要求五行配合四季来进行政治运作,实质是四时之教令。这种“时令”思想在战国之时十分盛行,各家著作中均有体现,当时的“时令”模式主要记载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管子·五行》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其书中的纲领所在,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内容与《礼记·月令》几乎一致。
我们来看《礼记·月令》中的时令模式,其中记载有四时十二月所行之政,以立春之月为例,强调要“春行木政”,其云:“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此言天子在立春之时迎春于东郊,返国后乃命三公发布德教,施行恩惠,又命大史之官掌管天文及日月星辰之事。又云:“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御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又云:“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其中列举了很多在立春之月该做之事和不该做之事,该做之事如教民稼穑,命乐正入学习舞,祭山林川泽之类,均是顺应生气之事。不该做之事也有很多,如禁止伐木,不要掀翻鸟巢,不许杀害幼虫,不可兴起战事之类,都是为了防止逆生气而动。在立春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此时阴阳调和,必要顺应初春之盎然生气,呵护大地之蓬勃生机,断不可有杀伐之事发生,这才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而《管子》书中的“时令”模式与《月令》篇有所不同,内容十分丰富,核心内容是如何解决五行与四季相配的矛盾。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以春季配木,夏季配火,秋季配金,冬季配水,而将土分布于四时之中,事实上是将土消散于四季之中;第二,在四季之外增加季夏,以季夏配土,实际上形成五时,即五季。由此,五行在运行中便与五季、五方、五味相配使用,是以木配东方为春季,火配南方为夏季,土居中央为季夏,金配西方为秋季,水配北方为冬季。这两种配对方案在《管子》一书中均有体现,下面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管子》一书涉及四时与五行思想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四时》《幼官》《五行》与《轻重己》四篇文献中,这四篇也被认为是《管子》书中代表阴阳五行学说的作品,其中涉及不同的时令模式。《管子》中的《四时》《幼官》为一系统,都是政令与春夏秋冬之四时相配。《五行》中的时令模式为另一系统,乃将政令与五行相配,并将一年分为五时,每一时为七十二日,天子行政即以此为准。而《轻重己》的行政模式更为细致,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八天,春夏秋冬各为九十二日,又将四季分为八个四十六日,以此作为君主行政的参照。
先看《四时》中的时令模式,其云:“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知四时”,即知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政,此乃国之基业也。其中有关君主所行四时之政,试略举如下: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宗正阳,治隄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靁,行秋政则旱。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节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遫至,贼气遫至,则国多菑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
在《四时》这一篇的理论体系中,春季与星、风相配,夏季与日、阳相配,秋季与辰、阴相配,冬季与月、寒相配,可见君主行政与四时有关,并不涉及五行。其中有“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靁,行秋政则旱”之语,这是四时所不能行之政,如果逆时行政,如春行夏、秋、冬政之类,便会出现一些如欲、霜、雕之类的异常现象。而且在春季行政这一条中,有“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之语,与《二三子问》篇“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民悤(总)相(惕)以寿”之语类似,可见二者有共同的思想背景。总而言之,《四时》篇是以春、夏、秋、冬配以东、南、西、北和星、日、辰、月,一一列举每季该行之政与不该行之政,强调顺时行政则吉,逆时行政则凶。
《幼官》亦云:“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耗。……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幼官》篇对逆时行政所造成的灾异之象有更详尽的描述,如春天之“肃寒”“多雷”“掩闭”,夏天之“多风”“雨雹”“霖雨”,秋天之“生叶”“生华”“虚耗”,冬天之“阴雾”“多雷”“烝泄”,此均由不行四时之政所造成。可见四季有其生养休息的规律,一步错乱,则步步错乱。
再看以《五行》篇为代表的时令模式,其将一年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为七十二日,以此配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不再以四时作为区分单位,而是以五进行区分,以便能更好的配合五行之运行。其云:“日志,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臧任君赐赏。……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
此将五行作为基本的划分单位,从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士师之官以治事,总别列爵,整治官吏;从丙子日开始,要按照火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行人之官以治事,修理沟洫,发放赏赐;从戊子日开始,要按照土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司徒之官以治事,敬慎农事,宽刑缓罪;从庚子日开始,要按照金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祝宗之官以治事,选禽兽与五谷,敬祀祖庙;从壬子日开始,要按照水的德性来行事,此时天子命令使人之官以治事,制造弓箭,以备狩猎。以上是“五时”该行之政。
木、火、土、金、水之“五时”各有所行之政,若是逆天时而行,就会有灾异,以甲子日为例,其云:“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赏赐,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此时天子若是不赋不赏,大斩伐伤,国君就会有危险,甚至危害及太子、家人、夫人和长子。
以上是《四时》和《五行》的时令模式,下面我们来看《轻重己》的配对方式,其云:“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
《轻重己》与《四时》《五行》不同,此是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八天,春夏秋冬各为九十二日,又将四季分为八个四十六日,分别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天子要按照时节进行祭祀并且发号施令。但实质上还是四时的模式,四时是基本的划分单位,由此扩充为八,为十二,越来越详尽。
可见,《四时》《五行》《轻重己》三篇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时令模式,实际上可归纳为两种,《四时》和《轻重己》两篇是以四时相配,《五行》则以五行相配。《二三子问》篇“理顺五行”“必顺五行”所反映出的“时令”思想当最接近《五行》篇中的行政内容,表现的是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与历法、政治的结合。但帛书《二三子问》篇只是简单提出“顺五行”的思想,要人们顺应天时以行事。而在《管子》中,五行与四时、五方相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时空体系,以春季、东方与木相配,夏季、南方与火相配,土与中央相配,秋季、西方与金相配,冬季、北方与水相配。这种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排列方式已显示出五行相生的理论,这都是《二三子问》篇“顺五行”思想所没有涉及到的。由此可见,《管子》中的时令思想比《二三子问》“顺五行”思想要成熟一些,这不仅是古代节气的汇编,而且渗透着浓厚的政治思想。
综上可知,“时令”思想的核心是天子行政的思维模式,强调统治者在行政中要顺应四时之代序、五行之生克,并与天干地支等配合起来,认为每一季节有当时该行之政,顺之则吉,逆之则凶,而所谓的灾异之象就是由于逆时而动造成的。具体内容就是四时之教令,即依靠天时运行而在人间设立“教令”,认为人事要合于天道,体现在君主行政上就是“令有时”。圣王治理天下,必当知四时,顺四时,这是帛书《易传》所要表达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春夏秋冬之四时以及木、火、土、金、水之五行的运行能够影响政治,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思维模式,人需要因天之时展开农事活动,其中透露出的是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模式。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联系的整体中,政治生活与农事活动均需按照四时的运转来进行,这就是“人与天地参”。
但是帛书《易传》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思想特征呢?以《二三子问》篇“顺五行”的思想特征来看,不排除其中有齐学的特征,朱伯崑先生认为:“楚地帛书本《周易》经传文,多半来于齐学。”(16)朱伯崑:《帛书本〈系辞〉读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陈来先生则直接认为:“帛书所见的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应有三个主要流派,这三派不一定同时,可能发展有先后。三派在解易、学易方面的宗旨互有不同,即鲁儒易学、齐儒易学、楚儒易学,这在帛书《易传》中都有表现。”(17)陈来:《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而《管子》一书中的大部分作品又是完成于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具有鲜明的齐学色彩,当时最为流行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因而《二三子问》篇“顺五行”与《管子·五行》篇存在思想上的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应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