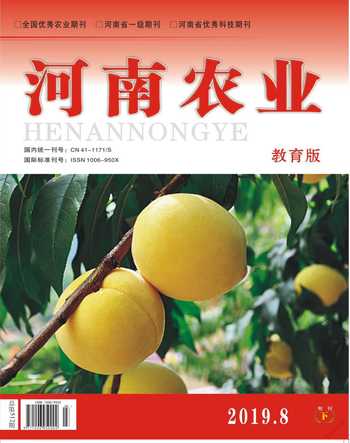论文化的阶级性与教育性
马艳
摘要: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从文化的阶级性和教育性入手,区分了法国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当下社会的阶级性。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的阶级性和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其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与文化有关。文化的教育性在当下体现在家庭生活上。布尔迪厄的观点由于时代的特点具有局限性,需要辩证看待。
关键词:文化;阶级性;教育性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以下简称《区分》)一书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部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对世界学术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布尔迪厄在论述文化的阶级性和教育性时采用的问卷调查、测量分析、深度访谈、人种志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是今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布尔迪厄在《区分》一书指出的文化的阶级性和以此为逻辑起点的区分,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特别是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批判性继承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垄断资本主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当今的信息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区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决定着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教育发展。
一、《区分》中的文化学思想
布尔迪厄在《区分》的开篇就提出了文化的阶级性和教育性问题,并在此后用大量的图表和案例来验证这一问题,并得出一个看起来非常令人绝望的结论:文化的阶级性是文化的首要特征,文化的教育性是次要特征,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学历和文化认知水平,但要想简单地仅凭通过学历提升就实现文化的阶级晋升是不现实的。当然布尔迪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论证“文化的阶级性和教育性”这样一个文化问题,而是借助人们关心的表象的文化,从日常的吃、穿、读、看等生活、学习、娱乐活动着手,进而探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不同阶级至今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法国贫富差距的文化现实,与老子所指出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类似。
布尔迪厄在《区分》中的文化学思想还体现在受教育者在读大学的专业选择上。正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在法国的不同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受教育者,在大学学习的专业大致有这样一个规律:农民家庭的孩子多选择文科和理科,工人阶级的孩子多选择建筑和工程,大资产阶级的孩子多选择商科、经济、管理等专业;即便是同一个阶层内部,因为性别不同,男生多选择理科,女生多选择文科。
二、文化的阶级性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的阶级性是布尔迪厄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振聋发聩的呐喊。这种呐喊不仅惊醒了沉睡在西方自由主义大旗下被民主和博爱所蒙蔽的资本主义下层民众,也穿越时空给中国人以文学文化的阶级性一个启示。如以张岱年、方克立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所主张的文化的四个方面内容来看——“一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二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三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四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纲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区分》中的“文化”,主要以后两种为主。
(一)文化的阶级性突出表现在文化的不平等上
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器物,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样的戏剧,读什么样的书……这是布尔迪厄在《区分》中通过大量数据和案例来证明了的事实。这种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而他的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不能怀疑之处做的学问就是文化的阶级性。
文化的阶级性是当下中国很少谈论的词汇,一是因为我们的國家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当今的社会文化主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分类侧重于使用者的话语权,例如,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学院派的精英文化和消费为主的大众文化。
文化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阶级社会的文化不平等上。例如,说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解决的文化诉求是很难一致的。即便是现在,我们要用那些名言警句,至少要说出来源于何时的“谁”,而这个“谁”,又必定是在某个领域的翘楚或突出贡献者。否则,路人甲、路人乙等引车卖浆者之流是不配命名某物或说过某话的。对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凭借在资本主义殖民统治中发家的那些“日不落帝国”,虽然如今已经风光不再,但依然靠着他们建立并主导着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指手画脚。
为什么在古代社会的平民难以出文化精品,关键原因在于古代的劳苦大众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对文化无暇顾及。即便是真有“赋到沧桑句便工”的经历和体验,也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缺乏文化表现的手段和技能,不能青史留名。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狭义的文化层面,在古代的社会平民是无法享有文化的权利的,特别是在活字印刷术之前的中国和古登堡推广印刷术之前的欧洲,识文断字都是贵族的特权。即便到了今天,人们所说的“读书是最廉价的高贵”,正是对这种文化的阶级性的一种现代注解。所以说,科技进步可以缓解或者隐藏,但不能消除文化的阶级性。这种文化的阶级性和不平等性集中体现在:至理名言是文化贵族的特权。
(二)古代中国文化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上
在古代中国,文化的阶级性是显而易见的。孔子念念不忘的“克己复礼”之“礼”,是自周天子而至庶人一以贯之的礼法制度,是君臣父子必须恪守的社会规范,比如修齐治平。西汉时期形成所遵从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则进一步固化了文化的阶级性。魏晋六朝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则使这种文化的阶级性达到了顶峰。以杜甫诗歌的阶级性为例: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评价杜甫在成都浣花草堂的屋顶茅草有“三重”,是文化阶级性的表现。40多年来对这种评价的态度不一而足,其争论的焦点就是杜甫的诗歌具有的人民性、时代性无可辩驳,但其诗歌的阶级性或诗歌中反映的文化的阶级性并没有形成共识,甚至现在很少有人谈论杜甫诗歌的阶级性。如果把杜甫的诗歌放到整个唐代来看,杜甫是其中官职较低、遭受苦难较多、反映社会现实最为深刻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代表了从隋代开始科举取士以来那种读书人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家国情怀。但不能否认的是杜甫诗歌的阶级性,主要是代表了中下层士人的文化阶级性。这种文化的阶级性,自然要比门阀盛行的六朝要进步,但也仅限于此。这种文学文化的阶级性,直到五四前后才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呐喊声中逐渐式微,但其中蕴含的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审美范式和民本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后要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的阶级性在当今社会已经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上
布尔迪厄认为法国文化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上,这种家庭生活包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从每天早晨是吃面包还是喝牛奶开始,吃什么类型的面包,喝哪个品牌的牛奶,和谁一起吃早餐,用的是什么餐具,在哪里吃早餐,都是文化的阶级性展示其威力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阶级性之所以不能被打败,在于阶级内部的内婚制度,这类似传统婚姻的“门当户对”。这种内婚制在印度就是不同种姓之间的不能通婚,在先秦时代表现为为了后代的优生优育而产生的同姓贵族不能通婚而在不同姓诸侯国国君之间的互为通婚,这种诸侯国之间的通婚又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贵族间的联姻。这种文化的阶级性的一种变体就是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100年过去了的今天,高呼恋爱自由的当下青年在无暇选择婚恋对象之后再次将婚姻的主导权交由父母,当然这种权利只是在某些人群的某个时段的某些事上,真正成了家立了业之后,核心小家庭的生活已经取代了千百年来承袭的大家庭聚族而居的特征。即便如此,文化的阶级性依然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文化的教育性及其当代价值
布尔迪厄对文化的教育性持悲观愿望。这种悲观性弥漫在《区分》一书的序言、正文和附录中,让人读后心底不由升腾起一种悲凉之情。布尔迪厄的这种悲观性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的教育性和受教育者的阶级出身有关
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是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与手段。但文化再生产的发生不是由单一的学校教育系统造成的,他认为文化再生产是包括家庭、社会及教育系统三位一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校只是文化再生产的‘转换器’,学校通过教育对社会结构进行复制,然后将‘教育产品’(学生)输入社会。”也就是说受教育者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在他提升文化的教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这种文化的教育性能提升到何种程度,主要和受教育者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有关。对原生家庭依赖性越大,提升文化的可能性和教育性就越差。换言之,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的教育性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人的文化的影响是自动化和自如的,属于潜意识的层面。这是后天的学校教育无论怎样弥补也追赶不上的先天性优势。“有些事情人们永远也无法领会,若不是一开始就领会:人们无法让某些冷酷而野蛮的人理解邦瑟拉德的芭蕾舞和拉封丹的寓言魅力和流畅”。
(二)文化的教育性和受教育者的经济收入有关
当经济收入足以应对受教育者在求学过程中的各种需求,那么这种文化的可教育性就越大。當然这种关系也不一定成正比。一旦经济收入远远超过了教育支出,而这时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时,就会出现一种炫耀式的消费文化。布尔迪厄还指出这种炫耀性消费多出现在不够产生经济收入或收入较少的富裕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身上,也就是如今网络语境中的“拜金女”和“富二代”。
(三)文化的教育性和沲教教师有关
接受不同程度的学历教育和在不同学校受教育,都对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可提升程度有影响。在家庭出身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受教育者,其提升的可能性和可提升空间与受中等教育的受教育者相比要小得多和少得多。同样,在巴黎重点大学和在外省的某专科学院的毕业生,其文化的可教育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切,都和其在受教育过程中接触的施教教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教师的学历、职称、教学水平、责任心和师德师风相对较高时,学生通过教育提升的可能性就相对较高,当然这种关系是暗含的。
四、布尔迪厄文化学观点的局限性
庄子在《秋水》中指出认知受限于时间、空间和教育程度。布尔迪厄的文化学观点也是如此。只是他主要从法国、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人手,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了解相对较少。因此,在学习借鉴《区分》及他的其他作品时,要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区分”。比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就说:“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的阶级性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也和民族文化有关。
此外,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的阶级性及无力改变的幻灭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人的渺小感在面对庞大无比且固化的社会分层和资本市场时在文化上的延伸和表达,这从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性。从舍勒的文化社会学观点来看,布尔迪厄的这种无力的幻灭感充斥着资本主义市民的怨恨情绪。当前我国所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中的“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做法,就是对布尔迪厄认为的文化的阶级性的无力感和贫困的遗传性的一种精准狙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