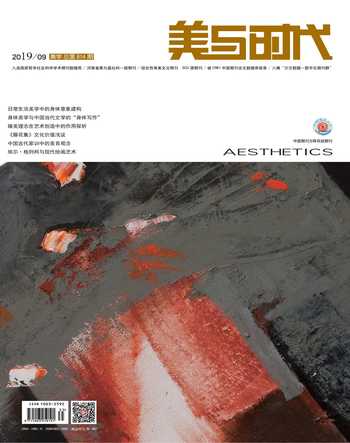日常生活美学中的身体意象建构
摘 要:在1949到1963年之间这段时间里,妇女题材宣传画经历了数次嬗变。由早期的劳动者形象建构,到随后性别特征的显现,再到上海月份牌画风格在60年代初的短暂回潮,宣传画塑造了新型的妇女形象,演绎了以“新气象”为关键词的审美风尚。这些作品突破了过去文人画和上海月份牌画那种狭窄的选题,将自己关注的范围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一种初级阶段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实现了公共意志与民众意愿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新中国;宣传画;妇女形象;新气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扬州大学2018年教学改革研究博士专项课题“基于问题导向的文本研读模式构建与实践”(YZUJX2018-21B)研究成果。
1949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气象”的宣传画,将“新气象审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启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初期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宣传画中妇女形象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在此之前,大众美术领域里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绘画种类之一是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月份牌。月份牌里的时髦迷人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将女性之美充分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却又将女性推向“花瓶”角色的审美困境。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来审视,这就是一种身体被作为客体且被消费的状态:“在流行的文化图景中,身体总是被装扮、修饰、重构、展示、炫耀、观看、照料、消费,承受各种规划、理念、冲突,却绝少显示出主体的身份和尊严。”[1]相比之下,这些宣传画中的女性则是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语境下创作出来的,“劳动”成为代替“花瓶”的关键词。与民国月份牌里的女性形象被遮蔽在少数男性“窥视”视野不同的是,新的妇女形象从一开始就力图面向整个社会,通过政治与审美相结合的形式将公共意志和群众愿景结合起来,催生了一种新的生活美学。
一、妇女劳动者的形象建构与“新气象”审美时尚
从解放区时期开始,“左翼”文艺一直在通过作品告诉大众:权利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自己奋力争取的果实。同样,妇女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也不可能消极依靠男人的赐予,而必须自己积极主动去争取。由于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力量,所以必须通过劳动来取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指引下,女性开始从月份牌里的“花瓶”“尤物”形象,换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新形象,作为意识形态宣导载体的宣传画便直接反映了这种展现社会“新气象”的审美意图。
从月份牌到新宣传画,女性形象变迁的背后是妇女地位的变化。早在抗战时期,通过强调妇女的权利和义务统一而开展社会动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这项声势浩大的基层社会动员工作甚至还让彼时日本情报机关感到深深的不安。针对“边区”婦女解放运动的相关研究在日本方面也同步展开,其中草野文男《支那邊區の研究》[2]就在第三章“普察冀边区の概况”(原文为“普察冀”,实应为“晋察冀”——笔者按)言简意赅地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义制度下”,中国妇女生活苦闷,多半充当男子的玩物。而边区“抗战支那の妇人运动”则试图从根底上改变这种局面,通过女性平权运动来改变社会结构,从而实现边区整体社会动员,突破中国发展路上的结构性瓶颈。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最为担心的,因为妇女社会动员工作一旦完成,就意味着能对日作战的边区有生力量又多了一倍。
1949年之后,妇女解放被视为“人民当家作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宣传画中对“劳动妇女”形象的强调,既包含了推动妇女解放和反对性别歧视的国家意志,也展现了创作者和社会大众对女性获得平等权利和建设新社会的热切期盼,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大众期盼的有机统一。中国现代诗学有所谓“诗言感觉”一说,其实宣传画也同样强调那种呈现于画面中的诗意和感觉,或者也可称之为图像性的气氛美学[3]。这种气氛美学力图通过审美化的日常意象来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系列宣传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劳动妇女形象是如何在一种社会新气象的氛围中进行建构的。在周令剑《学习红军长征的战斗精神,征服自然,建设我们的祖国》(195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这一幅宣传画中,妇女主角的职业身份是地质勘探队员,为配合这一职业形象,创作者赋予她接近国字脸的圆润而饱满的脸庞、有力的粗手指,以及坚毅的眼神。与建国前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上海月份牌女郎强调女性身份不同,她身着勘探工人职业装,蓝色布质外衣里是干净整洁的白色衬衫,服饰呈现出中性化色彩。虽为单幅绘画,但创作者试图通过画面切入而给予该画超越静态的叙事情节性,他将红军长征攀爬雪山的图片置于全图上方的蓝天位置,而且作为追忆,红军爬雪山一图用的是黑白色,与全图彩色形成鲜明对比。而翁逸之的《感谢农民兄弟的支援,使我们生产有了保证!》(195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在构图上与上述周令剑的作品具有一致性,都是典型的40年代苏联式的图画配上底下红字说明的模式,一般是大约占全图7/8的图画配上占全图大约1/8的红色字体。与解放区时期侧重版画平面构图有所区别的是,50到60年代的新型宣传画积极借鉴苏联新古典主义侧重光影营造的立体感和纵深感。翁逸之这幅画在透视感上较周令剑的作品更胜一筹,画面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是工厂生产棉织品,上半部分是农民拉着牛车将棉花原材料源源不断送入工厂,而纺纱女工作为画面的主体将上下部分在画面和观众心理逻辑上连通起来。上半部分严格遵循透视的原理,以水平线上的消失点确定农民牛车队伍构成这一弯延伸线的深度。在全图画面右侧呈直角三角形的纺纱女工,面色展现的是劳动人民式的偏黝黑的红润感,与上海月份牌里美女们那种白粉底上的胭脂红有着刻意的差别。这种面色力图塑造的,不但是自然与人工的表面差别,更是劳动阶级的热爱工作与中产阶级好逸恶劳的内在品质的差别。翁逸之的其他妇女题材宣传画延续的也是这类“劳动妇女”形象,如《要把社里的猪养得又肥又大!》(195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这一幅画当中,身着青蓝粗布衣裤的女社员正在刷洗一头壮硕的肥猪,她头上的红裹巾是唯一带有女性特征的装饰。新气象之下是妇女通过职业劳动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努力,展现的是“个人生活的小事与国家建设的大事融为一体”的工农化的新时代精神[4]。
诸如此类“劳动妇女”形象的宣传画还有很多,如丁浩的《我们为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而自豪》(1954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哈琼文、游龙姑的《提高技术,争取更大的节约》(195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都是40年代苏联式构图。丁浩在此作品中描绘了一位电焊女工,身上洋溢出的是铁一样的热情和朝气。而哈琼文、游龙姑画笔下的两位女工,也是一心专注于纺织工作的劳动英雄形象。“劳动、游戏、仪式”原本就是身体主体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上的展开方式,构成了所谓社会形式感[5],于是这些“劳动妇女”的角色样态就成为了新型宣传画“新气象”审美风尚中的主要妇女形象。
二、“劳动创造幸福”理念下的性别特征
如前所述,在新宣传画中的“新气象”审美中,“劳动创造幸福”是最核心的理念。“劳动”作为那个时代的关键词,直接影响到宣传画里的妇女形象。劳动不但是人类改造生活的自由自觉的主体实践活动,而且是女性藉以争取与男性平等地位的重要途径,所以让“劳动妇女”凸显为新女性需要主动去效仿的正确形象。宣传画表达的主流意识形态很清晰:妇女需要的不是满身商业脂粉气的优雅,而是职业劳动焕发出的无穷力量。这就像后来身体美学理论所言:“身体在陶醉于自己的强力感时便会进入美学状态,变得轻盈、敏感、兴奋。在这种状态中,怀有强力意志的身体在创造、给予、享受、狂欢、陶醉、自我提升,在让思想成为生命力丰盈的内在现实。”[6]
不过,虽然“劳动创造幸福”是贯穿20世纪50到70年代的核心理念,而“劳动妇女”是这一时期女性唯一“政治正确”的外显形象。但是,如果对这一时期进行细致考察,还是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间的显著差别。大致说来,50年代初期的宣传画更偏重于女性的“战斗性”,使得女性形象呈现出“去性别特征”的中性化趋势。而随着国家的稳定发展,从50年代后半段开始,宣传画中女性的性别特征开始愈加显著地展现出来。
苏联宣传画的印迹在50年代初的新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上还较为明显,甚至有的中国宣传画除了里面是中国人和汉字之外,与40年代苏联宣传画外观基本无太大差别。而且,由于刚刚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出来,此时的宣传画里的所有人物都是战争动员对象,所以无论男女都呈现出一种战斗者形象。因此,50年代宣传画里的“劳动妇女”形象基本侧重在“劳动”性质而非“妇女”特质上。在职业劳动上创造自我价值的新趣味,成为宣传画表现的核心,这既是当时国家意志希望凸显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也是建国前长期作为男性附庸、遭受男女不平等的女性翻身做主人诉求在艺术文本上的集中展现。
无论是丁浩的画作还是前述的周令剑、翁逸之的画作,里面的妇女形象一律与女性特征絕缘,全部采用中性化的风格,这与解放区带来的“左翼式的清教徒”审美惯性相吻合。在强调战斗精神的解放区审美中,革命斗争被视为第一位而被大力推崇,个人爱欲因带有某种危险的诱惑意味而被刻意排斥。
对女性身体的凸显由于可能会带来革命意志的腐蚀而被有意回避,中性化(甚至是男性化)成为这类宣传画中的主流。这一点倒是与苏联宣传画有所区别,因为苏联深受法国新古典主义画风的影响,其宣传画中的男性与女性体格的描绘都较为严格地遵循人体比例,以便展现出一种大理石雕塑般的力量感和崇高感。于是,在苏联宣传画中,作为女性重要特征的胸脯就毫无避讳地成为突出表现的对象。在诸多苏联画作中,女性的形象是与她们丰满的乳房联系在一起的。比如195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以12张一套的明信片形式向全国发行的56开《苏联宣传画》中,男性四方形的健硕胸脯和女性浑圆的乳房成为了苏联新公民健康有力体魄的标志。但这一点就让中国同行感觉到有些尴尬,因为苏联新古典主义风格是建筑在苏俄文化底色之上的,而这种对肉体轮廓特征的强调,到了以延安文化为底色的新中国风格中就遭遇到了“水土不服”。当时,新中国文化沿袭延安以来的“左翼式的清教徒”风格,对这种充满肉体之美的人体特征还有着相当的忌讳。但中国的“左翼”文化工作者们又不便直接表达自己对肉体的“忌讳”,因为担心被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视为“老封建”。于是,在两难处境之下,50年代的中国宣传画创作者采用策略性的回避方法:要么给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裹上厚衣服,以便不露声色地模糊掉女性曲线;要么在女性形象胸前设置诸如“手捧棉花”“举起稻穗”等情节,委婉遮盖敏感部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50年代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并且贯穿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震荡,但经过十年和平建设之后的中国开始呈现出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审美欲望。这反映在宣传画中,就是60年代初的不少画家已经逐步突破50年代过于注重战争和革命气息的框架,开始把生活气息灌注进劳动场景当中。于是,他们画笔下的“劳动妇女”形象,其侧重点逐步从“劳动”这一端移向“妇女”特质那一端。在1963年前后的不少宣传画创作者那里,努力在劳动场景中更大程度地展现女性之美就成为了他们突破之前重复了十年画风的转型方向。对应地,同样是贯穿“劳动创造幸福”理念,60年代初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显著的女性性别特征。
同样是表现乡村生活,同样是身着农民衣服、短发圆脸,也同样是表现劳动场面,但在诸如盛此君的《稻香千里飘,人人逞英豪》(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类的宣传画中,妇女身上淳朴的女性之美已经突破顾忌,热情地洋溢出来,与建国初期“中性化”“男性化”的形象有着显著的区别。又如徐寄萍、王柳影的《新农村》(1964年,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一四联长条形宣传画。其第一幅画里,女主角身穿大红上衣,扎着马尾辫,背后两只燕子绕着柔美的柳树飞翔。这种柔美风格的绘画在50年代是较为少见的。在其他三幅画作中,女性形象的职业身份分别是农药女工、施肥女农和电线检修员,脸上展现的是唇红齿白的愉悦笑容。她们背后是诸如花朵、绿茵、稻浪等具有装饰效果的浪漫化物象,物象和人物构成一种审美张力,彰显出的是新时代妇女那种健康活泼的女性之美。可以说,在当时的宣传画创作者笔下,劳动建设是为了革命,但更是为了富于诗意的日常生活,“新气象”生活美学的风尚在这一时期就以刚健中带着柔美的风格而呈现出来。
三、上海月份牌画风格在60年代初的短暂回潮
如前所述,在“左翼式的清教徒”的革命理念里,女性的胸脯是象征着诱惑和欲望的危险标志,解放前的上海月份牌里就满是这种弥漫着欲望的女性形象。但与诸如徐寄萍、王柳影《新农村》宣传画里的女性形象相比,她们上衣已经不加掩饰地勾勒了自己作为女性凸起的胸脯。这些直接展示女性特征的宣传画在当时的语境下包含着一种危险:审美欲望压倒革命意志。所以,它们在60年代初昙花一现之后,随即就被70年代的“再革命化”的“革命妇女”形象所取代,而且也给画家们的创作带来了麻烦,日后成为了他们利用宣传画宣传“资产阶级色情趣味”时无可推脱的图像“证据”。毕竟,在长期强调思想和道德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中,身体一直都属于“被忽略、低估、贬抑”的状态[7]。
在这一批昙花一现的柔美宣传画之中,李慕白和金雪尘创作的《人勤花香》(196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相当值得一提的。这幅宣传画完全摆脱了苏联式宣传画那种新古典主义的特征,真正具有了新宣传画独属的中国特征。这幅画使用的是现代欧洲光影立体构图,表现的却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趣味。但这幅画“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其浓烈的上海月份牌气息。作为商业推销重要载体的上海月份牌,其绘制的直接目的即是通过美女图来吸引受众眼球,从而为提高商品销量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月份牌创作者们将时尚元素引入这种新年画之中,最突出的就是旗袍在画作中的广泛运用。旗袍既是当时作为时尚之都的上海最流行的服饰,又是最能勾勒女性身体之婀娜的贴身服装,极能吸引观者的窥私欲。于是备受创作者青睐,在那个“摩登女郎”常被“污名化”的时代,这些月份牌画在中国迅速地产生了深远的影響力[8]。
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月份牌画成为被新政府关注的对象。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一号文件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对包括月份牌画在内的流行绘画的改造问题:“在某些流行‘门神’画、月份牌画等类新年艺术形式的地方,也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这些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在50年代初对月份牌画的审查和改造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些冲突,比如当时上海宣传画方面负责人陈烟桥的一次讲话还引起从业者的惶恐不安:“你们所保留的旧年画有多少我们统统知道,希望大家能自动报出来,不然卖到哪里可能都要追回来交还给你们。”[9]但新政府主要整肃在背后掌控月份牌画创作内容的商家,以及月份牌画中的反动落后因素。至于月份牌画这一画种却并没有被简单化地禁止,月份牌创作者也没有受到排斥,而是被组织起来,将月份牌画技法运用到对社会新气象的表现之中。而且这些创作者还被政府作为老艺术家聘请来培养年轻画家,组成创作新年画的新团队。
其中,李慕白、金雪尘等人就这样在新时代中成为了新中国宣传画创作的重要画家。作为解放区曾经的“穉英画室”成员,何逸梅、金雪尘、李慕白等人在杭穉英的带领下,在月份牌画创作中打造出了具有较高创作水准的团队,具有相近的创作风格。在本文提到的李慕白和金雪尘创作的《人勤花香》这幅画中,旧上海月份牌画的某些风格和趣味都有“浴火重生”的迹象。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类型的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海月份牌画“胭脂美学”风格的部分复归,但并非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立足于新的时代精神之上的“扬弃”,继承了前者追求女性特质的审美精髓,又脱离了前者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带着的“铜臭味”,跟新中国崇尚劳动的理念相契合而又突破了“左翼”传统理念中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而不能体会生活之美的偏执和狭隘。
画中的这一女性,上穿米黄衬衣,下着淡蓝长裤,头扎马尾辫。这些都是新中国城市女性典型的朴素穿着,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慕白、金雪尘两位作者在创作时加入了浓郁的月份牌画趣味,跟他们在解放前为阴丹士林创作的月份牌画风格趣味极为相似。这种“穉英画室”风格有一种基本模式:女性面容姣美迷人,身材凹凸有致,通过脸型和兰花指等细部风格来展现女性的柔媚,画面底部往往用娇艳的花朵起到装饰和烘托氛围的效果。女主角望向远方的眼神,在平面的构图中创造出一种超越画面的空间感。
在《人勤花香》这幅本应该展现劳动主题的宣传画里,创作者却展现出了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上海时尚趣味。这其中最“媚美”之处就在于创作者对女性身体的描绘:这是一幅用描绘贴身旗袍画法来创作新社会城市女性的“变种”上海月份牌画。它打破了50年代模仿苏联式宣传画的窠臼,却与即将到来的60年代后半段的“极左”革命趣味严重冲突。
作为“肉体”的身体存在,在保守意识当中一直是一种很可能危及“革命理性”的欲望之物,但从现代身体美学的角度看来,既然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那么审美活动的承担者必然基于“感性的、劳作的、拥有表象”的身体,而身体正是一个长期遭受蔑视却是每个个体生命思想和情感出发的地方[10]。虽然身体不应被简单化地视为肉欲场所,而应当被视为是思想与世界沟通的中介。但在特定语境下,比如在“极左”革命趣味看来,肉体依旧是危险的挑衅之物,不但活生生的肉体需要包裹起来,就连艺术作品中的身体意象也要设法屏蔽。
但在这60年代初的短暂“回暖”之中,“穉英画室”风格的上海月份牌画为了凸显女性曲线的美媚,在几处细节上着力刻画:发式、脸蛋、手姿、胸部。这些细节就在整体意义上构成了女性的本真之美。当然,如果要挑刺的话,《人勤花香》还是能找出不少缺点。比如在这幅宣传画里,女性手指造型是纤细的,这显然不是“五大三粗”的工农劳动妇女的手指,而她脸庞的肤色被设置为白里透红,而非黝黑之中透红,这都是典型的城市趣味,没有直接展现劳动妇女的革命建设意志。此外,这幅画中对女性胸部的描绘也已经越出界限。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上海月份牌画出于吸引眼球的角度考虑,在画面中描绘女性胸脯时,特意让乳形在旗袍上挺出,以便体现年轻女子身体的性别特征。作为直接的呈现,隔着薄薄上衣所显露的乳尖形状是这些上海月份牌画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用土布衣服勾勒出了旗袍装束的省腰和省胸效果。在杭穉英的《华屋春嬉图》《阴丹士林小姐——陈云裳》《李香兰》、金梅生的《双义同风》《人面桃花相映红》等民国月份牌画里,其中的女性无一不是这样让乳尖形状在薄上衣显性的形态①。
如果说月份牌画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窥视下对女性的艺术规训,那么新宣传画中的妇女形象就是一种女性之美在文化政治上的博弈,虽然发展过程中也有波折,但在50到60年代初都呈现出一种健康发展的趋势。当然,具体到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语境之中,仍然可见政治意识形态对身体的某种规训和制约。回顾整个50年代新宣传画的女性身体外观,可以得出结论:女性上衣呈现出苏维埃式的浑圆形状的乳房轮廓,已经是革命语境下新中国绘画中女性特征能容忍的最后底线。因为至少作为社会主义同盟的苏联、波兰等兄弟国家也是这样表现女性身体,浑圆也可被解读为母性和健康的象征。但《人勤花香》里的身体形状已经走得更远,是上海月份牌画风借助新时代女性服饰这一外壳的复归,连乳尖的轮廓都一览无遗在画面中呈现出来,这种已具备现代时尚气息的绘画手法,在当时国家的整体意识形态氛围中显得有些特殊。在女性身体上近似于《人勤花香》的,还有忻礼良的《巧女散花》(196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少数几幅画。《巧女散花》描绘的虽是纺织女工,但其实是按照解放前上海月份牌里的仙女形象来构图的。忻礼良将人物置于画面的中心,使受众观看纺织女工时需要采用仰视的视角,而画面构图中的花朵摆幅构成了非对称的立体效果。画家通过人物的体态,特别是细腻的手和面部表情,将人物喜悦丰盈的内心情绪外化,具有较强的审美感染力。其技法上糅合了月份牌画和苏联风格,而本质精神上却是新的审美风格。创作者用苏联风格冲淡了上海月份牌画的“美媚”,但又吸收了“美媚”之中的柔美,填补了苏联风格过于刚硬的不足,加上解放区风格的融入,使得其中蕴含的不是涂脂抹粉的漂亮,而是真正的从内在丰盈向外彰显的健康之美。
诚如当代学者许徐所言,从“图像政治”的角度看去,宣传画的核心使命就是为了“使政治理念更加活灵活现”[11]。由于作为主体的身体“同时拥有感性和理性”[12],而且政治理念等意识形态也需要通过身体审美而彰显,“从潜在走向现实”[13]。所以,宣传画也需要通过身体来传达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讯息。而优秀的宣传画并不是直接從属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是听从更加高远的“文化政治”的召唤。
在这样的氛围中,诸如《人勤花香》《巧女散花》等生活型宣传画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们不再是简单化的政策传声筒,而是超越直接政治属性而走向了更加广泛的“文化政治”的范畴,实现了政治意涵和审美韵味的有机统一。以《人勤花香》《巧女散花》为代表的这一批画达到了新中国妇女题材宣传画又一次新的高峰。这几幅画作虽然在当时的宣传画里属于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让今人管窥到当时上海气氛的宽松,以及彼时都市审美风尚的逐渐恢复。
革命是为了更好的建设,劳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那么通常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繁荣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更加注重审美性而淡化斗争性,无论是职业劳动还是日常生活都逐渐趋于审美化。新中国宣传画中的“新气象”审美风尚正是这种社会演化在艺术领域的体现。
不过随后政治大气候的变化迅速改变了60年代初的文化生态,反映在宣传画中即是革命性、战斗性特征的空前增强。跟50年代强调“劳动”,60年代初推崇“生活气息”显著不同的是,“文革”时期宣传画突出的是“革命性”,而且领袖主题几乎席卷这一时期的宣传画创作。具有轻松愉快特征的“新气象”审美风格就此在60年代骤然被转化为有些异样的“文革”风格。
四、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3年之间这段时间里,妇女题材宣传画经历了数次嬗变。早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形象建构,赋予了女性形象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利意识。而进一步的“劳动创造幸福”理念下的性别特征的显现,则将之前中性化风格回归到对女性特质的重视,特别是升级版的上海月份牌画风格在60年代初的短暂回潮,让既具有女性柔美特质,又不脱离文化政治范畴的健康向上的女性形象透过宣传画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尽管在60年代后半段因为历史的原因走向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但不可否认的是,50到60年代初的妇女题材宣传画仍然与其他的宣传画一起创造了宣传画史乃至现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突破了过去文人画和上海月份牌画那种狭窄的选题,将自己关注的范围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一种初级阶段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实现了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的有机融合。在这些宣传画构造的宏大审美意识当中,女性不再只是旧式闺阁中的怨女,也不是商业宣传中涂脂抹粉的“花瓶”,而是用劳动创造未来的新女性,而这些绘画也就在此节点上实现了艺术介入现实的重要文化政治作用。这一系列探索实践为新中国的文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并树立了宏大的格局观,故而对于今日艺术创作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注释:
①在现实的旗袍制作中,早期的京派旗袍以宽松的平面造型为主,衣身没有省道应用。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海派旗袍开始引入西式立体剪裁,用了胸省腰省设计,胸、腰、臀的曲线凹显出来之后,胸脯也就在外衣上显山露水起来。为了在性感和温婉之间寻找平衡,旗袍制作者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那就是在前胸和领口等处进行刺绣,这些诸如凤凰、喜鹊、月季、牡丹、梅兰竹菊等图案,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了肉体轮廓特别是乳尖轮廓在外衣上的直白表达。即有学者所谓“紧紧的包裹不仅没有突破中国人的风化底线,还有了另一种韵味。”(刘瑜,孔诗曼琦.海派旗袍与中西服饰审美研究[J].大舞台,2015(7):62-63.)
参考文献:
[1]王晓华.身体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3.
[2]草野文男.支那邊區の研究[M].东京:国民社,昭和十九年二月十日印刷本(1944):23.
[3]罗小凤.诗言“感觉”——20世纪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J].文学评论,2013(6):41-49.
[4]付玉竹.公共艺术视觉说服的途径与意义——以1949-1976年宣传画中的农民形象为例[J].文艺争鸣,2018(9):196-200.
[5]王晓华.身体主体间性与个体审美能力的生成[J].河北学刊,2011(3):25-31.
[6]王晓华.西方主体论身体美学的诞生踪迹[J].学术研究,2009(11):129-135.
[7]王晓华.身体视域与生命美学的理论建构[J].美与时代(下),2018(5):5-11.
[8]唐娒嘉.20世纪30年代社会媒介的“摩登女性”想象[J].妇女研究论丛,2017(5):79-89.
[9]杨冬.论建国初期上海月份牌年画改造[J].美术观察,2016(8):105-111.
[10]王晓华.身体思想的整合与中国诗学的重新出场[J].上海文化,2018(2):15-26.
[11]许徐.图像政治:《红色中华》宣传画的图像学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1):133-136.
[12]王晓华.伊格尔顿的主体论身体美学[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11):1-7.
[13]王晓华.西方美学身体转向的现象学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15(5):108-115.
作者简介:简圣宇,博士,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批评、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