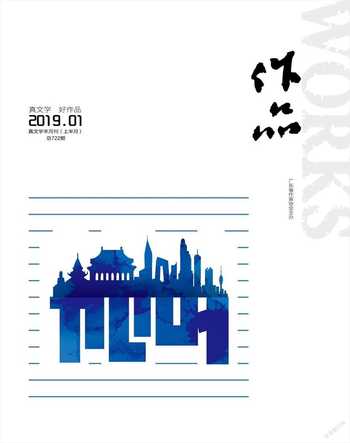每个作者都是不同形态的纳博科夫
赵文
三十年前,中国先锋派作家们讨论卡尔维诺、纳博科夫、川端康成;二十年前,《活着》《长恨歌》还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十年前,先锋文学不再先锋,纯文学走向一条愈加孤独的路。
如今,不说写纯文学的作家,只怕能静下心好好阅读纯文学的读者也愈来愈少了。纯文学像孤军奋战的勇士,残阳如血,英雄挽歌。于是,纯文学在叙述形式上悄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穷途末路,而应该是曲线救国。
毫无疑问,《咱那个》是一部实打实的纯文学作品。但作者着实在叙述和结构上动了一番心思,把原本可以写成煽情的,旖旎的故事,写成了悬念的,有趣的故事。
纳博科夫曾表示,不应该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小说一开始就埋下伏笔,读者的心被“咱那个”这根线紧紧揪住,在作者精心设置的种种悬念中寻找答案。若单论故事,并不复杂,有趣的是,作者一直在节外生枝,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而“咱那个”也极为不稳定,一会是这个,一会是那个。这种寻觅者和被寻觅者的双向不稳定性,使得一个平常的故事,读起来悬念迭起,险象环生。
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我”翻开张子轩笔记的那一段。那是一堂精彩的文学课。作者用张子轩之口,对《包法利夫人》等经典的重新认识与当代文学如何突破瓶颈做了一次新的尝试。可以说,这是一篇既有纯文学之纯,又有新技巧的探索,更具有说服之力的评论的小说。
小說中还有一处一闪即逝的描写。“我”看张子轩的《把经典刻在心上》花了四个小时,没喝水,身子没挪动一步。我觉得这是作者从内心渴望前辈和晚辈一同维护文学的尊严而发出的呼唤,毕竟这个世界,钢筋混凝土包裹着的都是一颗颗柔软的心。每个读者心中的洛丽塔都不一样,每个作者都是不同形态的纳博科夫。
作者有很深厚的文字驾驭功底和娴熟的搭建结构能力。在作者鬼使神差般的文笔下,“咱那个”变得扑朔迷离,就像小说中提到的一首歌名《不存在的存在》。存在与不存在,不正是当代纯文学的尴尬处境吗?如果我们仔细读结尾,不难发现,这也是作者的尴尬。“咱那个”是作者的臆想,“咱那个”是作者的爱人,“咱那个”是张子轩,“咱那个”又不是张子轩,“咱那个”可以是任何一位作家,“咱那个”也可以是任何一名文学爱好者,“咱那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们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