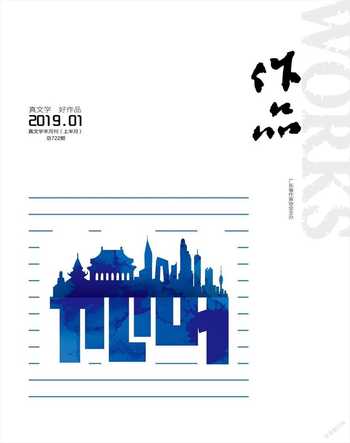要去莫斯塔尔吗
葛芳
要去莫斯塔尔吗
莫斯塔尔是什么?
一首歌,还是一种饼干的名字?
倪小丫的购物袋里装满了小南瓜和土豆,沉得很。闺蜜林晨的电话打来时,她正在拼命追赶地铁。好不容易找了个空隙坐下来,接通,林晨的声音很模糊,时断时续,但掩饰不住兴奋劲儿。倪小丫无意间瞥了一下窗外灰扑扑的站台,一个胡子拉碴的流浪汉在垃圾桶旁乱翻腾。莫斯塔尔——林晨依旧孩子气地嚷嚷。倪小丫喉咙干咳了一声,问,莫斯塔尔是什么?电话挂断了。
一个月以后,倪小丫怀上了第二胎。政策放开了,生就生呗!国家鼓励生。老公沈山轻描淡写地说。
回到家,倪小丫捏着妊娠化验单怔怔的,她想电话一下林晨,有些事和闺蜜商量,更会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男人说到底是自私鬼——生吧,养吧,嘴巴上轻轻一绕,结果全是女人的事。
林晨关机。她神出鬼没,倪小丫常数落她,老大不小了,该找个人把自己嫁了。自己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林晨还单身一人,三十五的年纪很尴尬,这城市优秀的大龄剩女太多,不结婚,以后老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怎么办?
她忽然响起地铁上接的电话——她隐约记得,林晨兴奋地叫着“莫斯塔尔”,那天倪小丫忙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洗洗刷刷,就忘了再和林晨联系。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她单位部门的领导换了,她得适应新领导的节奏和口味,写材料挖空心思,关键领导是个女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文件上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有误。
林晨是一个特别有新鲜感的人,这和她没结婚也有关系,一直是小女孩的腔调,眉眼、口吻、说话的姿态,也还是女孩式的。譬如她会晒着阳光伸长腿晃荡,然后眯缝着眼说,哦,阳光不错,我要买件新衣裳让自己开心。她喜欢桃色口红,唱歌很好,养一只白色小泰迪。出远门时她会把小泰迪寄养在对门的一对老夫妻身边。
林晨父亲死得早,母亲在她大学毕业不久也仙逝了——倪小丫对林晨总有种怜悯呵护之心,觉得她命太苦,没靠山没父母,孤零零一个。孤零零,是倪小丫最害怕面对的,她会联想到一棵光秃秃树上哀鸣着的乌鸦,一堵没有颜色的墙,一朵墙角独自开放的花。她受不了这样的境况。
她问沈山,莫斯塔尔是什么?
沈山忙着打游戏,耸耸肩,说,不知道。
倪小丫有些来气了,说,生生生,我生了第二胎,你照样打游戏,还怎么过日子?
沈山说,这不还没生吗——放心,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爸妈,你爸妈,这不一堆的人服侍?
倪小丫的头轰一下子炸大了。昔日婆婆和她关于孩子教育抢夺战的镜头历历在目。婆婆说,孩子那么小,哪能独立睡,不行,要放在我怀里,捂着我胸脯睡。婆婆又说,沈山小时候不都是吃我嚼过长大的?哪那么多讲究?
倪小丫的心怦怦乱跳,好像要挣脱令人窒息、监牢一样的胸腔,坚决不行——她把自己的手摁得发青。女儿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她和婆婆的关系也一度演变成一触即发的敌对状态。
她想林晨了,林晨的名字常被人误认为凌晨,凌晨的熹微,雾蒙蒙的,人迹板桥霜,就马不停蹄上路了。林晨喜欢这样的状态。林晨是她闺蜜,当然也是她倪小丫的精神垃圾桶,每当她承受不住要絮叨控诉一番的时候,她就电话林晨,然后小姐妹拉她去喝杯酒狠狠地把生活中不堪的庸俗倾倒出来。
什么狗屁科长啊!
什么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
林晨让喝得晃晃悠悠的她回家,然后捶着沈山的肩膀说,照顾好你老婆!别让她生气!
倪小丫打开窗帘,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中。她想林晨又折腾什么去了?一惊一乍,当然她没有牵绊,没有负担,可以随心所欲,这样的人生,始终在梦中,在路上,真的挺好。
林晨喜欢她女儿,每次来,赤着脚,俩人在地板上玩得一般大小。她在厨房做饭,看见她俩咯吱咯吱笑得把沙发垫扔得东一个西一个。女儿也喜欢林晨,说,林阿姨身上有桂花味,林阿姨说话也是甜的,好好闻啊!
林晨说,做我干女儿哈!
好!女娃乖乖巧巧答应,一百个讨欢心的那种。
倪小丫心想,还真是投缘了,林晨没爹娘没孩子,认个干女儿倒是最贴切的了。
沈山可不乐意,说,疯丫头一个,被她要带坏的。
夫妻俩也就被窝里说说这档话。沈山诋毁闺蜜,她还是生气了,转过身不睬沈山。沈山是个马大哈,游戏玩累了,揉揉眼也睡了。倪小丫睡不着,她想男人真没心没肺,啥不用操心,汽油价又涨了,贷款的钱每月要放进去,女儿培训班的费用现在居然要交年费啦!
她问过林晨,你不害怕孤独吗?
清晨,一切都还是黑魆魆的,林晨搭上去往远方的火车。火车遥遥,把她带往高山、深林、峡谷、溪涧。车厢里有几个人聊得火热,各自在分享旅途心得。林晨还是喜欢把自己抛入孤独的状态,看着窗外出神。
她又问,你不成家也好,你有喜欢的男人吗?上过床的有多少?
林晨伸出一个手掌。
五个?五十个?倪小丫的心又怦怦乱跳起来,好像这和她很关联。
林晨嘘地笑开了,瞧你那表情——五个,太低估我了,五十个,又太高估我了,本小姐活到三十五岁,跟十五个男人上过床,还是有的——
她想捶她,狠狠捶她!她才沈山一个。其他男人的好坏,她都没法比较。
黑夜里,她睡不着。散架一般的累,缠绕着她。她又担心明天早起不了,做早饭,送女儿上学,打冲锋一样,神经高度紧张——林晨比她会看男人,她说男人的品位时仿佛在品一道菜一样,倪小丫心想沈山是一道什么菜呢?酸辣土豆丝还是红烧狮子头?仅此而已。
她索性起床,试着再拨。还是关机。
她想她没有必要担心。莫斯塔尔,可能是一种饼干,意大利甜点,林晨吃货一个,最喜欢在淘宝搜索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她侧弯着脑袋,一只手拿本书,一只手抓住饼干往嘴巴里送的模样很迷人。那天,就在她倪小丫家中,她系著围裙做排骨汤时,发现林晨坐在飘窗上,如此状态,她愣了半晌。在自己家中,她倪小丫从来没有这样休闲和惬意过,没有这样的心情和时间,她忙忙碌碌,把自己搞得像转轴一样,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把阳台客厅布置得花花绿绿。
她想,她俩以前在宿舍时就像是一个合体,现在变化差异太大啦——她不晓得是她倪小丫变得越来越庸俗,还是林晨越来越向着诗和远方在奔走?
沈山起来,上厕所,回到床上瞬间又呼噜震天。
他的手机屏幕亮了,在黑夜中一闪一闪,格外刺眼。
倪小丫凑上去看,是微信信息。她一般不去研究沈山的隐私,这是夫妻间起码的尊重,但那信息提醒让她悚然一惊。
林晨发来的,文字很短:睡了吗?
他们之前何时有了联系?文字虽短,但绝对是不一般的关系,直截了当。倪小丫想起前几天丈夫沈山游戏到很晚才睡,起码一点钟,今晚破天荒地早早扔下游戏睡觉。
倪小丫喉咙焦毛,有些短路,为什么林晨不发她微信?是怕吵醒她影响第二天起床送孩子?也有可能。
又来一条信息。
你床上姿势酷毙了,至今回味。
瞬间黑屏。
一种被子弹击中的感觉,初始无痛,但有血从胸膛缺口处洒出,然后,巨大的疼痛感袭来,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倪小丫真希望自己中真实的枪,然后周身麻木、抽搐,眼瞳变得大而无光。她亲眼见证过死亡,她的一个亲戚,干枯的手在空中划了两圈,随即直挺挺去了。
——太快太短促,亲戚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情绪,死亡就降临了。倪小丫恰巧来探望,她脖子一处僵硬,怎么也转不过来,直到那户人家放了响炮,告知全小区老人去了——她才回过神来。她想,死亡就在一刹那,她好像看到一个森然的鬼影闪现,又倏忽哧溜走了。
现在,鬼影幢幢。
一个是她闺蜜,一个是她丈夫。电视机里最烂的肥皂剧会这样设计。她不明白生活中竟真会如此荒诞,一点也没有提醒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前因后果。倪小丫干愣愣地缩在客厅沙发一角,她听见电子钟嗒嗒的走动声,月光在移动,阳台外就是小区树林,有一只鸟扑棱棱飞起,发出微弱的啾啾声。
她是客廳里的一个揉皱了的布艺沙发,还是那愣头愣脑的电子钟?他们在床上的时候完全把她忽略了,但她偏偏是客观存在的——
让她不能容忍的是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的欺骗,飘窗上那盆月季花假惺惺地开得这么茂盛,旮旯里的扫帚柄这样神气活现地挺立,还有,林晨看的那本书《你好,忧愁》还在,也肆无忌惮扫视着她倪小丫——你这十足的傻瓜!
莫斯塔尔。
莫斯塔尔?
沈山就像是莫斯塔尔,不可捉摸。她去厨房转了一圈,一个月前买的土豆还在,在角落里变绿并严重渗入到内部,倪小丫原想把它丢了,可总是忘记,她记起来拎土豆的时候她接到有关莫斯塔尔的奇怪电话,然后就没了下文——发霉的土豆有毒,明天她还拿来烧菜给沈山吃吗?
厨房里刀具明晃晃,当然,她不会神精失常,像林晨提起过的台湾作家李昂小说中《杀父》情节一样去行事。她只是好奇,她问沈山莫斯塔尔是什么时,沈山耸耸肩,一脸茫然坠入游戏的样子。真是会装!他在游戏她。她不明白他何时长了心智,会十八般技艺,会把生活当游戏一样假假真真扑朔迷离。当然,他早已不是她心中的男孩,以前瞧着他总觉得傻大个,要她来哄他、照顾他。如今她明白过来他现在是个男人,一个彻底的男人,而且属于渣男一类。
莫斯塔尔。
莫斯塔尔?
她想她要疯了——这个咒语、巫术一类的词儿,她小不小被它笼住囚禁。她打开手机,百度搜索一下,应该是音译过来的词语。输入进去,真的跳出来“莫斯塔尔”四个字。
“莫斯塔尔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莫斯塔尔以一座古老石桥著称。老桥将居住在河两岸的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居民联系在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3年9月9日,波黑战争开始,老桥两边的民族互相仇杀,老桥被炸毁。”
她继续查阅,查得头痛欲裂,大量的历史地理政治背景。她读高中时最害怕这些,而林晨相反,最感兴趣,她站在地图前,仿佛君临天下的女王,要把每个吸引她的点都涉足。
她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月前林晨打她电话时应该是在去往波黑莫斯塔尔的路上,兴致勃勃,风尘仆仆。她已然和沈山有了关系。她告诉她去莫斯塔尔的寓意是什么?
整个波黑战争死了那么多人,27.8万人。塞族、穆族、克族彼此仇恨。她终于理清了这些政治背景。当然,现在老桥修复了,把原来炸毁时掉在水里的石块打捞起来原样修复。老桥也成了旅游胜地,挤满了游客。中国是免签国,直接打飞机去。
她是不是也该抛下所有虚妄所有日常,去老桥边会一会这个闺蜜呢?
俩人在桥边喝一杯波斯尼亚咖啡,晒着太阳,说些虚伪的贴己话?然后她倪小丫趁其不意将林晨从老桥推下,去那湍急的河流洗净灵魂吧——
她不会这样,臆想并不代表现实。她只是对自己有了心灵的关照。
她回到卧室。沈山醒了,他正儿八经坐在床上,像尊佛。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
像梦的呓语,倪小丫轻轻说了一句,明天去莫斯塔尔吗?
她捋了一下前额,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时间,也没钱。她轻轻抓起他的手,引着它划出了一座桥的模样,然后又缓缓放下,好像他是个盲人和聋子。
没多久,小区楼下传来汽车引擎发动声。好吧,也许,明天倪小丫真要去莫斯塔尔了。
白色之城
外面很冷。
她尝试着推门,寒流从缝隙里钻进来。树叶可怜地晃荡在枝头,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
咖啡机磨豆的声音吱吱响,还是昨天那个酒保,平顶头,手脚麻利,衣领洁净,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她在世界杯足球赛见识过几位足球明星,于是她固执地认为他就是克罗地亚人。
她在贝尔格莱德。她决定这一天不出门,窝在酒店,干什么都可以。昨天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他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都是他的错。
那时她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的自由广场,坐在教堂台阶上读完了一个短篇小说,很久没有这样投入读文字。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眼泪涌出,小说里那个男主人公有多孤独啊,他在铁路边的旅馆进进出出。小说还配了爱德华·霍泊的油画。广场上鸽子飞起来,掠过她的头发,她忽然忘了她是谁,身在何处。
贝尔格莱德的一日游,她随当地旅行团出发。导游喋喋不休,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他一刻不停讲述着当地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听得她昏昏欲睡。后排是一对中国小年轻。男生英文较好,默默在听,女生叫小月,喜欢摆拍。
他站在窗前抽烟。
他在窗格上摁灭香烟,随即扔掉了烟屁股。
她曾警告过他抽烟会导致多种毛病。他笑着说,他村上活得最长久的老爷子就是抽烟最厉害的。起初她爱上他还要归结于那淡淡的烟草味。烟是很普通的烟,红南京,以前江苏人爱抽这个。她在一所大专读贸易,而他已经是河海大学的高才生了。
她不想让自己回忆。回忆是一条长长的铁轨线,老套、过时、甜蜜和心酸杂糅,且一去不复返。她看见小月兴奋地拍打着男友的肩膀,女孩笑起来有个酒窝,白色衬衫扎在牛仔裤中十分英挺。
即将生发的感觉,她想,恋人在奔向激情的时候都是这样。
他的烟屁股扔得到处都是,只要有孔可插的地方,他都不会放过,最可恶的是还浇了水,有时看上去像一汪便池里的污秽物。她为此和他争吵过。
他先是好脾气,然后不说话,夜晚他揽过来吻她,一笑泯恩仇的那种。她闻着他的烟丝味却睡不着了。夜晚是没有阳光的,她的心跳需要在阳光下加速。他大约是感觉到了她内心的骚动,温柔地按揉她,熟稔、准确,她犹如小鹿听话般臣服。
小月在修道院苹果树下叽叽咕咕。果子太多了,很自然地从枝头掉落腐烂在地上,空气里都是甜稠的味道。她不知道小月认识男友多久了,既然开始,就像一根箭会嗖嗖向前进。修道院的湿壁画宗教色彩很浓,有一幅剥落严重,圣徒面容悲戚但平和,她联想到了敦煌壁画里的飞天。
她等着酒保上白葡萄酒。
Enjoy。酒保轻轻说了声,谦和儒雅。他好年轻啊,应该才二十出头。
她記得那个男子。在火车站走了很远,正在谢顶的脑袋、皱纹深深的前额、开始灰白的胡子,他在跟踪一个女孩,无意识地跟踪,只是厌倦了日常生活的不堪,忽然心怀美好地追逐一个目标,然而并不掠夺。
她想叫住他,她嘿一声从喉咙里冒出了一个单词就噤声了。
她叫住他干什么?他并没有什么不轨之意——
她喝了两杯白葡萄酒。这儿距离火车站不远,初来乍到,也没什么事,手胡乱插在兜里就走到了。破败颓废之意让她惊诧,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到伊斯坦布尔豪华的东方列车途经的一站,如今门可罗雀。铁轨旁稀疏的草尖摇晃,站台旁仍有一些生锈的咖啡桌椅,水泥地面裂痕到处可见。速度很慢、车况较差的老式火车会开过,缓缓地离开站台,驶向布达佩斯,驶向萨格勒布——像一部老式电影,黑白色,冒着雾气,轰隆隆向前,虽过时,却让人怀旧。
那个男子从捷克过来,和他妻子。两人的婚姻已经发生了要命的问题。
她想她的情况也差不多,是婚姻发生了问题,还是人在走向中年时碰到了无法绕过的梗?
最初她发现丈夫的不轨是从银行里发过来的账单信息而引发怀疑。一个城市商业银行,她几乎不和他们打交道,但他们很执拗地发过来。确切地说,和她丈夫有关,他负责打理上海杭州的两家企业。再后来,她发现他和这个银行的女经理来往过密,女经理大学毕业三年,头发短得不能再短,身材火辣,酒量很好。
这样的中性女孩,不晓得是怎样吊人胃口?
她看见他翻来覆去地折着一张纸。一张白纸,刚从打印机里抽出来。他原本想打印一份材料,忽然收到一条信息,于是手足无措,忘记了该要做的事情。他折纸,拆了折,折了拆。
如今他心平气和地把纸抚平,说,离婚协议已经签好。
离得了吗?女儿是在半年前送到英国读高中的,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业和心态,她把一切都瞒得滴水不漏。分床不分居。他脱掉内裤,没心没肺地晃荡,她用余光隐忍地打量着,她想,他在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银行经理前也晃荡着软塌塌的东西。也许,哈——它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不管怎样,他两鬓开始发白,肚子发腆,他好无耻,要把他们辛苦打拼的财富,不,严格说来是把她的财富拱手让给不劳而获、不要脸的九○后吗?九○后太精明,大数据时代晓得她家的银行卡上到底有几个零。
她咬了下嘴唇。掠夺、侵略——赤裸裸的战争。她一下子联想到了贝尔格莱德城堡广场的裸体将军雕像,他站在高二十米的罗马柱上,一手握剑,一手放飞和平鸽,俯视着萨尔河和多瑙河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
她顿时明悟这位将军的决心,她也可以一无所有,愿意铸剑为犁。
在疾驰的原野上她打了个盹。金黄的麦浪在夕阳下恢宏大气,一整片,一整片。啊,是一种燃烧后的蚀骨之情。凡·高就是这样交付真心而崩了自己。反光镜里,她看见小月靠在男友肩膀上嘟着嘴睡着了。她也是九○后。脸上是阳光洁净的。
二十多年前,她和他也是这样山高水阔走中国。
小月男友应该是东北人,低调。她想,二十年前的他,也这样。他的憨厚,他的笑容,他的牙齿,他的下巴,他的头发,都凝固在风里了——岩溶凝成,清清爽爽,如果一直保持,该多好啊——
她不停地按保存键,怕一不小心丢失,手机里的照片,电脑里的工作台账。她是工作狂,经常加班到深夜回家,正是因为她的执拗,公司的外贸单才如雪片般飞来。她嗅着香樟树浓郁的芬芳,听见小溪水潺潺流淌,高档别墅区的环境是不一样,她原以为她苦尽甘来可以慢慢品啜生活的滋味。
火车站的男人折回来。她在梦里见过他,浓黑的大胡子,眼神忧郁,他摊开手,手上空空荡荡。她听不清他的发音,法语?俄语?德语?还是塞尔维亚语?她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明白他的焦虑、无助、脆弱。
她去厕所撒了尿,然后掏出手机在网上买了一张塞尔维亚的机票。免签国。她不需要通知他什么,想走就走。
女儿出去半年了,情况属于基本稳定。每个人都在学着自己走路,她想,她也要重新走路。至于他,那是他自己,他是自己的主宰者,管他个!
喂。
两天以后,她接到他的微信语音电话。她中国的手机卡暂停。
嗯,是我。
你在哪儿?
很远。
有多远?
她抿了抿嘴唇,她不想告诉他,但是告诉他和不告诉他一样,都已经没有意义。
塞尔维亚。她嘟囔了下。
哦。他惊愕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其他字音了。
她匆匆摁掉了通话键。贝尔格莱德的气候比中国冷,她踩着枯叶在树林里穿梭。高大的椴树望不到顶,心形状树叶飘转堆积。她听自己走动时细细簌簌的声音,光影交织于密林深处。她想到美国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写的诗歌《林间小路》,忍不住泪水上来了。
深夜,她打开酒店电视。有一个台居然播放着十分黄色的性交画面,她没有立即摁掉,她想她是过来人了,还有什么要屏蔽的?她盯着电视机呆看了五分钟,胸口一阵恶心,巨浪浊天,她到卫生间去干呕了。
她想,也许那中性女经理也是这样恬不知耻地和他交媾——她想把那糟糕的電视画面抹去,可越是费劲越是清晰,啊,他赤裸着下身,掀开窗帘,他已经忘记了羞耻。
小月晒了微信九宫格,“傻傻地两个人走街串巷,今天是个好日子,遇到许多结婚的新人,超多帅哥美女,超多大长腿,还发现这里很多都是爸爸在带小孩。”
嗯,她明白过来,这对小两口是蜜月旅行,攒足了婚礼贺喜的钱来欧洲了。男孩笑得十分配合。她加了小月的微信,心想在国外万一需要帮忙什么的。
她想,小月已经在给她丈夫灌输观念了:爸爸要学会带小孩,爸爸要会持家。
女儿从小是他带大的,家里两辆车的油是他负责加的,厨房里的菜是他烹饪的——这些又怎么样呢?和他吵翻的那天,她怒气冲天,一脚油门不知道开了多久,后来断油了,暮色四合,她在高速公路上哭,她不知道汽车的油箱门究竟在哪儿。
酒保的眼神澄澈,他在擦拭高脚酒杯,专注、投入,十分享受。
爱尔兰咖啡早已经喝光,白葡萄酒也两杯下肚。她在角落里挥了挥手,酒保走过来,她想对他说,你只比我女儿大两岁。
女儿终于十八周岁了,一直嚷嚷着要独立出来租房子,英国住家太麻烦了管头管脚。她对女儿生气,嚷嚷什么呢——难道你不怕贞操太早地被人夺去?这世界,什么都在抢夺,贞操被夺走是早晚的事情,信任、财富被夺走也是早晚的事情。
她张了张口,吐了个单词,“another”。
酒保又递上来一杯白葡萄酒。她想告诉他,离婚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净身出户。她是企业的独立法人,她企业的所有资产并不是夫妻共同拥有。她会和律师在这方面动足脑筋。
即便这样,很难。律师最后在电话里保留了这句模棱两可的话。
她懊恼地揉搓着纸团。她看见捷克男人站起身,到对面报亭买了盒烟,红色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停到他面前,他想了想,轻轻一拽之后,就上了车。她几乎是没经大脑思考,留了二十欧元在桌上冲出门,足够,贝尔格莱德物价相当便宜。
正午,气温骤升,贝尔格莱德的天气就是这样,阳光底下是意想不到的热,昼夜温差厉害。
她奔走得后背心发热。她索性也跳上电车,她听得见人们脸对脸、背对背互相挤搡所发出的模糊的声音。她警觉地双手向后摁住背包,万一护照、银行卡被盗走了可是个麻烦事,她听人说,有国际犯罪团伙专门盯着中国来的游客。她是典型的亚洲人的脸,个子不高,脸部的蝴蝶斑隐约可现,不年轻,也没衰老的迹象。
她眼睛有些发晕,电车上没有那个捷克男人。
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反正欧洲人的脸差不多。她沮丧地下车,她被自己弄得很是错乱。要好好捋一捋。天空倒是蓝得轻柔,好像在召唤似乎要溃败的她:有什么!有什么!天塌不下来的——好好看看,那么蓝!那么一望无垠!
她跳下车,站在荒僻的电车轨道上傻等,见识了一些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社会主义野蛮现实的建筑,不加修饰旷放的线条,怪诞的结构,让她想起了意大利建筑摄影师Roberto Conte 说过的话:“漫步在这座城市,它的粗犷和超现实感,有着令人窒息的重量。”
还是回到老城,她在米哈洛伊大公街无目的地游走,走累了,就找露天咖啡厅坐下来,懒洋洋地晒着秋后的太阳,像蜥蜴一样四仰八叉地摊开来晒着。
阳光泻在十九世纪奥匈帝国时期的建筑上和各种色彩交织。她忽然留心起那些小细节,一盏突兀的波希米亚水晶吊灯、一家书店门口贴着物理学家尼古拉·斯特拉的海报、一只鸽子停留在街心汉白玉大理石直饮水装置处——古老的铜孔里射出弧度之水。她特地凑上去学着欧洲人模样去喝水,嘿——果然,她孩子气得意笑了。
手机在震动,微信语音要求通话。
她揿掉了。
又来一条微信。
女儿知道这事吗?
她也懒得回。女儿已经十八周岁,有独立的意识去判断。
她叫的牛排上来了,油炸土豆,配上蘑菇汤,她已经几天没有让自己好好吃一顿了。蘑菇汤,有些淡,得加点盐。
贝尔格莱德空气好吗?
他忽然问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不错。她礼貌性地回了。
见她有了松动,他继续发微信。
注意安全。
嗯。
能收回吗——
收回什么?
他沉吟思索了足足有十分钟,然后他的信息发过来。
收回离婚协议。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罪责。
牛排七分熟,血丝仍在,她以前不习惯吃,现在拿起刀叉下手精准。她轻轻嚼着,他用了“罪责”两个字,看来是用心斟酌过了,罪责好像只是关乎道德,和法律无关,起码她是这样认为的,她不想现在就来判断这些鸟事——扯鸡巴淡的事,她忽然冒了句粗话。
她沿着米哈洛伊大公街继续往前走,她又登上了卡莱梅格丹古堡。全世界不少情人喜欢坐在城堡上眺望远方的萨瓦河和多瑙河。小月和她的先生一定会在。他们看夕阳、携手登城堡、傻傻地搞个两人大头自拍照,年轻人玩起来就是这样酣畅自在。
不容易啊,这样一个古城,四十四次被不同的军队征服夷平,三十八次被摧毁,但是一次次在废墟中重生。
城堡仍有古罗马遗风,白色的石头层层累叠。她站在最高处,张开了双臂,风从远方来。悲伤无处不在,阳光也无处不在。东欧的阳光紫外线辐射依然有些猛烈,她把墨镜戴好。手机下载了十几首歌,倒腾着来回播放。她和女儿时差才一个小时,如此之近,她没有告知她。
手风琴拉起,一首伤情的老歌骤然回响,前南斯拉夫《啊!朋友再见》,她和以前的他唱得陶醉。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她高声唱着,像个民族女英雄,从城堡一直唱到酒店,洗澡时莲蓬头花洒下她仍亢奋唱着。而捷克男人正行色匆匆,在铁路与公路的交叉点转换又转换。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