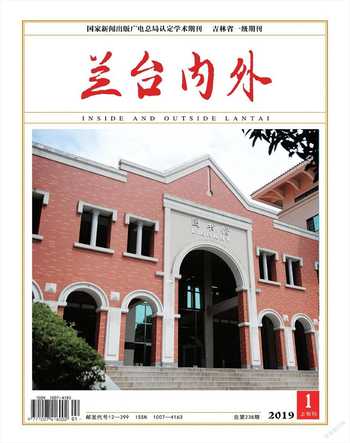从甲骨、竹简看清至近代的版本技术
高田
摘 要:从甲骨到竹简,人类由与自然关系而来的形象思维赋予其形象性。由此,甲骨、竹简决定了之后文献版本的形象性。虽然形象性的方式一再变化,但本质没有改变,直至清到近代的复制技术的不断完善,以人工的复制发展着人与自然的形象性关系,不断增加人的份量与作用。由刻板到印制,复制速度的提高,改变了人们获取文献资源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版本学以其与社会联接的基础性,将进行学术研究的家学转化为外部的大众共享资源。
关键词:形象;复制;技术
甲骨自汉字出现即是文献的承载物,所以甲骨文是最早的版本形式。甲骨上的记载最初是用来记事的,这也是商周之时社会生活的必要表现。商周社会制度的完备,阶级分化的鲜明,管理社会事物需要指令性的秩序,以指令来指导社会生活。于是甲骨文记载的即是这样的指令,先把要做的事情记下来,然后有序的进行,形成社会的秩序。既然是指令,当然由君主定制,所以甲骨文最初都是由其书写的。商代以神本观念进行统治,商王是最商祭祀,其以通神的巫祝活动,将假意于神的指令记在甲骨上,然后按其行事。后来巫师成为专门的职业,通过占卜来辅助君王行事,卜辞遂成为甲骨文的主要内容。一切事情皆通过占卜来进行,成为既定的社会风俗,即甲骨文所承载的文化事项。文字一出现由上层的君王掌握,而记载文字,即文献的媒介,最初的版本形式甲骨文,是为少数的上层阶级所持用的经典。所以版本最早只对统治阶级有意义。之后先秦时期以竹简取代甲骨,新的版本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占卜性的指令到礼乐的规范,但版本的经典性没有改变。诗、书、礼、易、乐、春秋成为用竹简书写的经典文献,成为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依据,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但经典版本仍为统治阶级所有,成为其统治的工具。既然是经典,所以是不可复制的,也没有复制的必要,因为它是上层阶级用来统治大众的,必须保留在少数人手中。竹简使用的时间很长,直至秦汉、魏晋都在使用,虽然在竹简上写字费力,竹简笨重,不易保存,但在造纸术发明之后的很长时间,仍为统治队级所使用,可见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们不会去考虑便利性的问题,考虑的只是经典性,治人的作用。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由早期承接奴隶制度的人身强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意识的提升,人身依附不再像之前的程度,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自然会有文化生活的要求。于是隋唐之前到隋唐用纸质传抄的文献增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大众文化的需要。特别是唐代小说体裁的发展,唐传奇的广泛传播,是适应大众以文化产品自娱所求。宋之后坊刻的增多,大都刻制大众喜欢的小说等读物,去满足大众的文化生活需求。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刻本已不仅仅是服务大众,许多精美的刻本为学者治学所用,渐渐发展为对各种板刻的鉴赏与保存。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大众世俗文化的兴盛,一是学术的更快发展。而家族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其具有家族特征的家学的代代相承,是治学的最好途径。自然也承担起致力于版本学发展的责任。
元明两代皆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重刻板,特别是宋代的精美雕板。至清,在道光鸦片战争之前仍然是以刻板为主要的文献传播方式。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新的技术的进入,原有的刻板统一性也被打破,版本的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石印、影印、铅印、排印在这一时期同时被使用,且此起彼长,最后是排印技术引发了现代的版本学。
一、甲骨、竹简的形象性启示
甲骨文皆是形象性的文字,以画物体对象的轮廓来指示对象,这也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体现。由于人处在自然之中,即目所见的是直感的物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以形象性的认识为特征。所以在商周之初,神本观念的形成即是一种形象性思维。人们想象出一个虚假的神的形象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神是自然意志的体现,按神的意志行事,便是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可以顺利的生活下去。自然的形象性决定了人的思维的形象性,人最初都是通过直感的经验获取认识,然后付诸行动。之后周代的礼乐文化虽然以一定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了抽象性的特征,但以乐的形式来支持行为规范,同样是付诸形象性的。所以记载当时文化的文献也是形象性的文字组成的,而以甲骨这样的自然物来承载,不仅是因为这样的介质易于刻字,且可以长久保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自然性质的自然界本有物,以它来承载以形象性文字表达出来的人类文化结晶,文献,正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的依赖,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性的表达。也可以说甲骨文献的形象性象征着人类思维的形象性。
之后的竹简所记载的文献,由篆书、隶书写成,虽然和甲骨文相比,象形性减弱,是更成熟的定形文字,但它们仍是象形文字,用它们书写的文献仍是人们以形象性思维处理社会事物,从而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看法的媒介。但是作为成熟文字记载的文献,毕竟带上了抽象性。是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提升,对自然、社会认识的深入,开始由现象看本质,规律性的认识促使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但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这是自然形态决定的,不能改变的。不过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开始相配合,去指导社会生活,除了以前的秩序,开始有了分类,在文化上的体现,是日常生活与作为文化集中体现的知识分离,有了专门治学的阶层。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出现,自成体系,并相互争论与交流,使学术分成更细的学科。这个过程中,以竹简承载的文献功不可没,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依据的研究,演生了各派的思想体系。这些在后世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以抽象性为主,但仍是以具体可感的生活实践为基础,最终是为生活行为服务。所以到了这一阶段,文献形象性没有改变。再后来,秦汉直至魏晋,除了竹简外,又出现了帛书等文献形式,版本单一性的改变标志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学科分类的更加细致。但是版本的形式仍是自然物,帛书是以自然物质织成的布匹为媒介而成的,所以还是脱离不了自然的形象性。
隋唐之前,至唐,开始以纸张抄写文献,人工造纸术生产出来的专门文献媒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自然媒介形态,这也是学术繁盛,学科发展,各个学科独立性增强的表现。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文献的形象性被改变,学术仍然是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直至人与社会的关系服务,思想是为了具体可感的实践,所以文献还是形象的。版本的形式虽然以人工技術为基础,但文献的形象性决定了版本的形象性。
自宋有了刻板的版本,人工雕板需要颇高的技术,而以刻板为依据的纸墨复制,更是体现了人工的重要性。这说明此时学术的发展,已不再是为治学而治学,许多的学者已充当多种角色,他们直接为大众服务。如很多小说家、戏曲家直接为大众的文化娱乐写小说,写剧本。大众的需要是大量的,之前的文献抄写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提高文献的生产量,人工的复制是必要的,即是人们思想意识独立性的增强,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使之前分工愈细的治学与日常生活的分离,重又拉近了与日常的距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性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但这自然的形象性,为什么要以人工的加强来实现呢?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人工技术的提高,正说明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增强,虽然不能改变形象性关系,但可以改变人在此关系中的份量,即人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大,人可以更好的控制这形象性的关系。所以刻板的人工技术,特别是复制性,是版本形象性进步的表现。
之后元明,至清道光鸦片战争之前,仍是以刻板为主要的版本,对于人工的依赖,不是退步,而是进步,因为这说明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作用又增大了,可以以不断的复制改变人处理与自然、社会中事物的方式,以速度的提高,实现实践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刻板功不可没,虽然其仍具形象性。到了近代,复制技术进一步发展,已臻完备,石印、影印,特别是排印,大大提高了复制的速度,与灵活性。也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那不是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性已经变化了,版本不再具形象性。自然的形象性没有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性也不能改变。改变只是人驾御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的份量在增大。所以作为人类文化集中体现的文献之版本的以形象性本质为基础的形式的改变,正标志着人类的进步。
二、清至近代版本技术的家族版本学趋向
清至近代由刻板到印制的转变,将复制的方式不断完善,出版的质量提高,数量更是大大增加,满足着大众普遍的文化需求。学术与世俗文化界限的进一步模糊,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会影响到学术的独立性。虽然学术最终要为社会实践服务,为大众服务,但必须以其独立性为前提,因为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才能为更高质量的知识普及作好充分准备。而在普遍性已成为清,特别是清末、近代的主要倾向时,怎么解决普及知识与学术的矛盾呢?其实前代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宋代的家族版本学负起了学术研究的基础性责任。在清代至近代同样可以以家族版本学解决普及知识与学术的矛盾。特别是近代以大众知识普及作为发展国力的前提条件,更要解决好这个矛盾。以学术研究作为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储备。这时,家族版本学可以担起这个重任。家学以代代承续的方式保持家族特征,为治学提供了完好的环境。学术研究正需要这样的继承性,以保证独立性。而家族版本没有间断的持续正是这有力的保证。
从技术的进步来说,印制应该是家族版本形成的主要形式,因为这样可以以便捷性提高出版的数量,为学术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资源。但没有看到学术研究需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印制技术虽然速度快,灵活性大,但灵活性同时带来了错误。所以家族版本在使用新技术的同时,也会保留刻板。刻板的精细可以保证文献的质量,这无疑是治学所需要的。而家族版本的代代相承,也需要一个精良的版本。刻板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其印制不可比拟的准确度,时间赋予它的历史感,成为家学的象征的。吴兴许氏杏荫堂民国间(清)许浩基撰《文父山年谱》,刻本,清楚的说明了这一问题。总之,家族版本在保证治学的同时,为将学术转化为大众知识作了充分准备。因为家族版本学的基础性,与整个社会的联接,决定其可以把内部资源顺利的转化为外部的大众共享资源。
参考文献:
[1](清)许浩基撰,文父山年谱[M].吴兴许氏杏荫堂民国间刻本
[2](民国)萧一山,著.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民国)王金绂,著.近代中国地理志近代中国地理志·中国经济地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4](民国)郭湛波,著.民国丛书第一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5](民国)孙曜,编.民国丛书第三编.·春秋时代之世族[M].上海:上海書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