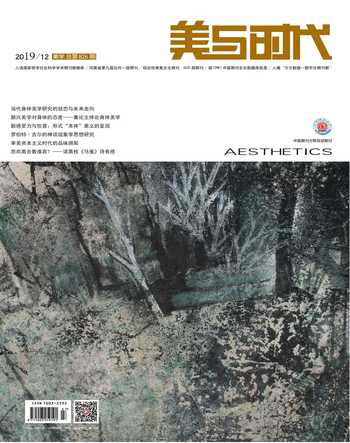新兴美学对身体的态度
摘 要:从意识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对身体的发现、忽视和重新发现的历史线索,认为“我”是身体,又不仅仅是身体。身体孕育了意识,而意识统摄、协调身体,高于身体。从这个角度讲,“身体是主体”这一命题,是值得商榷的。而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与身体必然有重要联系,但把精神或心灵作为身体的功能,进而确立身体的主体地位,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也是值得商榷的。而要考察身体的建构过程,必须从意识诞生之初开始,没有意识能力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
关键词:意识;身体;自我;主体;身体美学;新兴美学
近年来,身体美学声名鹊起,对身体的关注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不可绕过的主题。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与身体必然有重要联系,但把精神或心灵作为身体的功能,进而确立身体的主体地位,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或许还是值得商榷的。
在建构身体美学的论述中,王晓华教授把以往的全部美学称之为精神美学,意思是以精神为主体的美学。其实这个论断是不公允的。通常人们在讲“主体”概念的时候,是指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并非仅指精神。所有人都知道:人是动物,是生物性存在,身体是精神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精神或心灵就无从说起。当然,我们在讲“人”的时候,的确偏重于“人”的本质,即精神性。这种对身体的忽视的确有其深刻的原因,是一种历史必然的结果,了解这一点对恰当地评估身体的作用及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要考察身体的建构过程,我们必须从意识诞生之初开始,没有意识能力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
一、第一次发现身体:自身(me)
作为动物的猿人,他们知道自己身体的存在吗?他们会保护、美化、医治自己的身体吗?黑猩猩面对危险会选择逃避,这是保护它的身体吗?笔者认为不是。保护生命和保护身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前者可以是一种本能,而后者需要单独关注身体的能力,这种能力,黑猩猩是没有的,猿人也没有。美化和医治身体更是一种高级的能力,不仅依赖人对身体的觉醒和关注,也依赖相应的文化背景和技术中介。
即便意识活动已经萌芽,猿人也不会立即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相反,他们首先感觉到(无意识地)的是自己身体中那个似乎控住着自己的“小人”——精灵,再以“推己及人/物”的功夫想定身外的所有实体都有精灵①,这就是泰勒所谓的“万物有灵”时期。这个时期,原始人目光向外,只知道关注精灵之外的一切,笔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他意识阶段[1]78-85。在这一阶段,“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认识自己,而是全身心的感知对象界”[1]85。
身体也是他们感知的对象之一,对身体的觉醒源于对死亡的感知。而对死亡的感知又是基于对睡眠的经验,至今我们还把死亡称之为“长眠”。原始人有了靈魂的观念以后,可以很好地理解睡眠:当灵魂出窍,短暂离开身体,身体就丧失了感知和行动的能力,它睡着了。一开始,原始人还没有办法区分睡眠与死亡,他们把死亡当成了睡眠(长眠)。后来发现,身体(尸体)开始腐烂、发臭(原始人并不理解“腐烂发臭”的意义,只是觉得不方便),为了方便灵魂回来找到自己的身体,就必须想办法保存、保护身体(尸体),这也就是古埃及“木乃伊”产生的原因。至此,人类从保存、保护尸体开始,发展出复杂的葬礼、葬俗、葬制,最终意识到身体的死亡,并慢慢关注到自己的身体。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身体”,它是灵魂的居所。至此以后,身体意识在人类心灵中扎下了根,并且产生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机体逻辑,即原始人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为标准的意识活动的逻辑。这种逻辑是身体行动的内化,是形式逻辑的基础。身体意识的诞生使原始人能够真正区分开“我”与“你”。这时的“我”还是一个“身体化”的“我”,一个能动的身体,即焦点在身体而不是在灵魂的“我”,身体的感觉被凸显出来,用王晓华教授的话说:我就是身体,这相当于英语中的“me”;而这时的“你”,则是身体之外的一切事物,它们被当成是为“me”存在、为“me”服务的有感知活动的实体。
对身体的觉醒,自然产生了对身体的保护、美化和医治的动机。这样,客体论的身体美学就产生了。原始人在身体上涂抹各种艳丽的色彩、挂上各种猎物的蹄角或插上各种鸟类的羽毛,或许有不少实际的功用,但这样做的确有美化身体的效果。到后来,人们挂上各种玉石、玛瑙等等加工的珠子,其美化身体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但总的来说,原始人的身体美学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吸引异性或恐吓敌人。
二、对身体的忽视:自我(I)
在他意识阶段,原始人对灵魂的感知是无意识的。只有进入到自意识阶段[1]86-96,人们才意识到自己有意识活动,即人有了对意识活动的意识能力。这就让人发现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精神世界。这个发现就是对“自我”的发现,这个“我”相当于英语中的主格“I”,它意味着主宰内在世界的“我”。这个“我(I)”不仅操控着外在世界(就像“me”一样),它还操控着内在世界,它通过注意、记忆、想象等心理能力有目的地调配、组合、编辑内在世界的各种元素:表象、意念和语言。人们发现,在身体的某处存在一个“思考的器官”,孟子认为这个器官是“心”,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器官是大脑。正是这个“思考的器官”控制着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认识、把握这个会思考的器官,进而认识、把握精神世界就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了。对身体的忽视就成为必然,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自意识阶段”。
柏拉图讲得很清楚,他把精神世界称之为理念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现象界(包括身体)不过是理念的“流射”,是理念的影子,是不真实的。我们要努力达到理念世界,就必须摆脱现象界的束缚。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囚室,是追求真理的障碍。因此,“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2]。苏格拉底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冷静地喝下毒药,放弃身体,只为了灵魂的纯净。亚里士多德关于“本质”的理论,也支持了对灵魂的关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象是不重要的,本质才重要。而灵魂正是人的本质。他在谈到“善”的时候,认为有三种善: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在这三种善的事物中,我们说,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3]总的来说,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社会就在努力摆脱身体的影响。虽然其间有几次小小的反复,仍不足以为身体正名,更谈不上拨乱反正。到17、18世纪,身体更是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说在笛卡尔之前,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能见到身体的依稀影子,那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二元论哲学就把这点依稀的影子也消灭殆尽了。身体完全是不必要的东西,思维(理性)借助数学通过逻辑推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之后的理性主义哲学就一直成为西方伟大的哲学传统延续下来,鲍姆嘉通的“美学”与身体无关,仅仅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理性认识。康德也讨论了感性认识,仍然没有讨论身体;黑格尔从没将目光停住在身体之上,倒是花费毕生的精力建构起庞大的精神哲学体系。
对身体的厌恶有几个原因:(一)认为身体是欲望的化身,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于是产生了对身体的规训,产生了禁欲主义。(二)认为身体是情绪的载体,主观情绪和自身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会严重影响对事物的客观认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导致谬误、造成失败。这一点,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三)身体的病痛让人受不了。身体的病痛促成生理学、医学的发展,但仍然无法解除身体的病痛。如果没有身体,就不会有身体的病痛。老子早就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四)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完全遮蔽了身体的地位。近代以来,理性主义获得的重大成就是那么光彩夺目,人们根本无暇顾及身体,甚至更进一步,对与身体血肉相连的感性也故意拒之于千里之外。
自古希腊以来到20世纪初,身体遭到故意的忽视,客体论身体美学也遭到故意的忽视。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身体是情欲的化身,是罪的根源,不再美化身體。修道院里的修女和修士身穿宽大的黑色长袍,看不出身体的轮廓;一般民众也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关注的是理性的美、心灵的美,也可以说是身体之外的美。从关注的主体看,这一时期同样是精神美学,即审美活动的主体是精神或意识活动。当然,自从意识诞生之后,它就以各种形式(精灵、灵魂、心灵)成为主体,身体从来没有成为主体过。
三、对身体的重新发现
文艺复兴重新肯定身体,其实是出于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反叛,算不上具有身体意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感性生活的追求虽然与身体具有一定的联系,这与基督教的衰落、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关,但身体意识仍然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身体的重新发现是20世纪以后的事。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极端理性主义②(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负”)造成严重灾难,对身体的保护再次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个是对意识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与身体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不借助身体就无法理解意识问题。
哲学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关注身体了,只是还没有成为主流。叔本华认为:“对任何能动的生命体来说,从意志出发就是从身体出发。”[4]意志和身体是同一的。而尼采则是直接肯定了身体,“我完全是身体,此外什么也不是;灵魂只是身体上某一部分的名称”[5]。进入20世纪,哲学家们的身体意识更加强烈了,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福柯把身体摆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他认为身体是可变的,知识这种权力把身体作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从身体出发,建构了一种身体哲学(身体现象学)。他把身体和身体的行动理解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我们移动的不是我们的客观身体,而是我们的现象身体,这不是秘密,因为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作为世界某区域的能力,在走向需要触摸的物体和感知的物体”[6]145。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灵魂的作用,但是这种消解是不彻底的,“因此,在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之前,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应该是意识本身的一种可能性,问题在于了解有感觉能力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有感觉能力的主体能感知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身体的话”[6]134。“有感觉能力的主体”能够感知“身体”,这表明二者不是一回事。
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还没能很好地理解和承认别人的存在时,他们会借助理性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种冲动最终会把理性推向极端理性主义,而极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相通。以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历史必然有一种最好的存在(理想社会),以为事情必然有一个最好的结局,这些想法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存在,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办法追求罢了。从莫尔的乌托邦开始,理性主义以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想主义面貌出现,经过圣西门、孔德、马克思,理想主义越来越精致③。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管理艺术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有条件追求“理想”的结果了,极端理性主义的社会土壤已经形成,于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两次战争直接伤亡人数近亿人;各种乌托邦也出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了雅利安人的利益,不惜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身体)。他们以极端理性主义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其手段十分残忍。这种恐怖的结果促使人们再次思考如何保护身体(生命),身体意识已经觉醒。
这种身体意识也表现在形形色色的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中。毕加索把身体撕裂再重新加以组合(《格尔尼卡》),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利则使用夸张变形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身体(《内战的预兆》),更是具有一种视觉爆炸力。总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具有了高度自觉的身体意识。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是高举身体主义的大旗,开始追求身体的感受性和刺激性,甚至有些过分地放纵身体。女权主义者提倡的女性化写作,被人蔑称为“下半身写作”,显然是一种身体写作,它也是基于身体的感受性和刺激性而兴起的。这种解放身体、解除对身体的一切束缚的要求开始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
近几十年来,科学一直没有放弃对意识的研究,尽管不少人断言科学无法研究意识,因为存在解释鸿沟(作为物质的大脑是如何产生主观体验的?)。随着分子生物学和脑神经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意识与身体是分不开的。像丹尼尔·丹尼特那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消解了传统的“意识”概念,他把意识还原为意向系统的意向性行为。
总之,自尼采以来,人们重新发现了身体,并给予身体很高的地位。这既是对极端理性主义的回应,也是意识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身体仍然是客体,即使像丹尼尔·丹尼特那样的唯物主义心物哲学家,也没有把身体看成主体。西方的身体美学依然是客体论身体美学。把身体看成主体,进而建构主体论身体美学,这种努力取决于身体能否成为主体。
四、身体能否成为主体
主体论身体美学能否成立,取决于身体能否成为主体。而身体能否成为主体,关键又要看如何理解“主体”这个概念。传统上一般把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称为主体,与之相对,人所把握与认识的对象称之为客体。主体与客体是成对出现的概念,这意味着:言说主体,就必有客体在场,不管你说没说到它,反之亦然。显然,“人”作为主体,他不等于身体,还应该多一点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识(灵魂/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意识使“身体”成为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但是王晓华教授认为:“从有意识地建构世界的一刹那,身体的主体性就诞生了。主体性就是身体有意识地组建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正因为有了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身体才能让世界人化,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如工业)成为‘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才能对事物做出美或丑的判断。”[7]由此看来,身体的主体性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有意识地;(二)建构世界。这在笔者看来,它就是一种意识或精神活动。王教授又说:“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基本思路:人就是身体,身体是生活和审美的主体;精神不过是身体主体的功能和活动。”[8]在这里,身体已经成为主体了,它并不是依赖于“精神”而成主体的,精神不过是“身体主体”的功能和活动。很明显,王晓华所说的“主体”与我们所说的“主体”不是一回事。对他而言,身体是自动者(能动)、是自立者(站立)、是实在者(实体)、是实践者(活动),这就是他所说的主体的具体含义。他没说身体是感受器,是感觉、情绪、意识和思维的载体,他把精神消解了,把精神还原为身体主体的“功能和活动”。
这种消解精神(灵魂)的努力不是孤立的,是与重新发现身体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彼得·沃森认为灵魂是人类思想史中三大思想之一,它甚至比神的概念还重要[9]9。“简单而言,灵魂理念比神的理念更经久不衰;甚至可以说,灵魂理念的演化超越了神、超越了宗教,因为连没有信仰的人,或者说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都会关注内心世界。”[9]1055但是,灵魂的概念终将“终结”。对上帝的探究促进了理性的发展,而理性反过来瓦解了上帝的观念,促进了科学的进步。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对上帝信仰的动摇,发展到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这表明人们对灵魂的态度,越来越淡漠;理性主义不仅推动了医学、神经科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还促进了对基督教所谓“灵魂”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灵魂”概念的虚妄;世俗化的大都市生活也让人们不再关心灵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消解了灵魂的意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心态”等等社会的、思想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灵魂的观念[9]1000。
瓦解灵魂的观念是重新发现身体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不把灵魂的观念瓦解掉,身体意识就树立不起来。但是,笔者认为“身体意识”与“身体是主体”的意识是不同的两种观念。前者意味着“身体”成为现代意识的核心概念、重要维度;而后者意味着“身体”是某种形式的最高存在,在身体之外,并不存在操控身体的主体(精神)。
丹尼尔·丹尼特的意识发生理论是消解灵魂或意识比较成功的理论,他在《心灵种种》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称之为“生存检验之塔”:意向系统按其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达尔文式造物、斯金纳式造物,波普尔式造物和格利戈耳式造物。以此解释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发现:意识不过是意向系统综合效应的高级形态罢了。也就是说,在意向系统之外或之内,并没有特殊的意识活动:意识就是意向系统的意向性行为。
达尔文式造物,它处在这个塔的最底层,它是最原始的。它适应环境的方式非常有限,完全遵循达尔文的自然进化的规律,通过基因重组和突变,盲目的产生各种候选的生物。当大自然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调整自己内在的结构以适应新的环境。
丹尼尔·丹尼特把达尔文式造物的一个子集,称之为斯金纳式造物。斯金纳式造物会(通过条件反射)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新的环境,但它的调整还处于盲目状态,绝大多数调整行为都会失败,只有极少数成功了。
如果斯金纳式造物能够幸运地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想办法避免自己可能造成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对所有可能的设计进行一次筛选,把那些有可能造成错误和危险的选项删除掉。这意味着能动体具有了在内环境中进行选择和学习的能力,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丹尼尔·丹尼特把这种能动体称之为波普尔式造物。因为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让我们的假说可以替我们去死”,意思就是说能动体足够聪明,可以选择不同的可能性去接受环境检验而不必亲自去冒险。
波普尔式造物是斯金纳式造物的一个子集。我们人类当然是波普尔式造物,还有其他的生物也是。要把人类与其他生物分开,还得有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格利戈里式造物。理查德·格利戈里是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关于信息在产生妙招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格利戈里式造物是波普尔式造物的一个子集,它有两个世界:一个内在的世界和一个外在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标志着格利戈里式造物心灵的诞生。他多了一种特殊的工具:语言。丹尼尔·丹尼特这样说:“与这些造物相比,格利戈里式造物通过利用他者所发明、改进与传播的心灵工具里体现的智慧而受益于他者的经验,从而向着人类水平的心灵机巧迈进一大步。由此,它们学会了如何更好的思考它们下一步应该思考些什么,等等,从而产生出没有固定清晰极限的、深入的内部反思之塔。”[10]
从达尔文式造物到格利戈里式造物的发展过程,丹尼尔·丹尼特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心灵不过是越来越高级的意向系统的特殊(意向性)行为。这个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它取消了“解释鸿沟”这样的“难问题”[11];以第三者(观察者)的角度,取消了“主观体验”的问题;也取消了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不赞成他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對笔者来说,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对“反思”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丹尼尔·丹尼特把“反思”理解为意向系统对内环境或内在世界的自动操作,就像它们对外环境或外在世界的自动操作一样。我认为“反思”是对意识活动的意识,即我能够意识到我的意识活动,并进而对这种意识活动进行操作。心灵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依赖于我们对内在世界的控制和操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意识产生很久以后的事。打猎的原始人他可能会去踩点,可能会做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可能要让自己知道在什么地方才能获得猎物,但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在心里面已经对自己的计划有一个全面的详尽的安排和设计,更不能认为他有对这种内在设计进行详细审查的能力。事实上,在这里笔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原始人有没有内在设计的能力?
(二)原始人有没有对这种内在设计的能力进行审查的能力?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意识行为,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反思行为,是对第一个意识行为的意识。这两个问题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基础;后一个问题则是一个更高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在大脑里进行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也不会立即产生对这种意识活动进行审查的能力。这种对操控内在世界的能力进行审查的能力,那是若干年以后在自意识阶段才会出现的。正是因为人具备了对意识活动的意识能力,他才第一次真正区分开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不会再把头脑中的想象(包括做梦、幻觉)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自此以后,人类才真正有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具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
丹尼尔·丹尼特采取旁观者的立场从外部观察意向系统的意向性行为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有问题的。这虽然很容易取消“主观体验”的问题,却不能取消“主观体验”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主观体验,我感觉到痛苦、愉悦或者忧愁,这些情绪、感受、观念和思想从旁观者的角度是观察不到的,它需要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描述。再说,旁观者即第三人称的意向性行为不正(也)是需要解释的意向性行为吗?凭什么用旁观者的意向性行为来解释别人的意向性行为?
总之,丹尼尔·丹尼特意向性理论是有问题的。在笔者看来,人的心灵有一个嵌套结构。它的最底层是一个意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发展阶段。他的第二层就是对第一层意识的意识,我们通常称之为自我意识,它起着对第一层意识的审查与监督的作用。那么在第二层之上,还会不会有第三层意识,起着对第二层意识的意识进行监督和审查的作用呢?这是会有的。那些智慧超群的所谓天才、超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意识的意识也会有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会监督和审查自我意识,以便防止自我意识在监督和审查第一层意识的时候犯错。那么会不会在第三层再嵌套第四层,甚至在第四层还嵌套第五层以至于无穷呢?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正像丹尼尔·丹尼特所说的那样,当数据量大得惊人、肉体和大脑无法承受的时候,变革就会出现,一种划时代的新方式,就会产生。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方式,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我们看到,即使在唯物主义心物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那里,意识被意向系统(身体)的意向性取代,身体也还不是主体。我们认为,身体是意识的物质基础,意识一经产生,它就发现身体,统摄身体,超越身体。
我们不惮其烦地讨论丹尼尔·丹尼特的意识理论,其目的就在于证明:很难把意识还原为一种(意向系统的)行为或现象。
其实,王晓华教授的论证逻辑与丹尼尔·丹尼特的论证方式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强调“身体是能动体”,暗含着把意向性、意识或精神化解为“能动性”的意思:体现为一系列神经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按照某种意愿(意向性)驱使身体进行复杂的实践活动。但这是不对的。意识活动或精神活动(意向性)只是身体(能动体)在某一特殊阶段出现的现象(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所有的身体(能动体)或身体(能动体)的所有阶段都有意识活动或精神活动。狮子、黑猩猩、机器人和人的身体都是能动体,但我们很难承认狮子、黑猩猩和机器人是主体;同样,婴幼儿、丧失意识的植物人或某些精神病患者,我们也很难承认他们是主体。如此,即便“能动性”是“主体性”的表征,我们也无法认同“身体是主体”的观念。
五、新美学的身体意识
(一)新美学就是体验美学。我们所说的新美学是相对于此前一切传统美学而言的。它之所以“新”,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融合论基础之上的体验美学。在我看来,世界的本源是融合,即一个没有主体、客体,没有矛盾的世界。笔者在1997年《论美是矛盾的解决》一文中,对融合论作了初步的论证。“融合,就是超越主客体的规定性。”[12]在该文中,不仅提出了两种达至融合的途径,还进一步提出了“美是主客体规定性的超越,也就是主客体的融合”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体验美学》一书中,笔者从意识的发生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在无意识和他意识阶段是主客体不分的融合阶段,只是到了自意识阶段,人有了对意识活动的意识能力,才把自己从环境中区分出来,才有了主体与客体,有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世界[1]74-116。在意识诞生之初,世界是一个融合的世界,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环境不过是人身体的“外骨骼”,是人的身体的延伸、扩展,人与环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只能在环境之中通过自己的身体体验环境。这种体验并没有因为主客体的分离而消失,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一直延续了下来。体验,成为我们把握这个主客体融合的有机整体的唯一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融合论成为体验美学的本体论依据。
体验美学摒弃了传统美学的话语体系。没有主体、客体的概念,甚至也没有快感、美感之类的概念。体验美学的话语体系由这样一些核心词语组成:意识、融合、体验、感受、表达,等等。我们从意识发生学的角度确立体验美学的合法性,最初的意识状态是主客体不分的融合状态,并且这种融合状态即使在主客体分离之后仍将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延续下来,它需要一种全新的关注,这就是体验美学,一种全新的美学。有体验就有感受;有感受就要表达;物化的表达就是艺术作品。
(二)體验的身体性体验离不开身体。原因不在于身体是能动者或实践者,而在于身体是感受器。神经纤维遍布于身体各处,它们能够搜集到足够多的内外刺激信息,将其传送到大脑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感觉、知觉,产生相应的情绪或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出现了。从心理机制角度讲,体验是对刺激信号通过特定的通路(体液通路、神经通路)在特定的大脑区域表征出来这一过程的感知。这种感知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有意识的。审美体验一般是有意识的。显然,体验具有身体性。“身体性是体验最本质的特点,意思是不仅体验的过程离不开身体,体验的结果离不开身体,体验的表达同样离不开身体。”[13]从这个意义上说,体验美学与身体美学有相通的地方。
体验既有身体性,反过来,身体自然有体验性。强调身体的体验性,这或许能给身体美学一个全新的维度,打开一片新的疆域,从而避免“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促使身体美学从舒斯特曼的层次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我是身体,但我不仅仅是身体。我是身体,这个“我”或“身体”其实只是“me”,并不是“I”。也就是说,在他意识阶段,“我”就是自身,“我”以自身为中心,一切为了这个自身,发展为自身中心主义的意识水平。比如,以自身为中心的方位名词(前、后;左、右;上、下)构成庄子所谓的“六合”;以事物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进化为以自身为原点的绝对位置关系;以自身的身体构造类推万物的内部结构;以自身的身体需求为唯一的至高的需求,身体以外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等等。只有在这种意识水平上,身体才能通过移动、触摸、抓握、加工外部物体达到改变外部世界的目的,当然这种目的是为我的。这种意识水平一旦固化传承下来,就是武志红在《巨婴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巨婴”就是没有多少智力活动的巨大的身体,它以自身为中心,为目的,它不知道别人的存在,别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一旦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它就会情绪爆发,毁灭别人也不惜毁灭自己。显然,建立在“巨婴”身体之上的主体论身体美学是毫无意义的。
当意识发展进入自意识阶段,意识意识到了意识活动的存在,自身(me)变成了自我(I)。也就是说,意识不仅意识到了自身(me)的存在,它还意识到了意识活动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意识才能明白自身(me)的需求——表现为意识活动——并判断其现实性和合理性。自我的诞生,不仅使原始人具有了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还使原始人具有了区分这两个世界的能力,知道哪些事情是自己的想象,哪些事情是现实世界真实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原始人在“以自身(me)为中心”的意识水平上进化为“以自我(I)为中心”的意识水平。自我(I)不仅知道自身(me)的需求,他还知道影响满足自身需求的条件。因此,自我是以问题为焦点的、以找到问题为前提、以解决问题为手段,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一句话,自我超越了物质性的身体,具有了一个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精神世界,具有了对这个精神世界中的意向、表象、想象、语言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我是身体,但又不仅仅是身体,我还有意识活动与意识能力。身体(me)操弄外部世界;而自我(I)操弄内部世界,并且自我(I)还担负着协调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行动的责任。
(四)意识活动诞生于身体,又高于身体不是所有的身体都有意识活动。低等动物对刺激有全身性反应,这种反应不是意识活动;高等动物有初级意识活动,但绝大多数意识科学家也承认高等动物的初级意识活动不同于人的意识活动。另一方面,也不是身体的所有阶段都有相同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弱的过程。就猿人而言,他们有情绪活动,并在情绪活动基础上,因为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增强,产生了初级意识;随着注意力和记忆力进一步增强,人不仅可以注意和记忆外在现象(包括看不见的现象),还可以注意并记忆内在世界的精神现象,意识水平就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自意识阶段。到了20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意识水平又上升了一个层次,达到超意识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主体与客体融合在一起了,一个超越了矛盾双方各自规定性的融合世界出现了。身体与意识融合在一起了,身体是有意识活动的身体;意识活动是有身体的意识活动。但在潜意识深处,意识仍然统摄着身体。身体是孕育意识的物质基础,但意识已经产生,它就必然要统摄、协调身体。因此,对我来说,我始终无法理解身体如何成为主体。
相反,我有一些担心。把身体当成主体,会不会产生一种专制性的身体美学?既然身体是主体,既然身体有很强的感受性,那就可以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达到控制主体的目的。为了美化、合法化这种目的,人们可以创造一种“身体美学”。我希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但某种形式的“身体美学”仍有可能提供“规训与惩罚”身体的合法性。
注释:
①迈克尔·托马塞洛在《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一书中采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据,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儿童“把他人理解成为有意向(心智)的行动者(就像自己一样)”(第14页)是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其实,这论点还可以扩大范围:儿童在自然条件下容易把身外之物均理解为像自己一样具有意向(心智)的行动者。其结果就是万物有灵。
②考虑到理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和严重后果,我宁愿把盛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唯科学主义称之为极端理性主义。
③参见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二部分。
参考文献:
[1]谭扬芳,向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体验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22.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2.
[5]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
[6]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5.
[7]王晓华.身体主体性的起源与审美发生论:主体论身体美学论纲之一[J].河北学刊,2009(3):59-63.
[8]王晓华.走向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5-12.
[9]沃森.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M].胡翠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10]丹尼特.心灵种种:对意识的探索[M].罗军,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91-92.
[11]布莱克摩尔.对话意识:学界翘楚对脑、自由意志以及人性的思考[M].李恒威,徐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1.
[12]向杰.论美是矛盾的解决[J].社会科学,1997(10):35-38.
[13]向杰.审美体验:美的实现——兼论审美体验在生命美学中的意义[J].美与时代(下),2018(7):5-11.
作者简介:向杰,中共四川省宣汉县委政法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