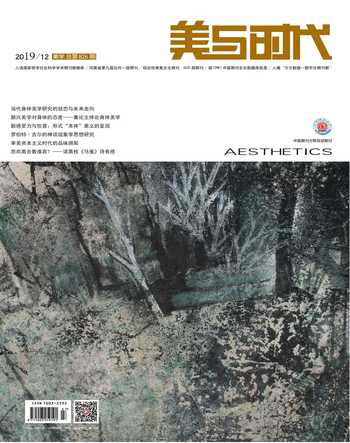新感受力与坎普:形式“本体”意义的呈现
方莹 董天倩
摘 要: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形式“本体”意义指向先验的客体,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形式“本体”意义则转向了经验的主体。同时,西方古典哲学中形式所蕴含的事物发展与变化的动态之义使得形式的意义具有了从先验的客体转向经验的主体的可能。“新感受力”和“坎普”是蘇珊·桑塔格形式美学中重要的范畴,它们呈现了西方现代哲学中指向经验主体的形式“本体”意义。“新感受力”因强调个人感性经验的本位而可被视为形式本体之发轫,“坎普”则可视为对形式本体意义美学实践的观念表达。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形式;本体;新感受力;坎普
美国时间2019年5月6日,一场以“坎普:时尚扎记”(Camp:Notes on Fashion)为主题的展览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将17世纪至今来自古琦(Cucci)、莫斯奇诺(Moschino)等时装周品牌设计的250余件服饰作为展品,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对非自然事物、技巧和夸张事物热衷的一种审美态度”,这就是桑塔格在其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中提到的“坎普”风格。“坎普”以及与“坎普”关系极为密切的“新感受力”作为桑塔格形式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因强调了主体经验,特别是个体审美体验对理性的超越,而展现了桑塔格形式美学中“形式”的本体①意义。
如今,这两个以“内容”超越“风格”、“审美”超越“道德”的范畴在当今各种展示个体经验的审美文化和艺术实践中,不断地被借用以作为它们的理论资源。这恰也符合在现代语境中,形式已由先验的形式转变为经验的形式、人们对经验形式“本体”内涵的讨论即是对个体感性经验的讨论的这一观点。正如该展的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所说:“多年之后重读札记,让我觉得桑塔格讨论的‘坎普’和当下有着更强烈的相关性:不仅是在时尚领域,更是在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
一、作为“本体”的形式概念溯源
为了搞清楚“新感受力”和“坎普”中蕴含的的形式“本体”内涵,我们有必要对形式的“本体”内涵进行溯源。
(一)语言学中形式(Form)的“本体”内涵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中对“形式”(Form)的释义,“Form”既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作为动词时,“Form”是“本体”意义的形式。
“Form”作为动词则有以下几种意义:1.开始存在(start to exist);2.(使)形成(to start to exist and develop;to make sth start to exist and develop);3.使成形(make shape/form);4.使排列成,排成(to move or arrange objects or people so that they are in a group with a particular shape;to become arranged in a group like this);5功能,作用(have function/role);6.影响(have influence on)。
形式的“本体”意义指事物及意义存在的根源,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形式”作为“根源”时,它既是数、秩序、理式等先验形式,也是寓于现代艺术中的经验形式。“形式”作为“动力”时,表现在“形式”是事物是其所是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直接指明了这点。
(二)“先验的客体”——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形式”本体内涵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理形式的论断第一次提出:形式即根源。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们通过朴素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和猜想,认定“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数字所代表的比例和安排使其成为万物之根源。数的形式在这里是先验的,代表一种神秘的秩序。
柏拉图的“理式”是先验形式的典型代表,并具有本体的内涵。柏拉图用两个概念eidos和idea来指称他认为最真实的存在物,即本体。Eidos、idea都来自于古希腊语中的动词Eido,它是“看”的意思。这两个词是同义词,但是派生的方式不同。柏拉图选用这两个概念是基于从肉眼的“看”(eido)类推到灵魂之眼的“看”(也是“知”),从肉眼所见的外在的形状(eidos或idea)类推到用理性才能把握的事物的内在形式。Eidos英文译作form,也就是形式的这个单词。Idea才是我们常常说的理念。在英文中,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既被叫做Theory of Form,也被叫做Theory of idea.两个概念互换没什么差别。可见,如果从英文原文来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柏拉图哲学既可叫做形式论,也是理念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直接指明了形式的动态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其生成和发展都由“四因”而来:“形式因”规定事物是什么,是事物是其所是的依据。“目的因”则是指事物“追求什么”,是事物目的之达成,而目的之达成也就是本质的实现,即形式被确定。“动力因”是事物的本质和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动力,因此与形式属于同一类原因。“形式”“目的”“动力”均是关于事物之本质的实现,也即是“形式因”。唯有“质料”表示事物生成的潜能,用来解释事物“从何而来”的原因。为此,亚里士多德将“四因”归结为“两因”——“形式因”和“质料因”。由此可见,“形式”具有使本质实现的含义,它自身也具有实现本质的动力。因而,形式具有动态的内涵。
总之,“形式”不仅是事物生成的根源,还内含发展和变化之动态意义。“形式”呈现了“be”和“becoming”的关系,具有指向先验客体的“本体”的内涵。
正是因为“形式”既可以表示根源,又内含变化和发展的动力,因而使得其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外在形象。贺拉斯的“合式”、荣格的“原型”、胡塞尔的“意向”、维特根斯坦的“图式”、海德格尔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无不见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形式的影子。这就是“形式”的魔力所在。尽管它在古典时代主要朝向先验的客观精神,却能从侧面深刻地揭示人类认识世界的内在规律。正如赵宪章所说:“柏拉图的‘理式’作为范型和Form,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不仅仅是注意到世界万物的自然形式,而且深刻地揭示出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的‘内形式’——整个宇宙生成演进的内在精神范型。这当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注意力从‘自然’转向‘自我’之后取得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成果。”[1]72由此,“形式”具有了从先验的客观转向经验的主观的可能。
(三)“经验的主体”——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形式”本体内涵
以形式为代表的“本体”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主要指向一个外在于人的先验客体,但在现代哲学中,“本体”则转向了人自身,指向经验的主体。
现代以來,哲学家们开始对近代的理性主义进行反思,认为只有通过恢复认知主体的本真,也是作为人的本真的存在才可以解决由理性主义带来的困境。现代哲学中,“本体”指向了“存在者”,这既颠覆了古典将“本体”视为先验客体对象的传统,还试图解决近代哲学将主客体严格对立所带来的困境。这一转向在哲学史上表现为诸多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发起挑战。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认为,以往哲学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因此,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事物本身的研究,转向非理性的直觉,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们的观点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即“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更为直接地指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从“存在者”身上返回到“存在”。古典的世界秩序以先验的“存在”为中心,面对它,人始终是被决定的和被动的,人并不能认识自我、认识自己,只有通过从属于上帝、理念或者规律才能认识和把握自己。存在支配个体、规律支配个别使得古典世界得以和谐稳定的运行。当西方由古典进入近代再到现代,理念、上帝等终极“存在”的权威开始瓦解,人在面对“存在”时不再是从属和被支配的角色,开始以一种“存在者”的姿态出现。所谓“存在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2]11。“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不妨说,就是要从存在者身上来逼问出它的存在来。”[2]8形而上的“存在”不再是唯一的和确定的,相反,“存在”总依赖着“存在者”而存在,即主体的、特殊的经验代替了理念、上帝和客观规律成为“本体”。
这种视主体的本真为“本体”的哲学世界观意味着认识世界的路径从“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从理性走向了感性,从客体走向了主体,从客观走向了主观。感性的美学和艺术因而具有阐释世界的可能,加之“就美学和艺术学的一般涵义来说,‘感性’总是同‘形式’联系在一起”[1]257,所以,阐释艺术中感性的形式即是阐释世界。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将这种寓于艺术中的感性形式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在他看来,“‘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3]。张法认为,“意味是绝对理念的替身。由于意味是不可言传的韵外之致,所以‘形式’是用来讲清意味的工具。因此,塞尚、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都认为自己所画的形式就是世界的内在形式”[4]。至此可知,形式的“本体”内涵由古典的先验形式转向了现代的经验形式。
在现代语境中,形式的“本体”内涵是经验的,它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主体只能以直观和感性的方式把握它。主体的感性与作品(客体)中经验形式的感性相遇共同完成审美活动。正如阿恩海姆所说:“人们面对着的世界和情境是有着自身的特征的,而且只有以正确的方式去感知,才能够把握这些特征,观看世界的活动被证明是外部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观看主体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5]这也即是说,作品(客体)是一种经由主体知觉活动重新建构过的客体,作品中的形式也是由主体知觉建构的形式。由此可知,主体知觉与客体的属性间具有“同型”或“同构”关系,因而人的感性经验秩序可以作用于作品形式秩序,对作为经验形式“本体”内涵的把握可以从人之感性经验的维度进入。
综上所述,就形式的“本体”内涵而言,在古典时代,它是先验的形式,代表客观精神实体。在现代语境中,它转变为经验的形式。由于人的知觉与对象的属性间具有“同型”或“同构”关系,所以对经验形式的“本体”内涵讨论可以由对主体感性经验的讨论开始。此外,形式所带有的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的内涵使形式“本体”含义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成为可能。“形式”概念在历史的流变中所呈现的丰富意义也是形式动态内涵的表现。
在苏珊·桑塔格“新感受力”和“坎普”两个美学范畴可发现形式的“本体”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她对于存在主体的重视。
二、新感受力——形式本体意义的发轫
20世纪60年代,桑塔格接连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1963)、《反对阐释》(1964)、《论风格》(1965)、《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1965)四篇份量十足的评论文章为电影、摄影、现代绘画等代表大众文化的艺术类型赋予了新的审美价值。“新感受力”是桑塔格最爱使用的术语之一,同时也是桑塔格形式美学观首要的关注对象。桑塔格的新感受力中的“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新感受力”所指的人之感性经验,桑塔格将之视作认识和判断现代艺术及文化现象的标准。1965年,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One Culture and New Sensibility)一文中提出“新感受力”(New Sensibility)这个概念。但对感受力的崇拜并非桑塔格首创。在18世纪的英国思想界,感受力已经成为美学和诗歌的热论中心,英国人将之称为“感受力的激情的意识”,以此来解决理性不能解决之道德和价值的问题。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在《人的特征、风气、见解和时代》中提到了感性经验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仍将美的事物的本质归结为于真理、比例、秩序和对称,并认为美存在于物体的形式和那赋予形式的力量之中。因而,这里的“形式”所代表的还是古典的先验形式,经验的感受力仍在先验的理性之下。可见,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夏夫兹博里与现代知识分子桑塔格在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夏夫兹博里所说的带有古典精神特质的感受力并不等同于桑塔格的新感受力。对感受力有着另一番见解的20世纪诗人——T. S.艾略特对感受力的阐释与桑塔格有着更多相似的地方。
20世纪初,T. S.艾略特在其文章中针对诗歌提出了“感受力的断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艾略特认为,十七世纪诗人身上的感受力能够从感性的感受出发立即感受到思想,他形容就像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芳香一樣。但是往后的诗人的意识中,感受与思想两个部分出现断裂,诗人们要么一味地依靠感觉,要么一味地思维。艾略特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感受力的断裂”。“感受力的断裂”使得诗歌变得空洞和乏味,因此,他认为诗人应该竭力恢复“感受力的统一”,使诗歌恢复到之前理性与情感、思想和形象完美统一的境界。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对此种观点进行了回应:“尽管T. S.艾略特在一篇著名论文中谈到十七世纪就已出现某种‘感受力的分离’,从而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上溯现代史上更久远的年代,不过,把这一问题与工业革命连在一起,似乎在理”[6]340-341。由此可知,桑塔格所言的“新感受力”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感受力”的对象是工业革命背景之下出现的新艺术及文化现象,桑塔格反对以美-丑、高雅-低俗等粗糙的二元对立标准来评价它们,为此,她提出人的感性、直观体验才是判断它们的首要标准。
(二)“新感受力”以人的感性体验为主要认知方式的实质是对现代形式“本体”意义的映射。“本体”的形式可以决定事物如何存在,因而新感受力能够调和“两种文化”。置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革命的历史背景中,桑塔格发现了分别代表感性与理性的两种文化形态:文学—艺术文化和科学文化。桑塔格质疑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离,特别对C.P.斯诺重科学而轻视艺术,将艺术的功用拱手让位于科学,以及一些人认为的,艺术在自动化社会将要丧失功用的看法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艺术的独立发展的天性将会受到扼杀。她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幻觉,是发生深刻的、令人困惑的历史变化的时代产生的一个暂时现象。我们所目睹的,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不如说是某种新的(具有潜在一致性的)感受力的创造。这种新感受力必然根植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得的诸如速度(身体的速度,如乘飞机旅行的情形;画面的速度,如电影中的情形)一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那种因艺术品的大规模再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泛文化观点的体验”[6]343。桑塔格将新感受力视为一种可以调和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粘合剂,新感受力可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基础即是个人化的体验。个人化的体验使得“文化”一词不再是是奥特加·加塞特所定义的文化泛指,而是同科学文化一样是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把握问题的特殊手段方面的积累和外在化”[6]340。从语言学上来说,“Sensibility”的其中一个意义:(尤指易受伤害或影响的)感情(a person’s feelings,especially when the person is easily offended or influenced by sth),已经包含个人感性体验的这层意义。新感受力与桑氏形式美学的关联也存在于“个人体验”这个关键词当中。新感受力既是对个人体验的充分发挥和运用,同时亦可看作是对“存在者”世界观的肯定。现代形式的“本体”内涵还在于:主体的感性经验秩序影响客体的形式秩序,因而个人化的体验可以改变“两种文化”的间离关系,“坎普”即是桑塔格对此的实践。
文章中桑塔格并未明确指出新感受力到底为何,但是在诸如“比起我们储存在我们脑海里的那些思想储存物所塑造的我们,我们之本是甚至能更强烈、更深刻地去看(去听、去尝、去嗅、去感觉)”[6]347。“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首要地是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6]347-348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新感受力的本质就是忠实于个人体验,个人的特殊感官经验是衡量一切艺术和文化的标准。这是由存在者个体的感性经验出发来诠释世界图景的再现,也是桑塔格形式美学中形式主体意义的呈现。
三、“坎普”——形式本体意义的实践
1963年12月,桑塔格所作的《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Camp”)在发行量低于一万册的《党派评论》上发表。当时很多活跃于纽约知识分子圈的评论员都认为桑塔格凭借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一夜成名”。1964年12月11日,该文章的梗概以双栏、五段的篇幅发表在《时代》杂志上。这让她为更多人熟知,也使得她立即成为了知识分子名流。时年三十岁的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开始与“坎普”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晚年,她已不再关注大众文化,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现代美学范畴仍然绕不开她。文章是桑塔格以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为对象所作的笔记和注释,除却开头对坎普内容的简要概述,剩余大部分则由8段王尔德的言论和58段桑塔格对此的阐释构成。就写作形式上来说,文章以一种代表坎普精神的平面化、反阐释的形式进行。对此,作者本人的解释是:“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些。以一种正经和专题论文似的方式对待坎普,只会使人不知所措。”[6]321-322
“坎普”这个现代美学范畴对桑塔格形式美学中现代形式“主体”意义的实践首先表现在“坎普”与新感受力关系密切,“坎普”的艺术在桑塔格看来是彰显新感受力的有力武器,“坎普”的眼光是新感受力的具体审美方式。
从语义上看,“Sensibility”的第二重含义尤指文艺方面的感受能力、鉴赏力、敏感性(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deep feelings,especially in art and literature),这明确了“感受力”的适用范围,即艺术和文学。桑塔格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6]343。
20世纪的诸多艺术实践加入了科学和技术的元素,如不再拘泥于传统乐器声音,而去使用改装的乐器以及合成声和工业噪声的音乐,还有摄影、电影这些完全依靠技术媒介的艺术类型。观众欣赏这些带有“坎普”性质的艺术依赖于新感受力,同时这些艺术形式又促进了新感受力進一步调和科学和文学艺术间的对立关系。
新感受力消减高级与低级文化之分,为“坎普”的审美对象——大众文化赢得了一席之地。两种文化界限的模糊,艺术实践中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化的介入使得原本诸多的二元对立遭到挑战,最受关注的当属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纷争。高级文化即是精英文化,属于高级文化中的艺术品因为其独一无二性而笼罩“灵光”;低级文化(或流行、大众文化)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依托媒介和技术进行大量复制的生产方式是最为拥护高级文化的精英阶级所诟病的原因之一。桑塔格反对以复制为借口就完全否定大众文化价值的单一判断标准。她认为“有趣”才是判断艺术优劣的唯一标准。大众文化的出现突显出新感受力的强大力量,懂得欣赏大众文化有助于人们培养新感受力,而新感受力又促进艺术吸纳更多有意思的元素。大众文化使得日常生活与艺术间的距离日趋渐近。桑塔格敏锐的觉察到这点,她以札记的方式将过去仅仅用来形容同性恋的“坎普”一词的意义外延扩大到了大众文化之上。“坎普”以生动和鲜活的方式呈现了新感受力的特质。
《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独特的札记写作方式也是新感受力的外在表现。这种札记式的写作方式,不难看到罗兰·巴特的影子。桑塔格对罗兰·巴特极为推崇,她曾说过:“我想巴特将会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特立独行者,即以比他最狂热的崇拜者现在所宣称的还要更伟大的作家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7]罗兰·巴特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先驱。他颠覆了文本需要有确定主题、意义要有明确的指向的传统学术思维,而将文本视作是不断游移的、没有原初性和恒定象征意义的实体,因而提倡碎片性编织的写作方式,试图以一种开放和无定向的语言方式揭示那个“闪耀的能指星群”,即一种由多个角度组成的更为完整的意义体系。《关于“坎普”的札记》中非线性、网络状的语言符号结构呈现了新感受力多元化的特征。
“坎普”对现代形式“主体”意义的实践还在于“坎普”能够改变人们对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判断。坎普所强调的“严肃性”就是改变的方式。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的内容方面,桑塔格首先对“坎普”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梳理,从18世纪初一种不同以往的感觉讲到19世纪出现一种晦涩、敏感的特别趣味,即“坎普”的前身。紧接着她将“坎普”视为一种感受力,并对其特质进行了分析。由此得到结论,坎普不仅是代表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态度。
“坎普”的内涵存在于散文式的书写中,譬如:“‘坎普’显然是现代的,是复杂性的一个变体,但并不等同于此”[6]320“它不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感受力”[6]320“坎普的实质在于其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6]320“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把世界看作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即坎普的方式,不是就美感而言,而是就运用技巧、风格化的程度而言”[6]322“坎普也是一种见之于物体和人的行为中的品性”[6]322“坎普是兼具两性特征的风格”[6]325“纯粹的坎普范例非蓄意而为;它们绝对严肃”[6]328。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总结出坎普的几点特征:非自然因素、严肃性,唯美主义。
“非自然”意味着对象带有不同以往的特殊含义,作为主体的人以“严肃” 的态度造就了“非自然”的客体对象。“非自然”是“两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指科学技术融入艺术后所形成的新艺术,如加入了艺术设计风格的日常用品。日常的生活因为人为技术因素的加入而变得具有审美价值,不同于传统艺术只针对高雅提出审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新感受力,也是“坎普”最为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具有坎普精神之人的特征——“十分纤弱以及极度夸张的人物”“女性化的男子或男性化的女子”显示出坎普独特的意义产生方式。女人加上引号成为“女人”,此时“女人”不再只是生物学规定的雌性哺乳动物,而包含了诸如母性,美丽,诱惑等更繁复的意义。在坎普的“非自然”属性之下,日常生活用品和女人有了特殊的含义。意义不再是单一乏味的,主体以“坎普”的态度面对客体,客体有了更深刻和多元的内涵。
“坎普”与“严肃”的关系微妙而暧昧。“坎普”要求以一种严肃的眼光看待浮夸或媚俗,而传统的价值评判只要求对高雅艺术施以严肃态度。这种带有严肃性质的目光拉平了高雅和低俗的审美价值,甚至将低俗变得高雅,即如果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低俗之物,那么低俗之物也有可能具有高雅的审美价值。作为现代形式本体的人通过“坎普”的眼光改变了对象的性质,也即是主体经验形式改变了客体形式秩序。如在《色情的想象》中,桑塔格高扬色情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她以“坎普”的态度面对色情文学,改变了色情文学与低俗的欲望有关的本质。但“坎普”也并非是古典学者身上所带有的绝对的严肃。带有坎普色彩的严肃,桑塔格将之称为“失败的严肃”,这里的失败性关键在于对待事物的严肃程度。她认为,“坎普既拒绝传统严肃性的那种和谐,又拒绝全然与情感极端状态认同的那种危险做法”[6]334。可见,“坎普”中的“严肃”是游离在古典主义的绝对严肃和现代主义轻浮夸张之间的。
唯美主义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主张艺术不受道德约束,反对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代表一种以审美判断为标尺的世界观。因而培养能够捕捉美感的感受力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在桑塔格看来,“坎普”即是这样一种感受力,是对技巧和风格化的描述。
桑塔格对坎普感受力的书写不论是形式上采取的札记式、散文式的写作方式,还是内容上一再强调的以审美和非道德判断的视角看待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都指向了一个结论:以新感受力来理解和表现事物的方式,不是从概念、内容、思想、知识去理解,而是从语言描述、风格、形式去感受。概念、内容、思想本是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本质属性,现在桑塔格宣称那些都是一种僵化的思想,而描述、风格、形式因其所具有的活跃、自由的品质才可以用来描绘今天的艺术和文化现状。这意味着理性与感性的相互补充和交融,精英与大众,高级与低级不再对立,强调人的感性经验的新感受力是促成这种文化现实的关键要素。正如当代学者Ellen Willis所说:“《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提出的就是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界线的模糊。新感受力的出现,证明了这才是以非文字形式为主体的当代文化的方向所在。感知、感觉、吸引的形式和感受力的类型,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元素。”[8]
四、结语
现代语境中,形式的本体意味指向了主体的感性经验,在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中,这一内涵显现在 “新感受力”和“坎普”两个美学范畴中。新感受力是理解“坎普”的基础,“坎普”是具体化的新感受力。新感受力强调以人之感性经验为准则,重塑现代艺术和文化现象的价值。而“坎普”既作为重塑后的代表美学范畴,又是一种更具体的看待事物和重塑事物的“眼光”。究其根本,“坎普”范畴关系到“看”的问题。坎普是通过肉眼的“看”(eido)进入内在观照,继而以“坎普”之眼光改变对象的意义。以“坎普”看待现代艺术文化现象即可洞见现象之下的本质,也可以改变对象之价值,使得对象“成其所是”。正如开篇提到的那场以“坎普:时尚扎记”(Camp:Notes on Fashion)为主题的展览,当观众用“坎普”的眼光看待时尚,时尚似乎也具有了新的意义。
注释
①“本体”一词在哲学中表示本源,即事物生成的根本原因。成中英先生认为,“本,乃根源,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并在动态的过程得出结果:体。体,是一种目的。本,在成为包含目的的‘体’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存在的起因。”由“本”至“体”的动态过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中,事物逐渐成形,意义不断生成,“本体”因而代表根源,也代表事物的生成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2.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3]贝尔.艺术[M].周金怀,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
[4]张法.二十世紀西方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32.
[5]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97.
[6]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22.
[7]桑塔格.重点所在[M].陶洁,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0.
[8]Ellen Willis.Three Elegies for Susan Sontag[J].New Polities,2005(3):118-123.
作者简介:方莹,硕士,安顺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学理论。
董天倩,硕士,安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王阳明《月夜》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