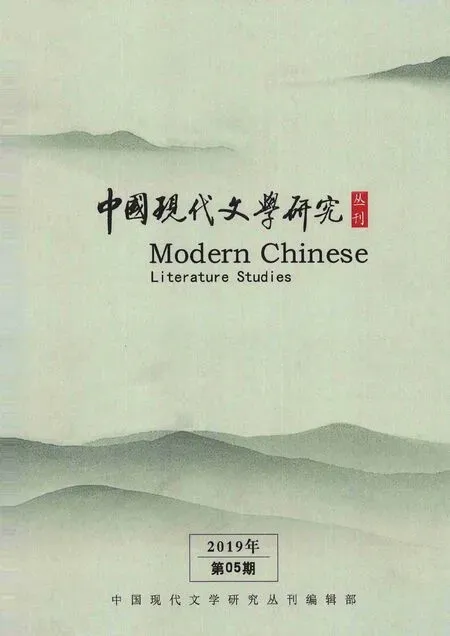《晶报》与郭沫若佚文※
金传胜
内容提要:新发现沪上小报《晶报》曾刊载郭沫若与张丹斧、叶玉森的往来书信,揭橥了郭沫若与小报文人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频通诗函、切磋学艺的一段交游史,展示了郭沫若文学与学术交往的另一侧面,呈现了旅日期间郭氏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卓然成家的背后“故事”。郭、张、叶三人能跨越新旧两派之壁垒与畛域,就共同的学术兴趣而刮摩淬励的文坛旧事,堪称一段佳话。
《晶报》作为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份著名小报,以其创始早、销量广、发行时间长而被称为“小型报的巨擘”,与《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并称小报界的“四大金刚”。该报本系《神州日报》附刊,1919年3月3日始独立发行,先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晶报》的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其一是广告,其二是社会新闻,其三为时事政治,其四是通俗文艺作品。其文艺内容以小说和小品文等趣味性消遣文字为主,网罗了袁寒云、周瘦鹃、包天笑、张恨水等著名文人。据郑逸梅所述,《晶报》的主持者对外一切由余大雄负责,对内则由张丹斧负责。张丹斧,原名张扆,又名延礼,字丹斧,别署丹翁,原籍江苏仪征。他是南社社员,“生平著作虽多,但什九为游戏文章和打油诗”,时人赠以“文坛怪物”的徽号。早年主编《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后转入小报界,任《繁华报》《大共和日报》《神州日报》主笔,兼为《上海画报》《小日报》《世界小报》等报刊的特约编撰。他不仅与同乡的李涵秋、毕倚虹等文人相熟,而且和胡适等文化名流亦有过从。
近日笔者在查阅《晶报》时,发现其中刊有郭沫若的多篇集外文字,包括书信、旧体诗等,兹一并披露于此,并试作考释。
一
1933年6月22日至24日,《晶报》连载署名“郭沫若”(此文署名郭沬若,原刊用“沬”之处现并改成“沫”,不再另作说明)的一封长函《致丹鱼》,随文添加了编者注。兹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郭沫若先生自日本千叶县寄来一函,乃与在下及红鱼先生谈龟甲文字者,即宝藏原迹,别录副本,载之本晶,以飨同道。丹注。)
红鱼丹斧两先生惠鉴:友人寄来五月廿七日及廿九日《晶报》各一份,得见两公对于拙著有所评骘,甚为快意,惟红鱼先生谓余“强认羊甲为狗甲,则好奇之过”。微觉于私意有未当。盖事本不奇,仆实无缘强好也。今于拙说有未尽处,略为左右敷陈之。
考“羊甲”之释,创于罗氏,然于卜辞,凡所谓“羊甲”之羊,均作若,无一作羊者。而从羊作之字,如、如、如羞、如義、如美、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等,无虑3百数十见亦无一从作。(有字,在前编卷一第三十六页三片,乃敬字,罗误释为羞,有字,乃地名多见,字未可识,罗强释为羔,自不能据为典要。)本此可知,羊实判然二字,罗以为羊者,乃因胸中先有阳甲之成见,以字形略类,故拜借赵高故智以为比附,别无根据也。
(丹案,郭先生名满全球,叶先生胸罗万卷,我就这门瞎说八道几阵,引得好稿子来,欢迎极矣。顽学问的先生们,等着饱眼福罢。)
(丹案:郭先生验出敬字上之狗双耳朵,不许羊角专美,绝顶天才,鑱破造化,可爱哉。而“及”“节”“句”“纠”诚非二物,然则亦甚合训诂。我对此说,允无间然,但我研究卜词,造诣至浅,于文字义例,所最心折,向惟叶红鱼董作宾两先生。不知两先生对此尚有异议否?至白袍小将金祖同先生,正跃跃欲试,其亦不知作何感想也。)
(丹案:郭先生新著金文一书,余老友黄叶翁购而读之,非常钦佩,屡向我言其奇妙。惜书店此书卖罄,无从购看,殊△想也。)
显然这是郭沫若1933年6月14日写给红鱼、丹斧两位先生的书信。时在日本的郭沫若读到友人寄来的5月27日、29日的《晶报》,因“两公对于拙著有所评骘,甚为快意”,然对红鱼先生的评骘不以为然,故投书二人,陈述己见。所谓“拙著”当指《卜辞通纂》。该书考释出了河亶甲(戋甲)、沃甲(学界多释为羌甲,郭释为狗甲)和阳甲三位殷王。
丹斧、丹均指张丹斧,红鱼则应是叶玉森。叶玉森字荭渔,别号红鱼、红渔等,江苏镇江人,南社成员、古文字学家。早年从政,宦游既倦,乃于1930年应交通银行秘书之聘,公事之余,仍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直至不幸病逝。郭沫若1933年6月11日致田中震二信函中写道:“《晶报》有二页载丹翁与洪渔二位评论《通纂》文字,乞暂假一阅,拟作覆。”这表明郭氏所谓的“友人”可能是田中震二。
查5月出版的《晶报》,果在27日、29日登有署名“丹翁”的《致红鱼先生》和署名红鱼的复信《复丹翁先生》。原来,叶玉森购阅了郭沫若关于甲骨文的著作《卜辞通纂》,对于郭沫若的部分释文持有异议,因而与张丹斧谈及。张丹斧复函研讨,认为“如郭先生再加充分训诂之证据,吾人亦可从其说也”。叶在《复丹翁先生》中首先称许“郭沫若氏之《卜辞通纂考释》,缀合残片,搜集异辞,厥功甚伟”,继而认为“惟强认羊甲为狗甲,则好奇之过”,并进一步举明义士《殷虚卜辞》之例阐述自己的观点。郭函坚持《卜辞通纂》中的说法,但对叶玉森“父丁”非“沃丁”之说表示接受。
看到郭沫若的长函后,叶玉森针对郭氏的商榷意见进行了答复。回信以《复沫若》为题连载于1933年6月28日、29日《晶报》(署名“叶红渔”),全函如次:
沫若先生左右:前致丹翁一笺,涉笔谐谑,宜为贤者所诃,乃蒙俯择狂言,节取父丁之说,虚怀若谷,倾佩良深。近年治甲骨文学者,董理之勤,创获之富,箸(今作“著”——笔者注)书之勇,惟先生与董先生彦堂,冠冕当时,并堪拜倒。大箸《卜辞通纂》,断定殷祖沃甲阳甲,核之卜辞,卅次适合,使殷代文献粲然可征,功诚大矣。惟羊狗之辨,犬豕之殊,重荷见商,请更缕陈一二。先哲造兽类象形文,往往就某兽之一部或数部,用为特征,如牛角挺而上翘,羊角△而下曲,并以角之一部为特征,着笔虽简,使人一望而知,神乎技已。殷代犬字外有无狗字,似为疑问,惟先哲如必须造一象形狗字以别于犬,虽至棘手,然亦不能借羊角以状狗头,如尊说挂羊头卖狗肉者然。先生谓侧视羊形无用作偏旁者,洵为卓见。予颇疑正视形之羊字为初文,故同时,或异时所造之从羊诸字如美義等,亦并用正视羊形,侧视形之羊字或带索者当为后起。商金器铭羊字屡见,均作曲角正视形,并初文也。惟子商甗亚形中有羊乙二字,羊作(《攈古录卷》一之三第三十一页)乃正视带索形羊字。与亚乙爵之,(又卷一之二第十六页)作侧视带索形者,当为一字。断不能释甗文为从系从羊,爵文为从系从狗也。且卜辞中固有正视带索形之羊字二,见前编四卷五十页七版,及八卷六页一版。与甗文正同,可互证也。予前揭明义士氏《殷虚卜辞》七百十八版“甲寅卜其禘方一羊(侧视带索形)一牛九犬”之辞,如依尊释,以狗易羊则殷代祭祖用牲,乃一狗九犬并献,似觉无稽。先生乃谓九犬之犬,首大尾小,脚促背臃,以释豕为宜,又谓尾端略拳,如非明义士摹误,则当是殷代卜师契误。予按明义士书七百十八版,字体较大,摹写尚精,似不至误。犬字作,系爪,不加腹线,(犬之腹线,或加或否。)系爪之犬字,如前编三卷二十三页六版,又七卷二十五页四版,八卷四页七版,亦屡见之,即用为偏旁之戾字兽字亦多系爪,概不加腹线,而犬之剽悍矫捷之状如生,许君谓犬狗之有悬蹏者也。故先哲造犬字,即以爪为特征,若豕字,则除短尾外,惟状其大腹,故必加腹线,或于腹线外注一小画,为大腹之识别。如前编四卷十七页六版云“贞禘牺(人名,作买鸟以矢形,姑从某君说释牺),三羊(正视形)三三”。此辞与前揭明义士书七百十八版之辞,句例相同,一比勘之,便知何者为豕何者为犬。而侧视形及侧视带索形之羊字,确非先生所断定之狗字矣。惟予固赞同先生沃甲阳甲之说者,微觉先生二说,均未能圆。姑妄言之,以鼓先生之兴趣。(一)羊甲何以为沃甲。殷代疑不讳嫌名,阳甲之前,固不妨有羊甲,侧视形之羊字,与古夭形必相近,又羊夭为一声之转,故羊甲讹传为夭甲,复增形为沃甲,犹卜丙之讹为外丙,是卜辞之羊甲即沃甲矣。(二)虎甲或象甲何以为阳甲。董先生之释为虎甲者,先生则释为象甲。实则甲上一字,殊态孔多,或巨口厉爪肖虎,或卷鼻大腹肖象,又或圆颅曲尾肖他兽。吾只认为兽形而已,否则释虎若象均不应增口。其为阳字者,按金文玺文之阳字,或省作昜字,昜形之较古简者,上则肖首,下则肖脊尾足形,颇似一兽。或古昜字为兽形象,讹变为昜耳。其从口者,即许书唐之古文暘,乃书暘谷之暘,从口犹从日也。昜暘当为一字,是卜辞之昜甲暘甲,即阳甲矣。此二说也,平淡无奇,尚足发先生一噱,愿更辱教之,海山梅炎,珍卫千万。叶红渔再拜。
郭沫若在同年7月5日致友人田中庆太郎的书简中写道:“兹有启者,《晶报》前月廿八、九两日,叶红鱼氏(即叶玉森)对于《通纂》续有评骘,祈假我一阅为祷。”通过向田中借阅《晶报》,抑或直接收到叶的书柬后,郭沫若作函复之。7月17日《晶报》发表署名“郭沬若”的《答红鱼》,即郭氏回复叶玉森的笺札:
红鱼先生惠鉴:承教殷殷,并有过蒙奖挹之处,甚感且愧。羊狗之辨,前函仍有未尽,今再补陈之。
由落款可知此信写于7月7日,继续申说“羊狗之辨”的学术话题,在《卜辞通纂》一书多次论及“甲”的前提下,力主应释为,并指出此字“确是狗字初文,象帖耳人立之形,此乃狗之惯态”,这一见解后来于郭沫若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中再次出现。
1933年8月11日《晶报》同时刊载署“郭沫若”的《致丹翁》和张丹斧的答复,全文如下:
《通纂》一书,书肆主人想已寄达。畴昔公言卜辞中羊狗似未同见,今觅得一例:“丁丑卜宾贞,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妣、食,羊三、用狗十。”
右见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引第三一三例,骨藏北京大学国学门云。今案“丁妻二妣”即祖丁,其配有妣己与妣癸也,文例至足珍异。
丹谨答曰:丁妻二妣,打破我的卜辞纪录,惭愧惭愧。《通纂》收到,此书编得博大巧密,得未曾有,读之咋舌。断片接头,如是之多,诚为伟业。即补插拓本,随加说明,亦饶兴趣,而索引奇字之精神,又岂清卿、雪堂诸老附录待问所可企及哉?其所择尤之甲骨,疑东邦菁粹,毕具于此,无怪是书,为世界学者所重视。至新义创获,时迈前贤,册纸光柔,如拊玉臂,俱堪引人入胜者也。静心读之,当益启我茅塞,先书数行,以申谢悃。
《通纂》即《卜辞通纂》4册,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5月出版。由两信不难推知,郭沫若大概见到《致丹鱼》文后“惜书店此书卖罄,无从购看”的按语,因而特意将此书寄赠张丹斧。张氏对此书的内容与印刷质量大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3年10月4日,《晶报》于第三版再次刊载郭沫若的《致丹翁》(署“郭沫若”),兹抄录如下:
日前赴东京,在子祥处得见《晶报》,尊评《通纂》,过蒙奖△,愧愧。弟近复有《古代铭刻汇考》之作,内容为殷刊余论、金文续考、石鼓文研究、汉代刻石,凡若干种。尊处如有新鲜资料,能供给我,至为盼祷。囊承赠伊侯古图一片,已收入△△二字。罗氏混为一谈,殊出意外。
同版亦登载了署名丹翁的《复沫若》:“公研究甲骨天才,自为同辈之冠。雪堂老矣,何能不让公独步,而《通纂》中之世次贞人,并补董氏之不足,此真好书,足以津逮学者。弟所藏零星小品,一时未暇多拓,意者颇有出人意表之文字体例,足以助公发明,先当检出数种呈教。”
郭沫若信末虽未具时间,但可推测作于1933年9月间。信中的“子祥”即日本友人田中庆太郎,字子祥,东京文求堂书店的老板。郭沫若1928年2月至1937年7月流亡日本期间,是文求堂书店的常客,与田中交往密切。正是在田中的支持与帮助下,文求堂出版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重要的甲骨金文研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刊》《卜辞通纂》等。文求堂还出版过梁启超、钱玄同的著作,以及追忆纪念王国维的文集《王观堂文选》。由两信可知,郭沫若在田中处见到《晶报》,对于张丹斧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赠送“伊侯古图一片”深表感谢。郭沫若又向张氏介绍了自己的近作《古代铭刻汇考》,并请求他能够提供“新鲜资料”。张丹斧表示愿竭力效劳,拟将所藏的“零星小品”检出几种寄与郭沫若。
二
1934年2月23日《晶报》再次出现署“郭沫若”的《致丹翁》,节录了郭沫若写给张丹斧的信札:
(上略)寿州鼎铭,去岁友人录示其一,以未见拓本为憾。尊拓尚未接到,大约金先生尚未付邮也。其楚王名“盦”,弟疑即楚幽王熊悍,盦熊古音相近,楚王盦章之为楚惠王熊章,正为左证。从心干声,干古文作。古文凡圆点,均演为横画,此多一横画,亦犹之作也。说文有字,南以为声,恐即此字之演化。器出寿州,自当在考烈王二十二年东徙寿春之后。幽王乃考烈王子,于年代亦宜。其他文字,尚有所见。俟见拓本后,再录呈教。“”即胾字,之蒸对转,假为烝,当是烝尝之本字。商锡永先生之《殷契佚存》,搜罗丰富,印刷精良,为近来罕见之书。其第四十三片“麋一豕册一麈百”。乃七十之合文,商误释为七。余求之数年,今一旦得之甚为愉快。此与五十作,六十作,八十作同例。菁华及林泰辅书,尚有一例,他日当为考以详之。又其三六〇,三六一、三六三,诸片之藏陈氏者,即其第三片之破碎。公试比观之,可知余言之不谬。弟苦资料缺乏,闻庐江刘氏收藏甚富,惜无缘寓目。近蒙其寄赠《善斋吉金录》一部,颇多精品。其圣之夫人曾姬无恤壶二具闻亦出寿州,不知与楚王鼎同坑否?(下略)
同版《丹附答》(署“丹翁”)则是张丹斧的答复:“金君拓片,此时想已寄到。一二日晤而问之,如未寄,弟即自寄。尊论数目字例,万确万确,已为学者所推服,公于接连片段,功劳犹大极矣。善斋吉金录,弟日前在秦曼青先生寓楼翻阅一过,果精妙,文字之足以发明新例至多,容暇叙述,博兄训正也。”
展读两函可知,张丹斧曾将自己收藏古器的拓本赠给郭沫若,邮寄人“金先生”应即金祖同。信中的“庐江刘氏”指现代收藏家刘体智,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善斋吉金录》是刘氏所藏古器图录,4函28册,1934年石印,陆续刊行,乃近代青铜器领域的重要著作。刘体智曾将此书赠予容庚、徐中舒、商承祚等学者。1934年2月10日,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信中有“张丹翁复有信来,问候先生”之语。2月12日再次致函田中:“上海刘体智昨日寄到《善斋金文录》一部,《大系》所需图像及拓本,大致备齐,拟着手编纂。”信文之外另有文字道:“《楚王鼎铭》三纸,自上海金祖同假得,乞摄影(原大),盖面文与鼎沿文可合作一幅。”由此可见,郭沫若约2月10日接到张丹斧一信,11日收到刘体智所寄书籍。同在12日,郭沫若有函致金祖同,谓:“手书奉悉,承示楚王鼎拓本三件,敬谢盛意。”说明郭沫若12日收到金祖同来信及楚王鼎拓本,立即转寄田中庆太郎,请他翻拍拓本,为《两周金文辞大系》用。
因上封《致丹翁》中谓“近蒙其寄赠《善斋吉金录》一部”,但发信时尚未收到金祖同所寄拓本,可推此信只能写于11日晚间或12日早间。另据丹翁《杂记》(载《晶报》1934年1月20日)中“昨得海东田子祥氏书,云郭新印古代铭刻汇考,将邮以赠我,我当报之以古物拓片,聊助多闻”的叙述,当时张丹斧与田中庆太郎亦有鱼雁往来。
时隔一年后,《晶报》1935年3月22日第三版刊登丹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热心推介郭沫若刚在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不久的新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力赞郭“近来造诣之高,多有突越前修处”。据“偶翻郭氏前所惠赠卷册,时有触悟,皆足瓣香。此箸晚出,价直弥可想见,至图录刊印之美,犹其余事尔矣”诸语,可知此书系郭沫若所赠。8月29日登载丹翁的一则短文《沫若传矣》,透露张丹斧新近收到郭沫若寄来的再版定本《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张氏浏览后,“觉其博大精微,得未曾有”,进而高度称誉了郭沫若的学识与贡献。此书1935年8月仍由东京文求堂印行,共3册。可知甫一出版,郭沫若就将其寄给了张丹斧。
同年10月29日,《晶报》第三版刊载丹翁的《沫若书诗》一文,释录了郭沫若落款“十月十九日”书赠给张丹斧的一首诗(随文刊印了郭的手迹,见右下图),全文如下:
郭沫若先生,赋诗见赠,滑稽之韵,令人解颐。功力既深,对仗弥巧,草法鸾翔凤翥。足敌△师。爰释其词曰:“贞观龙飞矣,谁能识典型。黄门淆黑白,丹子出蓝青。弄斧频施斧,解铃还系铃。何时捉曹操,(予前和诗有‘此事使君与曹操耳’之句)相与絜罍瓶。”今又步原韵云:“密用右军笔,全超智永型。池宜水尽黑,炉已火纯青。诗信迎来使,门扃听按铃。梅花亦知己,含喜在琼瓶。”墨迹揭载,以饷鉴家。

11月16日《晶报》第三版又刊出署名“丹翁”的《沫若诗函》,揭载了郭沫若寄给张丹斧的诗函,其中诗云:
在东笔钢不笔毛,与君作书偶研墨,炉头且喜苔特青,池中那有水能黑。月令寒气嗟总至,汧沔方舟叹囱逮。(自注:逮字若稍失韵,然读入声可通)(丹注:逮字正当读如得,公诚邃于音韵学者也。)郑玄注总犹猥卒,始知愚虑诚一得,实近蒲而远郿,□□之过日月蚀,快鸣石鼓□□□,□□□□莫惜力。(丹注:凡□皆未审出何字。)
信函仍为节录,如下所示:
(上略)方舟囱逮句,近复得一证,《礼·月令》“寒气总至”,郑注“总犹猥卒”,总即囱。均忽之一证也。释郿牵强,如可释郿,何不可释鄜。要在全审文,石鼓说为文公时物。(下略)
郭沫若诗函讨论的是石鼓文《霝雨》篇的释解问题,主要涉及“”字的释读和“方(舫)舟囱逮”一句的理解。而以旧体诗的形式来阐发本来严肃的学术论题,则显示了郭沫若的文人雅趣,同时也与惯用游戏笔墨的张丹斧甚为合拍。
三
时至1937年6月26日,张丹斧在《晶报》上发表《郭沫若氏之〈殷契萃编〉》(署“丹翁”),再次对郭大表赞扬:“甲骨之学,并世大贤治此者多,我但惊佩郭沫若氏之天才卓识,为手屈一指。新著《殷契萃编》,考覆之精,影响之巨,文笔之达,皆得未曾有,适荷遥赐,寓目版章如玉,已觉兴会飚举……”可知此年郭沫若亦将新出的《殷契萃编》(文求堂书店1937年5月石印本)寄赠予张丹斧,郭、张两人的书信联系至少达四年之久,并未中断。
稍前的4月5日,《晶报》第2版刊有郭沫若的一首旧体诗,并交代了此诗的由来:
廿八日晨陪凤子女史谒郭沫若先生,临行先生赠凤子二十八字。(祖同录存自东京寄)
生赋文姬道蕴才,霓裳一曲入蓬莱。
非关逸兴随儿戏,欲起燎原自死灰。
1937年3月至6月,凤子应东京中国国际戏剧协会的邀请,到日本公演《日出》,其间结识了郭沫若并与之多有交往。郭沫若赠凤子的这首七绝严格说来已非佚文,因凤子在《怀念郭老》(1992)一文中曾经引录。丁茂远编著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中亦以《赠封禾子女士》为题考录此诗。书中注释云此诗发表于1937年6月6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晶报》发表此诗明显要早于《国民公报》,很可能是它的初刊处,系由祖同(即金祖同)抄录后自东京投寄。但依据另一则新闻报道,此诗是凤子在东京银座回宴日本各界友人时,郭沫若赴宴时赠予凤子的。由于此则报道发自4月底,且使用了“日前”“最近”等模糊时间,在准确度上不免要打些折扣。故原诗更可能是3月28日金祖同陪凤子拜访郭沫若时,郭氏给凤子的临别赠诗。
值得注意的是,金祖同与张丹斧、叶玉森的关系非同寻常。金家在上海二马路(今九江路)开设中国书店,主要经营收购和出售古籍,是沪上文人学者经常光临的场所,故作为小主人的金祖同与众多文化精英多有交集。早在1933年6月2日的《晶报》上就登有金祖同的《〈君休性急〉补》,嗣后金氏的文字不时见诸该报,如《寒云书跋零拾》《奄城访古记》《闲话金山卫访古》《记平湖葛氏传朴堂藏书》,及其与张丹斧等的通信等。金祖同于1931年经鲍扶九介绍,问业于叶玉森,初识殷墟卜辞。叶玉森于1933年8月7日不幸病逝,金祖同特撰《忆红鱼师》以示悼念。其后,金氏协助收藏家刘体智整理校录其收藏之甲骨。1936年7月,金祖同到日本留学,成为郭沫若弟子,继续研治甲骨学。学界此前曾发现郭沫若致金祖同的两封书信,均作于金祖同赴日前。1934年2月12日郭沫若致金祖同的书函中写道:“葓渔先生逝世,最近始得闻之,深为震悼,闻所著有《殷虚书契前后编考释》,不识有出版之希望否?”看来叶玉森的死讯直至半年后方为郭沫若获悉,同时郭也十分关心叶氏遗著的出版情况。由此,叶玉森的《复沫若》可能是叶氏生前写给郭的最后一通书札,当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通。
结语
郭沫若在致田中庆太郎、叶灵凤等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张丹斧,因此学界之前仅知郭氏流亡日本期间与张曾有书信往来,但对于两人的具体交往情形并不清楚。由于张丹斧与《晶报》的特殊关系,郭沫若致张丹斧、叶玉森的书信等文字出现在该报上并不奇怪。作为享有盛誉的新文学作家,彼时郭沫若虽流亡海外,但在国内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关注度。张丹斧将本属私密的郭氏函札公诸报端,显然并非仅仅为了让读者“饱眼福”,而是一种苦心孤诣的编刊策略,欲借名人效应来吸引眼球,增加报纸销量。从已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得到了郭沫若的默许。如郭沫若1934年3月28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中明确提及“上月中旬《晶报》曾刊载小生信件,千祈暂假一阅”,应即此年2月23日《晶报》所刊之《致丹翁》,表明当时郭沫若对《晶报》上自己的书信与相关信息甚为关切。只是郭本人未能及时予以汇辑,后来的研究者们亦未按图索骥,钩沉索隐,导致这些文字长期散佚。
要言之,新发现的这些史料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它们揭橥了郭沫若与小报文人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频通诗函、切磋学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游史,展示了郭沫若文学和学术交往的另一侧面,呈现了旅日期间郭氏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卓然成家的背后“故事”。郭沫若曾在《殷契萃编·序》中对金祖同的帮助深表感激:“去岁(即1936年——引者注)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赍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爰不揣谫陋,择取其一五九五片而成兹编”,此已为学界所共知。依据《晶报》上的文献,我们或可做出以下阐说:除金祖同的鼎力襄助外,郭沫若在甲骨学研究上的成就,亦离不开张丹斧、叶玉森等所给予的支持。郭与张、叶的交往中,田中震二、田中庆太郎与金祖同等曾先后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此外郭沫若广搜博取、不矜不伐、择善而从的治学风范亦在这些佚信中展露无遗。或许张丹斧、叶玉森毕生未曾与郭沫若晤面交欢,但三人能跨越新旧两派之壁垒与畛域,就共同的学术兴趣而磨砻镌切的文字往来,堪称一段文坛佳话,值得今人记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