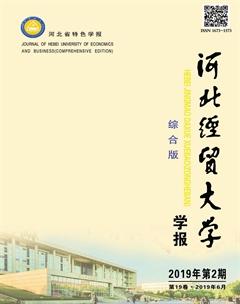同一序曲上的不同音符:鲁迅与吴宓的翻译观比较
王婷 杨清珍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西方著作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但是,无论是译介的材料还是具体的译介方式以及使用何种语言作为译介的媒介,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想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在翻译中,鲁迅一直主张直译,除了坚持用白话文翻译外,还积极引进欧化的句式和词汇,意图“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及通过翻译改造中国语言,进而实现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吴宓主张意译,不仅力求文章顺达,更注重“新材料入旧格律”,以实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关键词:直译;意译;鲁迅;吴宓;文学观;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9)02-0021-06
一、引言
鸦片战争以降的文学启蒙与文学变革都与国内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晚清的大规模翻译潮如此,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迫使精英阶层不断寻求改良之道,从洋务运动的“器”的层面的改造,到戊戌变法的“制”的层面的改革,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语言”层面的革新。这些层面都存在着文学与翻译积极推动的身影,构成了近代以来的文学启蒙与翻译浪潮。近代以来的大文学家往往具有文学家与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如茅盾、周作人、鲁迅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文学家鲁迅的翻译思想以直译为主,最广为外界所知的是其“硬译说”。
一直以来,文学家吴宓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为外界所熟知。当历史的迷雾散去,吴宓的文化守成者的角色也逐渐被后来的学人所认同。文学创作领域,不管新文化运动进行的如何如火如荼,不管白话文已经成为教育界、报界、小说界通行文体,吴宓依然坚持用古文作诗、创作。这种文化守成主义的文学观体现在翻译领域,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其翻译所采用的文体也多为文言,表现在翻译方法上则为“意译”。
影响翻译的因素有多重,主要有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标准的拟定和翻译方法的选定。笔者拟从译者的翻译策略入手,具体则体现为以吴宓与鲁迅的直译观和意译观为切入点,试图指出鲁吴二人的翻译观实则是二者不同的文学观在翻译上的体现。
二、“直译”与“意译”的定义
“直译”与“意译”的概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佛经翻译时期,“直译”指的是直接翻译,与其相对应的是“重译”,即现代意义上的“转译”。赞宁在《宋高僧传》中指出,“直译”指的是佛经直接从印度传来后,直接翻译为汉语;“重译”指的是,佛经从西域传来后从胡语“重译”,然后再翻译成汉语。[1](P33)
“直译”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则到了晚清时期。此时的“直译”,又叫“直叙”,基本上包括按字直译(音译专名)、直译日文文法、引进西书中的标点符号、使用文内注以及依事直叙等具体的翻译手段。[2](P56)此时的“直译”在文体上依然大多采用文言文。与“直译”对立的是“译意”。“译意”即“译意不译词”,仅翻内容不译语言形式。
到了新文化“五四”时期,“直译”有了新的内涵,并首次出现“意译”这一概念。这一时期的“直译”在技术层面上与晚清的“直译”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是,与晚清的“直译”只限于翻译的技术层面并受到翻译主流排斥的边缘文化地位不同,这一时期的“直译”观大行其道,超越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翻译人通过“直译”观的表达,对翻译、对文学乃至对整个文化的话语權的争夺。文体上,“直译”观表现为用白话文和欧化的语体文来翻译。此时的“直译”包括以下几重含义:第一、文体上,白话文,具体到遣词行文上,采用欧式的词法;第二、内容上,不随意删减原文。与“直译”相对应的是“死译”。“死译”指的是“逐字翻译”,即不考虑上下文语境与英汉句式语序的不同,而采用固定的字典意义进行翻译。
“意译”一词的正式出现开始于五四时期。[2](P64)这个时期,“意译”的定义与解释有很多。艾伟在《译学问题商榷》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如吴致觉先生认为,“不照原文之字面或句法而述其大意之翻译谓之意译”;孟宪承先生认为,“意译为运用译者自己语法及结构之翻译”;董任坚先生认为,“‘意译是述译而已”;杜佐周先生认为,“为求读者便利起见,当以意译为佳;但以不失原意为准则”。[3](P160-180)概括起来,认为“意译”等于述译或译意的观点,实在是对“意译”的曲解。这是因为,“五四”时期出现的“意译”是在反对梁启超式的“豪杰译”“新瓶装旧酒”的基础上立论的,反对的是晚清以来盛行的述译、歪译。“意译”与“译意”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译”为中心,译文的顺达是实现翻译成功的手段,目标语文学形式服务于翻译,以保持对原文的忠实为前提;而后者则以“意”为中心,翻译为手段,翻译服务于目标语文学,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并不是翻译的重点。
因此,“意译”与“直译”的区别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隶属于同一个阵营,基于对翻译定义的共同认知,即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以“信”为前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翻译风格的不同。“意译”成为“直译”的补充,是达到忠实和信的另一条途径。[2](P65)
三、鲁迅与吴宓翻译观的比较
(一)鲁迅的文学观
鲁迅成长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目睹的是中国国运的日益颓唐。鲁迅曾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远渡日本学医,以期一方面去医治国民的身体,另一方面启发民众的思想。但是,在仙台医专的学习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医学并不能医治人的精神。“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4](P4)鲁迅认为改变民众的精神比身体更重要,而第一步则是走文艺的道路,开展文艺运动。开展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莫过于改造自己的语言。鲁迅认为,中国的语言有其内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不够精密,缺乏逻辑性。这方面的不足会让民众的思想缺乏逻辑性,从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鲁迅看来,改造本民族语言的方向有三种: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异样的句式句法。[5]归纳起来,就是一要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语法句式结构来改造汉语;另一方面,则是要从中国的语言文化宝库中去挖掘新的东西。其中,鲁迅践行的最多的是用外国的句式句法来改造汉语。
如何用外国的句式句法来改造汉语?在文学创作方面,鲁迅积极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尤其是欧化的白话文。“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6](P621-625)在鲁迅看来,第一步便是通过翻译文学来改造现有的汉语言文学。在这方面,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一样,积极地从事翻译活动。纵观鲁迅一生的学术成果,七百多万字的翻译与创作作品中,翻译就达到了三百多万字。翻译活动对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狂人日记》受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影响。只是,在引进翻译文学改造现代汉语的过程中,鲁迅走得更远也更极端,也因此引来了很多不解,如与梁实秋的长达八年的翻译论战,以及与赵景深关于“milk way”翻译的争议。
可以说,鲁迅个人的翻译创作实践展示了汉语的发展之路和进一步改造国民性的一个出口。最大限度地去“拿来”西方的句式句法改造中国的语法的途径,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就是直译,甚至是“硬译”,“宁信而不顺”。倘若像晚清时期的梁启超提倡的“译意不译词”,抑或是像严复所主张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对于汉语言的改变则只涉及到内容的引进,而无关语言形式的改变,更不涉及通过语言形式改变国人的逻辑思维判断。鲁迅的直译观是与其文学观一脉相承的,是其文学观在翻译上的体现。
(二)鲁迅的翻译观——以直译为特征
鲁迅的“直译观”并不是始于翻译活动伊始,而是随着自身的翻译实践以及文学观的改变逐渐形成的。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1903年6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哀尘》。受当时的翻译风潮以及林纾等人的影响,无论是《哀尘》还是《斯巴达魂》,此时鲁迅翻译文体还是以文言文为主,采用的翻译手法也多为当时的主流翻译方法,如编译、改译等。直译风格的形成则以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发表为标志。此时的周氏二兄弟不满于以林纾为代表的乱译误译之风,决定自译短篇小说来纠正翻译时风。①但是,真正将直译乃至硬译风发扬光大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了。
鲁迅的直译观归结起来有以下两点:第一、强调语言形式与思想的正相关,具体到翻译实践,在使用白话文翻译的基础上,用欧化的语体翻译,弥补白话文的不足,以期通过改造语言来改造民众的国民性;第二、翻译标准上的“宁信而不顺”,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则为逐字逐句的直译。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硬译观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读者和一切的文学题材。鲁迅将翻译的读者群分为甲乙丙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甲乙两类读者,也不皆适用硬译观。鲁迅认为乙类读者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是创作;至于甲类读者,则是主张“宁信而不顺”。[5](P13)“宁信而不顺”不是只要“信”而不要“顺”,而是意图在于“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就是话不够用……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5](P42-43)“宁信不顺”是实现既信又顺的过渡,鲁迅是不反对既信又顺的译文的。鲁迅认为,“宁信不顺”的状态不是翻译的终极状态,“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5](P14)“自然,世间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7](P15-16)至于乙类读者,鲁迅虽然没有主张一定要用“硬译”的翻译方法,但是他也主张“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5](P43)
通过引进新的语言形式、结构来改造汉语,从而进一步改造国人的思想,肯定了语言形式对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样的“直译”或者说“硬译”方法有时候存在着阅读的困难,不可否认鲁迅的有些译文是不忍卒读的,如“这制度,言其意思,便是在文化底方面,是应付精神的最微妙而且高尚的要求的社会底和国家底生活机关的衰颓与破坏”[8](P332)由此,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鲁迅这些难以卒读的译文是其本人的翻译水平不够呢,还是其故意为之?
早在鲁迅译文出版伊始,就有人指出鲁氏译文的晦涩难懂,认为其译文是“死译”。梁实秋曾就鲁迅的“硬译”有过猛烈的批判,认为其译文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9](P347)面对这样的指摘,鲁迅指出其译文的作用在于“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10](P475)可见,所谓不顺或者是“死译”的译文实则是鲁迅的故意为之,是为了建设新语言的需要,是与其文学观相一致的。进一步说,是鲁迅想通过翻译改造汉语,壮大本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进而实现民众思想的改造与中国的救亡图存。鲁迅的直译观更多地体现了翻译与文学的交互作用,以及在本民族语言系统内部出现危机时,通过翻译引进的语言形式、结构对本民族语言的革新。
(三)吴宓的文学观——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为特征
长期以来,由于主张使用文言去作文、作诗,吴宓及其代表的“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的,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猛烈攻击。鲁迅认为“学衡派”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11](P281-283)
但是,透过历史的尘埃,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的文化守成者的角色逐渐受到学界的认可。乐黛云认为,学衡派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其与自由主义、激进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12](P26-31)
吴宓虽坚持用文言文作诗,白话文作文,但是,对于白话文的态度是包容的。这也反映在后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办刊宗旨和实践上。在《文学副刊》第一期中,吴宓指出,“对于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别,亦一例平视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惟美为归,惟真是求,惟善是从。”
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一文中,吴宓将当时存在的文体划分为五种,即诗、文、小说、戏剧、翻译。新材料指的是以下内容:即如五大洲之山川风土国情民俗,泰西三千年来之学术文艺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学等之书籍理论,亘古以还名家之著述,英雄之事业,儿妇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致极小,靡不可以入吾诗也。又吾国近三十年国家社会种种变迁,枢府之掌故,各省之情形,人民之痛苦流离,军阀、政客、学生、商人之行事,以及学术文艺之更张兴衰,再就作者一身一家之所经历感受,形形色色,纷纭万象。[13](P269)
就翻译而言,吴宓认为其是实现“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13](P277)可以说,翻译是吴宓实现文学理想的重要窗口。凭借翻译,西方的经典思想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被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同时也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新材料。在新文化思想的热潮中,在尚新弃旧为时代主流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实践,吴宓所扮演的都是一个守成者的角色。当然,文化的守成不仅在于引进的新材料纳古今之精华,更在于渐进地改革旧格律。
根据吴宓对时存的文学体裁所作的划分,旧格律在不同的文学体裁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诗歌中,旧格律指的是“古近各体,而旧有之平仄音韵之律,以及他种艺术规矩”[13](P268)在文中,旧格律指的是古文。吴宓认为“而古文者固吾国文章之最简洁、最明显、最精妙者。”[13](P269-270)在小说中,旧格律指的是长篇章回体。但是,此处的章回体已经不仅仅是传统中文小说中出现的样式,而且融合了西洋的长篇小说的行文方式,欲“昌明国策,融化新知”。吴宓认为,“而章回体之长篇小说,艺术尤精,其中之规矩法程及词藻,均宜保存之遵依之,同时更须研究西洋长篇小说之艺术法程,以增广之,补助之,而进于至美至善,此所谓旧格律也。”[13](P274)在戏剧中,“宜恪守旧剧之规矩,方为合用”[13](P277)。但是,吴宓不同于复古主义者,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入亦是他文学活动的一个重点。他赞成戏剧中人物的对话用白话文,但是布景的说明亦坚持用文言文。在翻译中,坚持用文言文、古体诗去翻译西方作品,并主张译文的文体与原文的文体相对应。
因此,以阿诺德文化保守主义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学理依据,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了解,吴宓逐渐形成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为特征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是一种渐进式的文化改良主义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反映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体现为以“意译”为特征的翻译。这种以“意译”为特征的翻译,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有以下特征:第一、行文须顺达;第二、采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文体,即文言文;第三、翻译内容的选择上,多选阿诺德、白璧德等人推崇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但丁、华兹华斯等。当然,作为吴宓思想源头的阿诺德和白璧德的作品的译介更是吴宓翻译的重中之重。
(四)吴宓的翻译观——以意译为特征
翻译观上,吴宓支持严复的“信达雅”,反对硬译、胡译,主张意译。吴宓认为,译有三要:一者,申明原文之意;二者,以此国之文达之而不失原意,且使读者能明吾意;三者,翻译之文章须自有精采,是即严又陵所谓信达雅也。翻译之法无定,或逐字逐句译之,或通篇译其大意,要视为之者如何耳。[13](P277-278)
在吴宓的翻译观中,忠实原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译文的练达,最后是文章的精彩。吴宓赞同德莱登关于翻译方法的分类,即直译、意译和拟作。他认为,三者之中,直译窒碍难行,拟作并非翻译,过与不及,实两失之,惟意译最合中道,而可以为法。至于意译之法,简括言之,词藻尽可变化,而原意必不许失,执两用中,求其适当而已。[13](P277-278)因此,吴宓虽承认翻译的方法并不固定,但是逐字逐句译也好,编译也罢,都必须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做到文章的顺达,即必须是在意译的视阙下进行翻译。
吴宓的意译观概括下来有以下两点:第一、忠实原文,保持译文的顺达;第二、译文文体的选择。吴宓认为:凡译者必其于所译原作研究有素精熟至极毫无扦格含糊之处……译文或用文言,或用白话,或文理有浅深,词句有精粗,凡此均视原文之雅俗浅深如何而定,译文必与相当而力摹之,并非任意自译。[14]译文文体的选择与原文的文体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原文是文,那么,译文也须是文,且是文言文;如果原文是诗歌,译文须是古体诗;如果原文是小说或者是戏曲,译文的文体可以是白话文。“除戏曲小说等其相当之文体为白话外,均须改用文言。”[13](P278)
吴宓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们一味地采用白话文放弃文言翻译的主张。吴宓认为语言的改制不可一蹴而就,语言有其内在的规律。通过翻译固可以引进新材料、新思想,但是新材料必须入旧格律。“故翻译之业,实吾前所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13]
(五)鲁迅与吴宓的翻译观的比较
鲁、吴二人的翻译观看似南辕北辙、不可调和,一个以“硬译”为特征,一定情况下,可以牺牲译文的通顺性,意图通过矫枉过正式的新词语新句法的引入,实现“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救国主张;一个主张“意译”,注重译文的通顺性,反对句法句式晦涩难懂的白话文,“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以实现文学的渐进改良、社会的渐进改革。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并不反对文章的顺达,除了“硬译说”,鲁迅还提出“丰姿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15](P14)对于鲁迅而言,同时实现译文的通顺与原文的忠实是翻译的理想状态。如若不能保持二者的和諧共处,则“宁信而不顺”。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是鲁迅翻译观的底线,是翻译的最低标准,是好的译文的过渡阶段
但是,从上文关于直译与意译的定义来看,鲁迅的直译观与吴宓的意译观无疑具有相通的一面,即他们的翻译观皆以忠实原文为基础,皆隶属于广义的直译观。鲁、吴二者在翻译观上最大的区别在于翻译的文,而翻译文体的选择实则与其各自的文学观息息相关。鲁迅主张迅速使用白话文,是激进的文化观,吴宓则认为文化的革新不可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是改良的文化观。
鲁迅主张使用白话文来翻译,而吴宓大多数情况下用文言文作为译文的载体。但是事实上,吴宓并不反对译文中白话文的使用,“除戏曲小说等其相当之文体为白话外,均须改用文言。”[13](P278)可是,吴宓口中的白话文与鲁迅的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吴宓的白话为“中国式白话文”,是语言体系的改良,不与文言相冲突[16]。吴宓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不加选择,一味弃旧扬新,更不赞成其文章中出现的语句不顺、难解的白话文。吴宓并不反对语言文字的革新,只是反对文字的激进变革。吴宓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17],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翻译为主要的媒介),要撷取西方的精华,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诺德、白璧德等人的思想。文言文亦不可尽废。“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17]而鲁迅的“西式白话文”则是对过往汉语言体系的全面变革,倾向于废除文言,全面引进西方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材料。一方面,鲁迅欲通过翻译中的新句式、新语言的引进来改变文言文逻辑不足的问题,进而通过语言逻辑性的增强提高民众思想的逻辑性。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民族危机最重的阶段,外有列强凌辱,内有军阀割据,此时的民族自信心最弱。此时先进的中国人迫切向外、向他处寻求救亡图存之法。因此,中国旧时的一切,糟粕也好,精华也好,很容易被抛弃,很容易出现矫枉必须过正的想法。在文化观上,就容易出现一些激进的主张,比如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18](P338)“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18](P350)
鲁迅这一激进的文学改革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其对于吴宓以及学衡派的公正评价。鲁迅对学衡的评价后来成为学界的基本论调,使得学衡与“甲寅派”一起成为复古、守旧的代名词。鲁迅的评价虽没有直指吴宓,但是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审稿人,甚至是幕后赞助人②,这篇评论无疑是对吴宓的办刊主张的完全否定。针对鲁迅的指摘,吴宓虽承认“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19](P235-236)但也进一步指出,鲁迅的批判只是针对邵祖平一人,并指出邵祖平的文章得以发表全因胡先骕一力推荐,“斯乃胡先骕之过”[19](P236)这也从侧面回应了鲁迅的批评,即吴宓不认可鲁迅对学衡的评价。
鲁迅对吴宓的直接批判则见于《“一是之学说”》。主要的还是围绕文言与白话的兴废问题。针对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提出的融贯中西,取中西之精华而学之想法,鲁迅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反驳,而只是围绕标点和一些措辞的使用表明吴宓所倡导的“执中驭物”的不合理之处。可以说,鲁迅对吴宓的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有以偏概全之嫌。
因此,以阿诺德文化保守主义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源头,力求中西文化融通融合的文化观决定了吴宓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必定是以改良和渐进为特色的,体现在文学上就是用文言文作文,以古体诗作诗,表现在翻译上则为译文为文言文,注重文章的顺达,即以“意译”为特色的翻译观。而鲁迅主张通过矫枉过正式的文学革命的形式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文学观决定了“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即译文中以白话文作为语言媒介和大量欧化语式和外来词语的出现。“直译”观也好,“意译”观也罢,集中反映的是不同的文学观在翻译领域的表现。集中在吴宓与鲁迅身上,则聚焦在翻译文体的选择上,即白话文的使用与否。
四、结语
面对愈来愈深的民族危机,鲁迅与吴宓二人皆看到了翻译对于引进新思想、改造国民性的作用。然而,鲁、吴二人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却产生了分歧。鲁迅尚直译,坚持原文与译文在思想与形式上的一致性,即主张引进欧式句法和词法。吴宓尚意译,更加注重原文与译文之间思想的准确传达与否,反对佶屈聱牙的译文的出现。“直译观”与“意译观”之间的矛盾不在于忠实原文与否,而在于于引进的新材料到底入的是哪种格律的问题。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到底走循序渐进式的文化改良还是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文化革命。鲁迅不仅赞成新材料须入新格律,而且认为西方的新格律也须入中国的新格律—白话文中。因此,鲁迅的译文中会出现一些欧化的句式与表达,有些表达甚至晦涩难懂。这些不是鲁迅的翻译能力不足,而是鲁迅的有意为之,是其文学观在翻译场域的体现。
鲁迅认为,中国的旧有的语言存在着逻辑性不足的问题,其不仅否定一直以来通用的文言文,更急于引进欧化的句式与表达来丰富白话文,冒句式不够通顺、不被理解也在所不惜。而吴宓则认为新材料须入旧格律,即须保持译文的顺达,以及文言文的使用。吴宓受安诺德和白璧德思想较深,走的是文化改良的道路。体现在文学上就是重视将中国旧有的思想经典与西方的思想进行融合,“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此,以“意译”为特征的翻译观是吴宓的“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文学观在翻译方法的具体体现。
注释:
①《鲁迅致增田涉信》,1932年1月16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②在《吴宓自编年谱》中,吴宓指出“《学衡》杂志本无经费。社员亦毫无捐助。自始至终(1921-1933年),所有办大小事,需用之款无论巨细。以及每次开会有时,梅君提议:星期日到下关开会,藉图一次欢乐醉饱。之茶点费,纸张笔墨,尤其邮费,寄出杂志。此为大宗开支。全由宓出钱付给。故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個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胡翠娥.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艾伟.译学问题商榷[A].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魯迅.自序[A].呐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论翻译[C].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77.
[6]鲁迅.玩笑只当他玩笑[A].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7]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鲁迅.鲁迅译文全集:第四卷[M].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2008.
[9]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A].《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0]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杂文全集(上)[C].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11]鲁迅.估《学衡》[A].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2]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13]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A].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4]吴宓.梦中儿女·编者按[J].学衡,1922(b).
[1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A].鲁迅论翻译[C].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77.
[16]王雪明.制衡·融合·阻抗[D].上海:复旦大学,2008.
[17]吴宓.论新文化运动[A].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8]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A]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9]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艾 岚
Abstract: In movement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mass of western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ncern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different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whether it being the choice of genre,or the target language. As one of the radicals in this movement,Lu Xun holds that western book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 a literal way,in process of which,modern Chinese and English syntax should be adopted to reform Chine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As a conservativ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Wu Mi advocated liberal translation,not only striving to make the article easy to read,but als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to old rules",so as to realize "the quintessence flourishing and melt the new knowledge".
Key words: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Lu Xun,Wu Mi,literary outlook,translation the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