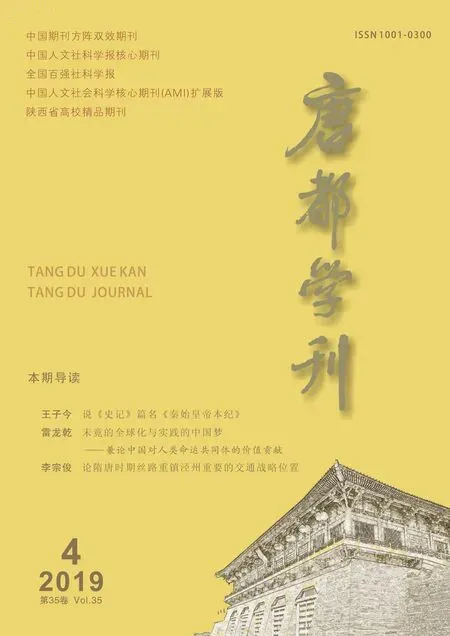秦二世“坏宗庙”试解
邱文杰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贾谊《过秦论》为汉初著名政论[注]《文选》即收录其上篇列于“论”体之首,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1《论一·过秦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07~709页。。司马迁所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篇末录有其文,《史记索隐》引邹诞生说,谓“太史公删贾谊《过秦》篇著此论,富其义而省其辞”[1]283。《过秦论》下篇在论及秦二世时有这样一段表述: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其中,“坏宗庙,与民更始”一句,中华书局《史记》1982年标点本、2014年修订本都以“坏宗庙与民”连读[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4页。《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7页。此处标点略有调整。。《史记集解》在此句下引徐广说“一无此上五字”,点校者的处理或受此影响。再者,“坏宗庙”“与民更始”在秦史文献中极为罕见,所以梁玉绳《史记志疑》即认为:
徐广谓一无“坏宗庙与民”五字,甚是。二世无坏宗庙之事。“更始作阿房宫”为句,谓复作阿房宫也。[2]
但此后俞樾《诸子平议》认为“与民更始”四字应单独成句[注]参见俞樾《诸子平议》卷27《贾子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44页。实际明人凌稚隆所辑《史记评林》亦作如此断句。参见凌稚隆辑《史记评林》(第一册),广陵书社2017年版,第590页。。近年来,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简中有所谓“二世元年诏书”,其中有“宗庙”“与黔首更始”等相关表述: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事)及箸(书)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面)吏、黔首其具(俱)行事,毋以(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注]释文参见张春龙、张兴国:《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载于《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相关校改参见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通释》,载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收入所著《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释》第十四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362页。
此外,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亦载有类似表述:
北大汉简整理者即在注释中引述贾谊《过秦》与兔子山二世诏书,并指出了其中的联系:
简文说秦二世“坏其社稷,燔其律令”,未见于传世文献。贾谊《新书·过秦》称二世“坏宗庙,与民更始”,其说与《赵正书》有相似之处。《赵正书》下文李斯称秦二世“灭其先人”,当指“坏宗庙”而言。[3]191
此处将“坏宗庙”和“与民更始”点断[注]相关句读又见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北京论坛(2016)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2016年,第10页。王志勇《〈史记〉新考》,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8页。王文在句读校改时亦曾引兔子山诏书与《赵正书》,但仅关注到“与民更始”的句读问题,未涉及“坏宗庙”问题。,同时提示《赵正书》“灭其先人”与“坏宗庙”之关系,值得重视。但句读校改之后,“坏宗庙”单独成句则需进行解释,本文即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出土与传世文献试为申说,以就正方家。
二、二世皇帝元年“议尊始皇庙”平议
实际上,有学者已经指出“二世元年分明载有将襄公以下之历代先君庙尽行‘轶毁’事,贾谊语盖谓此”[注]参见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页。尽管此处仅为推测,但据笔者目力所见,只有该书提到这两者的关联。。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益阳兔子山二世即位诏书“宗庙吏(事)”即与《秦始皇本纪》所载二世元年(前209)这份“议尊始皇庙”诏书有关[注]参见邬文玲《秦汉简牍释文补遗》,“秦汉史研究动态暨档案文书学术研讨会”论文;此处转引自王子今《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载于《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相同意见还见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考释》,收入所著《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下面对此次元年庙议做具体分析:
(二世皇帝元年)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注]参见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注释。韩兆琦《史记笺证》,第493页。“或在西、雍”一句标点参考王子今:《关于〈史记〉秦地名“繁庞”“西雍”》,载于《文献》2017年第4期,第5~6页。
此处群臣奏议相较二世“议尊始皇庙”之诏令要求远为丰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古者”至“不轶毁”是其理论依据。“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这一记载多见于先秦儒家经典。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指出“此议与《穀梁》《王制》《礼器》《荀子》合,博士之议固存也”[4]。皮锡瑞《经学历史》在探寻经学在汉代之前的源流时,也提到此次庙议事件:“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文;见《秦始皇本纪》。……良由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5]58周予同在注解中说道:“博士,秦官。秦焚书后,博士伏胜藏《尚书》,至汉,以传朝错,即博士尚守遗书之一例”[5]61。意即此次廷议,群臣所奏“天子七庙”之说应主要来自儒家思想。但秦王朝已经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三十四年(前213)两次分别否决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封子弟功臣”的劝谏,即此时的秦王朝已经废除诸侯之制。所以,此次庙议是在秦朝已全然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二世与群臣最终仅截取“天子七庙”之名,诸候、大夫之庙则因郡县体制被废弃。这是先秦以来宗庙制度发展的重要变革,也应当是贾谊批判二世“坏宗庙”所包括的内容。这亦与西汉中后期兴起的“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6]3079不同。
后半部分就是在“天子七庙”的理论指导下群臣给出的具体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奏议中“所置凡七庙”,学者认识有分歧,一说此七庙包括始皇庙:
此时所立皇帝“七庙”中,除了秦始皇庙和秦襄公庙外,其他五庙极有可能是秦始皇以前五代祖先宗庙。秦始皇庙作为秦皇帝宗庙始祖庙,世世不毁。其余六庙将随世数的递进,亲尽后依次迁毁。[7][注]相近观点还参见范云飞《从新出秦简刊秦汉的地方庙制——关于“行庙”的再思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40,2016-05-03。
但此说与二世“尊始皇庙”之主旨难以契合,将始皇庙列为七庙之末,即使作为“帝者祖庙”也未尽尊崇之义。还有学者认为,所置七庙与始皇庙分属两个序列,其说可参:
“始皇庙”作为二世的父庙,规格已经够高了,如欲再增,只有将始皇庙升格为天子“祖庙”,由天子“独奉酌祠”,而不再祭祠襄公以下诸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的诸庙,合并为“七庙”,由“群臣以礼进祠”,从而使始皇庙成为秦帝国第一代祖庙。这样,既符合“天子七庙,虽万世世不轶毁”的古礼,又适合二世推崇始皇的现实需要。秦国的宗庙系统经此重新编组,就形成一个新形态的国庙系统。[注]参见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第188页;具体标点改动还参见同页注释。相近观点又见韩兆琦:《史记笺证》,第500页。张益群《秦—西汉时期皇帝宗庙制度变革及其政治文化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页。
从上下文意来看,后说将此次庙议分作先王“七庙”系统与“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系统应更符合事实。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再来理解此次庙制改革,便可以有新的认识。二世“议尊始皇庙”与秦始皇“议帝号”一样,对秦帝国皇帝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庙议确立以始皇庙为秦王朝皇帝祖庙,不仅是二世自身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举措,客观上也使得宗庙系统完成了从“天子—诸侯”向“皇帝—郡县”的彻底转变。
此处还需辨析出土文献中出现的“泰上皇”与“泰上皇庙”问题。近年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出现“泰上皇庙”的表述:“泰上皇祠庙在诸县道者……325/0055(2)-3”[8]202。有学者将之与汉高祖刘邦在其父去世后“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6]68相联系,认为“秦始皇、汉高祖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秦朝以县道为单位立庙,西汉则是以郡、王国为单位”[9]。这是较为合理的推断,对于我们理解贾谊“坏宗庙”的认识亦有启发。
整理小组认为“此令称‘泰上皇’,后又有‘二年’纪年,其抄写年代必不早于秦二世二年”[8]226。其所谓“二年”纪年,实际是指同书所载“泰上皇令”“二年曰复用”(简329-331)之令文,但学者也指出此“二年”应为秦王政二年[10]。笔者认为后种意见更为合理。又由于此简下端字迹漫漶,所以详细内容无由得知。
二世元年庙议之后太上皇庙应该已经并入襄公以下迭毁过后的七庙之中,其地位在二世时应有相应调整。下面我们可以结合秦史中皇帝神性的抬升与西汉太上皇庙的安排两个层面分析此说的合理性。
有学者据里耶秦简“更名木方”中“泰上观献曰皇帝[观献][注]释文参考游逸飞《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选释》,武汉大学简帛中心:《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天帝观献曰皇帝[观献]”以及里耶简中令史的“行庙”记录,并参考岳麓秦简的材料,认为:
里耶“秦更名方”还记载了皇帝祭祀承袭了天帝祭祀的仪式。意味着皇帝等于天帝,秦始皇帝被充分神格化,泰上皇亦然。岳麓秦简与里耶秦简两相参证,可推测迁陵县的泰上皇庙使用的祭祀仪式是原先天帝祠庙所使用的祭祀仪式。我们甚至可进而推测秦始皇在迁陵县立的不只是泰上皇庙,可能还有自己的始皇帝庙。秦始皇在活着的时候就在郡县广立始皇庙,让地方官吏以天帝祭祀仪式祭祀始皇帝他自己。原因无他——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皇帝的神权无远弗届,直至天边,这似乎就是秦代普立郡县宗庙的真谛。[11]
从上文分析来看,二世既然下诏“议尊始皇庙”,则秦始皇生前自行立庙的可能性不大。里耶秦简记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相合,有学者指出“‘追尊’使用‘皇’而非‘帝’,既与‘皇帝’可相参照,又与‘皇’较‘帝’为高,却又较‘帝’号虚化,可相联系”[12]。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同时“泰上观献曰皇帝”“天帝观献曰皇帝”两条与“庄王为泰上皇”同时出现于更名木方,也说明皇帝与泰上皇之不同。
此外,皇帝得到等同“泰上”“天帝”的待遇,实际后者也是一种虚化的神权符号,这与将“泰上”冠于“皇”字之前有可模拟之处,更进一步证明秦始皇时庄襄王之宗庙待遇不太可能是“原先天帝所使用的祭祀仪式”。而且,在秦始皇时代,伴随着始皇个人神性的抬升,先王“宗庙之灵”开始逐渐让位于始皇“陛下神灵”,这可以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依据。有学者曾指出秦始皇非常重视“宗庙”在其并天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3],但笔者注意到,李斯等人在与始皇的奏对中实际已经有将天下一统是“赖宗庙之灵”转化为“赖陛下神灵一统”的趋势,这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的两次廷议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始皇曰:“……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廷尉议是。”[1]235-239
从上述表述来看,尽管秦始皇两次提及“赖宗庙”,但李斯奏对则是“赖陛下神灵一统”,那么他是在奏议中有意抬高始皇个人的神圣性,其后,始皇三十四年周青臣亦有“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1]254的相近表述。所以,从李斯到周青臣,再到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始皇“陛下神灵”应是逐渐抬升的。所以,“先王”与“皇帝”之间的张力实际在始皇时代已有所显现。
所以,学者所提示“秦更名方进一步揭示皇帝神格化的内涵:皇帝不仅是天下的统治者,更是可以取代‘泰上’、‘天帝’的神明”[14]等信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实际皇帝名号的神格化应与李斯奏对中所谓“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密切相关,由“宗庙之灵”到“陛下神灵”正体现出这种神格化的演变趋势。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就如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一样,他们作为帝国的开创者,既需要追溯自身的来路,同时又必须凸显开国始、太祖的神圣性。所以,始皇此举更可能是先推尊其父为太上皇,这样就使得始皇帝与秦“先王”之间有了过渡或缓冲,但太上皇又不同于真正的“皇帝”,所以就更可能是从“宗庙之灵”转向“陛下神灵”的一个过渡阶段,其地位应处在先王与皇帝之间。
始皇死后,二世的合法性实际来自“遗诏”和“宗庙事”,也就是兔子山诏书开篇所宣称的内容。但他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与始皇称帝时已完全不同,他是在其父已然称帝之后即位,所以,如何处理始皇的宗庙地位就成为其即位后的头等大事。秦二世只有通过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以及“天子独奉酌祠始皇庙”才能实现“二世皇帝”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还有,从上文分析来看,秦更名木方中“泰上”“天帝”与“皇帝”的对应已体现“陛下神灵”的发展,二世元年庙议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宗庙系统中抬升始皇作为帝者之祖的神性。所以,二世时“泰上皇庙”理应归入“先王七庙”,以示“帝者祖庙”的区别。
尽管目前缺乏更为详细和直接的证据,但我们对照西汉初年的历史,也能为上述论点提供佐证。观察汉初历史,我们发现,不唯泰上皇之名号与立庙一事秦与汉相同,汉惠帝在高祖下葬后同样也与群臣有过议尊高祖庙的举动: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1]392
惠帝与群臣议尊高祖庙的地点值得注意。《汉书》同叙此事,作“反至太上皇庙”。这是因为彼时高祖尚未确定庙号,汉家唯一的宗庙即是刘邦所立太上皇庙,所以在太上皇庙为刘邦议庙号是合适的。
但秦二世诏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的现实情况与汉不同[注]顾颉刚曾言“汉初立庙本无计划”。即因刘邦出身平民,汉惠帝也无需如秦二世一般需要处理庞大的先王宗庙问题。参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八册《汤山小记(四)》“韦玄成、匡衡等请庙、寝、园以亲尽迭毁与其波折”,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八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页。,因为秦王朝统一之前还有长达五六百年的“先王”时代[注]秦自襄公始封诸侯至秦二世而亡,《秦始皇本纪》所附《秦记》与《秦本纪》《六国年表》所载年数不同。参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364页。相关辨析又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32页。。同理,秦二世与群臣为始皇议庙必然要在统一之前历代先王的基础上进行,这也就是群臣为何提出“自襄公以下轶毁”的问题。二世时所面临的太上皇仅是秦历代先王中与始皇血缘关系最近的一位,在他即位之时,太上皇这一名号的象征意味应大大弱化了。所以,秦二世所面对的问题与西汉初年刘氏宗庙除刘邦外仅存太上皇庙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汉中后期进行宗庙迭毁时,太上皇庙也是亲尽宜毁的对象。
惠帝初年,其与群臣所面临的仅是从未践天子位的“太上皇”,复因当时“天下初定,远方未宾”,所以才“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6]3116。但到元、成时期,就出现宗庙系统过于庞杂的问题: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6]3115
所以,汉廷也面临宗庙的取舍,韦玄成等人曾上奏:
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注]《汉书》卷73《韦玄成传》,第3118页。西汉中后期宗庙制度改革参见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27~446页。
如上所述,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高帝庙作为“帝者太祖之庙”,“太上皇”庙“宜毁”。反观秦朝,秦“先王”祭祀系统也极为庞大,所以秦廷群臣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安排秦“先王”宗庙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尊始皇庙”。他们的方案也是尊始皇帝庙为“帝者祖庙”,但由于先王系统过于庞大,肯定不能全部毁弃,从而找到“自襄公以下迭毁”的方案,但迭毁之后的先王祭祀礼仪必然会因始皇庙作为“帝者祖庙”而有所区别。
对照西汉宗庙制度的发展,我们认为,秦二世与群臣所面临的情况较汉惠帝时更为复杂。既要在秦先王宗庙系统的基础上“议尊始皇庙”,同时必须对先王系统进行改造,以突出始皇庙作为“帝者祖庙”的特殊地位。因此,二世与群臣对宗庙系统的改造应如钱杭等学者所说,分为先王“七庙”与始皇“帝者祖庙”两大系统。
至于秦始皇时所立之太上皇庙,尽管目前缺乏直接材料,但从二世元年的庙议,以及皇帝名号逐渐神圣化的趋势,乃至西汉宗庙迭毁时亦毁太上皇庙的举动,都能说明太上皇及太上皇庙在秦二世时期的地位应伴随着始皇地位的抬升而有所下降。所以,此次庙议实际是在宗庙系统中实现从秦国向秦帝国的转型:从纵向时间线来看,秦二世迭毁先王庙,使得先王宗庙与帝者祖庙形成两个序列,从而实现始皇庙作为帝者祖庙之尊崇;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及空间格局来看,秦二世进一步巩固了剔除诸侯之后的“皇帝-郡县”的全国宗庙系统,而且仅仅皇帝有资格“奉酌祠始皇庙”,而地方郡县对始皇庙之祠祭则完全与血缘或宗亲无关。天子、诸侯、大夫的庙制序列亦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这次宗庙系统的改革最终实现了宗庙制度与秦“皇帝—郡县”体制的真正适配。
三、“过秦”——从“尊始皇庙”到“坏宗庙”
秦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实际包括先王“七庙”与始皇“帝者祖庙”两个系统。同为二世元年的兔子山诏书在开篇也有“宗庙吏(事)”的记载,上文所引邬文玲、陈伟等学者已指出可能与“议尊始皇庙”有关,笔者认为此说是合理的[注]除前文注释所引,王子今也注意到两种文献之间的联系,并认为“所谓‘宗庙事’,似乎宜于结合较宽广的政治崇拜传统和国家权威信仰的意识背景予以理解”。参见王子今《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载于《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第82页。确实如此,始皇庙地位之“尊”,正在于其与“先王庙”之间的区分。。同时,贾谊《过秦论》所谓“坏宗庙”实际也应来源于此,只不过其所侧重是在秦先王“七庙”之迭毁。实际上,秦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之内涵非常丰富,如上所论,群臣必须在合理安排先王诸庙的基础上为秦始皇这位秦朝皇帝之祖尊立宗庙,这就使得兔子山诏书之“宗庙事”其实也应该包含上述两层含义。当然,诏书明显偏重“尊始皇庙”而确立二世自身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而贾谊之批判二世“坏宗庙”则偏重二世对先王宗庙之迭毁。因此,二者所论均为《秦始皇本纪》所载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事。
需要说明的是,二世在诏书中宣扬之“今宗庙吏(事)及箸(书)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与贾谊《过秦论》所谓“坏宗庙”之批判大相径庭。我们以为,贾谊的批判实与其所处之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环境有关。
《过秦论》《赵正书》与兔子山二世元年诏书这三份文本存在微妙的联系。我们看到,前两者的相关表述实际均来源于后者。“与民更始”一语就极为明显,我们在叙述秦二世时期历史的传世文献中很少见到这一语汇。即使存在于《过秦论》中,历史上诸多学者也多认为当依徐广之说进行删节。
但从兔子山诏书原文来看,《赵正书》与《过秦论》这两种西汉初年的文本就直接如实引用了二世诏书,当然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各自对二世的批判。除此之外,《赵正书》中的“燔其律令”与兔子山诏书中的“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可以相互联系。同时,兔子山诏书中“宗庙吏(事)”与《赵正书》“灭其先人”以及《过秦论》“坏宗庙”亦可对读。由此可知,《赵正书》与《过秦论》保留了某些历史细节,他们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司马迁《史记》成书以前,因此其所保存之吉光片羽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据《史记》记载,贾谊入仕以前即“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且被廷尉吴公“召置门下,甚幸爱”[1]2491。所以,其青年时代之读书、游历应主要在惠帝、高后时期,则《赵正书》等文献肯定包含在“诸子百家”之中,或者说至少此种对秦始皇以及二世时期的历史叙述以贾谊之博学是应当熟知的,而且彼时去秦亡不到三十年,二世诏书必然世所习知。此外,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吴公的身份,他“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因此对秦王朝的统治实况应较为了解,贾谊在其门下,日常问对中必然对秦朝史实有所涉及[注]傅乐成即认为贾谊应当深受吴公影响,“贾谊受知于廷尉吴公,而吴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贾谊虽非吴公弟子,但受吴的影响,则可以想见。故谊少时虽以能诵诗书属文见称,然亦‘颇通诸家之书’,且明习法令,熟谙制度”。参见所著《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49页。。因此,贾谊《过秦论》等政论思想与其被吴公“召置门下”的经历可能有密切关联。如此,我们再来看“坏宗庙,与民更始”的具体语境:
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注]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16页。此处标点略作改动。
此处节引之首段是在批判秦始皇“王天下”而不能改弦更张,其中就有对其尽废分封的不满。“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是较为明显的表述。“殷周之迹”与“三王建天下”实际也属同类。秦始皇三十四年咸阳宫之议,博士淳于越即有“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的表述,即是劝谏始皇分封。自然,贾谊此处更深层次的涵义当指安抚臣民使不为祸乱,但其对封建的态度则无疑是肯定的。
接下来“今秦二世立”一段,实际是贾谊“替秦二世设计了一个救亡自存之道”[15]。但事实上,秦二世也在“缟素”之时进行了一番改作,即兔子山元年诏书所言宗庙、律令、解除故罪等方面。所以,贾谊此段的逻辑是以自己的立论批判二世的政策。
在这样的文本情境下,我们看到在“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之后紧接“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两句,则是认为二世应该复行封建,对功臣、宗亲应当“裂地”“建国”。
王夫之《读通鉴论》即指出贾谊此论之背景:“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16]萧公权在探讨贾谊思想时也曾引用这两句话,认为“贾生对于始皇之郡县制亦不能同情”,其又举“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并且进行了总结——“贾生此论欲兼用封建、郡国之长,盖亦根据汉代之实践经验以立言,又非纯惩秦弊矣”[注]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9页。王兴国所著《贾谊评传》也提到“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贾谊“把秦二世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参见所著《贾谊评传附陆贾晁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确实如此,贾谊认为封建制也必须顺应时势变化而进行灵活调整,他在劝谏文帝调整诸侯封国时就曾举高祖刘邦灭异姓功臣而立诸子的做法:“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为不可,故蔪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6]2260-2261此外,我们从引文第三段中也可看到“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表述,实际分别可以对应宗室与忠臣,亦能凸显贾谊对秦统一之后实行彻底的郡县制的批判。汉初诸帝因无先王问题,所以对宗庙的设立并无统一规划。高祖时令诸侯王立太上皇庙,惠帝时亦令郡国诸侯立高祖庙。所以贾谊所处时代汉王朝的宗庙系统应为“皇帝—诸侯/郡县”模式。诸侯王国亦各有宗庙。
反观秦二世元年庙议结果,其不仅迭毁先王庙,而且在继续始皇所确立之郡县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的新的皇帝宗庙系统。不难推想,如果秦没有二世覆亡,则秦始皇时在郡县所设太上皇庙亦会因始皇庙作为帝者祖庙的影响而逐渐式微,因为本质上太上皇还是属于先王一系,其过渡性在始皇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二世时因其父皇帝称号之已然确立,其现实意义和价值当有所削减。同时,李斯“赖陛下之神灵一统”的表述既有迎合始皇之意,同时还为其下文“皆置郡县”“置诸侯不便”提供法理依据。因为皇帝神性及其地位之抬升,又参以相对完备的官僚制系统,诸侯就彻底被排除,西周以来的宗法分封亦完全瓦解。“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这一先秦宗庙系统就仅保留“天子七庙”。所以,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的举措在身处汉文帝时代的贾谊看来,一是迭毁先王庙定然会对先祖有所不敬[注]明人徐孚远《史记测议》在“所置凡七庙”句下将二世迭毁先王宗庙、独祭始皇庙的行为与东晋桓玄相对照,认为二世因不祭其祖而亡国灭身——“桓玄祭不及祖,晋人以为讥。今秦二世亦不及其祖,自身而失之,二事同也”。参见陈子龙、徐孚远辑:《史记测议》卷6《秦始皇本纪》,吴平等编《〈史记〉研究文献辑刊》(第三册),影印明崇祯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上栏。,二是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后形成的即是从皇帝到郡县的宗庙体系,因不复行封建,而与汉初诸侯、郡国广立宗庙的体制不同。而且亦无“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注]《汉书》卷5《景帝纪》,第138页。颜师古引张晏说,“王及列侯岁时迁使诣京师侍祠助祭”。这种保持皇帝与诸侯王、列侯血缘认同的举措,所以此宗庙之制既不合汉人所理解的殷、周之制,亦有违西汉初年的宗庙体制。

至于“坏其社稷”,则是指对功臣的屠戮,亦即《赵正书》的核心议题,在李斯这段话之前,子婴在劝谏二世时曾列举赵、燕、齐三王残杀忠臣、重用佞臣因而亡国之事,随后有一句总结——“是皆大臣之谋,而社稷之神零福也”,此处实际是将社稷与大臣(忠臣)建立联系。因而,《赵正书》中“坏社稷”实指二世不听子婴、李斯等进谏而屠戮功臣,从而与燕、赵、齐三王一样自毁社稷。所以,兔子山诏书“宗庙事”、《赵正书》“灭其先人”与《过秦论》“坏宗庙”这些表述都提示我们,二世元年的这场庙议对秦末汉初的历史曾有过较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文本都产于生在《史记》成书以前。而且与《史记》相比,《新书》的叙述重心不在二世得位之正与不正[注]陈侃理曾指出“贾谊《过秦论》也不见对二世即位的正当性有何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其立论大致以二世合法即位为基础,看不出‘胡亥不当立’的意识。贾谊在文帝之初年仅十八岁,应是生于刘邦称帝以后;出生地洛阳在战国末已属秦,当地人在反秦战争中未见突出表现。他的言论,应当反映了反秦楚人以外存在的另一种历史记忆”。详参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而在于他不听谏言、不改始皇之道,这一点与《赵正书》的叙述逻辑比较近似。又从他们三者都保留有“与黔首(天下、民)更始”这一语汇,我们可以推断,《赵正书》与《过秦论》应该都是以秦王朝当时的官方正式文告(即诏书)为基本叙事框架而进行立论,尽管他们对二世的举动基本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但却也为我们理解秦王朝末年的一些历史事实提供了帮助。
综上所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如实记录了二世元年庙议的具体细节,随后兔子山诏书则是秦廷向全体郡县颁布这一宗庙改革成果,而《赵正书》与《过秦论》对二世宗庙改革进行批判,实际是为各自观点服务,前者侧重二世不听劝谏、诛戮功臣宗族,后者则是批判二世不行封建、不改始皇之道。所以,我们在理解《赵正书》作者及贾谊对二世宗庙改革的批判时,需要跳出《史记》所载二世阴谋篡位的逻辑(因为《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相关记载都将二世的诸多行为与其阴谋篡位相联系),回到《史记》以前去认识汉初文本对二世政策的解读,这样对秦末历史或许会有更丰富和多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