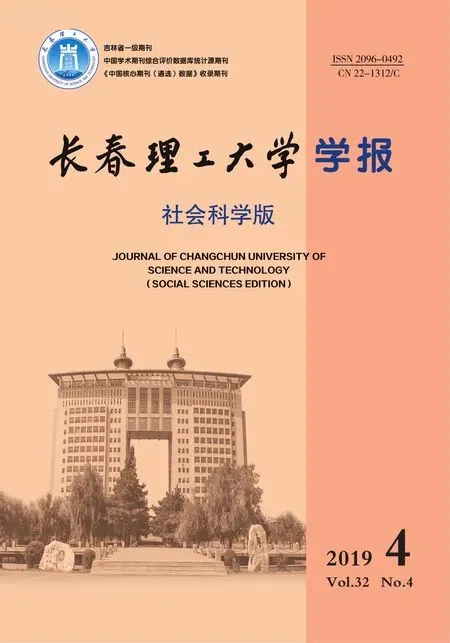黎锦扬小说《花鼓歌》的空间政治解读
李媛媛,祝远德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小说《花鼓歌》是湖南“黎氏八骏”之一的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1915-2018)的代表作,1957年一经出版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其中一部分经稍许修改后拟名为《守旧之人》于同年在《纽约客》杂志发表,黎锦扬因此成为第一位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的华裔作家。次年小说被音乐剧大师罗杰斯和汉默斯坦改编成同名音乐剧于百老汇上演,在持续的热度中小说于1961年被环球电影公司改编为同名电影,并开创了亚裔演员在美国银幕的第一代演艺事业。2001年,《花鼓歌》在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重新改编下再次在百老汇上演。舞台和荧屏由此成为小说在文学空间之外的延伸。
族裔小说的主题往往围绕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展开,在冲突中争取空间生存环境的抗争是对种族空间政治的隐喻性体现。《花鼓歌》描绘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生动图景,和传统黑人族裔小说不同的是,小说中并不存在殖民和奴役的成分,“是一部有关生活琐碎的小说”[1]。受中国社会“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影响,黎锦扬并没有大力着墨描写文化交锋的火花和异域生存的沉重,而是用轻快诙谐的笔调带出华人移民在唐人街的活动日常。因此,“《花鼓歌》的喜剧基调也让视族裔斗争为严肃大事的华裔批评家们无法接受”[2]。尽管如此,黎锦扬玩味个性的写作中还是夹杂着其身为华人的异乡生活经历的感悟。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3]。小说主人公们在美国的空间生存体验折射出作为少数族裔中更少数的华人无论是在活动圈、工作前景、社会地位还是发展空间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流或强势集团构想的空间秩序的主导。
一、唐人街:“空间表征”体现的空间政治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空间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结合日常生活体验、种族、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性别等多种因素,提出了包含“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环节的“空间三一论”,以此阐释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其中“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及其施行的秩序相联系”[3]。象征着文化大熔炉的美国生活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其中弱势种族群体的利益往往与强势种族构建的“空间表征”规约相悖,后者把前者引入并限制在其构想的空间秩序中。《花鼓歌》中的主人公63岁的华人移民王戚扬和他的家人生活的华人聚居圈唐人街便是“空间表征”的产物。历史上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在旧金山,小说的背景地点就设置在这里。现实中的旧金山唐人街于1850年前后形成,美国西进运动影响下的“淘金热”和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吸引了大批华工背离故土远渡重洋。19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铁路的全线竣工、西部金矿的逐渐枯竭和暴力排华事件的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搬进唐人街生活。华人高密度聚集的唐人街的存在反映了白人主流社会对“空间表征”的规划和设计,作为《纽约客》杂志的首篇华裔小说,《花鼓歌》揭示了历史上这一特殊空间的存在。
“唐人街有一条非正式的边界线,东边从布什大街起到西边的拉尔金大街上”,“南边从布什大街到百老汇大街”[4]146,在王戚扬的眼中,“超过布什大街以外的地方就不属于唐人街,而是外国领土了”[4]5。这条“非正式的边界线”既是把白人区和华人区隔离开的物理线,也是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特点的心理线,它如同隐形的篱笆,成功地在白人和华人之间筑起一道心理防线并将他们区隔开来。物理空间的区隔使两者产生心理和精神隔膜,难以近距离接触彼此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华人聚居区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华人数量增多的问题,而是“在唐人街之外,没有其他住所会收留华人”[5]。由此可见,“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3]。“唐人街”是由于种族歧视和白人的传统偏见及经济因素造成的,其空间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折射着白人空间权力形成的历史。
被美国主流社会隔离下的唐人街就像一座孤立的“监狱”,受到强势群体空间表征的监管和规训,华人在空间区隔中自觉遵守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王戚扬已故妻子的妹妹谭太太就是自觉遵守这一空间秩序的“典范”。她主动参加成人学校公民班学习,“背诵着美国宪法的每一个单词”[4]31,法律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最强大武器,谭太太生活在主流社会的空间表征中,在等候移民局的审查中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高智“苦力”:空间实践的规训性和挑战性
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的另一环节“空间表征”通过“空间实践”建构,前者以话语性和意识形态性为特征牵引后者参与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空间实践”包含日常语境下可容行为的社会成规,在空间表征的规训下,社会成员的空间实践通常表现为规约性的空间行为,从而内化为强势群体构想的空间秩序,但也不排除部分成员对空间表征的质疑而表现出来的对规约的挑战和逾越。《花鼓歌》中在白人空间表征中生活的华人们,有的内化了白人空间表征,其空间实践服从于空间表征,有的意识到种族空间秩序的虚构性和社会建构性,因而对其发起挑战,以期重构社会空间秩序。王戚扬的儿子王大在加州大学读书时的好友张灵羽就是综合了这两个过程的例子,他既认同又质疑白人空间表征,表现为前期的驯从和后期的挑战。
张灵羽是典型的高智“苦力”,他在加州大学拿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却当了杂货店店员,“我的新职业既是我的自救,又是我们同胞的运气,就看我怎么看待它了”[4]21。主流文化所建构的空间秩序认为华人是先天低智不健全的,只能成为铁路工人、洗衣工、餐厅服务员等“苦力”,只有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才有资格从事脑力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甚嚣尘上的“黄祸论”和从1882年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排华法案形成了一次次排华浪潮,这使大批华人被迫退出能和白人产生竞争的行业领域。“华人移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白人的种族歧视话语强加给他们的改造,最终使他们在白人打造的秩序中确立了自己处于社会底层与边缘地位的身份”[6],于是,华人移民们习以为常地从事为主流社会可容的工作,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了他们社会空间的缺场,以至于华人弱势话语在主流舞台上群体失声并逐渐消音于历史进程中。政治学博士是“高智”的象征,即使在主流文化中也足以担任社会要职,然而华人的身份外衣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由此张灵羽便成了和普通华人无异的“苦力”。王大从加州大学学习了四年经济学之后试图找寻一个适合于他专业的工作,在奔波数周之后却发现自己无工可做,在放弃了经济学的学历加成之后王大找到了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小说还提到“有一位博士在渔人码头的餐馆洗盘子”[4]20。和张灵羽一样的华人知识分子乐天知命地接受白人规约下的空间秩序,在空间实践中驯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空间表征的规训,无疑是小说最大的讽刺。
尽管规训权力强大地掌控着社会运行,却并非万能到可以消除监狱式社会的一切反抗。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张灵羽很清楚,掌握着权力的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构建有利的空间表征,而这种空间表征无时无刻不在限制着华人的职业和身份。毕业之后的张灵羽选择去了洛杉矶,尽管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成为了杂货店店员,但他还是先于继续留在唐人街的同辈一步从而挣脱了唐人街的枷锁。经过了一两年的空间实践之后,张灵羽已经不满足于白人空间表征对于他的身份安排,开始对主流社会发起挑战。“我正在购买一家杂货店。一桩小生意,但我打算把它逐步做大”,“我现在是个杂货专家,有博士学位。十年之后,我要拥有一家超级市场,二十年后,我就会有一系列连锁店”[4]223。张灵羽的空间实践有意识地挑战白人通过构建空间表征所建立的白人商业秩序,努力建构华人主体性的表征空间。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分界、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7]。张灵羽运用其所学的政治学知识建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其空间实践体现着他对白人所设定的空间表征的挑战和对定义自身的主体性的表征空间的重新设计。
三、“近北区”和“湘雅茶楼”:“表征空间”的阐释性和逾越性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中,“表征空间”属于社会成员的生活空间,展现个体成员在“空间表征”影响下的“空间实践”效果,因此也是受控空间和被动体验的空间。空间表征通过话语和权力制约表征空间,个体的表征空间在阐释空间表征的同时也可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挑战并逾越空间表征,以此表达其对于强势集团的空间政治立场。这种逾越性通过表征空间的偏离和缺场展现,由此表征空间呈现出依从或反抗空间表征的形态。
表征空间“覆盖物理空间,象征性使用物体”[3]。《花鼓歌》通过“近北区”阐释了权力空间表征和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表征空间。“近北区”即小说中提到的格兰大道北段的街道,如下图所示:

椭圆形状内的区域即为“近北区”,也就是靠近外国人住宅区的唐人街。王戚扬对于近北区的态度是嫌恶的,“走在格兰大道的北端,他并不觉得舒畅,因为那里散发着浓烈的腥臭味,令他作呕”[4]6。脏乱差是历史上白人群体对于华人聚居区的刻板印象,然而这种看似专属唐人街或华人聚居区的“混乱”与“肮脏”却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白人的空间逼迫下他们不得不蜷缩在唐人街这一狭小的区域中形成的。唐人街的“近北区”由于其更加靠近白人生活区的地理位置因而比其他区域更加强烈地受到白人空间表征的制约,从而表现出比唐人街其他区域更加窘迫的表征空间,这直接决定了其狭小潮湿和腥臭的面貌。这就是生活在白人的表征空间里普通华人移民的生存现状,在唐人街本来就狭小的生活空间中,“近北区”的华人居民还进一步受到白人的空间狭迫,如此表征空间阐释的是主流社会所建立的人种差别的空间表征。
但是,除了表依从的阐释性之外,表征空间还具有反抗特征的逾越性,它通过个体表征空间的偏离和缺场展现,这种缺场是主体性的人为选择的结果。表征空间与个体成员生活居住的具体物理空间相连,进入个体生活的物理空间具有精神和社会特质。小说中的“湘雅茶楼”便是华人个体偏离白人空间表征的表征空间的最好阐释。茶楼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空间,湘雅茶楼位于一个不知名的小弄巷里,是王大和张灵羽享受地道粤菜的所在。“如果没有人带路,美国游客根本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而且鲜见有美国人被带到那里去”。[4]19这里的茶楼是存在主义式的,是个体华人逃离主流社会强大空间表征的喘息的一隅,是可容他们建构主体的物理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8]。湘雅茶楼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确定的空间来安放并维持华人秉性,体现了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人的选择和存在的超越性,是个体华人偏离和挑战白人空间秩序的表征空间。
表征空间的逾越性还表现为主体性的社会生产缺场。王戚扬的儿子王大,28岁从加州大学毕业之后经过尝试最后只找到一份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这遭到王戚扬的强烈反对,“我不许你去做那份工作”,“我们家没有人可以去给别人洗盘子”[4]14,作为华人移民的上层代表,王戚扬希望王大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四年空间实践到最后可以偏离主流社会的空间表征而建立对应自己知识背景的表征空间。事与愿违的结果让王戚扬做出继续供王大念医学院的空间尝试,这是设计定义华人主体性表征空间的内在需求,目的在于超越白人为华人设定的表征空间,从而建立华人真正的表征空间。王大在白人空间表征下的规约性的社会生产实践被中断,完成了社会空间不在场的人为选择。
空间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包含历史、民族、政治、文化、宗教等多重要素。《花鼓歌》的空间关系表征着种族政治关系。作为成功打入欧美文艺市场的“‘急先锋’式的先驱人物”[9],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以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为参照,用英语书写中国人题材,描写了身处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华人移民在白人空间表征下的空间实践。在《花鼓歌》所描述的唐人街权力化的空间表征中,华人知识分子经历了从规训性的空间实践到对白人空间秩序发起挑战,同时,在普通华人移民被狭迫的表征空间中,也有对强势集团主导的表征空间的反抗。黎锦扬通过描写小说主人公们在美国的空间生存体验,揭示出华人移民无论是在活动圈、发展前景还是生活空间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群体构想的空间秩序的主导。黎锦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华人主题叙事那样停留在对华人刻板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描述了华人移民为了建立自己的主体表征空间所进行的迂回尝试,为华人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正名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