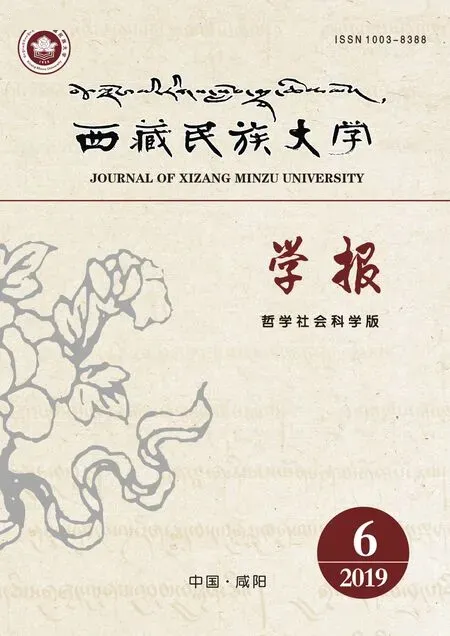乾隆年间“成都将军”之职能及对康藏地区的影响
刘波,何 达,吴艾坪
(1.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0;2.西南民族大学科技处 四川成都 610040;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1)
一、引言
近年来,学术界对研究乾隆年间清廷治理川边藏区的论文与专著各有一些,研究范围较广。涉及清廷与地方土司之间的关系、战后政治秩序的重构、经济的恢复、相关人物传记等方面①。其中,彭陟焱发表的《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析》《清代嘉绒地区“厅”的设置及其影响》《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3篇文章,从地域的角度对清廷大小金川战役后的重建工作进行了概括与梳理②;黄清华的《〈御制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考析》《〈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解析》两篇文章从金川地区考古碑文的角度,对碑文中涉及傅恒、阿尔泰、温福、阿桂四位清军将领的事迹进行了梳理,并佐证了《清史稿》《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金川纪略》《圣武记》《金川琐记》《绥靖屯志》等典籍关于清乾隆大小金川之役的记载③;陈潘在《沙济富察氏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一文中也从人物传记的角度对富察氏的几任成都将军相关职能进行了概述④;定宜庄在《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一文中,通过将成都将军与清代其他各处驻防将军进行对比,分析了成都将军的相关职能特点⑤。
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史料和档案的记载,分析整理清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创设的起因与目的,梳理归纳成都将军的地位与职权,论证总结成都将军运用其相关职能在康藏地区的作用及影响。
二、“成都将军”创设的起因与目的
乾隆四十一年初(1776),前后耗时近三十年的大、小金川战役最终以清廷的胜利告终,大战结束后,清廷设立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简称成都将军),统辖川边藏地。成都将军的设立是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延续与发展,是应清廷完成大小金川战役后对川边的统一和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需要而产生的。
(一)巩固大小金川战役的成果,恢复康藏地区社会生产
清乾隆一朝两次平定金川战役,前后耗时数年。第一次金川战役发生在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1749);第二次金川战役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耗资八千余万两⑥,投入数以万计的多省官兵参战⑦,历经万难才换回了战役的最终胜利。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清廷在战争胜利前夕就开始筹划设立成都将军。根据《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八十九,乾隆四十年八月癸卯条记载:“将来经久恒规,自当以屯田为妥。两金川地面,可耕之土甚多,而绿营兵众,屯种又其所习。今新疆各处耕屯,俱已收实效。阿桂向为伊犁将军,屯政乃所深悉,将来金川营务,自当酌仿而行。至成都满兵,必须移驻打箭炉,该处控制诸番,远抚西藏,实为扼要之地,并须添设将军镇守。”从中可以看出,清廷在大小金川完全平叛之前,就根据康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距京畿遥远等实际因素,并借鉴在完成对新疆统一后设置的伊犁将军的驻防模式,拟在打箭炉设立将军,驻防绿营和满兵,并实行屯田,从而为在大战结束后金川地区的相关事宜进行统筹安排,进一步稳固战役成果,恢复康藏地区的社会生产。
经过成都将军与四川总督的经营,受战争影响较大的两金川地区战后恢复事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壬子条记载:“成都将军特成额、四川总督文绶、提督明亮奏:两金川屯务,前经奏明,酌存绿营兵四千名,并拨留屯练二百名,给地耕种。兹各屯透雨沾足,督饬各兵,勤力耘耔,所有拨留种地屯练。及调赴各屯之携眷屯兵。及各降番民户,俱相率力作。以冀有秋……又已半载。番地宁谧,差防无误。”《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九十二,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已丑条记载:“……八年以来,该降番等久沐深恩,各安耕作,遇有差遣,莫不奋勉出力,无异内地民人。恳准改土为屯,除去降番名目。又称降番等生齿日繁,男妇约计九千余名口。”又有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戊申条的《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七述:“调任四川总督保宁奏:金川屯务,经前任将军、参赞等丈出地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亩,节年屯员,广为招徕,穑事日兴,荒土尽辟。除原丈地已垦外,多垦地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亩,仍照例每户给三十亩,并限六年升科。查各屯官役喇嘛人等,及岁修桥梁等项,需粮九百余石,俟升科后,统计新旧地亩,并汉牛一屯。每年共应征粮一千二十一石零,各项供支,自可有盈无绌。”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自设立成都将军以来,川康藏地区的经济恢复呈现良好趋势,战后政治局势得到了稳固,该地区人口增加、人民生产生活步入正轨,这也达到了最初清廷设立成都将军的预期目的。
(二)“节制绿营,控驭番地”
大、小金川地广人稀,内连川省、外接西藏,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两金川战役结束后,如上所引清廷在该地区实行改土为屯政策,调遣大量绿营兵至该地执行屯种,恢复生产。“成都将军”作为清廷最后一个设立、同时也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将军级驻防,其创设之意皆在“节制绿营,控驭番地”。
大战结束后,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正式颁布诏书设立成都将军。根据《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己卯条记载:“前经军机大臣议覆,定西将军阿桂,筹办善后事宜案内。令于大功告成后,特设成都将军一员,驻防雅州,统兵镇守节制绿营,并于两金川之地安设营汛移驻提镇,以资控驭。今两金川全境荡平,即应驻设所有成都将军员缺,即著明亮补授移成都满兵一千至雅州,随将军驻守。其原设之成都副都统仍留驻省城分兵防守,俟二三年后再令将军驻防成都,副都统移驻雅州,永资绥靖边围之益。所有移驻满兵事宜,及两金川设镇安营诸事,统令阿桂、会同新设将军及该督等、妥议具奏……现授明亮为成都将军,移驻雅州节制,而提督桂林,则令其移驻美诺。”
清廷对于成都将军在设立后所产生的影响寄托了重大期望,乾隆帝曾颁布诏令对成都将军设立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条记载:“命议成都将军统辖番地事宜。谕军机大臣曰:昨授明亮为成都将军,节制绿营,控驭番地,已明降谕旨矣,该处所以设将军之意……今费五年之力,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始能将两金川削平。扫穴俘渠用申国威而肃法纪,兹议于其地安营设汛移提镇大员,统兵驻守,并添设将军,驻边弹压。固足以震慑诸番但所设之将军。”
从乾隆帝对成都将军颁布的这条诏令可以看出,作为清廷最后一处设立的将军级驻防,成都将军拥有相对于其他驻地将军而言有更大的权力,如节制绿营,管理“番地”文武等。清廷也通过赋予成都将军相应职能弥补了其他驻防将军所具有的缺点,其中节制绿营是成都将军最明显的特点。根据《清通典》卷七十二记载:“成都将军标下绿营官兵,中军副将一人、左营都司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兵五百名、右营守备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兵五百名。”⑧
最开始清廷以八旗兵分驻各省要地,称为“驻防”。顺治元年(1644),《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八月甲申条:“上以将迁都燕京分命何洛会等统兵镇守盛京等处,以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左翼,以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统之右翼,以正红旗梅勒章京硕詹统之。八旗,每旗满洲协领一员,章京四员,蒙古汉军章京各一员,驻防盛京。”
随后陆续在各省险要之因时制宜地增派八旗兵分驻,按驻地的性质、兵员的数量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不同级别的将领,统率所属旗兵。将军是八旗驻防的最高统帅,驻地多在省会城市。经过清前期的发展,至乾隆时期,全国共设驻防将军13名,成都将军是乾隆朝设置的最后一任驻防将军。各地驻防将军所统领的军队仅限于八旗满兵,绿营一直属于总督所辖。“绿营规制,始自前明。清顺治初,天下已定,始建各省营制。绿营之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绿营隶禁旅者,惟京师五城巡捕营步兵。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⑨
纵观有清一代,清廷往往通过将八旗、绿营分制,从而达到使各地总督(节制绿营)、将军(节制八旗)相互牵制以防止军权独大的目的。但此法亦有缺陷,其导致针对某地平叛镇压等军事行动时军队归属问题复杂,军事效率低下,这同时也成为晚清因满兵战斗力下降,导致淮军、湘军崛起的原因之一。
论清廷赋予成都将军可节制绿营特权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三。其一,从宏观国内背景而言,平定大小金川战役后,相对于清廷入关前后设立各地驻防将军时期而言,无论是边疆危机还是统治内部矛盾都趋于缓和,这为此时给予一方驻地将军于绿营节制权提供了可能。其二,从中观地域因素而言,成都将军所辖地域乃西南边境,是为藏族、羌族、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相对于蒙古、索伦、锡伯等北方部落和内地汉族而言有较大差异。历朝历代对该地的控制较弱,统治基础薄弱,清廷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使其作战时的军事效率更为高效,让成都将军节制绿营,与满兵作战时的配合更加便利,不失为良策。其三,从微观个人因素而言,首任成都将军富察·明亮乃乾隆帝的内侄,图绘紫光阁,是清廷当时最为信任的将军之一。故派遣明亮为首任成都将军拥节制绿营之权是对其信任的。另外,参与平叛大小金川的兵丁大多由满蒙八旗和东北的部落兵丁所组成,可谓清廷“嫡系”,这也减少了对成都将军节制绿营的顾虑。
(三)衔接川边,远抚西藏
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⑩,有清一代八旗驻防主要分布于京畿附近及山海关至凉州一代的东部地区,辽阔的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尚属空白,成都将军的设置弥补了此不足,从而也促成了全国八旗驻防体系的建成。[1](P103)而成都将军及四川总督、总兵所率领的屯于康藏地区的部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一朝应对藏事的主力部队,其设置体现着清廷“该处距藏稍近,消息易通,可以就近调度”的战略构想。
廓尔喀之战⑪被称为乾隆帝“十全武功”的最后一功,成都将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十一,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癸丑条记载:“川省现有应办军需事务,李世杰驻守成都,距藏较远,于筹办一切,究恐鞭长莫及。省城现无应办要务,又有藩臬在省,足资照料。朕意打箭炉为兵丁粮饬出口之处,且地当适中,该督何不移往驻防?该处距藏稍近,消息易通,可以就近调度。而内地亦无难兼顾,且使口外人众,知有总督在彼,威势较大,更足以壮声援而资策应。”
乾隆五十四年(1789),藏廓双方签订协议,第一次廓尔喀战役结束。此役是清代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联合抵御廓尔喀入侵的一次阶段性胜利。但是,以巴忠和驻藏大臣雅满泰为首的各大臣因贪功对实际情况隐瞒不报,也为廓尔喀再次进犯西藏埋下了隐患。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以清廷和藏方未按约支付足够的银圆为由,出兵千余,再次进攻西藏,夺占聂拉木。成都将军成德率领屯于川边藏区的满兵、绿营、藏军,由打箭炉前往西藏。因作战不力随后免去鄂辉、成德之职,以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初八日,福康安奉旨与廓尔喀议和。
纵观两次清廷反击廓尔喀战役,共计三任成都将军(鄂辉、成德、奎林)参与其中。在反击廓尔喀战役期间,清廷的主力部队大多由屯驻于川边藏区的满兵、绿营、藏军组成,且在成都抽调了一部分兵力,及时开赴战场,对于战事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成都将军为能够及时支援西藏战事,维护西藏地区局势稳定,对西南边疆安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取得战役的胜利并不是由个别将军大臣一人之力所决定的,前往西藏剿灭廓尔喀的部队是由满、汉、藏、羌、彝等多民族构成,各族人民在战场上浴血杀敌,官民一心,体现出多民族对外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精神。另一方面,成都将军、四川总督与云南总督、驻藏大臣、朝廷钦差等各方力量协同合作,使得军事效率大为提升,粮草补给等后勤保障及时到位等也是该系列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清廷的这两次反击廓尔喀战役鲜活地体现了清廷设置成都将军以衔接川边,远抚西藏的战略构想。
三、“成都将军”之地位与职权:总理川边藏区大小事宜
成都将军一方面作为清廷全国八旗驻防体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最后一处将军级驻防以及西南地区唯一的驻防将军,它与其他驻防将军又有所不同。它是以成都将军以及各级别驻扎大臣为主干的,下辖文(民政)、武(军事)两套系统的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总归于成都将军和四川总督、提督管理。成都将军在其管理职能方面,兼顾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康藏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清廷设立成都将军后,在总结其他地方驻防将军与地方总督之间职权不明的基础上⑫,下诏:“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与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悉心妥议具奏至各土司内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等职。其每年轮班入觐时,应作何按次轮派,并听将军核定。”[2](P153-154)
此外,在经费和养廉方面,清廷给予成都将军较大空间。《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戊辰条记载:“各省将军,原定岁支养廉,及米豆草折银两,多寡悬殊,似宜均齐,以昭平允。除盛京将军,原支二千两,伊犁将军,原支三千两,两处事物较繁,自应照旧支给,其余各驻防将军,繁简相仿,请均以一千五百两为准。其新设成都将军,亦如之。”清廷在明确规定了成都将军与其余多地将军养廉相等的情况下,于一个月后即《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丙申补充道:“……今日据阿桂奏称:赏号一项,系沿川省之旧,不但将军参赞等各有赏号备用,即总督衙门亦有赏需银两数千两等语。总督养廉丰厚,遇有奖赏之事,理应于养廉内,自行赏给,何得复备赏需款项,此实相沿陋习,极宜删除。唯新设之成都将军,管辖众番,每有必需赏犒之事,而所定养廉较少,若再令其自行发赏,未免不数用度。自应酌量加添,俾无缺乏。著传谕文绶,即将该督衙门所有赏需一款,永远裁去,其成都将军,每年应添给养廉数千,以供赏用。”
简言之,清廷给予成都将军一系列关于管理康藏地区的权力和经费,而乾隆一朝历任成都将军也完成得较为出色。纵观乾隆一朝,成都将军的职能应当是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而得以逐步完善。
(一)军事交通方面:统率军队,保持武备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时任成都将军明亮奏请:“军机大臣议覆、成都将军明亮奏称、通藏要路之硕板多、石板沟、巴塘、里塘四处。道里辽阔,间有夹坝。请于各营汛明干都司、守备内,拣派四员分驻,以资弹压。又请于里塘地方,添驻土马兵一百,以资巡哨。”又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时任成都将军明亮上奏:“两金川善后事宜,已办有就绪。所有塘马,除郫县、灌县、映秀湾、桃关四站。照内地例,归地方官经管外。其桃关口外,草坡至噶喇依,共二十五塘。自草坡至二道桥、令桃关汛员经管。自卧龙关至巴朗拉、令卧龙关汛员经管。至桃关口外,经过瓦寺、鄂克什、两土司番地,道路荒远,各塘止有汛兵五名。请酌派土兵五名当差,再自成都至广元一带,每驿奏留台马八匹,以供驰递,今请裁。”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成都将军鄂辉奏请:“其巴塘迤东土司地方,归川省将军督提衙门就近管理;至江卡、乍丫、察木多并移驻后藏各营汛台站,统归驻藏大臣总理。”这些奏折都被清廷所接纳,并立即着成都将军执行。诸如此类的奏折在《清实录》《清史稿》等史料中不胜枚举,此处不再累述。⑬
(二)治安稳定方面:镇守关卡,巡边守土
史料中也记载了成都将军处理川边藏区一系列关于维护地区治安稳定、社会平稳的事例,兹举例一二。乾隆四十四年(1779),理塘土司所属热寨地方之麻塘寺遭到瞻对夹坝的抢掠,由成都将军特成额料理。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都将军特成额亲赴三暗巴(今四川省白玉县)平叛三暗巴贼番抢劫事件,协同总兵成德迅速殄灭三暗巴贼众,因三暗巴系川边通西藏的咽喉之地,故成都将军特成额平叛此事使得通藏道路得以恢复通畅,两地经济贸易继以往来。⑭
(三)社会经济方面:屯田生产,征调经费
兹列举成都将军特成额参与的筹办江卡地方善后事宜为例。其规定有四:
“(1)江卡地方业经剿定,自应酌派弁兵,分防驻守。从前察木多因控制西藏,设立游击一员,千把外委六员,驻兵三百三十一名。抽出兵一百名,把总外委各一员,拨归江卡守备管理,驻防镇压。(2)江卡既添兵防驻,自宜相地筑碉,以资栖止。(3)千总胡世杰,熟练番情,派令经理番地事宜,移驻江卡。营官东纳,错截茶包,致滋事端,应彻带回藏。其江卡营官,令郎卡多尔结充补。(4)炉厅米石,起运在途自应分别远近,酌运收贮,其江卡支剩米面无多,即令该驻防守备收存,以供支领。均应如所请办理。”⑮
以上史料说明川边康区大规模战役虽然没有爆发,但地方上治安状况仍不稳定,各民族间的矛盾、清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土司之间的摩擦依旧不断,但在乾隆年间几任成都将军“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川边康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业已颇见成效,对于川边康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人事管理方面:考察官吏,定其升迁
成都将军设置后,清廷规定康藏边地官员的升迁调补、考察考核,均由成都将军以及四川总督共同办理。具体包括所辖地区官员的大计举劾、俸满甄别、终养、告病乞休、丁忧等政治生涯的方方面面。[3](P129-131)
四、“成都将军”设置对康藏地区的影响
(一)加强清朝对川藏地区的统治
清廷在赋予成都将军比其他内地驻防将军更多权利和充足经费的同时,为防止其“事权专重,擅作威福”,在创设之初即明确规定:“若日后将军或因事权专重,擅作威福,扰及地方,干预民事者,总督原可据实陈奏。又或总督轻听属员之言,于番地情形,动多牵制,致误公事者,将军亦当据实奏闻。朕惟按其虚实,秉公核办,以定是非,必不肯有所偏向。”⑯清廷这一给予地方大员充分权利及相互制衡的地方管理机制,使得乾隆一朝历任成都将军能够合理行使自身职权,在川边藏区统一管理八旗驻防官兵、节制绿营,总理该区的军政事务,从而加强了清朝对川边藏区的统治。
(二)对川边藏区道路的畅通和社会的稳定起了促进作用
最初为巩固战争成果,稳定边疆而设置的成都将军,经过乾隆一朝历任将军的管理和川边人民的共同建设,有效保障了川边藏区道路的畅通,多年的屯种也促进了该区社会的稳定。在成都将军设置的十二年后,时任四川总督保宁奏:“金川屯务,经前任将军参赞等,丈出地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亩,节年屯员,广为招徕,穑事日兴,荒土尽辟。除原丈地已垦外,多垦地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亩……统计新旧地亩,并汉牛一屯,每年共应征粮一千二十一石零。”⑰川边藏区屯务的自给自足,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有利于清廷政策在该区的落地和执行
平定大小金川后,清廷在川边藏区颁布了一系列善后政策,成都将军的设立对这些政策的落实和执行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战后,清廷在该区实行的移民屯种、土司轮流入觐、推崇黄教等政策,与成都将军的职责逐一对应。乾隆四十一年,成都将军奏称:“今于两金川之地设营驻兵,令提督统兵分守,并於近边添设将军控驭,以保卫尔各土司使长享太平之福,此又朕善后之殷怀也。尔土司等年来出力随征,共効恭顺甚属可嘉,已节次加恩奖赏,并命照回部之例,轮班入觐……令于冬间,由将军、总督、提督等照料进京,俾之随班朝贺,瞻仰受恩,尔等并得身受龙荣,増长闻见,岂非尔等之大幸欤。至尔崇尚佛法,信奉喇嘛,原属番人旧俗,但果秉承黄教,诵习经典,皈依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修持行善,为众生祈福,自无不可。若奔布喇嘛,传习咒语,暗地诅人本属邪术,为上天所不容。”与清廷这一推崇格鲁派黄教的政策相呼应。乾隆四十三年,成都将军特成额奏:“据绰斯甲布、及布拉克底、巴旺等土司禀称,该土司地方俱兴建喇嘛庙,学改黄教。又巴旺土司将幼子二人,送广法寺学习经典。”批:“好事也”。⑱
五、结语
乾隆年间设立成都将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川边藏区的统治,远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虽然该时期成都将军中也有在诸如廓尔喀战役中欺君瞒上、贻误军事等不足之处,但从整个战事的局势,以及川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谐等方面来看,成都将军在乾隆一朝对于清廷西南边疆的统治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当时的土司制度下,清廷除了借重地方力量维护其统治外,成都将军设立后,在该地区统率满兵、绿营,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行屯兵屯田,为远抚西藏、促进该地区生产恢复提供了重要后备力量;进一步推进改土归流为清廷中央政令及时到达,提升行政效率产生了推力。此外,也给后世治理川边藏区,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留下了值得参考借鉴的历史经验。

附录:《清朝乾隆年间成都将军简表》
[注释]
①详情参见:彭陟焱.成都将军的设置及其在治理川西藏区中的作用[J].西藏研究,2010(1);潘洪钢.乾隆朝四川杂谷厅改土归屯述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4);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J].中国藏学,1993(1);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J].清史研究,2011(4);张羽新.清代治藏要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等论著。
②详情参见:彭陟焱.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彭陟焱.清代嘉绒地区“厅”的设置及其影响[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5);彭陟焱.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J].西藏研究,2004(4)。
③详情参见: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考析[J].西藏研究,2004(6);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解析[J].四川文物,2009(2)。
④详情参见:陈潘.沙济富察氏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2).
⑤详情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J].中国史研究,2003(4).
⑥第一次金川战役的军费为1000万两左右。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四年六月十八日策楞题本《为遵旨议奏事》。第二次金川战役的军费为7000万两左右。详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五,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卯条。
⑦仅以第二次金川战役为例,清朝前后调遣了吉林、黑龙江、湖北、云南等七省,满、汉、土官兵,总计十四余万名。详见:(清)郑栖山编纂、张羽新点校:《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上),第1卷,全国图书馆微缩复制中心出版,1991年,第12-15页。
⑧详细参见:(清)官修《清通典》,清浙江书局版,影印本,第799页。
⑨详细参见:(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第3981页。
⑩详细参见:《清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康熙五十七年八月辛卯条。
⑪历史上廓尔喀之战主要分为两次,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藏廓发生贸易纠纷,适逢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正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发生内争,沙玛尔巴请求廓尔喀兵相助。于是,廓尔喀兵以“西藏运往之食盐掺土”此为借口,乘机进攻西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廓尔喀人以大清国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圆为由,出兵千余,再次进攻西藏,夺占聂拉木。关于两次廓尔喀之战的详细经过。参见:拉巴平措主编,马丽华、季垣垣副主编:《钦定巴勒布纪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⑫“但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尚属有名无实且番地事宜仍由地方文武办理。仅禀知总督而行。而将军无从过问。非但呼应不灵。即于绥靖蛮陬之体制。亦不相合。现在文绶为总督明亮为将军。自不虞有掣肘若将来接任之员。或彼此稍存意见。即不能资和衷任事之益且恐不肖员弁。久之故智复萌。不免仍蹈前辙。尚不足为一劳永逸之计。此乃善后事宜之最切要者。”详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条。
⑬详情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十一,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乙巳条;卷一千十一二,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辛巳条;卷一千三百三十三,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辛巳条。
⑭详情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七十九,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壬寅条;卷一千一百三十,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庚子条。
⑮详情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九十,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庚午条。
⑯“……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尚属有名无实且番地事宜仍由地方文武办理。仅禀知总督而行。而将军无从过问。非但呼应不灵。即于绥靖蛮陬之体制。亦不相合。现在文绶为总督明亮为将军。自不虞有掣肘若将来接任之员。或彼此稍存意见。即不能资和衷任事之益且恐不肖员弁。久之故智复萌不免仍蹈前辙。尚不足为一劳永逸之计。此乃善后事宜之最切要者。不可不及早酌定章程。俾永远遵守。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毋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建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具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汛,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题奏。应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极宜,亦归画一。”详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条;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丙申条。
⑰详情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七,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已丑条。
⑱详情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丙申条;《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六十七,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戊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