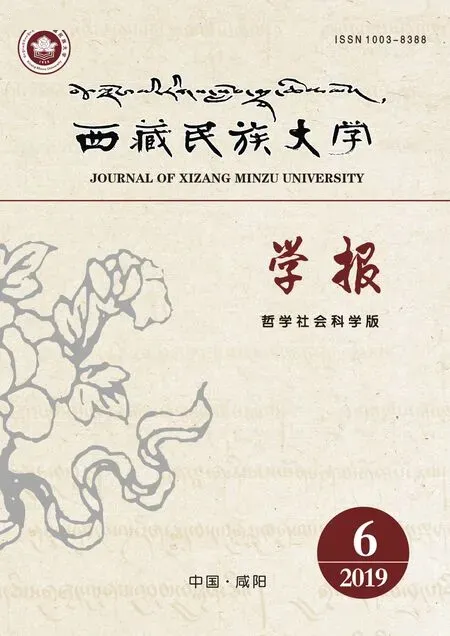试论藏族社区的空间生产与情感归属
朱雅雯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广东广州 510665)
T村落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镇,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海拔约2900米,气候常年高寒缺氧。该区域主体民族为藏族,具有浓郁的藏文化传统。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T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是如何被纳入城市空间的空间如何转型又如何承载起情感诉求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空间概念的生产与村落的空间
空间原本是自然地理的概念,在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之后,空间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其重点是如何从文化的层面进行空间意义的阐释。
“人们并不把空间看成是思想的先验性材料(康德),或者世界的先验性材料(实证主义)。人们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人们区别了社会空间与几何空间,及精神空间。”[1](P39-40)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并不是一种物理性的自然存在,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是社会产品[2]。空间被划分为三个层面: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1](P25)。哈维在他的基础上又将其细化出了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联空间三个维度。他们都认为空间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应当被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被放置于一个复杂联结的体系中加以看待,如此才能展现空间本身的丰富意涵[3]。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同时具有复合性内涵。列斐伏尔着手建构起一个空间本体论的社会理论框架,从而与福柯等人一同开启了一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4]。黄应贵认为,空间虽独立存在,但却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空间可被视为一种宇宙观或一种象征,空间被视为文化习惯,空间建构是一种认知架构[5]。孙九霞和苏静的研究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精神空间、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6]。杜若菲认为瑞尔夫的研究中提到地方的三重属性物质、功能与意义可以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类型相互对应,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了空间、功能、情感的三元论以讨论地方重塑的机制问题。“只有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空间再生才是成为重塑地方历史和情感、保有地方差异、避免地方卷入资本循环和重构而成为抽象空间的途径。”[7]就夏河县而言,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北内陆地区,但在历史上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被称为是汉、藏、蒙、回四大文明的十字路口[8],吸引了李安宅、于式玉、埃科瓦尔、克兹洛夫等一大批学者来此调查研究。该地区尤其在民族文化交流互通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空间位置的优越性尤其在拉卜楞寺建立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从而在周边藏区中起到中转、联结的核心作用。
Tsering Wangyal Shawa绘制于1930年的地图[8]说明了拉卜楞寺广阔的势力范围以及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位于青海、甘肃、四川三省交界之处和中国西北部的交通要塞之地。据民国时的统计,拉卜楞寺的可耕地面积近74万亩,辖区内的土地均属寺院所有,只准佃户租种,无权典当、买卖或转让。[9](P140)该寺也有众多的所辖部落。“清末民初时拉卜楞寺的宗教势力统治范围达原循化厅辖南番二十一寨,东至土门关接导河县界;南至陌务寺(即美武寺)接临潭县界;西南至大湖滩邻青海地界;西至多瓦、关秀达青海省贵德县界;北至瓜什济寺接循化厅界,周围辖境约1600平方公里。”[9](P140)
新中国成立后,该区域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为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拉卜楞镇附近村落的大多数耕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修建学校、政府单位、医疗机构、大型商场以及城市公共设施。一些靠近寺院的耕地还用于修建宾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呈现出了空间上非常鲜明的混合性,这个混合性包括了多民族元素的混合、城乡建筑的混合以及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混合。有学者认为,甘青藏族社会的组织和结果存在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居于城镇、营汛或其附近,主要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多与其他民族如汉、回、撒拉等杂居共处,大致相当于“熟番”的概念;第二种类型是居地离城镇、营汛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部落;第三种类型是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10]。由此可以看出,如文献记载,拉卜楞地区村落因其个体差异分属不同的类型,T村落村民在历史上作为拉卜楞寺直属教民,凸显了与寺院的密切联系,当属第三种类型,即以寺院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经济方面又呈现出第一种类型的特征,即农业和半农半牧的形式。这种寺院为中心的组织形式随历史和村落的现代化进程而发生了转型。
二、村落转型与记忆变迁
在传统藏族社会中,藏传佛教寺院既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文化教育中心。“僧人们在政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们不仅是宗教人士,也使政体运作……对于蕃酋们来说,寺院代表着区域统治的焦点。西藏后期佛教王国的先驱者们都是以寺院权力为中心的。”[11]拉卜楞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拉卜楞寺旁边T村的山神阿弥华勒合(ཨ་མྱེམྱེས་དཔའ་ལགས།)一大片周围的区域被叫作噶然隆哇(མགར་བ་ལུང་བ།,汉语意为铁匠沟)。这一片区域在历史上距离拉卜楞寺市场最近,曾经有十多家铁匠铺子,现在只剩下了两家。这里还有拉卜楞最早的驿站,所有前来贸易的人都会在此地歇脚。该社区拥有经商的历史传统,商业氛围较浓厚,另外由于靠近拉卜楞寺,位于地形平坦开阔的大夏河河谷地带,也有农业种植的历史,该区域的空间类型一直以来都是较为特殊。人们认为夏河地区是围寺而商、围寺而城的城镇类型,寺院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中心作用[12]。
拉卜楞寺始建于1709年,寺院建立之后,为了给寺院提供经济、劳役、教民上的支持,根本施主黄河南蒙古亲王将自己的属民送给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这批人长途跋涉来到夏河,在寺院周边定居,逐渐扩大为村落。形成了依附——定居——变革——发展的脉络[13]。
如上文所述,该社区和拉卜楞寺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直属关系。拉卜楞寺建立前周边没有村庄,属草原,自寺院创建后逐步形成了拉卜楞十三庄,该地区总体属于农业和牧业的交错地带,在洒乙昂(地名)一带种植有大麦、青稞、油菜等农作物,T村也包含在内。20世纪50年代,该村落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给别人下苦(夏河方言,做苦力)为生,次要来源是商贩、副业以及农业。20世纪50年代开始,夏河经历了民主改革、人民公社运动,80年代又进行土地改革,社区的空间类型与归属在不断发生变化。[14]
T村被划归入夏河县九甲乡管辖,其居民类型包括两类,农业人口和城市居民,两类人员在同一空间中杂错居住。城市居民主要包括获得了正式工作的公务员、教师等国家公职人员,由城镇社区进行管理,其余的人口为农业人口,由九甲乡进行管理。直到2004年,撤乡并镇,撤销九甲乡,所有人口并入拉卜楞镇,户籍类型也改为非农业户口,以城市社区的方式进行人口管理,只能以打工为主要的生计方式。
在村落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该社区复杂的变迁,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村落被一步步纳入城镇化的区域范围中,村落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人们对于空间使用类型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寺院曾作为当地社会重要的空间重心而存在,也寄托了当地信众的宗教情感,像拉卜楞寺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寺院,在整个藏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夏河得以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寺院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村落转型发展的今天,拉卜楞寺成为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因为紧邻寺院,有些人在周边开起了小商铺售卖旅游纪念品,有些以开家庭旅馆为生。
在T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其他要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城镇化使得原来村落的组织形态从乡村转变为城镇社区;生计方式从原来的农牧生产转变为农牧业、商业、服务业等兼营的新的生计方式。村民们仍然信仰藏传佛教,表现为村落民众在拉卜楞寺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中的积极性较高,在民众中特别是老年人中转经等信仰宗教的活动仍然是其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T村依托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民族风俗、族群意识、宗教信仰、历史记忆等,创造出独特的空间秩序。而“这种空间秩序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语言符号系统,并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的空间建构。”[15]拉卜楞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之一,在安多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房屋万余间。虽然城镇化的发展使得T村落景观有了很大的变迁,但寺院在整个城镇景观中仍然独具特色,影响着拉卜楞镇的空间建构。寺院也是藏族民众共同的信仰中心,是宗教情感得以释放的空间。
总之,寺院在历史上作为藏族社区发展的重要角色,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城镇化过程发生生计变迁与村落转型,寺院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转经道上人潮涌动,老人们手拿玛尼珠串,一遍遍转动经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寺院成为农牧民群众情感的精神支柱。
三、神山崇拜与仪式参与
当空间层次缩小到村落的层级,在村落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情感空间是神山。山神崇拜是安多藏区重要的信仰。[16]山神有不同的力量和等级,一个部落、一个村庄或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都有山神,只是供奉人群和力量存在差异。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出生地的神山是自己一辈子要敬奉的,不会因为人口迁移变动而发生改变,一生当中神山是人们的保护神和心灵的寄托,神山力量强大,可以庇佑子孙,福泽信奉的百姓。44岁的才让叔叔给我详细讲述了战神演变的过程以及神山阿弥夏勒合的故事。
以前,藏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是苯教,信仰万物有神灵,对战神非常崇拜,后来整个藏区信仰藏传佛教,后来演变成对自己一生当中不顺的东西,看不见的邪恶的生灵的对抗。佛教进入青藏高原之前,箭是一种标记,是先遣部队在大部队来之前做的标记,在主要的山上插上箭,表明行进路线,后来箭代表一种英雄,像大山一样的英雄。插箭的时候我们把(箭当作)武器送到这里来,你(神山)就保护这片土地,保护我们。佛教提倡的是慈悲为怀,这里面掺杂了很多佛教的内容,不提倡英雄崇拜,后来这些内容就慢慢淡化。
神山也是有等级的,低级的一些山神,我们只是煨桑①供奉,我们不磕头,但是可以给他许愿,你给我帮一点忙,保佑我什么的。人死了以后,这些小山神不能帮你任何忙,他们属于世间神,死了以后起不到任何作用。人死之后,只有佛法僧才能拯救你。神山也是一步步的修炼升级,阿弥夏勒合是一般等级的,比较年轻。
关于阿弥夏勒合也有一段传说。四世嘉木样活佛去西藏学习,回来的时候在路途遇到他,那时他还是个魔鬼,形象就是一个穿着兽皮,提着人头的罗刹,眼神狰狞可怕,手中有刀子。后来四世嘉木样活佛把他带到了这里,封给他一个位置,让他改邪归正,步入正道,告诉他如果你走白道的话,我就让很多人去供养你。后来他也接受了劝化,成为了类似于居士的身份,狰狞的形象变成了正常的人的形象。嘉木样活佛将他安置在刚刚进入夏河县城的这个位置,成为夏河的第一个守门人,让他守护这个地方。他既是守护神,同时掌管这一片的财富,也是财神。后来,外来人逐渐增多,打拼很辛苦,外来人认为供养他可以办事情更加顺利,所以很多外地人都跑到那里去煨桑供养他,因为他很愿意帮助外地人。②
从上面的讲述可以看到,阿弥夏勒合神山接受教化,皈依佛门之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供奉,也是很多外地人祈求庇护的保护神。T村落区域性的神山还有很多,另一个自然村的神山一共有6座,每年在不同的时间接受插箭供奉。这6座神山分别包括:阿弥华勒合、拉然噶柔、扎西隆魁、吐合衮、占金姆和卓梅沃什则。
传说阿弥华勒合是个年幼的孩子,是村子里孩子们的保护神,如果谁家的大人打孩子让阿弥华勒合知道了,他就会生气。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一和五月十五,人们来这里插箭供养,祈求孩子们平安幸福地长大。所使用的箭板较小。扎西隆魁每年五月初八插箭,主要是老年人来此,和吐合衮、占金姆神山一样,插箭参与的人员较少。卓梅沃什则主要是在二月十一这天煨桑祈福。最盛大隆重的要数拉然噶柔的插箭仪式,每年的六月十七举行,参与人数最多,箭也是最大的,箭板就有4到6尺,需要两个人共同抬到山脚下。人们一般都会选择骑马前往。如果自己家里的祖先曾经在此插箭过,那么后辈同样需要来这里插箭供养。
插箭仪式是很重要的山神崇拜的仪式活动,笔者在2015-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参与了村落多次的插箭仪式。
阿弥夏勒合的插箭仪式分别是农历正月初一和四月十一。农历四月的夏河,天气依旧寒冷,笔者于凌晨5:35从家里出发,6:10到达阿弥夏勒合山顶。一路上有很多人都背着大背包、抬着箭杆往山上走,包里有煨桑用的各类物品,糌粑、柏香、风马旗,有的人还拿一支挂经幡的木杆。此时山上已经有很多人,箭是在插箭前一日就已经被抬上来备好,用塑料布遮盖起来。6:15村落生产队队长召集大家开始插箭,年轻的男性喊着吉祥的口号,抬着箭杆在煨桑台上面熏一下柏香,意思是去除不吉祥的不干净的东西。之后,将箭杆抬到插箭的台子上,立在箭丛里面,接着其他的箭杆一一如此,先将所有代表各个村落的箭插好,再依次将各个家庭的箭插在箭丛中。整个仪式的参与人数不少于三百人,男性占80%左右,年龄主要以20-45岁的中青年为主,老年人相对较少。女性占20%左右,年龄分布较为分散,负责协助抬箭杆,或是煨桑祈福。村民到达之后都是先在煨桑的台子上熏一下箭,再在煨桑池里放上各类物品,口中大声念诵经文,叫着阿弥夏勒合的名字,之后将箭杆抬到插箭的台子旁边,交给站在箭池里的人,插好箭之后,去往旁边更高的山上撒风马旗、悬挂经幡。之后,插箭仪式结束,约7:30左右,村民们陆续返回。插箭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加强了群体间的认同,为情感提供支撑③。
插箭不仅是重要的民俗文化,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的期盼。箭板的制作并不容易,一下午时间只能做四五只箭,但制作的过程倾注了人们对和平、美好的希冀,对幸福、安康的渴望。插箭用的箭通常以一支长的木棍作为箭杆,箭板又称箭羽,用白色线绳将其固定在箭杆上,家里男孩子比较多的,制作时放两组箭板,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可以只放一组,箭代表了男性,是男人的武器。家里只有女孩的可以不去参与插箭,只去煨桑,煨桑时用一种竹子做枝条,上面放些羊毛来代替。羊毛代表财富,抹上一点酥油也是希望家里的财富多得像酥油一样。
箭板上会绑上彩色的布,金色代表太阳或者土地,蓝色是天空,白色是云朵,绿色是草地,红色代表佛祖。扎上哈达让整个箭更加好看,另外也是对山神进献哈达的意思。这支箭象征着阿弥夏勒合神山的武器,将不好的、不吉祥的东西都给消除掉,生活从此顺利平安。
在青藏高原这样严苛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事事如人意,人们需要随时做好准备接受挑战。高寒缺氧、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漫天的风马旗代表了对自然的祈求,高耸的长箭是给神山的礼物,浓烟缭绕的煨桑台是对神灵的献祭,无一不是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诉求。人们通过集体的联合共同完成这场献祭,共同保护家园。
神山崇拜是很多民族具有的多神崇拜的一种,其来源于自然对人的考验。在人类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代,各种自然灾害、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无法抵御的疾病等,对人的生存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人类必须寻求一种庇护,高耸的山峰是距离天最近的地方,于是被人想象为和神秘力量最好的联系纽带,对神山的崇拜、祭祀,可以愉悦山神,他就可以庇护人们免受种种灾难的威胁。夏河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是中国地形从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大夏河谷地四周众多的山峰,为具有奇特功能的神山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仅一个T村落就有多座神山。神山崇拜产生之后,为了表达对山神的崇敬,在固定的时间举行盛大的仪式,由于参加的民众较多,事实上成为整个村落成员相互交流的场所,增加了村落内部的认同和感情。高耸的箭杆随风飘动的经幡,袅袅升起的桑烟、空中飞舞的风马旗,成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景观,说明民俗文化在空间建构中的支配作用,也表达着村落民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情感。
四、草原情结与家庭归属
寺院是群众信仰生活的重心,神山崇拜是村落共同体的寄托,草原是群众的家园。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T村的定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逐步被纳入到城市社区的范围当中,但对于当地藏族人而言,对草原的热爱似乎流淌在血液当中。每年的农历六月都要举办香浪节,浪在当地汉语方言中意为玩耍,这个节日的重要内容就是去到广阔的草原上欢度时光、吃喝玩乐。较大规模的浪山通常由村落来组织,一些小规模的浪山一般是三五好友,几家人相约同行,或者是各家各户单独出行。从六月开始,先由寺院里的僧人阿克(当地藏族对僧人的尊称)带头浪山,接下来是僧尼阿内(当地藏族对出家尼僧的尊称),之后就轮到了普通大众。浪山并不是短期的节日,而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几乎贯穿了六月一整个月的时间。笔者在调查期间,也被多次邀请参与不同群体的浪山聚会。各个村落组织的浪山,需要准备大量的物资,要先向村民们收取一定的活动资金,再统一购买肉类、面粉、蔬菜、水果、饮料等食物,准备好炊具、柴火、桌椅、板凳、帐篷。由于人数众多,物资需要用卡车运送到浪山的草原上,每晚还要由各家轮流派人留宿在帐篷中,照看所有的物品。总之,浪山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差事,但对当地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个当地的朋友告诉笔者,由于气候的原因,每年只有极其短暂的时间可以欣赏到绿色的植被,如果不及时去草原上坐一坐感受一下难得的绿意,再想坐在绿色的草地上就没有机会了。他惬意地躺在草地上,用手轻抚身边的小草,洋溢着满眼的幸福与满足。
草原是藏族人的根,而家是最现实的归处。家不仅具有经济功能、生产功能,还是重要的情感归宿。这种情感包括了爱情、亲情。藏族社会家庭结构多为主干家庭。
家屋社会(house society)的概念是Levi-Struss(1987)[17]提出的,之后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18],家屋社会的概念成为亲属关系研究的新路径④。家屋是一个凝聚了空间、文化、情感、亲属等多重元素的共同体。“家宅是一种建制方面的创造,它能够将在别处因矛盾的取向而看起来相互排斥的力量组合起来……目的是超越一些力量在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难以调和的原则。通过这种可称之为二合一的方法,家宅完成了从内向外的某种拓扑学意义上的转换,用外部整体性取代了内部二元性。”[19](P210)村落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依山而建,居住人口多,但是居住面积相对狭小,尤其是噶然隆哇一带的山坡,住户一家紧挨一家而建,住房面积十分有限。传统的房屋是木结构与土墙的结合,现代房屋大多采用了土木结构搭建房屋框架整体,再使用水泥砖块砌墙。当地人认为,木质的房屋比起水泥的房屋更利于防寒保温,居住起来更为舒适。每套藏式的房屋基本包含有以下的几个功能:礼佛、居住、烹饪、会客、储藏,分别相对应经堂、卧室、厨房、客厅以及储藏室。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每个功能区的面积比较大,具体使用的划分也更加细致,比如卧室可能分为主卧、次卧、客卧等等,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人家,可能一个房间就涵盖了以上所有的功能。下面是一户普通人家的空间平面简图,可以大致看到家屋空间的功能分区情况:

X家屋一楼平面图

X家屋二楼平面图
每个家屋的设计,都包含了多种功能,家在藏族社会中同样具有丰富的意义。藏文化中,敬老是十分重要的传统,老人是家庭的财富,老人在家中具有极高的地位,等到子女长大成家后,会由其中一人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获得老人财产的继承权,这些主干家庭大多数都会为老人提供最温暖舒服的大房间,子女们住在条件较差的房间,以体现对老人的尊重。当地人的观念中,老人在家庭中最好的空间位置就是视野最好的房间,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中,轻而易举就观察到所有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活动,老人腿脚不便仍然可以感受到子女孙辈的日常,对老年人是很好的精神慰藉。笔者调查期间,常常走访村落各户人家,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善待老人、孝敬父母,这样的居处方式体现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尊重与关爱。
藏族社会中的家庭除了经济共同体职能、养育子嗣的职能之外,情感是维系家庭很重要的纽带。藏族社会的婚姻观念较为松散,结婚、离婚在当地人眼中都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婚姻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家庭的组建是对对方的绝对信任,如果没有了感情,也不必强求。有学者认为藏族社会中的家庭,应当更多地以经济共同体的功能来进行理解,笔者认为,藏族社会中的家庭其实更注重情感。传统的藏族家庭会有严格的性别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男性负责为家庭提供所需的食物和资源,以及进行对外交换等经济活动,女性负责家庭内部的劳动生产和家务劳动,这就需要男女双方具有更强的家庭观念,才能共同完成家庭的职能,对于家有着更多的依赖与牵挂。
T村传统的牧业生活,在族群的记忆中根深蒂固,尽管现代已经从农业社区变迁为城镇社区,但居民仍然对草原充满了感情,每年持续一个月的香浪节,就是对草原的回归,人山人海的人群、彼此相连的帐篷,表达了对城镇生活空间的扩展。当这种情感回归到日常生活空间的家屋之中,体现了具有生产功能、经济功能、情感功能等集聚的家的出现。T村落坐落在大夏河的一条狭窄的支流河谷的山坡上,平坦的建筑用地很少,大多数的家屋面积很小,而且建筑依山而建,建筑物非常密集。尽管如此,在家屋空间的构建中,藏民族敬老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使得家屋中老人的居室较大而且向阳温暖的房间,这也是藏民族敬老文化情感在家屋空间建构中的表达。
五、结论:空间层次与情感依托
本文讨论了藏族社区几个不同层次的空间类型,寺院、神山和家屋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空间与相应的感情体验联结。
寺院作为传统藏族社区的文化教育和信仰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当地人最浓厚的心灵寄托,当地人对夏河有极高的地方认同与归属感也来源于此。随着村落被纳入到城镇化的进程之中,村落原本的空间类型发生转型,而体现出一种空间上的混杂性。从村落的层级来看,人们可以通过神山崇拜寻求庇佑,得到安全感,获得村落共同体的支持和认同,是村落群体的凝聚。回归到个体的家庭层面,仍然沿袭了上述的空间逻辑,家屋空间是重要的经济劳动生产单位,同时更是家庭成员关系维系的重要场所,家庭为个体提供了最具体切实的物质和情感归属,家庭的纽带将个体集聚,空间安排体现了深切的情感关爱。
总之,寺院、神山与家屋,从不同的空间层次三位一体为个体提供了情感的全面支持。日常生活中,不同空间的生活实践向我们展示着当地村民的情感体验,大到寺院、神山,小至家屋,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最深切的情感。
[注释]
①煨桑是藏族普遍的一种供奉方式,以燃烧柏香、糌粑等物品,达到净化、祈福、供养的目的。
②访谈时间:2016年5月15日,访谈地点:夏河县拉卜楞镇雅鸽塘。为保护访谈人的权益,本文均为化名。
③完麻加.森普神山崇拜及其社会整合功能[J].青海民族研究,2013(3);李玉琴.人神共场:神山崇拜的界域与认同——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的特质与意义的考察[J].青海社会科学,2013(4).
④李锦.嘉绒藏族的家屋与社会结构[M].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冯智明.身体与家屋空间的构建——红瑶身体的空间性及其象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