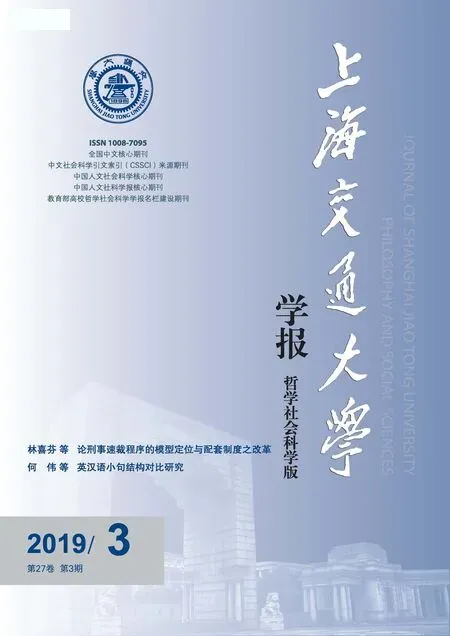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阐释及实现路径
——基于预防性司法救济的视角
唐 瑭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 201306)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司法救济制度近年来备受环境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自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及《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继修改以来,近五年间,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显著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赋予国务院。国务院根据《宪法》的规定,对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是从执法的层面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地。而环境公益诉讼则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司法层面的重要保障,也是最为重要的司法救济手段。学术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关注度持续未减,特别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责任承担、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始终忽视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的预防性功能。就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及学界研究来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围绕有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损害赔偿请求展开,以《侵权责任法》为法律适用基础。但是,这种以损害结果为重心的模式,难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功能。环境公益诉讼重要价值与功能是风险预防,而非损害填补。目前大多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也在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后的补偿性司法救济问题,而忽略通过制度设计阻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行为的司法救济。事实上,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价值应当体现在其预防性司法救济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对损害结果的填补。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除了发挥对环境损害结果的补偿性功能之外,还应当发挥其预防性功能。为此,本文将从预防性司法救济视角,阐释环境公益诉讼价值,并对域外相关司法经验进行考察分析,检讨我国相关制度的缺失,提出构建我国相关制度的实现路径。
一、 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价值阐释
(一) 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缘起
从环境公益诉讼价值功能来看,一般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包括预防性司法救济与补偿性司法救济。所谓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是指为了预防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对环境损害行为或存在环境损害之虞的行为进行阻却,依据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由国家司法机关所提供的司法救济。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是相对于补偿性司法救济制度而言的。补偿性司法救济是通过对已经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司法救济;而预防性司法救济是针对预防尚未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生态损害进行的司法救济。如何理解预防?关于“预防”的司法权威解释如下:“预防原则是指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或者环境破坏等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2.其中,最主要的应当是针对环境损害行为进行预测和防范。美国萨克斯教授认为预防性措施是环境诉讼的目标。[注][美] 萨克斯.保卫环境——公民诉讼战略[M].王小钢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00-102.目前,由于我国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关注不多,所以学界尚未对此达成共识。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模式主要包括救济对象、救济手段以及救济依据。首先,从预防性司法救济对象来看,预防性司法救济的对象应为导致或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行为;其次,从预防性司法救济手段来看,主要是指预防性的责任承担方式,例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停止侵害、禁止令等责任形式;最后,从预防性司法救济法律依据来看,预防性司法救济手段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而非《侵权责任法》。
(二) 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价值阐释
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能够体现风险预防原则、诉讼顺位以及其内在的道德性。
首先,应当体现预防环境风险。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功能。风险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科学的不确定性”。[注]彭峰.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之再探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26-130.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在环境法规范中表现为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危害结果的不确定性。为了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便提出了风险预防原则。1987年《北海宣言》指出:“投放海洋的危险物质与海洋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不确定性的,但是为了防止污染损害发生,应当采取必要的预防方法。”[注]陈维春.国际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J].现代法学,2007(5): 114.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模式针对可能的污染损害行为的禁止令制度所体现的内在机理亦是如此。
其次,符合司法救济的逻辑顺位。一般来说,生态环境的损害发生往往是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损害行为,就不会发生损害结果。因此,预防损害行为的发生尤为重要。对于已经出现致害结果的情形,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救济。然而,由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以风险预防为目标,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出现之前,针对可能具有环境影响的损害行为而采取的环境司法救济更加能够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本源价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救济性可见一斑,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应当是首先对损害行为进行预防性的司法救济,其次对损害结果进行补偿性的司法救济。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能够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在道德性,即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环境公益诉讼是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展开的诉讼。这里所讲的“诉讼的目的或功能”是与国家文化或者法律文化相关联的。[注]在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Catalys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Nigeria一文中,阿金里梅德(Akinrinmade)教授引用了拉吉夫·达万博士(Rajeev Dhavan)对环境公益诉讼定义的观点。他写道:“Dr. Rajeev Dhavan at a conference in Britain in 1984 describe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culture-specific phenomenon which was developed in America and confidently ex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这一定义中指出,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文化特殊现象”。此外,他还引用了萨拉特(Sarat)教授和沙恩格尔德(Scheingold)教授的观点,“Professors Sarat and Scheingold in their work observed that providing a single cross-culturally vali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is impossible.”指出,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统一的跨文化的有效定义是不可能的。再次证明,环境公益诉讼所包含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在不同国家所实现的目的与功能是不同的。这种国家文化或者法律文化的基因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在不同国家所实现的目的与功能有所不同。环境公益诉讼所实现的目的与功能可以归结为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权利与利益是不同。在一个国家内,环境公益诉讼包含哪些权利和利益,又是与其法律和文化所认可的道德性密不可分的。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内涵应当包括其所适用法律法规的道德性。这便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道德性。从显性的表现来讲,便是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究竟保护哪些权利和利益,以及保护形式来体现环境公益诉讼所隐含的道德性。
任何时期开展的司法救济都是能够体现当时的道德性。环境公益诉讼所体现的道德性在于对其所包含权利与利益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成为环境法“利益保护”道德性证成的核心理论。这与我国自古以来的环境道德观也是一致的。我国文化思想和法律思想中存在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6.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5: 5.“天人合一”的环境法表达即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保护”具体应当包括: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公民享受环境质量的保障以及对因环境污染可能引起的致害结果的阻却。对这种权利和利益的保护,环境公益诉讼是通过事前预防性救济来实现。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公民及其环境公共权利信托人(政府)享受环境质量,而非获得因环境损害产生的补偿性救济,更不是货币性的补偿性救济。
一般来说,生态环境的损害发生往往是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损害行为,就不会发生损害结果。因此,预防损害行为的发生尤为重要。对于已经出现致害结果的情形,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救济。然而,由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不可逆性,针对可能具有环境影响的损害行为而采取的环境司法救济更加能够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本源价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救济制度的内在价值可见一斑。
二、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面临的困境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心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上,其法规范构成主要包括实体法上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以及程序法上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近两年也有所发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赋予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职责,但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重心。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仍具有补偿性司法救济模式的特点,这种模式无法满足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前预防要求,将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如下:
(一) 补偿性司法救济对象的困境: 以侵权损害结果为救济对象
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对象即对何种情形可以进行救济,其本质上涉及起诉标准的问题。从法律规范上来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标准为损害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这一规定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诉讼救济理念。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主要是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注]根据我国主要的全国性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在其博客上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和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89件(其中由社会组织提起的112件)、审结73件,受理二审案件11件、全部审结。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37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审案件51件,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件。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十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便有八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注]这八起案件包括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山东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湖北恩施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库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例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与谢知锦等环境污染纠纷案,被告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非法采矿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毁坏。原告委托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评估报告作为本案主要证据之一。[注]该评估报告指出,生态修复项目的总费用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110.19万元;价值损害即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134万元,其中损毁林木价值5万元,推迟林木正常成熟的损失价值2万元,植被破坏导致碳释放的生态损失价值、森林植被破坏期生态服务价值、森林恢复期生态服务价值127万元。最终法院认定了被破坏导致碳释放的生态损失价值、森林植被破坏期生态服务价值、森林恢复期生态服务价值合计127万元属于生态公共服务功能的损失价值。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注重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填补,以环境公共利益求偿的方式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这就使得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走向民法化,[注]环境公益诉讼“民法化”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利益的实质保护,利益损害填补也并不能够实现环境法的真正价值。也有学者与笔者反向理解,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近几年呈“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而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整体价值决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化方法需要改进,环境公益诉讼从其价值实现而言,就是实现环境利益预防性保护的价值,而非损害填补。即以《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为基础,以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及其因果关系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标准。在侵权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的主导下,损害结果也必然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关键要素。
2017年我国《行政诉讼法》作出重大修改,第25条规定了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该制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诉前检察建议程序,二是针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诉讼程序。[注]2017年《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中,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程序使得行政机关履职的案件较多。这些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集中表现为两点: 一是行政机关覆盖面不广泛,主要针对环境保护部门的环境监管职责;二是重损害结果,以出现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标准。
(二) 补偿性司法救济手段的困境: 以侵害责任承担方式为救济手段
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手段涉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责任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从立法与司法解释来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与《侵权责任法》规定是基本一致的。《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8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6种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为预防性的责任承担方式,恢复原状为恢复性的责任承担方式,赔偿损失为补偿性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判决大都选择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包括环境修复费用、环境修复之前生态功能损失等责任承担方式。例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件中,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1.6亿元。初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在此案的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又如,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初审法院判决鸿顺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5.82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再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与谢知锦等环境污染纠纷案,被告谢知锦等非法采矿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最终法院认定被告赔偿127万元。[注]法院对此笔赔偿费用认定为生态公共服务功能的损失价值,包括被破坏导致碳释放的生态损失价值、森林植被破坏期生态服务价值以及森林恢复期生态服务价值。有学者认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基本样态之一为“诉讼请求日渐多元,赔偿损失是最主要的诉讼请求”。[注]吕忠梅,焦艳鹏.中国环境司法的基本形态、当前样态与未来发展——对《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的解读[J].环境保护,2017(18): 7-12.这些案件普遍运用侵权法理论进行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对被告的环境损害行为与环境损失进行论证;(2) 以货币化赔偿的量化方法对环境损失进行评估,以此作为被告承担环境责任的主要方式。因此,法院裁判选择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赔偿损失。赔偿损失事实上是一种事后救济手段,难以起到预防环境损害、生态破坏行为的作用。
(三) 补偿性司法救济依据的困境: 以适用《侵权责任法》为主的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依据即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所适用的法律。从目前我国的立法来看,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的特点有: 一是在程序法上主要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其中,《民事诉讼法》第55条系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起诉的主体资格;二是在实体法上主要适用《侵权责任法》。[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了环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了环境侵权责任,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有学者指出,“目前环境侵权案件无严格分类,其主要实体法依据为《侵权责任法》”。[注]吕忠梅,焦艳鹏.中国环境司法的基本形态、当前样态与未来发展——对《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的解读[J].环境保护,2017(18): 7-12.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实质上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其真正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责任法》。因此,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主要聚焦于通过《侵权责任法》寻求环境损害的事后救济。
三、 域外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立法例之考察
世界各国基于各自法律体系建立了有自身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准确地讲,域外的环境诉讼中并没有准确地对应翻译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我国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环境诉讼的概括化定义。从各国类比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相应规范来看,各国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文本的规定各有千秋,但通过司法诉讼来解决环境公益问题的目的是一致的,特别是从其功能上而言都具备预防性司法救济的功能。笔者将考察德国环境团体诉讼制度、美国公民诉讼制度和日本的公害诉讼制度中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相关制度,以资借鉴。
(一) 德国的环境团体公益诉讼之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立法考察
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性质类似的德国环境诉讼是德国环境团体公益诉讼。20世纪60年代德国开始提出环境团体公益诉讼。2002年德国修改《联邦自然保护法》,该法第63条赋予环境团体以诉权。在德国,环境公益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具有公法性质。[注]陶建国.德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德国研究,2013(2): 68-79.德国涉及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联邦自然保护法》《环境损害法》《联邦法律救济法》。在上述几部主要的法律规定下,德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有如下特点: 第一,预防性的司法救济对象针对行政机关的任何违反《自然保护法》行为,包括行政许可或行政决定。例如,政府违法设立自然保护区。《环境损害法》其救济对象主要针对政府对经营者违法的不作为。《环境法律救济法》则扩大了救济对象范围,不再限于违反《自然保护法》和《环境损害法》。例如,违反水法的行政许可。第二,申请诉前行为保全和发布临时禁令是预防性司法救济的主要承担方式。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诉前行为保全,针对的行为是起诉前不采取措施将难以实现环境团体的权利。《环境法律救济法》规定临时禁令,只针对具有重大违法可能的行为。第三,预防性救济适用法律系环境法律。例如,德国“里奈恩火力发电站许可计划”案。该案的请求权基础便是《环境污染防止法》《水管理法》和《自然保护法》,程序法救济依据是《环境法律救济法》。从该案可以看出,该案适用都是环境法律。因此,综上所述,德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救济制度的特点。
(二)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之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立法考察
学界在研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通常会类比美国公民诉讼。公民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环境诉讼中的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与环境公益诉讼并不完全相同。环境公民诉讼源于公民诉讼条款。最早规定公民诉讼条款的是1970年《清洁空气法》。环境公民诉讼包括两个程序,一是诉前通知程序,二是诉讼程序。[注]公民诉讼的基本规则如下:“公民诉讼的原告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先履行起诉前通知的前置程序,即在起诉前将被控违法行为以及自己起诉至意图向特定对象(联邦环保局、违法行为所在的州和违法者本人)发出通知,在通知发出后一定期限内(一般为60日),不得提起环境公民诉讼”。郝海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86.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具有预防性功能,其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特点如下: 第一,公民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对象是针对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不作为的非行政裁量行为。例如,1990年《清洁空气法》规定,美国联邦环保局监督污染者三年内空气达标。但是,环保局未制定发电厂的排污标准。1992年,其被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其他环保组织和部分州起诉,认为其怠于履行制定发电厂的排污标准义务。第二,公民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责任承担主要方式系禁止令(injunction)。公民诉讼以禁止令作为主要的救济手段和责任承担方式。一般来说,美国环境法的公民诉讼条款都会授权法院发布禁止令,要求停止污染行为,或者要求主管机关采取具体行动,以遵守法律规定的要求。例如,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TVA v. Hill)一案中,为保护一种濒临灭绝的鱼,法院认为,其违反《濒危物种法》,发布了一个禁止修建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大坝的禁止令。第三,公民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依据系环境法律,诉前通知程序起到了预防作用。据学者统计,有22部主要的联邦环境法律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注]王曦,张岩.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J].交大法学,2015(4): 27-38.法官在审理环境公民诉讼案件时,往往适用环境法律,从前述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即可看到《濒危物种法》得到适用。第四,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诉前通知程序制度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据统计,1995年到2003年,根据《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的规定,“受环境影响的公民向州和地方政府发送了729份诉前通知,最后,起诉到法院的有336件”。[注]王曦,张岩.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J].交大法学,2015(4): 27-38.在大多数案例中,州和地方政府都在诉前通知期内纠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注]王曦,张岩.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J].交大法学,2015(4): 27-38.综上所述,作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公民诉讼具有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特点。

表1 美国联邦环境法律对公民诉讼制度的规定条款
(三) 日本的环境诉讼之预防性司法救济的立法考察
日本环境法上也没有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概念。在日本,“以防止公害于未然,保全环境、保护自然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诉讼,在具体内容和在诉讼形式上都是多样化的”。[注]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2: 246.与环境公益诉讼类似的诉讼是住民诉讼、附加义务诉讼和公害的事前中止诉讼。日本环境保护诉讼之预防性司法救济特点如下: 第一,环境保护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对象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例如,住民诉讼主要针对对象为地方公共团体违法的环境保护公共行政措施,而且是与财产有关的行为。田子浦的泥状沉积物公害事件是较为著名的住民诉讼案例。法院最后判决,要求4家公司向县政府支付1000万日元的赔偿。[注]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2: 245.又如,附加义务诉讼针对的救济对象是行政机关对企业的事业活动的监督指导的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对事业者危害环境的行为放任,将会给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结果。第二,环境保护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救济责任承担方式为中止请求,表现为“公害的事前中止诉讼”。其主要涉及垃圾焚烧场、填海造地处理场、火力发电厂和高速公路等“嫌忌设施”,因为这些设施通常容易发生大气污染、产生噪声等环境污染之虞,所以需要防患于未然。在1964年“东京都垃圾焚场”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能更好地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取得‘行政中止’,制止填海造地行为,对环境保护更为有益”。[注]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2: 247.所以,中止请求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将来受害的预防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通过对德国、美国、日本的立法来看,预防性司法救济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对象,应当针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行为或不作为提起诉讼;第二,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责任承担方式为禁止令或中止请求;第三,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基础主要是环境保护法律而非民事侵权法。因此,从各国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相类比的环境诉讼经验来看,环境公益诉讼都应当突出其预防性救济制度的事前救济,而不是强调对环境损害和生态损害的填补性的事后救济。
四、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实现路径
环境公益诉讼应当体现风险预防的价值目标,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具有预防性功能,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建立预防性司法救济。通过对国内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现状分析以及对域外相关制度的考察,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构建以行政机关行为为救济对象,以禁止令为责任承担方式,以环境法律为司法救济依据的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救济制度。其实现路径具体如下:
(一) 预防性司法救济对象的突破: 针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或不作为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救济对象应当作出突破,包括行政裁量行为、非行政裁量行为以及不作为行为。第一,行政裁量行为。行政裁量行为也就是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此类行为应当包括取消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行为,其目的是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环境开发或利用的行为人,预防其不合法地产生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后果。例如,因飞机噪声取消机场的航空运输执照。第二,非行政裁量的行政行为。非行政裁量行为主要是指抽象行政行为。此类行为指土地利用规划、区域开发规划、环保机关制定排放标准等行为。第三,行政机关的环境保护上的行政不作为。此类行为主要是指行政不作为,即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环境监管职责。当然,对于行政不作为的行为监督,应当设置诉前通知程序,一是给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环保职责的机会;二是防止公民的诉讼权利的滥用。
(二) 预防性司法救济手段的突破: 建立禁止令或中止请求制度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救济手段应当作出突破,应以法院发布禁止令或支持中止请求作为主要的救济方法。禁止令或者支持中止请求,可以请求法院对企业发出,也可以对行政机关发出。针对企业发出的禁止令或支持中止请求,可以直接针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行为、措施以及正在进行的环境污染行为作出。针对行政机关发出的禁止令或中止请求,则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怠于履职行为或履职不到位的环境保护机构或可能影响环境的其他行政机关作出。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信息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的行为,法院可以通过发布禁止令或支持中止请求的方式,强制要求企业或者行政机关予以实施。
(三) 预防性司法救济依据的突破: 建立适用环境法律的制度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救济的法律依据应当作出突破,包括环境法律、行政诉讼法。具体选择路径如下: 第一,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基础,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适用环境法律,而不是援引其他实体法。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目前采取的是援引其他法律的方式,处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行为。[注]《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64条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和损害补偿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参照此条款规定,《环境保护法》可以增加一条规定,“对可能造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或负责的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组织或人民检察院有权申请法院发布禁止令”。第二,采用法律解释方法适用环境法律和《行政诉讼法》。这里涉及的主要法条是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条和第58条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上述规定体现了环境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因此,该条同样适用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第58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规定并未明确必须具有损害结果,因此应作为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救济启动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规定主要可以解释一些行政怠于履行法定环保法定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上述条款均应当通过法院的具体适用,使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救济制度真正得以构建。笔者认为,司法机构对《环境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的直接解释和适用更为重要,而不仅仅依赖于《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只有如此才能够使环境公益诉讼不再拘泥于对已有环境损失结果的诉讼上,而是能够发挥“阻止或者停止将要进行、正在进行或者已经进行的环境损害行为”的预防性救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