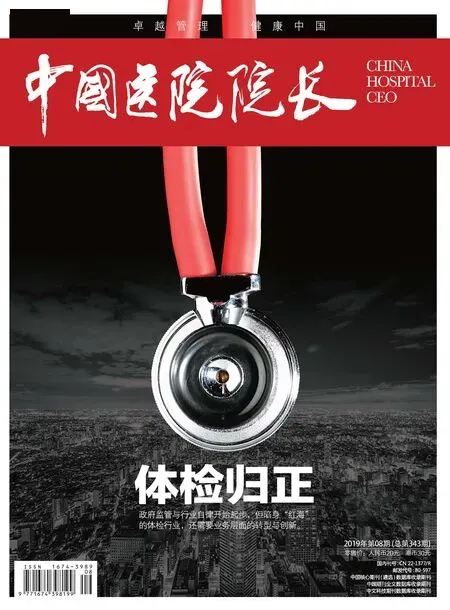中国新医改中公共财政转型的战略意义
文/顾昕
公共财政的转型,尤其是公共财政在诸如医疗卫生这样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自2009年启动以来,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新医改”)经历了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如公立医疗机构当中并非罕见的过度医疗行为,常常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诟病。一种极为流行的见解是把弊端的根源归结为政府财政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太少。无论是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各类公立医疗机构管理层,都在大力呼吁政府增加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医疗卫生界代表对于“政府增加投入”的呼吁更是不绝于耳。在很多人看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似乎就是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公益性淡化”的根源;而只要政府增加财政拨款,公立医疗机构自然就会“回归社会公益性”。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已经成为医改领域中的一句套话。
但是,财政部门则倾向于认为政府投入多寡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有限的财政投入如何使用。换言之,并非投入水平,而是投入机制与社会公益性的关系,更值得关注。早在2007年的“两会”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曾经表示,医疗领域中的问题决不是仅仅花钱就能解决的,“没钱是万万不能,但钱也不是万能的。只有把政府投入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当然,卫生部门对此也“深有同感”。在同样的场合,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批驳了“医改很简单,财政部拿钱就行”的说法,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卫生部与财政部观点一致,就是政府增加投入必须与转变医院运行机制相结合。光增加投入,不转变机制,是达不到医改的预期目标的”。
尽管如此,“政府投入不足”时至今日依然是医疗供给侧改革进展不利的一种托辞,其中不断包含有政府应该对公立医疗机构实施全额拨款的呼吁。卫生部门在2010年推出的“子长模式”,将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概括为:“政府全额拨款,公立医院回归公益”。2018年3月,“两会”期间,一位拥有政协委员身份的医界人士建议:把独立非盈利的卫生行业单位从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变成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这一建议赢得一些媒体的喝彩。这一托辞或呼吁貌似理据十足,乃至当医疗界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常常是不假思索的,而广大听者(尤其是新闻媒体)也都应声附和。然而,中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投入究竟足不足?医疗事业的政府投入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机构的支付究竟是不是政府投入的一部分?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究竟应该通过何种机制加以实施?这些问题,都亟待系统性地分析。

公共财政的医疗投入须遵循三大原则
毋庸多言,财政投入的多寡以及投入机制关涉新一轮医疗改革的走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而且,政府如何通过追加财政投入来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对于我国整个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因此,通过系统性分析直面上述问题,对于推进医疗事业公共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公共管理的基本原理、公共治理理论的前沿发展以及中国医疗事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可以断定,公共财政在新时代医疗事业中的投入必须遵循如下三大原则,而这三项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治理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第一,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投入,但由此而认为医疗事业应该由政府包办,那就大错特错了。医疗事业的投入来源应该多样化,有来自政府的,也有来自市场的,还有来自社会的。政府投入的目的,其一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慈善失灵),也就是在市场和社会资金不愿意投入、而民众又需要的地方和领域加强投入;其二是要引导市场和社会资金的流向,从而使医疗事业的宏观发展格局更好地符合公众利益。
第二,政府投入不只是财政预算投入。在国际上,医疗政府投入的增加意味着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公共财政支出既包括财政预算支出,也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换言之,医疗公共投入并不仅仅意味着财政预算投入,而公立医疗保险支出也是公共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举世皆然。增加政府投入,必须一方面强化财政预算直接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和支付水平。这是全球的通行惯例,中国只能并且应该同国际接轨。在中国,有关加强政府投入的呼吁,自觉不自觉地把政府投入简单地等同于财政预算投入,这是大错特错的,也深具误导性。这种观点忽略了公立医疗保险在公共财政尤其是政府医疗投入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全民医保的巩固与发展,公立医疗保险筹资和支出的总量会逐年攀升,其在政府医疗投入中的比重,会有所提高。
第三,增加政府投入不等于排斥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政府投入的增加需要跟进市场,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行政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充分发挥政府购买对于市场的引导作用;同时,政府投入更要致力于激活社会,让社群机制在治理创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全球性公共管理和福利国家改革浪潮的主线。公共治理现代化从国家大包大揽公共服务的所有责任向“公共支持私人责任”(public support for private responsibility)的理念转型,也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社会,即家庭、社区和非营利性组织,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政府主导等同于行政机制的主导,并采用回归计划体制的做法,或者将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进行板块式组合,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而忽视社群机制的作用,致使本应基于社群机制的法人治理和协会治理名不副实,更是中国医疗事业公共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短板。
公共财政的医疗投入重点是什么
具体而言,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扮演着医疗筹资和付费的重要角色。但是,医疗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单靠商业性医疗保险和慈善性医疗保险,不可能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因此,没有政府主导,单靠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全民医保根本不可能实现。没有全民医保,医疗事业的社会公益性也就无从谈起。既然如此,政府就责无旁贷,在这一领域扮演其应有的角色,以保险者、推动者和付费者的身份,推进全民医疗保障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医疗服务领域尽管也存在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但在医保体系覆盖全民的情况下,社会公益性中所有人有病能医的目标可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完全可以市场化运作,而营利性医疗机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医疗服务市场中展开竞争,只不过其各自的市场细分有所不同而已。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在市场和社会投入都不足的地方,即在基层(社区)、农村和偏远地区,加强投入,以确保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设立特别的公立机构,对医疗全行业实施一视同仁的监管(或规制)。
因此,公共财政在医疗事业中的投入重点,在于医保体系,在于特定的医疗服务地域(如社区、农村和偏远地区)和领域(公共卫生、基本卫生保健以及其他具有正外部性的特殊医疗服务),在于特定的服务事项(如监管)。事实上,自新医改启动以来,公共财政转型在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公共治理创新上,贡献良多。首先,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医疗筹资的政府职能回归,其结果是,中国卫生总费用大幅度提升,卫生公共支出占比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补需方”的强化及其制度化,不仅使医疗保险体系得以实现全民覆盖,而且还为新医改新时代全面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进而重构医疗供给侧激励机制奠定了基础;最后,医疗领域公共财政转型的方兴未艾之举,在于推动“补供方”或“投供方”的治理变革,即改变以往按编制拨款的行政化旧模式,代之以政府购买的市场化新方法。这些改革之举,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些转变的深远意义,只有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新发展战略,公共财政的运行在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公共财政在民生领域或国际上通称的“社会领域”(social sectors)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公共财政的转型体现了政府转型的某些新趋势,即从注重经济转向注重民生、从政府大包大揽的施政模式转向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模式、从依赖行政化等级体系转向运用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公共财政转型的具体体现有三:一是公共财政的卫生筹资功能强化,从而体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社会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承担主要筹资责任的核心职能;二是政府在增加卫生投入的同时,充分意识到责任的有限性,放弃大包大揽(即独揽卫生筹资和服务提供)的传统模式,更加注重动员非国有资本(即所谓“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提供领域;三是新增政府卫生支出更多地投入到医疗保障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的格局,推动医疗领域形成一种新的市场机制,即公立医疗保险机构代表参保者集团购买医药服务。公立医保机构成为参保者的代理人,扮演医药服务付费者的角色,行使为参保者集团购买医药服务的职责,在国际上被称为政府对医药服务的“战略性购买”,而以政府战略性购买为核心在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公共契约关系,正是新医改中所谓“市场派”的核心思想。
公共财政的转型,尤其是公共财政在诸如医疗卫生这样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是由两大截然相反的力量所推动的:其一当然是市场力量的释放;其二则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与社会保护体系的二元发展,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秘密。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市场转型。在2000年以前,中国市场转型的主轴是市场力量的释放。正是借助于市场力量的释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相当一部分民众陷入各种社会风险(social risks)之中,亦即面临因失业、疾病、伤残、退休等问题所带来的风险。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市场转型进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不再单兵突进,社会发展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开始成为新历史时期指导中国发展的全新原则。

没有政府主导,单靠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全民医保根本不能实现。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无疑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社会保护体系的完善是这一新发展理念的中心内容之一。在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保护体系在帮助民众防范与应对负面的社会风险从而推进财富创造上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只有在完善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护体系,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构建起来。
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离不开政府责任,尤其是政府在筹资上承担积极的责任。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公共支出的绝对水平及其占GDP的比重都提高了,其主要根源在于社会支出(social spending)的总量及其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都大幅度提高了。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看起来矛盾但却意涵深刻的现象,即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导致公共部门规模缩小,但是各国政府用于民生的社会支出水平却没有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同以往人们将社会支出视为纯粹消费的观念有所不同,当代社会经济史学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中公共财政社会支出的多少,尤其是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对该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公共财政社会支出的扩大,或者说社会政策的发展,不再是只花钱、无效果的社会消费,而是一种“社会投资”;社会支出所投资的领域,就是“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其重要性不亚于实体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的建设。一句话,社会福利国家(the social welfare state)已经并且应该转型为社会投资国家(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公共财政转型的关键——实施机制
当然,政府仅在增加社会支出上有积极的表现是不够的。公共支出如何产生应有的效果,才是公共财政转型的关键。传统上,一旦政府决定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一般都会直接设立公立机构直接为民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这种“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不仅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宰的地位,而且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福利国家中也一度非常盛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战后20多年福利国家的大扩张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弦更张,大力裁撤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公立组织。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福利国家收缩的大潮中,政府的社会支出并没有相应消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了民营非营利性组织,少部分甚至流入了营利性组织。由此,西方的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走上了“公私合办福利”(public-private mix of welfare provisions)的道路,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民营非营利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新模式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全球性福利国家的改革是全球性公共管理变革的主战场之一。在这一改革浪潮中,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日益走向多元化,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愈来愈多地参与到公共服务领域,但是国家并没有退出,而是扮演公共服务出资者、推动者和监管者的角色。针对这一改革浪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政策专家内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了“能促型国家”(the enabling state)的理念。这一理念旨在颠覆传统的福利国家观念,具体体现为如下三大观念性变革:第一,相当一部分公共服务从政府直接提供向民间提供转型;第二,从国家直接拨款支持向国家间接支持公共服务转型;第三,从国家大包大揽公共服务的所有责任向“公共部门支持民间承担责任”的理念转型,也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民间,即个人、家庭、社区和非营利性组织,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简言之,政府转型的核心在于如何增进市场、激活社会,通过市场化手段或民间非营利性的组织和行动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这已经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核心学术论题之一。
在世界各国,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都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福利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福利国家的转型同步,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虽然各国的改革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大共同趋势依然可辨:一是医疗保障体系走向全民覆盖,亦即走向全民医保,其中政府在医疗保障筹资中扮演积极而有效的角色,即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20世纪持续稳步提高,即便是在福利国家收缩的大背景下这一趋势也没有遭到逆转;二是医疗服务递送体系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其中政府以购买者(通过公立医保机构)、监管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参与到医疗服务的市场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国医疗保障领域以及公共财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变化,恰恰同全球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相吻合。在很大程度上,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即通称的“新医改方案”)在医疗保障和卫生公共财政的改革上,指出了与全球性大趋势趋同的新方向。
然而,公共财政转型对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治理变革所产生的战略意义,在既有的文献之中,无论是智库报告还是学术论著,都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