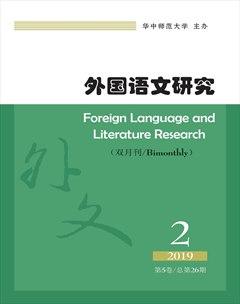小说《灿烂千阳》中的复调书写
内容摘要:小说《灿烂千阳》运用复调的技巧展示了杂语和它们各自所对应的意识,它们在共时作用下产生对峙,实现情节的急转和剧变,既是作者精湛写作技巧的展现,又是强烈情感的力量来源。各种杂语又进行对话,甚至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多种声音的对话,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揭示了阿富汗人的灵魂世界。对位法则下不般配的俯就、闹剧场面和临界点上的人物所体现的狂欢化精神则是对阿富汗男权世界的反抗。胡赛尼的复调书写是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也体现了作者作为西方社会的穆斯林为打破偏见积极寻求该群体与西方主流社会对话的积极姿态。
关键词:复调;杂语;对话;双重性;狂欢化
作者简介:吴龙桓,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
Abstract: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adopts the strategy of polyphony, skillfully presenting heteroglossia and their embodied attitudes. Their coexistence and confrontation push the plot to develop and as well as bring about intense emotions. Various voices can be found even within one character. Consequently, the inner life of Afghanistans is revealed. Carnivalism implied in condenscendence, farce, and characters at their critical moments articulate a resistance against Afghan patriarch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Khaled Hosseini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polyphony serves as an effort to set free from prejudice about Afghanistan and pursue a dialogue between Muslim society and western mainstream society.
Key words: polyphony; heteroglossia; dialogue; dualism; carnivalism
Author: Wu Longhuan is lecturer at Humanities College, Nanjing Arts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Her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aishuinunu@126.com
卡勒德·胡塞尼在《燦烂千阳》中对阿富汗女性的描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笔者认为,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小说中的复调书写。复调小说理论起源于巴赫金对陀斯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重点着落在思想性,热奈特从形式上进一步拓展了复调理论,而昆德拉对复调理论的阐释则考虑到小说文体与叙事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并表现出了对狂欢化理论及现象的偏爱(李凤亮 92-97)。《灿烂千阳》通过叙事结构上不同的声音、共时性冲突、多重性对话和对位法则的狂欢化因素,揭开了阿富汗女性神秘的面纱。在世人眼中,阿富汗贫穷落后,恐怖主义盛行。胡赛尼就读医学院时曾因为自己的阿富汗血统而被同学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象征(Hosseini C1)。911事件之后,业已从医的胡塞尼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美国社会对阿富汗的偏见,在家人的鼓励下,“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在业余时间投身写作,并以阿富汗三部曲屹立于美国文坛。胡塞尼一直在探究灵魂的悸动和人物内心的呼号,从未背离他当初投身写作的初衷。就叙事而言,《灿烂千阳》是一部承上启下并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斯特拉·艾尔古-巴克诗在评价《追风筝的人》时指出,“胡塞尼不喜自我意识小说,他相信讲故事的手法更重要,好的讲述方式会将读者一直牢牢抓住”(Algoo-Baksh 143)。他对叙事方式的重视在三部小说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手法也日趋娴熟。译者李继宏曾撰文指出《追风筝的人》“文笔略显稚嫩”(李继宏 428),第二部小说《灿烂千阳》的叙事则开始复杂化。胡塞尼本人也说,“就某些方面而言,创作《灿烂千阳》要比《追风筝的人》更让我满意,因为它是一个更为复杂且猜不到结局的旅程”(转引自尚必武 8)。读者在《追风筝的人》中看到的是一个灵魂饱受折磨的少年,作家在《灿烂千阳》中继续对灵魂的探究,文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思想开始对话,对位法则应用到作品布局,体现了矛盾性和两重性,所有这些特点在《群山回唱》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臻于成熟。可以说,《灿烂千阳》是有着明显复调色彩的小说,它的风格昭示了《群山回唱》的出现,而这种手法对于复杂内心世界的挖掘也是胡塞尼作品中情感力量的来源。
一、不同的声音和它们的主体意识
巴赫金将复调定义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巴赫金 29)。《灿烂千阳》中不同声音产生的土壤源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阿富汗。现代阿富汗既有强大的部落保守势力,也不乏努力革新的领导人。1919年阿曼努拉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他的政策几乎没有赢得大众的支持,却造成阿富汗社会文化精英阶层的重大分歧……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分裂,并传导至农村地区”(阿德尔 363)。这种分裂体现在小说中长达三十余年的一系列事件中,从国王执政、达乌德政变、苏联入侵、圣战者组织抵抗活动、马苏德被杀一直到塔利班执政,分裂也存在于中央政府力量与部落首领势力之间,城市女性与农村部落女性之间,革新与保守附着在各色人物身上,他们是作家描写的客体,也是这些意识的体现。小说中既有阿富汗男权社会的代言人,如拉希德,也有代表阿富汗美好品质和希望的人物,如玛丽雅姆和莱拉,还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识纠缠角逐的同一主体,如扎里勒。
代表着阿富汗保守势力的拉希德虽然年老,经济上也只是个尚能自足的手艺人,但在两位女主人公面前,却表现的异常强大。四十多歲的拉希德以极小的经济代价娶了只有十几岁的玛丽雅姆,把她当做生育工具,对她颐指气使。后来玛丽雅姆丧失了生育能力,等待她的就是无休止的家暴。拉希德七十几岁的时候,又娶了年仅十几岁的莱拉。出生于小康之家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莱拉也没有逃过玛丽雅姆的命运。拉希德能够肆无忌惮的作恶,是因为阿富汗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女人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存。这个人物的塑造从侧面说明落后保守力量在阿富汗的强大,是塔利班产生的土壤,西方社会因此对阿富汗产生偏见也就不足为奇。可贵的是胡塞尼在这样的偏见中,用复调书写呈现被西方读者所忽视的声音和主体意识,比如传统女性玛丽雅姆、开明的新女性莱拉以及摇摆于不同意识间的扎里勒等。玛丽雅姆是扎里勒与自己的女仆娜娜的私生子,被父亲抛弃,尚未成年便下嫁,婚后遭遇丈夫的迫害,是这个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造就的苦难中,她的隐忍、坚强和奉献精神不啻于黑暗中的航灯,指引着阿富汗新生代的代表莱拉走向光明和希望。作品中最令人信服的是对摇摆于不同意识之间主体的书写,扎里勒便是这些群像中的典型人物。他抛弃了娜娜母女,却又在种种场合表达着愧疚,和儿子亲自动手为娜娜母女盖屋,每个月送生活用品,每周准备礼物探望女儿,言辞极尽温柔耐心,却又能在玛丽雅姆登门之际狠心将其拒之门外。他亲手将女儿嫁给了年长她三十多岁的拉希德,后来却又千里迢迢跑到她家门前乞求原谅。以扎里勒为代表的人物身上体现了保守与进步之间的角逐,时而展示善良和美好,时而呈现罪恶和痛苦,体现了人性之复杂,也让人物的塑造更为真实可信。
胡塞尼刻画的芸芸众生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对应着自己的小世界。这些多元的小世界,一旦进入同一个事件,众多的意识尤其是迥异的意识便会对峙,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通过共时,不同的主体会发生对峙,如拉希德与两位女主人公的对峙,玛丽雅姆和莱拉在莱拉投靠拉希德之后的对峙,法丽芭与哈基姆的对峙等等。 这些对峙反映的是阿富汗政治时局的混乱。同一主体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共时作用下也会产生对峙,娜娜对扎里勒又恨又爱,扎里勒对娜娜母女又愧疚又嫌弃,玛丽雅姆在童年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婚后又因母亲自杀的负罪感而忍气吞声,失手杀死暴戾的丈夫却又觉得自己夺走了儿子的父亲而心存愧疚;莱拉被迫下嫁拉希德,她恨丈夫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察尔迈依。除了主体意识的对峙,共时原则也会导致令人瞠目的情节剧变(巴赫金 60)。玛丽雅姆来到扎里勒家之际,便是娜娜自杀之时;莱拉被拉希德痛殴之际,便是玛丽雅姆杀夫之时。通过共时,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聚拢,使作品形成强有力的紧张气氛,亦是作品强烈感染力的来源。
琼·史密斯在评论《灿烂千阳》时指出,与《追风筝的人》中的背井离乡不同,《灿烂千阳》的故事背景只设置在阿富汗(转引自Blumenthal 250)。胡塞尼通过众多意识的对峙,展现了阿富汗社会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通过他的书写,读者可以看到即使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也有着哈基姆,法苏拉赫毛拉,单莎伊,塔里克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人物;读者对阿富汗伊斯兰社会的认知将会有所改变,会摆脱贫穷、落后和恐怖主义的刻板印象。对人物自我意识的描写,众多声音以及事件中众多意识的对峙这些特点在《群山回唱》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升华,读者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各种意识之间的对峙也更为频繁激烈。复调小说的主旨是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自不同的独立意识,也正是这些独立的意识和悸动的灵魂构成了阿富汗。
二、不同声音的对话
在一个有着众多声音的多元世界,贯穿始终的对话关系将它们衔接起来。这种对话既包括涉及小说结构的大型对话,也包含了散见于作品中的微型对话。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玛丽雅姆和莱拉两条线索分头而进,一个是身世悲惨的私生子,一个是开明家庭的心爱女儿,在阴差阳错的命运中,她们先后嫁给了一个丈夫,两条原本平行线索交汇于此。两人在共同的婚姻生活中从敌视到情同母女,因为共同的压迫而携手。在拉希德对莱拉的一次毒打中,玛丽雅姆杀死丈夫,两条汇聚的线索在此又朝不同的方向延伸,两人就此别过,莱拉逃到穆里,玛丽雅姆入监然后被处死。莱拉在获救后去寻找玛丽雅姆的童年住所时,两条线索又最终交集,她与童年时的玛丽雅姆相遇在幻境,并能感受到玛丽雅姆的希望和未来在她身上得以延续。这种复式结构在《群山回唱》中发展的更为复杂,主人公之间不仅仅局限于对立式的组合,而是有着更多的混合,虽是不同的篇章讲述了不同的人物故事,但篇章之间有内在联系,并形成了复调小说的互文性(项霄 12)。通过这种手法,作者为读者设置了更多的阅读期待和惊喜。
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玛丽雅姆与父母的对话向读者讲述了她的身世,作者在此并未过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将这些非曲直留给读者品味。玛丽雅姆与扎里勒司机的对话讲述了认亲失败和娜娜之死,通过人物对话而不是作者的叙述,更好的表现了年少的玛丽雅姆对于耻辱的切肤之痛以及面对母亲死亡的惶然无助。玛丽雅姆与扎里勒妻子们的对话确定了她的婚事,与拉希德成婚之际的一番对话,为她今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了悲剧的伏笔。拉希德收留失去双亲的莱拉,他与莱拉和玛丽雅姆的对话确立了又一桩婚姻。玛丽雅姆和莱拉在三杯茶的谈话中,化敌为友,在互诉心曲中了解彼此的身世。小说主要人物关系结构也呈现着对位的对话关系。玛丽雅姆和莱拉起初是邻居,是苦难的承受者和旁观者,在莱拉嫁给拉希德后,是敌视和戒备的妻妾,在女人地位低下的婚姻里是心意相通的母女,也是面临社会压迫时的战友。在玛丽雅姆死后,莱拉寻访她曾经生活过的泥屋,尽管时空交错,但依然是她与玛丽雅姆一次心灵对话之旅,此时的莱拉知晓并理解了童年玛丽雅姆的困惑和渴望,她代替玛丽雅姆接受了扎里勒的悔过和歉意。从家庭的意义来说,她是玛丽雅姆血脉的延续,从精神层面而言,她继续了玛丽雅姆的成长,为未来留下无限的可能。
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具有双重性,因此,在同一个人物内心,也会出现不同声音的对话。正如巴赫金所言,对复调作品的主人公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什么”(巴赫金 82)。 玛丽雅姆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正是这种双重意识的体现。娜娜骂她是个私生子,扎里勒却称呼她为蓓蕾;扎里勒说带她拜访过树下埋葬的诗人,娜娜却说扎里勒在撒谎;娜娜说玛丽雅姆出生时自己是独自生产无人过问,扎里勒却说安排了娜娜在医院生产;扎里勒带给玛丽雅姆挂坠并说她戴上后像个女王,娜娜却说挂坠不值钱;娜娜在扎里勒不在的时候骂骂咧咧,扎里勒来拜访时却又很温顺,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笑的时候也不忘遮住坏掉的牙齿。童年的玛丽雅姆从父母的对话和自己的观察中,不停的探索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她的内心世界,类似的对话一直未曾停息,如发现拉希德的色情杂志之时,第一个孩子流产之际,种种声音将玛丽雅姆饱受折磨的灵魂袒露无疑。也正是这些声音的交锋展现了一个沉默但痛苦的阿富汗女性。
另外一位主人公莱拉出生在开明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因为战乱与恋人分离被迫下嫁老迈的鞋匠拉希德。她与玛丽雅姆的对比会让读者觉得她们是两个世界的女性,命运完全没有交集的可能。莱拉在答应拉希德的求婚之前,她的内心世界集结了多种声音,读者可以听见她对塔里克的爱,对生活的绝望,对玛丽雅姆的愧疚,也能听到玛丽雅姆的反感排斥和世俗标准对她这种行为的的评价。正是这一段对莱拉内心世界多种声音的书写让一个原本懵懂的少女一下子蜕变成刚强的母亲。此时,作者巧妙自然的完成了情节的反转,让莱拉走入玛丽雅姆生活的地狱。这一段衔接之精巧有力,不啻于四两拨千斤。类似的场景在后面的故事中还会再现,比如莱拉发现自己怀上拉希德孩子后那种爱恨交织的矛盾瞬间,与初恋塔里克百感交集的重逢时刻,这些不仅带来情节的急转,也向读者呈现了复杂的内心世界。胡塞尼将阿富汗女性在苦难冲击下内心的挣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丰满而具体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书写无疑是西方穆斯林群体有力的呼喊,是寻求与西方主流社会对话的积极姿态。可以说,胡塞尼用文学的方式开启了穆斯林与西方社会一种新的对话模式。“通过对话,可以增进理解,促进公平,这对于不掌握权力且边缘化的群体来说,尤其重要”(转引自Young 221)。小说中所展现的人性之丰富,并不逊色于西方社会中的人物,那么人们对阿富汗的理解就不会拘囿于贫穷和恐怖,而是会抛弃偏见,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范畴。
三、对位法则的狂欢化因素
胡塞尼本人虽是阿富汗裔,但自小接受西方教育,作品里体现的理念,如平等、自由、妇女权益等,无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潘苏悦 170),胡塞尼也强调过自己虽然写的是阿富汗故事,但他并不是阿富汗发言人(Adams R1)。由此可见,胡塞尼的写作仍然是西方文学的范畴。巴赫金提出的狂歡化是对应复调原则的一种情节布局和体裁,在他看来,狂欢化文学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穿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等名家作品之中,在近现代的狄更斯、斯特恩和爱伦·坡等人的作品中不断发展传承(巴赫金 221-223)。胡塞尼本人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伊恩·麦克尤恩和门罗这些西方作家(Evans 80)。所以,胡塞尼对西方文学中的狂欢化精神并不陌生。尽管《灿烂千阳》的基调悲伤隐忍,但它所描绘的世界是对立和矛盾的结合,对位法则下的俯就、闹剧场面和处于临界点上的人物无不体现着狂欢化的色彩,而这种狂欢化的精神对阿富汗单一的、教条的和独裁的男权社会无疑是一种反拨和削弱。
《灿烂千阳》里的俯就关系和闹剧场面发生在阿富汗传统社会遭到破坏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代,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对话结构体现的是不同阶层的声音和对峙,世界变得混乱荒诞,女性的悲剧实质上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玛丽雅姆是当地首富的女儿,却生活在贫困和歧视之中,豆蔻年华被许配给老鞋匠拉希德;哈基姆和塔里克思想开明,尊重女性,但他们高尚的灵魂却困在或残缺或矮小的身体里;玛丽雅姆在莱拉一家人的眼中是个可怜的女人,谁知命运弄人,莱拉在战争中失去父母,违心嫁给了拉希德,与昔日的邻居长辈玛丽雅姆的命运就此交织。高贵与低微,老翁与少女,年长女性与邻居小女孩,高尚与粗俗,包容与狭隘,这些鲜明的对比和不般配的俯就把美好事物走向毁灭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为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那么西方对阿富汗的关注不会局限于偏见,而是会理解这个国家的苦难,甚至为这些普通人的命运而有所行动。在狂欢化的闹剧场面中,人们之间的等级地位消失,充满了变化和骗局。这样的闹剧场面在《灿烂千阳》中并不鲜见,比如扎里勒探望童年的玛丽雅姆,拉希德向莱拉求欢。扎里勒每周会来探访娜娜母女,他和身份悬殊甚至连外表都落差极大的母女围坐一桌,场面尴尬又令人发笑。娜娜与扎里勒相互打招呼时生硬的笑,扎里勒对女儿温存的笑,玛丽雅姆面对父亲时幸福的笑,还有娜娜神经兮兮的笑,种种笑声仿佛掩盖了娜娜母女平时的苦难。另一个闹剧场面出现在拉希德收留受伤的莱拉这一场景。无论是莱拉、玛丽雅姆还是拉希德都未曾想到过他们会共处在同一屋檐下,然而战争却让这一幕成为现实。老鞋匠拉希德出现了种种古怪的行为,用刀叉吃饭,使用文明礼貌用语,笑声爽朗,甚至还热心为莱拉打听塔里克的下落。后来面对玛丽雅姆的质问,拉希德得意的笑声揭开了求欢这荒唐的一幕,陌生人带来的塔里克遇难消息更是他一手导演。荒诞的闹剧场面是阿富汗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使得悲剧的书写更加有力,也为后来对塔利班控制下极权社会的反拨埋下了伏笔,正如罗伯特·罗森(Robert Lawson)所说,“狂欢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引发欢笑,而是通过这种手法折射出其他传统美学手段不能表现的事物”(Lawson 46)。
《灿烂千阳》的情节布局本身是一种对话关系,塑造的人物也呈现对位关系。由于主人公常常处于临界点上,随时准备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一旦发生变化,他(她)们相应的对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往往结合了嬗变和危机,出现了加冕脱冕的仪式象征。童年的玛丽雅姆知道自己是私生子,面对母亲对父亲的指责,她认同母亲的痛苦但又崇拜父亲,在15岁生日的时候坚持要到父亲家登门拜访。然而,父亲拒不相见,母亲愤而自杀,之后玛丽雅姆被父亲匆匆嫁给拉希德。结婚时的签字和戒指交换正是加冕仪式的象征,玛丽雅姆告别了之前的天真,戴上戒指的她也种下了身为哈拉米的深深自卑和导致母亲死亡的罪恶感,成为鞋匠逆来顺受的妻子。莱拉也经历了类似的加冕仪式。她出生于开明的家庭,父亲非常重视她的教育,要培养她上大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然而一场战争夺走了莱拉的一切,她被迫嫁给拉希德,在签订婚约戴上戒指的时候,一个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美丽姑娘居然成了老鞋匠的妻子。通过这个加冕仪式,莱拉从小辈变成平辈,从邻居小女孩变成新妻,她与玛丽雅姆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个人从敌视到同情再到情同母女,她们之间的对位关系也随之变化。拉希德之死带来了玛丽雅姆的入狱和莱拉的出逃,此时的她们已经一无所有,脱冕仪式不是通过具体的物品来完成,而是她们相同的一个动作:闭上眼睛。玛丽雅姆在被处决前闭上双眼,内心却获得了安宁,因为她不再是卑微的哈拉米,而是以母亲的身份离开人世。莱拉之后寻访玛丽雅姆住过的泥屋,她进入泥屋后也闭上眼睛,看到了幻境中的玛丽雅姆,看到她的希望、信念和爱,自己也成为了玛丽雅姆的延续,成为阿富汗女性美好品质的延续。加冕脱冕本质上是一种更替和变化的精神,它不仅呈现了主人公命运的转折,更是蕴含了希望,是对阿富汗男权社会下女性命运的一种解构。
四、结语
作为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文化背景和故事发生地又是西方世界极其陌生乃至有着诸多隔阂的阿富汗,胡塞尼却在《灿烂千阳》中展示了一个生动真实的世界,揭示了阿富汗女性的苦难和希望,西方读者仿佛能感同身受。因此,胡塞尼在西方评论界备受称赞(Ghafour 54)。他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切入政局动荡下的阿富汗,运用复调的技巧为读者展示了众多不同的声音和它们所各自对应的意识,它们在共时作用下产生对峙,实现情节的急转和剧变,既是作者精湛写作技巧的展现,又是强烈情感的力量来源;它们又进行对话,甚至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多种声音的对话,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揭示了阿富汗人的灵魂世界;胡塞尼也通过不般配的俯就、闹剧场面和临界点上的人物来书写阿富汗女性的悲剧,其狂欢化精神是对男权世界的反抗。毋庸置疑,《灿烂千阳》的复调书写与隐含的读者也产生了对话关系,因为“读者的意识状态相对于作者、人物及整个小说世界而言,同样是对话性的”(汪洪章 20)。小说中描写的具有矛盾性和未完成性的阿富汗,不仅仅是离散文学中作者所寻求的家园归属,更多的是承载了他作为西方社会的穆斯林打破偏见的意愿和积极寻求该群体与主流社会对话的积极姿态。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的复调书写呼应了巴赫金复调理论所对应的哲学,即生活维度的丰富性、更多的可能性和个人的成长空间(Stone 696),因此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dams, James. “Doctor of Suspense: The Author of The Kite Runner Releases His Second Novel Today.” Globe & Mail 22 (2007): R1.
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吴强、许勤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
[Adle, C.,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VI: Towards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From the Mid-nine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Wu Qiang and Xu Qinghua.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Algoo-Baksh, Stella. “Ghosts of the Past.” Canadian literature Mar (2005): 143-14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eotics. Trans. Bai Chunren and Gu Yal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Blumenthal, Rachel. “Looking For Home in the Islamic Diaspora of Ayaan Hirsi Ali, Azar Nafisi, and Khaled Hosseini.” Arab Studies Quarterly 34.4 (2012): 250-264.
Evans, Suzy. “Offstage.” American Theatre February (2017): 80.
Ghafour, Hamida. “Afghan Secrets.” New Statesman 28 (2007): 53-54.
Hosseini, Khaled, and Tamara Jones. “An Old, Familiar Face: Writer Khaled Hosseini, Lifting the Veil o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Post 28 (2007): C1.
Lawson, Robert. “Carnivalism in Postwar Austrian- and German-jewish literature—Edgar Hilsenrath, Irene Dische, and Doron Rabinovici.” Seminar: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1 (2007): 43-48.
李鳳亮:《复调:音乐术语与小说观念——从巴赫金到热奈特再到昆德拉》。《外国文学研究》2(2003):92-97。
[Li, Fengliang. “Polyphony: A Musical term and Fictional Concepts—From Bakhtin to Genette then to Kunde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3): 92-97.]
李继宏:《<灿烂千阳>译后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Li, Jihong. “Postscript.”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潘苏悦:《从卡勒德·胡塞尼作品看“移民文学”的发展趋向》。《外国文学研究》6(2014):166-171。
[Pan, Suyue. “Analysis on Diaspora Literatures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Khaled Hosseni.”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4): 166-171.]
尚必武、刘爱萍:《托起“灿烂千阳”的“追风筝的人”——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塞尼其人其作》。《外国文学动态》5(2007):6-8。
[Shang, Biwu, and Liu Aiping. “The Kiterunner Who is Holding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About Afghan American Novelist Khaled Hosseini.”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5 (2007): 6-8.]
Stone, Donald D. “Meredith and Bakhtin: Polyphony and Bildung.”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9 (1988): 693-712.
汪洪章: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阐释学含义。《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08):18-26。
[Wang, Hongzhang. “Hermeneutics in Bakhtins Polyphony Fiction Theory.” FuDan Symposium of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2 (2008): 18-26.]
项霄:《论<群山回唱>的复调》(硕士学位论文)。南宁:广西大学。
[Xiang, Xiao. On Polyphony in Mountains Echoed (MA thesis). Nanning: Guangxi University, 2015.]
Young, Demon A. “The Democratic Chorus: Culture, Dialogue and Polyphonic Paideia.” Democracy& Nature 2 (2003): 221-235.
責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