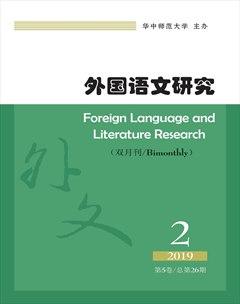为被禁言和沉默的历史发声
张甜 蔡圣勤
内容摘要:南非著名小说家安德烈·布林克的“现场写作”包含了对南非种族隔离时期被禁言、被压抑的历史的揭示。为了达成历史与现实的和解与妥协,形成观念的一致与社会重建,布林克认为南非公共知识分子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义务。本文试图通过批判《魔鬼山谷》中的白人主导叙事和女性的边缘化的历史事实,探讨文本中沉没在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里的历史问题,并为被其禁言和沉默的历史发声,体现了布林克作为作家对南非社会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关键词:布林克;《魔鬼山谷》;种族隔离;父权制;为历史发声
Abstract: The “writing at the spot” of South African famous novelist André Brink uncovers the silenced and repressed history in apartheid South Africa. To reach a compromise between history and present, form a consensus of ideas and stage social reconstruction, Brink argued that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South Africa should assume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Brinks meditation on historical problems repressed by apartheid and patriarchy, with the purpose of giving voice to the silenced, embodying his high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as a writer, to South Africa.
Key words: André Brink; Devils Valley; apartheid; patriarchy; giving voice to history
Author: Zhang Tian is lecturer at Wuhan College (Wuhan, 430212,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ture in English, western philosophy. E-mail: louisazhang910@163.com. Cai Shengqin, Ph.D.,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uth African English fiction, western philosophy, movi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link, 1935-2015)是南非當代著名的小说家、翻译家、文学理论家,与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和纳丁·戈迪默并称为“南非文坛三杰”。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笔锋力透纸背,为南非的阿非利卡文学和世界英语文学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纵观其近二十部作品可以发现,布林克以对社会弊端细致的观察、精妙的文笔,大胆的创作叩问两种形式的沉默:“男性支配下边缘化的女性的沉默,白人宏大历史主导下弱势族裔的沉默”(周小青 25)。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在南非政府实施的文字审查制度强权下,布林克仍然肩扛一位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长期口诛笔伐,对文字审查制度所禁止的话题(thou shalt nots)——性与政治,展开历史的与个人的对话。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刀,挖掘出被历史的长河所掩没的真实语言景观,为被禁言和沉默的历史发声。
布林克多部作品围绕着被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所淹没的历史和殖民地暴力的叙事,特别是白人宏大历史主导下弱势族裔的沉默和男性支配下边缘化的女性的沉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人道主义精神,其中可以看到布林克深深受到了阿尔贝·加缪的影响。布林克曾多次公开表示加缪是他的人生导师,“对我的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贝·加缪”(Diala 60-71),“加缪在情感和道德上彻底征服了我”(Baker 50)。而加缪的思想核心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布林克书写被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掩没的历史,叩问历史的沉默,其实也是将真实的历史和尊严归还给本该拥有的人。在布林克的众多作品中,《魔鬼山谷》(Brink, Devils Valley 1998)最能体现这一主题。小说记述了一个从“大迁徙”中分裂出来的阿非利卡社区雷米尔特家族的故事。他们在偏僻的魔鬼山谷定居下来,与世隔绝。布林克以犯罪记者弗利普·洛克纳为第一人称叙事,描述了这个反乌托邦社会:生者与死者共存,半人半兽随处可见,基础设施落后,山谷因长期干旱,一片颓败,疮痍满目,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魔谷掌权者打着基督教的幌子,利用极权统治社区,迫害女性,并执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婴儿被施以石刑——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社会的丑恶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反乌托邦的语言肌理中,犯罪记者弗利普试图挖掘并记录魔谷的历史,屡屡受挫,但最终挖掘出魔谷骇人听闻的秘密:对黑人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对女性的无下限的压迫。弗利普刨根问底,而记录魔谷历史的过程也渐渐唤醒魔谷里的女性。随着魔谷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弗利普也因挖掘历史而得罪魔谷当权者,不得已带着遗憾逃离魔谷。布林克通过弗利普来之坎坎的历史探寻过程,揭示了南非文字审查制度对布林克本人揭露南非历史的阻挠甚至胁迫的事实;犯罪记者在魔谷所见,直接暴露了南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暴力迫害;后期犯罪记者渐渐唤醒人们对魔谷集权的反抗,魔谷风暴肆虐,印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非暴力革命形式。旧的体制如果不再适应民众需求,势必崩溃瓦解。布林克表示:如果不试图用创造性的想象去抓取历史和历史中的沉默,南非社会将难以进步(Brink, “Interrogating Silence” 25)。总而言之,《魔鬼山谷》是南非黑暗过去的一个巨大隐喻,布林克的书写就是对过去的揭示。
一、白人历史主导下黑人的失语
自17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在南非最南端建立最早殖民据点开普敦,到20世纪初英布(英国人和荷兰人后裔)殖民者形成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欧洲白人向南非内陆不断蚕食,对当地黑人发动殖民战争,对他们进行血腥屠杀,以致当地部落布领曼人几乎被杀戮殆尽,霍屯督人和班图族幸存者也沦为奴隶。南非这片土地默默记录了土著黑人的血泪史(Ross 65-78)。1910年南非白人政府以法律形式推行世界上最极端,最完备的种族隔离制度,形成至今世界历史上种族主义最顽固的堡垒(90)。在白人主导的政治背景下,种族主义的影响渗透到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被奴役的黑人不断被边缘化,被“非人”化,造成在历史上的失语。布林克的另一作品《风中一瞬》女主人公认为,南非文明历史是开普城创造的,在内陆探险过程中,感叹自己是第一个进入内陆腹地的人,在创造历史,却完全忽略了曾经踏足此地的霍屯督人(Brink, An Instant in the Wind 86)。他的另一作品《血染的季节》当中也有类似表述:黑人斯坦尼听说男主人公本是教历史的,对着满墙的历史书籍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书不值一文,“因为你们这些白人始终认为历史就是在你们所在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而不在任何其他地方”(Brink, A Dry White Season 86)。从以上表述可见,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治背景下,白人成为南非历史和社会主流话语的主角,而黑人是被禁言的,被沉默的,被排除在主导叙事之外的,成为历史上缺失的一部分。通读《魔鬼山谷》,不难发现黑人在该作品当中是也缺失的,除了以下两种形式的存在:白骨和魔谷居民口中贬低的评价。
《魔鬼山谷》第一个与黑人有关的陈述是黑人的缺失:犯罪记者弗利普·洛克纳发现魔谷里没有黑人或棕色人种,让他有种身处中欧或月亮上的错觉,而后发现黑人是不被允许进入魔谷的,因为魔谷统治者们担心黑人会“污染”他们纯正的白人血统。这一描述恰恰印证了1948年当选南非总统的马兰所宣扬的“黑色危险”,他们推行彻底的种族隔离,“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倘若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的高贵血统就会被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污染而引起种族退化;如果允许黑人有平等的权利,白人就会被黑色海洋吞噬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余建华 132)。
作品中第二次提及黑人是犯罪记者与魔谷医生唐特·波比对话中,她认为让布尔人来到魔谷定居是上帝的意愿,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其到来之前是没有“人”的。当记者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魔谷里也许有布什曼人,唐特表示出极度的不屑:“那又如何?我们现在聊的是人啊。布什曼人只是寄生虫而已”(Brink, Devils Valley 106)。更耸人听闻的是,不幸在魔谷降生的黑人小孩统统被处以石刑,这些孩子被称为“倒退”(throwbacks),“因为在魔谷里生而为黑人是最大的过错(the worst sin of all)”(229)。
代表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魔谷第一代统治集团首领卢卡斯·先知者·雷米尔特认为上帝是位伟大的“分离者”(Great Divider),“他将光明与黑暗分开,将天与地分开,也将陆地和大海分开”。①“他也将我们(白人)与有罪的种族(黑人)分开。偶尔我们当中出现了带有原罪的人,就一定要将他从上帝的选民中移除”(177)。这个原罪者的就是黑人女性是辟拉(Bilhah),卢卡斯·先知者妻子米拉死后的发泄对象。先知者不在乎她原本姓名,直接从《圣经》中为她取名辟拉。辟拉在《圣经》中是瑞秋的仆人,瑞秋无法生育,将辟拉送给丈夫雅各布(36)。先知者表示自己别无选择才与黑人女性媾和,并援引《圣经》中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布的例子,表示他和他们一样,是凑合和黑人女性发生关系,生孩子。没人关心辟拉的真名,没有人试图了解她的故事,了解她的所思所想,在魔谷的叙事里,她的历史是被遗忘的。综上所述,魔谷掌权者利用宗教作为控制人心的枷锁,压迫黑人,将黑人赶尽杀绝,行径惨绝人寰。现实世界对黑人的残忍压迫和种族隔离反映到反乌托邦叙事当中,是魔谷黑人的缺失和对黑人婴儿的残忍杀戮,这也是作品中黑人被禁言的缘由。
二、父权体制下边缘化女性的沉默
男性支配和男性统治是西方他者哲学“父权制”的主要特征之一。父权制是一个把男性置于主导地位,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或体系,小到家庭生活、族群的私人领域,大到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男性均處于统治地位。恩格斯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恩格斯 63)。”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米利特 37)。性别压迫问题放在南非殖民话语中更具批判性。著名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在其论文《底层能否发声?》中指出:“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斯皮瓦克 107)。在这种殖民和父权制体制下,男性占据着社会最优资源,而女性注定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女性作为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南非官方话语之外,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她们的历史被遗忘。
2.1 女性的“边缘化”
父权制和男性中心主义即将歧视女性的观念压缩于传统的宗教观念以及意识形态中,公开或隐蔽地迫害女性。这些迫害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化不仅将女性训练成合格的“女人”,而且将“女人”束缚于卑贱的位置上,将女性“边缘化”,心甘情愿地接受男性的统治;在男性事物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在《魔谷》中,这一点体现得淋淋尽致。魔谷父权制意识形态把男人对女性的支配合法化了。掌权者为了维护以男权为中心的统治,限制女性的解放和思想独立,让女性依附于男人,向男权主义和父权制低头。在社区生活范围里,掌权者随意侵犯女性,并将唯一不肯屈服的女孩艾玛妖魔化,使其成为话题的禁忌,在魔谷社区中遭到“孤立”。从另一个角度看,艾玛因此被剥夺了声音,她的话无人相信。谷中不少女性聪慧伶俐,却无用武之地。她们想寻找机会去谷外探寻,学习,却纷纷被掌权者抓回逼疯。家庭为父权制的剥削提供了场所,在家庭中丈夫支配着家庭的生产和生育活动,女性提供的是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认为女性如果不知如何为丈夫做一块面包,受教育有何用处?(Brink, Devils Valley 125)此外,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施暴,迫使女性屈于从属的卑微地位。当犯罪记者弗利普·洛克纳无法忍受魔谷恶行,在教堂聚会时向女性们发问:“难道就没有一个女人对谷里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吗?你们难道也同意这种做法吗?”(356)他得到的是一片寂然,原来在教堂集会里,女性是没有权力发言的。没有发言权意味着被剥夺了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机会。
综上所述,在父权制的视域里,女性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工具,用以发泄,用以维持以男性为中心的体制。如此,女性的自由自主行动的潜力受到了压抑,女性作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受到打击,只能以客体、他者的形式存在,阻碍女性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李岩 112)。
2.2 为伟大的女性发声
布林克主张南非写作,无论是在种族隔离时代还是后隔离时代,不可避免地与历史中的沉默相联系(Kossew 134-146)。布林克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被沉默而坚决拒绝沉默的,如《沉默的另一面》中的汉娜。她的被沉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她因为身世孤苦漂泊,没有姓氏,她作为存在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因为不愿被侵犯而受到惩罚,被割去舌头。她的失声,即是历史的,也是身体的。
《魔鬼山谷》中被沉默的女性不胜枚举,但因魔谷当权者不允许纸质材料的存在(更不用说关于女性的事迹的记录),强行抹去了当地历史和记忆。犯罪记者弗利普克服艰难险阻,终于精诚所至,说服了魔谷当权者卢卡斯·死神·雷米尔特的妻子蝶莲娜向他吐露魔谷的历史。她告诉记者他来到魔谷所听到都是男性的故事的缘由:“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全部历史”(Brink, Devils Valley 232);然而魔谷历史上确有许多伟大的女性,她们的故事被魔谷男性当权者埋没,被沉默。而颇具讽刺的是,这些女性皆来自魔谷掌权者雷米尔特家族:卢卡斯·先知者·雷米尔特曾抛妻弃子,意图逃出魔谷,不幸坠崖摔断腿,其妻米拉将其背回家照料,从此落下驼背;在先知者最艰难的时候,米拉拯救了他,而后米拉积劳成疾,先知者却弃之不顾,任其病逝,甚至任随秃鹰啃食尸体,夺走了她最后的尊严(233);卢卡斯·宁录·雷米尔特虐待妻子桑娜和她与前夫的两个孩子,待他们长大,起兵反抗,失败被擒,在桑娜哀求下,宁录让她选择一个孩子活下来,桑娜拒绝做出抉择,最后均被处死,看似柔弱的桑娜当晚杀死宁录,为孩子报仇(236);强大的卢卡斯(卢卡斯·宁录之孙)因其围剿整个开普敦派来的突击队而被人铭记不忘,却很少人知道他美丽的女儿嘉娜(Mooi Janna)以身救父的伟大故事:为从突击队手上赎回父亲,嘉娜自愿留在突击队伍,惨遭践踏,而后父亲剿灭整个突击队,将奄奄一息的女儿救回,但因为女儿已被外人玷污(魔谷禁止女性与外界人通婚),不得不将其扔下悬崖,否则,嘉娜回到魔谷也会被处以石刑(237);卢卡斯·巨球(强大的卢卡斯之子)妻子凯塔琳娜原是魔谷奸戾之徒偷来的女孩,至死抵抗,渐渐被逼疯下嫁给卢卡斯·巨球,后死于难产(241)。最后蝶莲娜总结道,我们魔谷里有很多了不起的女人,但如果只听男人叙述是无法得知这些的故事的(243)。记者挖掘出来的却只是冰山一角,在长时间父权制的统治话语下,魔谷所映射的南非社会究竟有多少伟大女性被埋没,究竟有多少故事被遗忘?
三、为历史发声的过程
布林克通过犯罪记者在魔谷探寻历史的过程表达了自己对南非被禁言,被压抑的群体的深切共情,意图揭示当时南非当局的恶行,也表明了作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即非暴力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道路。魔谷代表着落后的社会体制。布林克安排弗利普来到此地,目的是为了揭露历史,还原历史。“在东方,独立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因此,国家就是一切,它体现的唯一职能或唯一属性就是政治强力统治,即暴力和强权”(衣俊卿 75)。而西方的情形完全不同,“国家体现了强力+领导权(同意)的二重性质,资产阶级不但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通过理性化的程度取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75)。“葛兰西的西方革命观的核心问题:革命的重心从暴力夺取政权向争取文化领导权转移”(74)。魔谷即一个微型的南非社会,布林克笔下的弗利普,单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魔谷社会大变革,而这也不是布林克安排他进去魔谷的初衷。
“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欲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必须冲破暴力革命观的束缚,确立一种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观”(76)。就魔谷而言,文化领导权掌握在魔谷当权者手中,第一代进入魔谷的卢卡斯·先知者·雷米尔特(Lukas Seer)建立了基于基督教的各种严苛而荒谬的制度。“国家的确具有并需要人民的认可,但是也要通过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培养人民的认可”(葛兰西 214)。魔谷掌权者通过每周三“神圣兄弟”举行所谓的《圣经》学习课程,严格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将女性置于被支配的地位,导致谷里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漠然甚至成为暴力制约关系。魔谷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扭曲的意识形态。人际的漠然和人心的麻木令人魂惊魄惕。魔谷掌权者的极权统治和霸权主义深刻蛊惑人心,人们“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意识形态)中来”(庄严 54)。魔谷居民的意识被掌权者利用宗教蛊惑,一致维护掌权者利益,包庇其弊,不向外人吐露。要改变魔谷暗无天日的社会惨景,就必须夺取当地文化领导权,揭开历史事实。“市民社会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衣俊卿 70)。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来自新闻界的犯罪记者弗利普代表的就是市民社会,而“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77)。弗利普为还原魔谷历史,困知勉行,造访魔谷知情者,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渐渐取得她们的信任,让其讲述魔谷历史,讲述的过程也是治愈的过程。布林克将叙事(讲故事)作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认为在讲述(story-telling)过程中,一个人的心灵和身体的创伤会得到治疗(Brink, “Interrogating Silence” 19)。所以,这个记录收集过程是作者将历史还给沉默的黑人和女性的过程,也是魔谷居民(尤其是女性)身心所受摧残在愈合的过程和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当弗利普与魔谷恶徒对峙,魔谷里的女人纷纷站出来支持他,与魔谷邪恶当权者奋勇抗衡(Brink, Devils Valley 358-362)。后期魔谷越演越烈的天灾预示着这个社会的土崩瓦解,而带来这一改变的不是代表着进步市民社会的弗利普一人,而是逐漸觉醒的魔谷群众。
布林克笔下的魔谷统治者利用集权统治迫害黑人和女性,而且将此历史事实进行掩盖,并告诫魔谷居民禁止向外人道。这暗含着布林克曾经遭受的南非文字审查制度,禁止抨击种族隔离,禁止批判当局,禁止书写黑人历史。文字审查与魔谷统治者禁止居民讨论历史如出一辙,均是对被禁言的受害者的蔑视与埋没。而布林克的书写却是对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狠狠的一记耳光,也是他试图将真实的历史还给沉默的黑人和女性的过程。
四、结语
在布林克论文“审问沉默:南非文学面临的新可能”中提到:“历史为南非作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沉默供其造访……因为白人历史学的主导话语长期以来不可避免地沉没了其他的可能性”(Brink, “Interrogating Silence” 22)。在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文字审查制度和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父权制的阴霾下,南非社会和历史的天空回荡着两种沉默:弱势族裔的沉默和女性的沉默。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夕,布林克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作为南非的小说家,职责在于:“说出体制所压抑的沉默,从而规避它的压制意图”(Kossew 134-146)。布林克通过书写《魔鬼山谷》,审视那些在种族隔离期间被忽略和被禁言的历史,为掩埋在南非历史长河中的弱势族裔和女性发声,并通过发声的过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是南非人道主义的“守夜人”,他的作品为南非的文学指明了方向,让人们度过灵魂的暗夜,精神的荒芜。
注释【Notes】
①See Bible: Genesi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92.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aker, John F. “André Brink: In Tune with His Time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5 (1996): 50.
Brink, André. “Interrogating Silence: New Possibilities Faced by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In South Africa: Literature, Apartheild, and Democracy. Eds. Derek Attridge and Rosemary Jo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14-23.
---. Devils Valley. Fort Washington: Harvest Book, 2001.
---. A Dry White Seas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 An Instant in the Wind. Chicago: Sourcebooks Landmark, 2007.
Diala, Isidore. “History and the Inscription of Torture as Purgatorial Fire in André Brinks Fiction.” Studies in the Novel 34 (2002): 60-7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ngels, Friedrich.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Stat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张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Trans. Cao Leiyu and Zhang X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3.]
Kossew, Sue. “Giving Voice: Narrating Silence, History and Memory in André Brinks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and Before I Forget.” Tydskrif vir Letterkunde 42 (2005): 134-146.
李岩:社会性别视阔下的“父权制”批判。《武汉理工大学学报》3(2016):112。
[Li, Yan. “A Critique of Patriarchy in the Context of Gender Inequality.”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 (2016): 112. ]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Miller, Kate. Sexual Politics. Trans. Zhong Liangm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9.]
Ross, R.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ege Education Press, 2006.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结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Spivak, Gayatri C.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A Spivak Reader. Eds. Chen Yongguo, Lai Lili and Guo Yingjian. Peking UP, 2007.]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Yi, Junqing.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axism. Beijing: Peking UP, 2008.]
余建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史林》2(1997):132。
[Yu, Jianhua. “The Rise and Fall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History of Review 2 (1997): 132.]
周小青:岔路口:安德烈·布林克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5(2015):25。
[Zhou, Xiaoqing. “Fork in the Road: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Andre Brink's Literary Creation.” A Dynamic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5 (2015): 25.]
庄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时代意义。《北方论从》6(2003):54。
[Zhuang, Yan.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Northern Forum 6 (2003): 54.]
責任编辑: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