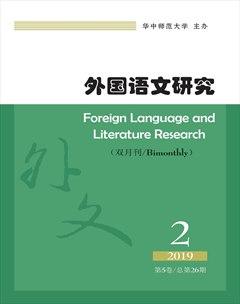论《别让我走》的科技与伦理
王桃花 程彤歆
内容摘要:著名日裔英国当代作家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叙述了一个允许克隆人存在的社会利用克隆人为人类进行人体器官捐献以延续人类生命的故事。通过科技伦理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视角来对科技如何拒斥克隆人伦理身份、如何颠覆人类伦理意识以及如何重塑社会伦理环境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我们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人类渐渐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抛弃传统生命伦理道德,造成科技吞噬伦理的现象。小说以平淡、冷静的叙事风格和写作手法给读者描述了克隆人的悲惨命运,并引导读者反思: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才是伦理道德永恒的本质。
关键词:石黑一雄;《别让我走》;科技伦理;文学伦理学批评
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Japanese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s science fiction Never Let Me Go describes a society in which human can clone themselves to donate organs to continue their life. By analyzing clones ethical identity, human beings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eth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bviously devouring ethics, and thus anthropo-centris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ith a leisurely narrative style and austere writing technique, Never Let Me Go describes the tragic fate of cloned human, which arouses the readers profound consideration that the eternal essence of ethics and morality is to respect and revere life.
克隆技术是用科学技术进行人工无性繁殖而产生生命的过程,其基因与本体的基因完全相同。自1963年印度生物化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在一次演讲上首次采用“克隆(Clone)”这一术语之后,科学界对克隆技术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展开。直到1997年2月,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上一篇文章向全世界宣告克隆羊“多莉”的诞生,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克隆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也标志着新生物技术时代的开启,更重要的是,这让人类开始了对克隆技术在未来能够造福于人类自身可能性的設想。然而,克隆人非自然有性繁殖而生,其面对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2005年,著名日裔英国当代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以克隆人为主题出版了他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凯茜的视角,讲述了克隆人凯茜及她的克隆友人露丝和汤米在与世隔绝的克隆人寄宿学校黑尔舍姆度过童年时光,少年时期到“村舍”接受为期两年的看护者职业培训,为以后照顾器官捐献者做准备,最后走上器官捐献的不归路,进行一至四次器官捐献后死亡的悲惨故事。自出版以来,小说凭借其行云流水的文字、新颖的故事情节和悲惨的人物命运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好评。2005年该小说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同年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评为最佳图书;2006年获得美国亚历克斯奖,并被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所赞扬;2010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别让我走》获得了第37届土星奖的“最佳科幻电影”提名奖。国外许多学者对小说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安妮·怀特黑德(Anne Whitehead)曾指出:“克隆人在《别让我走》中的社会里被看作非人类,所以也被当作非人类对待”(Whitehead 64)。而对于克隆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詹宁斯(Bruce Jennings)则指出:“随着生物技术的介入,人渐沦为一部组装起来的机器,即使正常人(相对克隆人)可能因为生物权力而更长寿,但是他们也不会像人一样活着”(Jennings 19)。人类应该具有高度的道德伦理意识,而利用科技发展之便向地球上其他物种施暴以求自身生命的延续是一种伦理丧失行为,没有道德伦理,人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在国内,浦立昕从权力与规训的视角对小说做了研究,他认为:“权力和话语在身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规训和建构”(浦立昕 114)。由于克隆人从小接受洗脑式规训,这导致克隆人不懂得反抗人类对他们的暴行。信慧敏则指出:“石黑一雄透过克隆人这面忧郁的镜子直视我们自己,审视人类的自私、欲望和贪婪”(信慧敏 134)。周文娟甚至认为石黑一雄刻画的克隆人与作家本人的日本民族身份相联系:“《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悲惨命运和无奈处境,以及他们绝对‘顺从不抗争的伦理意识,无不与日本文化‘效忠、‘捐躯责任意识紧紧关联”(周文娟 45)。可以说,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角度新颖、内容广泛,然而目前为止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科技对伦理的吞噬却被忽视,还未有人对此进行过相关研究。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各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伦理吞噬问题是发展科技时需直面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将运用科技伦理相关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科技如何拒斥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如何颠覆人类伦理意识以及如何重塑社会伦理环境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剖析科技吞噬伦理这一现象,旨在揭示克隆人所反映的伦理问题和科技进步对人类造成的伦理影响。
一、科技拒斥克隆人伦理身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一个由科技引导生活的时代,科技对人类的生活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一方面,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逐渐摆脱原始生活模式;另一方面,科技也逐渐朝着与人类探索科学的初心相背离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就是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生态污染,也给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带来了毁灭性伤害,造成了科技吞噬伦理的局面。
科技发展对伦理的吞噬并非一蹴而就,在《别让我走》中,它首先表现为人类利用科技建构了克隆人,但拒斥赋予其合理的伦理身份。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伦理身份指的是个体在一种伦理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国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者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1)。在小说中,凯茜等克隆人对自身伦理身份的追寻从未停止过,他们渴望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今后将归往何处,他们也渴望知道自己与外界的人类有何区别。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是自然有性繁殖出来的生物个体,且“人具有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规定性,是具有高度理性的动物”(杜明业 63),而克隆人则是人类利用生物基因技术无性繁殖出来的产物,克隆人没有合适的伦理身份,也违背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规定性。我们该如何看待自然有性繁殖的人类与利用其基因克隆出来的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利用科技制造克隆人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吗?
曹孟勤教授指出:“将人性作为科技伦理的哲学基础,在于人性能够为人们有道德地应用科学技术提供合理的解释。何以为善、何以为恶的价值判断的根据只能是人性。合乎人性的行为即为善,违背人性的行为即为恶。人性能够为价值判断提供形上学的依据”(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46)。人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判断善恶是非的根本尺度,在小说《别让我走》中,黑尔舍姆寄宿学校是一所克隆人学校,凯茜等克隆孩子从小就被送到这里,埃米莉小姐等是他们的监护人。克隆学生们统一被安排学习音乐、绘画、体育等各种课程,他们之中最好的绘画作品会被偶尔来学校的玛丽·克劳德夫人拿去放在她的“画廊”中,所以孩子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画出最能体现自己“灵魂”的画作;克隆学生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取代币,利用代币可以在学校的“交易会”和“拍卖会”上换取自己喜爱的东西来收藏。在这看似自由的表面背后,学校设置的规章制度却令人唏嘘。在黑尔舍姆,学生绝不被允许抽烟,学校图书馆里也没有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因为小说主角吸烟的情节太多了。每周一次的身体健康检查也暗示着孩子们:在这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有性爱关系,但无法生育孩子。克隆学生在黑尔舍姆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从不曾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怯于走出学校的栅栏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学校里不知从何时起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说,曾有学生不听劝阻跨越栅栏,结果第二天学生的尸体被发现绑在一棵树上,手脚都被砍掉了。
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流传的恐怖传说就像一个无形的笼子,将克隆学生们牢牢地圈在笼内,但即便如此,作为生物,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自我认知的欲望。为了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克隆学生们不断将自己与正常人类的“他者”做比较。凯茜回忆了童年时期与学校里的正常人类之一玛丽·克劳德夫人的一次接触:凯茜和她的友人突然出现在来访的玛丽·克劳德夫人面前并观察她的反应:“她只是僵站着等我们过去。……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她似乎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唯恐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意外地触碰到她”(石黑一雄 32)。夫人对待克隆学生们害怕、厌恶的反应和态度犹如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凯茜等人看到了自己真实的样子,他们渐渐认识到,他们与正常人不同。他们也曾被学校里新来的老师露西小姐告知:“你们是……特别的”(63)。至于他们特别在何处呢?终于有一天露西小姐忍不住告诉了学生们实情:“你们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你们的一生已经被规划好了。你们会长大成人,然后在你们衰老之前,在你们甚至人到中年以前,你们就要开始捐献自己的主要器官。……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而你们的未来,你们所有人的未来,都已经定好了”(73-74)。在学校大多数老师眼里,凯茜她们根本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说她们不足以成为人类,他们和待宰的牲畜毫无区别,没有灵魂,没有尊严。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克隆人都坚信自己有一个原型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在街道上或购物中心里刻意留心自己“可能的原型”,露丝甚至认为自己的原型是一位体面的职业妇女,继而跟踪一名形象与她想象的原型相符合的女性,在对这名女性进行一番观察之后失望而归,露丝愤慨地说:“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他们就是我们的原型”(152)。从这里可以看出,克隆人每分每秒都想找到自己的原型,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找到原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我,也许还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是怎样的,这就是他们在那个社会里想要确定自己伦理身份的表现。
程现昆教授认为:“科技应用中的伦理价值有正反两方面,正的方面是指积极的方面,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杰出科学家的道德范例在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反的方面指的是科技的不当应用和任意的扩张,造成科技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程现昆,《科技伦理研究论纲》129)。伴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克隆人的实现在技术层面上已经成为可能,但当今发达国家都一致反对把克隆技术应用到人类自己身上,因为人是自然之子,是通過有性繁殖产生,而克隆人却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刻意制造出来的反自然、反传统的生物,这些生物在历史长河里不曾出现过,一旦出现,必将面对人类各方面的质疑,他们难以在传统的人类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伦理身份定位。人类在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之间选择越过道德底线,把本应由人类承担的痛苦推给了克隆人。显然,人类虽然利用科技创造出克隆人,但拒斥赋予其合理的伦理身份,在人类利益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克隆人始终是异类,他们不会被善待,更无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克隆人对于人类来说没有生命尊严,只有利益,这是科技应用中伦理价值的消极一面。然而,科技对伦理的吞噬远不止于此,不仅克隆人受到影响,人类的伦理意识也同样遭到颠覆。
二、科技颠覆人类伦理意识
站在一般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起源于劳动,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及历史环境的产物。“人类最初的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关系的体现,是一种伦理表现形式,而人类对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好处的认识,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意识”(聂珍钊 14)。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人与兽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理性,人因为拥有理性所以才为人,兽因为没有理性所以才为兽。在小说所设定的社会背景下,克隆人产业是被允许存在的,且克隆人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捐献。他们注定将在成年之后捐献自己的器官,与人类饲养猪马牛羊为人类提供肉食与皮毛毫无区别,可以说,克隆人活着就是为了捐献。克隆人三个字中虽有“人”字,但他们却是和黑尔舍姆校外的普通人不同的“人”,他们“被出生”,然后“被死亡”,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克隆人器官捐献产业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让人类的伦理意识摇摇欲坠,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也逐渐消失殆尽,最终做出了反人性、反伦理的行为。
小说的第三部分把重点放在了一个叫做金斯菲尔德的地方,克隆人在那里履行他们的捐献“义务”。他们每捐献一次器官,就会被送往康复中心去等待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再进行下一次捐献,一般进行一至三次器官捐献后就会走向命运的“终结”(complete),而极个别身体很好的克隆人可以进行第四次捐献,但在第四次捐献之后就不会提供康复中心和照顾者的服务,克隆人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在那个普遍认为“克隆人非人”的社会里,以埃米莉小姐为主要负责人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努力为克隆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给予了他们丰富的课程教育,目的就是为克隆学生争取和正常人类平等的权益。就像人类通过狗的作揖、摇尾、转圈等动作来证明狗是通人性的一样,埃米莉小姐等人也想通过克隆人的画作来向世人证明克隆人是有灵魂的。实际上,在埃米莉小姐等正常人的潜意识中,克隆人是没有灵魂的,但克隆学生们的日常行为与正常人类并无二致,这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克隆人的画作与论文,都证明克隆人也是有灵魂的。但最后,面对来自社会权威的压迫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力,埃米莉小姐等人向这个残忍的捐献计划发出的挑战也只能无疾而终。
克隆人是非常向往正常生活、向往自由的,哪怕他们只有一线希望能获得三至四年的自由生活时间,他们都会拼命去争取。而作为自由的、聪慧的人类,却利用科学技术之便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剥夺克隆人的生存权、自由权,把克隆人当做待宰的牛羊一般对待。不难看出,在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面前,人类应有的伦理意识遭到颠覆,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怜悯。另一方面,非正常发展的伦理意识也加速了人类对社会伦理环境的扭曲塑造,社会权威对克隆人的道德冷漠让反伦理的杀戮行为在新的环境中成为合理的捐献行为。
三、科技重塑社会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19)。之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替克隆人的命运感到悲伤,是因为读者站在现实社会的伦理环境去评价小说中克隆人存在的社会伦理环境,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回归文本中的伦理环境去评价伦理,否则将出现文学批评的越界行为。黑尔舍姆学校对于读者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表面是克隆人的成长之地,但总让读者感到有些疑惑不解:既然制造克隆人的目的就是捐献器官,那为什么还要对克隆人进行文化教育呢?多年之后,埃米莉小姐终于向凯茜坦白:“如果学生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240)。读到这里,不难看出在埃米莉小姐等人眼中,虽然克隆人非人,但他们是有理由具备合理的伦理身份的,可惜他们为克隆人争取权益的活动依然抵挡不住权威机构的暴力,因为在那种伦理环境里,主流意识是克隆人尚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类,他们只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而最终也将为人类生命的延续而服务。
由于现实社会伦理环境和人类的伦理意识已经发展到了平等对待世间一切生命的高度,对于所有的生命,不论植物、动物或人类,都会抱有怜悯之心和包容心。但在小说中,科技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强劲力量去重塑一个培养克隆人的科学环境,且社会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克隆人非人”,克隆人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健康、延续生命而创造出来的用于器官捐献的“物”,克隆人没有人权,也没有法律地位,极少有人同情克隆人。在小说中,“捐献”(donation)和“捐献者”(donor)是极其微妙的两个词,小说伊始,凯茜就以自述者的身份向读者述说:“我的名字叫凯茜·H。我现在三十一岁,当看护员已经十一年多了”(石黑一雄 1)。所谓看护员,就是每个克隆人在进行器官捐献前可以申请成为器官捐献者的看护员,若护理水平够好,还可以申请多做几年看护员工作,意义相当于延期捐献。“捐献”和“捐献者”由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捐献者主动捐献,因为捐献本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自愿行为。而小说中的“捐献”并非克隆人自愿捐献,克隆人的器官捐献是一种被动行为,那么此时此刻,“捐献”的意义就等同于“待宰”,“‘捐献者也就成为了‘待宰者”(杜明业 95)。在这种社会里,权威利用“捐献”一词来转移公众视线、蒙蔽真相,把残忍的被动捐献行为描述成伟大的自愿捐献,使贩卖人体器官这种等同于杀人的违法行为巧妙地逃避了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从而重塑了一个冷漠而残忍的伦理环境。在那种伦理环境下,克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即是“保持健康,完成捐献”,经过多年的洗脑教育,克隆人麻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从内心深处就已经认定捐献是自己的义务,他们从最初就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
文学伦理学批评并非要我们评价伦理的正确与否,而是要分析这一系列伦理问题存在的原因。在过去,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等自然規律,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毫无改变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将拥有科技这一利器来改变过去不能改变的事情,面对眼前的巨大利益,人类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克隆人器官产业链。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产业就早已规模化,社会有着一套成熟、完善的克隆、捐献模式,各中间商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科学家的克隆行为,到克隆人学校的学业教育,直至最后捐献时期的医院看护等,都确保了克隆人将按照社会所规定的步骤一项项完成。这种行云流水的器官捐献产业对于身处现实社会的读者来说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但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所描述的社会却对此持认可态度,因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重塑了社会伦理环境,让有违伦理道德的越界行为成为可接受的普遍行为,这也是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
当下全球一致反对将克隆技术运用于人类自身,主要是出于对克隆人的一系列担忧与疑虑,例如克隆人也许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由于克隆人的繁殖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所以他们的出现也许会破坏家庭的完整性,抚养与继承问题将难以解决。另外,克隆人的出现也许会导致人类社会出现新的种族歧视,这对克隆人是不公平、不道德的。出于种种理由,即使克隆技术早已在动物界成功运用,但现实社会始终不允许科学界进行克隆人的实验。有人曾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拥有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伦理或道德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专利,是专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46)。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类极容易做出反伦理行为,所有利用科学技术能够实现的利己之事人类都选择接受,而不顾伦理道德的沦陷,就像在小说《别让我走》中,人类出于利己私欲利用科技制造克隆人,等克隆人长大成人之后夺取他们的身体器官再将之抛弃,这种行为是反人性的,它已完全违背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是科技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恶”的展现。站在现实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应该被投身于造福人类的活动,人类应该加强伦理道德修养,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人类应该理性面对,在利用科学技术使生活更加自由、幸福的同时,不应该违背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更不应该牺牲克隆人的生命来为人类创造利益。
四、结语
在《别让我走》中,不论是从克隆人的伦理身份、人类的伦理意识还是社会伦理环境角度来看,科技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观,若想在现实世界中将克隆技术运用于人类自身,则意味着社会需要解决一系列现阶段难以解决的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冲突问题,至少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无法在人类社会以正常的身份生存下来,他们从“出生”开始,一生的命运就已被人掌控。对于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谭国器、杨振武 1)。如果科技被有违伦理地不规范使用,则有可能造成科技异化,最终科技不但不会造福于人类,反而使人类陷入一种痛苦境地。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曾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3)。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并没有对克隆人的器官捐献产业进行任何道德批判,而是以平淡、冷静的叙事风格和写作手法向读者展现了克隆人一生的命运,也给读者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素材。对于未来克隆人是否会出现,我们暂时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不论何时,作为拥有理性、拥有高度文明的人类,我们应该保持批判意识,时刻反思新的科技发展是否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不应该随意伤害、践踏其他生命。众生平等是生命存在的主题,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伦理道德永恒的本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Cao, Mengqin. Humanity and Nature: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P, 200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程现昆:《科技伦理研究论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Cheng, Xiankun. A Stu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1.]
杜明業:《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外国文学研究》3(2014):60-67。
[Du, Mingye. “An Ethical Literary Analysis of Never Let Me Go.”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4): 60-67.]
——:《别让我走》:生命伦理的反思。《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5):87-100。
[---. “Never Let Me Go: Reflection on Life Ethic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5): 87-100.]
高正琴、李厚达:哺乳动物克隆技术及其发展历史。《生物学教学》1(2002):2-4。
[Gao, Zhengqin and Li Houda. “Mammalian Cloning Tech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Biology Teaching 1 (2002): 2-4.]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Ishiguro, Kazuo. Never Let Me Go. Trans. Zhu Quj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Jennings, Bruce. “Biopower and the Liberationist Romanc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40 (2010): 16-20.
聶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浦立昕:驯服的身体,臣服的主体——评《千万别丢下我》。《当代外国文学》1(2011):108-115。
[Pu, Lixin. “Submission in Never Let Me G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1): 108-115.]
谭国器、杨振武:江泽民主席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载《人民日报》2000年8月6日,第1版。
[Tan, Guoqi and Yang Zhenwu. “President Jiang Zemin Meets Nobel Prize Winners in Beidaihe.” Peoples Daily Aug. 08, 2000, p. 1.]
Whitehead, Anne. “Writing with Care: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1): 54-83.
信慧敏:《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当代外国文学》4(2012):129-135。
[Xin, Huimin. “The Postuman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2): 129-135.]
周文娟:无言的悲悯与诘问——《别让我走》创作思想与伦理意识索隐。《外国语文研究》5(2018):40-47。
[Zhou, Wenjuan. “Wordless Sympathy and Questioning: on Creating thought and Origin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Never Let Me Go.”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5 (2018): 40-47.]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