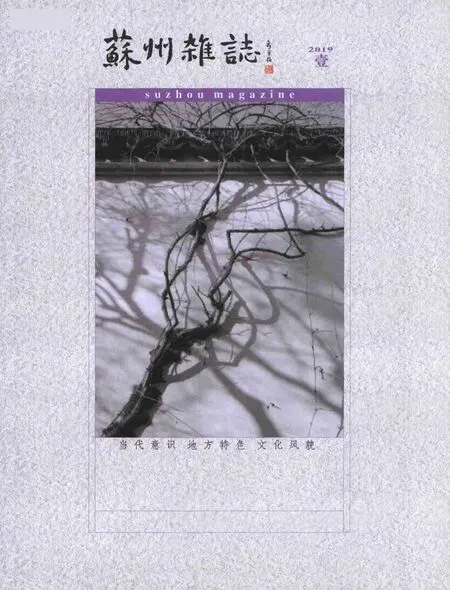花山隐居与支遁
小海


苏州西郊的花山,因了一位舌灿莲花的高僧,而成了苏州人心目中的终南山。“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陆机《文赋》)吴中山水因有了高士隐居而名世。
唐代诗人岑参曾在《太白胡僧歌》中感叹道:“山中有僧人不知,城里看山空黛色。”可常常却是:自古隐者留其名。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体系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可资仿效的足迹,如《论语·微子》中点出来的:“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里的“逸民”,实际上就是“隐士”。
也有一类隐居者,他们退出俗世生活的行列,出家修行,却又因隐而显,在世时就活成了传说。支遁,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位。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林公,别号支硎。他出身于一个佛教徒家庭,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王濛、殷融等名士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馀杭山隐居时,他研究《般若经》等经典。二十五岁出家为僧。其后,他回到吴地建立支山寺。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名士清谈,蔚然成风,支遁精通庄子学说,佛学造诣很深,书法善草隶两体。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表的仪容,一流的口才。终其一生,他交结名士,名士们推崇他,也更喜欢和他来往。
在以记载清谈家言行为主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的记载就有五十多个条目。近期得空,遍查了这些条目,发现实在有趣。
支遁的隐,说白了可不是为图走通“终南捷径”,谋取一官半职。他是出家人,除了著述,就是讲经说法。作为隐士,他其实又是怕孤独的,这可是隐士的致命伤。因此,他隐居山野时,养马放鹤。《世说新语》中说他“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有人说僧人养马不雅,他说:“贫道重其神骏。”又说“支公好鹤”,怕它们飞走,他弄断其翅膀,可看到它们徒然振翅无法飞翔的样子,又不忍心,于是“养令翮成,置使飞去”。就是养好羽毛后放飞。(以上参见《世说新语》之《言语》第二)其实,作为山野隐士,养马放鹤也并无不妥。
晋代名士喜欢养鹤,陆机、陆云兄弟在松江读书时,畜养的是丹顶鹤。陆机《羽扇赋》中还有“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作者托言宋玉力赞白鹤之羽制成的扇子正配名士之清雅,以区别于“掩麈尾而笑”的那些崇尚清淡的北方诸侯。多年后,陆机兵败被人所谗遇难时,叹息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见《晋书·陆机传》)引得后世的大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发出 “华亭鹤唳讵可闻?”的感伤之言。
支遁之后,隐士养鹤有了续篇,北宋处士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不娶无子,而植梅放鹤,故世有“梅妻鹤子”之说。而画家们笔下的山林高士图上,鹤也几乎是标配。这是后话。
可能支遁更喜欢大隐隐于市,这样他毕生所学所参就有了用武之地。以俗世眼光看来,最风光的一段,恐怕就是晋哀帝即位时(公元362年),哀帝多次派使者敦请他到京城,他住在东安寺,宣讲《道行波若经》,一时倾动朝野。
支遁的隐士生活,充其量只能算半隐。过一阶段,就有人请他出山,或者他自己主动出来,会会当朝名士们,打打嘴战,磨磨脑子。况且,他是可以随意出入帝王将相府第的,与达官贵人们都有交游。比如《世说新语》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所谓厌心,就是心领,满足。当然,因为支遁的半隐生活,且居无定所,有显贵名士一心想找他辩论、请益、验证而不得遂愿的,如:“殷中军(殷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出处同上)殷浩对《般若经》精微之处和世人感到晦涩难解的地方作了两百处标签、批注,想找支遁讨论,却没实现,至今物证都在。
支遁赢得广泛人望,主要靠三寸不烂之舌。他话风锐利,机锋迭出,辩才无碍,得到了喜欢清谈的晋代名士们的广泛“爱戴”。名士们“追星族”一般,连他的相貌都拿来说事儿。来看看当年领袖群伦的名士们都说些什么。王羲之一开始可真是看不上支遁,可一旦支公逮着了机会,“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进而,王羲之居然也加入了“外貌党”:“叹林公‘器朗神俊’”(《世说新语》之《赏誉》第八)。大人物谢安也说:“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世说新语》之《容止》第十四)名士孙绰则:“见林公:棱棱露其中爽。”(出处同上)
名士常常喜欢比较、比攀美誉度,正如清谈论争时要一较高下,他们时不时要打听和关注当朝名士人气指数排行榜,他们私下谈论支遁的话题可不少。“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殷欲制支。’”(《世说新语》之《品藻》第九)郗超请教谢安,支遁和大名士嵇康比,谁的清谈更厉害?谢安讲论辩时嵇康要不断努力奋进,才能脱身。支遁和殷浩各有所长,有高超妙论时,支遁可胜殷浩,若论滔滔雄辩,殷浩可胜支遁。
《世说新语》中留下了支遁在辩论现场的生动画面。“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这类辩论看多了,也发现,有些反诘,常常是逞口舌之快的意气之争。
支遁的好辩,有时到了不分场合的地步,当然,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世说新语》之《政事》第三)讲的是两位名士拉了支遁去看望何充(曾任骠骑将军),劝何充放下公务俗事来跟他们一起清谈。幸好,何充还有理智,直接怼了一句:我不看这些文书,你们哪能活命?“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间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谢玄在为父亲守丧,他跑去和人家清谈到夕阳西下。半路有人问他从何而来,他兴冲冲回复一句:今天和谢孝子畅谈了一番。剧谈这个词也因此流传了下来。名士辩论过程中的激烈程度也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林道人诣谢公(谢安)。东阳(谢朗)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两人争辩,旁观的妇人惊吓得唯恐避之不及孩子出意外。
支遁对南人北人学问的评断,尤为世人津津乐道。体现了他识人识学的功夫:“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
名士们甚至为了离支遁坐得近点而差点大打出手。“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谢万)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瞠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世说新语》之《雅量》第六)毕竟都是名士,君子风度还是要的。幸好,两个人因争座位引发的争执都没再放在心上。
《世说新语》中甚至把围棋称为手谈的发明权归功于支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支遁在一群清谈家中的魅力和话语权。“王中郎(王坦之)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世说新语》之《巧艺》第二十一)
怪不得,连鲁迅先生都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支遁的死,可以说是死于寂寞与孤独。其原因支遁自己说就在于“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世说新语》之《伤逝》第十七)讲的是他的知音法虔已离世,犹如匠石因为郢人死去就不再用斧子,伯牙因为钟子期死去而终止鼓琴。法虔走了,支遁呢,说话没有人听了,心中郁积,他预料自己这下子是活不长了。果不其然,一年后,他就离世了。这也不奇怪,过去的高僧能够预知时至的不在少数。唐人陆广微《吴地记》中有:“晋支遁,字道林,尝隐于此(指花山),后得道,乘白马升云而去。”据悉,支遁圆寂后,葬于花山北峰,后移至天池山后旁的北峰坞,由王羲之题其塔铭。(《支遁传》也有说支遁“太和元年终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支遁能够在他的时代以学识与辩才名震一时,流芳后世,我想了一下,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生逢其时。魏晋是个崇文尚名的时代,哪怕是贵为一代帝王,都认为文章才是千古事,对那些写出锦绣华章的古代文士学者艳羡不已,心有戚戚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鲁迅先生也说,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一个尊重名士、崇尚清谈的时代,学富五车、勤于著述、长于论辩的支遁,可谓生逢其时,如鱼得水。
二是善用比较互文手法。当时东晋清谈家们的主要阐发对象是老庄,重点宗奉的典籍是《庄子》。支遁在辩论中常常胜人一筹,就是他运用了“互文”手段。他的“比较文化”研究方法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一门秘密武器。作为高僧与学者,他有修证,有著述(他注释了《安般经》、《四禅经》等经文,并著有《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他阐发《即色游玄论》:“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日:‘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道林集·妙观章》),这种“即色本空”观点和佛教经典《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出一辙。要知道,至宋朝为止,《心经》可考的汉译有11次,现存9本。最早的译本据说是三国吴·支谦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但译本缺失,已不可考。可以想见的是,当时的士人尚未读到。流传开来,是因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 (402-413年),尤其是唐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649年)。传说唐僧取得心经后,回国这一路就靠这部经护身圆满归来,可见这部经的重要性。这是一部顿悟见性的了义经。如果支遁没有读过这部经,却能发挥到这个程度,只能说明他天资聪颖,是靠自身修行证悟到的,非常了不得。打通儒、庄、玄、释诸家的壁垒,自由、逍遥地出入,相互阐释,交相辉映,于一众名士中,他的清谈往往高妙超拔,“风神秀出”,也是理所当然。他的《庄子注》,是以自己精研的般若之学来重新阐释、建构庄子,做到了像他自己所说的“通览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不执着于一端,博与专相结合,运用比较的方式,博采众长,虚心广纳,灵通感应,直探本源,出奇制胜,这恰好就是他的方法论。
支遁所奉持的《般若经》应是大乘佛教中一个系列的总称,至少包括了《大般若经》《放光般若》等大小十部佛教经典。般若意为智慧,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据传,佛祖住世时,曾用二十二年时间来说般若经方面的经典。大乘佛法般若学在东晋的传播也有赖支遁等僧人在士人中的流布有关。想想支遁当年宣讲的即色即空观点,和今天的科学家们跟大众讲量子物理学、量子通讯卫星是否有几分相似?
三是讲究清谈技巧。支遁在清谈辩论比赛中每每胜出,往往是能发人之未思,未想,出新出奇,扬长避短,以奇制胜。他阐释庄子,尤其是其中的《逍遥游》篇,能以佛解庄,独出机杼,令名士时贤们折服赞叹。对魏晋清谈素有研究的唐翼明先生说:“清谈是有一套严密的规矩的,言词非常之讲究,不是一般的聊天,是很精美的言词,讲究辞藻的美丽,还要讲究声调的美丽。而且人在清谈的时候还要讲究风度之美,还要有道具,通常是三种形式:一种是由一个人主讲,这个人通常是大师级人物。第二种方式也是最多方式,是两个人论辩。旁边有欣赏聆听的观众,两个人辩论的时候,一方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另一方反驳,精彩的辩驳会持续几十回合。第三种是几个人共同讨论。”(参见唐翼明著《魏晋清谈》)虽然包括王羲之、王坦之、殷浩等一时之俊的名士对儒、道、玄诸家各有擅长,但在与支遁的长期论战中往往狼狈败北,难求一胜。原因也在于,支遁在清谈和论辩中,注意掌握时机和火候,有时是他精心准备的长篇独角戏、个人脱口秀,“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冯怀)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指当时论述《逍遥游》的郭象、向秀两位大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出处同上)有时,则宛若九方皋相马,不管雌雄颜色,直取本质。“(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世说新语》之《轻诋》第二十六)有时,摆出一付“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样子,然后寥寥数语,后发制人,从容不迫地直接秒杀对手,“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王濛)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世说新语》之《文学》第四)。因为他的能言善辩,不被支遁赏识的名士王坦之,愤而著述免战高论,冠冕堂皇,煞是可爱。“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世说新语》之《轻诋》第二十六)
“道人有道山不孤。”(苏东坡《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州的花山有幸,遇上了这位喜欢高谈阔论的高僧。山出名了,名列江南名山家族,位居吴中山水典册,历代文人雅士们纷纷为之作传。姚广孝《游天池记》开篇就讲:“中吴山水之秀而奇,惟天池为最。天池在花山之右,其广无十亩。”袁宏道《天池》:“山巅有石如莲花瓣,翠蕊摇空,鲜芳可爱。”天池、花山,一体两面。钱谦益《华山寺募缘疏》:“吴郡华山寺者,晋支公遁拥锡地也。灵峰郁起,青牛垂度世之文;古涧奔流,白马著飞山之迹。莲花一瓣,六时之刻漏交传;鸟道千寻,七宝之树声竞奏。”确实是篇美文。归庄《观梅日记》有:“华山固吴中第一名山,盖地僻于虎丘,石奇于天平,登眺之胜,不减邓尉诸山,又有支道林之遗迹焉。”上述华山,即花山也。
有文史学者推论,支遁来花山开山,当在东晋成帝咸康至哀帝兴宁年间(335—365),这一带的“支公洞”“白马涧”“支硎”都因他的传说而得名。怪不得,花山,旧时即有“就隐山”之别称。自此,历代名僧高士纷纷来此隐居,超然世外。“飘零书剑十年吴,又见西风脱尽梧。”《心史》作者郑思肖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明代有名士赵宧光、朱白民等人在此隐居。明清易代之时,江南士子的反抗最烈,遁入山林或剃度为僧的遗民又以苏州最多。吴中著名隐士徐枋的“涧上草堂”就在不远处的白马涧景区。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板桥杂记》作者余怀,晚年隐居苏州,经常出没于花山、灵岩一带山水间,收入《清史列传》的余怀小传中有:“晚隐居吴门,徜徉支硎、灵岩间,征歌选曲,有如少年,年八十余矣,尝撰《板桥杂记》三卷。”
地处苏州西郊的花山,从城里远望如同一道翠屏。《吴地记》记载:吴县花山“晋太康二年(281)生千叶石莲花,故名”。早在春秋时代,老子《枕中记》就有“吴西界有华山,可以度难”句。花山与天池山相连,紧邻着白马涧,可以说是有山有水的一座天然园林,也是姑苏版的桃花源。花山,因此成了江南归隐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所谓“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再所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几乎每个中国文人都有一个桃花源情结,归隐在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和理想国中。这是中国式的田园牧歌和精神故乡。
《易经》中说:“天地闭、贤人隐。”还有一句仿佛是对后世不得志之人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隐逸于心灵不受奴役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中,是否体现了一种古老文明的内在尺度?这是中国士子们为自己设立的另外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
“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山不曾空。”(王昌龄《龙标野宴》)大自然是最好的心灵抚慰剂,青山明月是最好的老师。传统文人历来以山水为师,山水明月是最好的导师、最高的训戒。当李白听到王昌龄远谪被贬为龙标尉的消息,写下这样的诗宽慰好友:“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所寄怀遣兴的依然是山水明月。这也是尼采的对大地说“是”。
“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唐罗隐《曲江春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体验,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并不总是消极的、苦涩的,小到个体生命体验、生死证悟,大到证道修行、文化传承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有人说“山中无隐士,世上无宰相”,其意为,山上没有修行人,世间就出不了好宰相。南朝梁时江南倒是出了一位“山中宰相”陶弘景。他隐居茅山,屡聘不出,可梁武帝每有征讨吉凶大事,无不咨询。列朝列代,设想一下,若没有隐士,无论在危殆之时还是所谓盛世,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形态都会少了几分颜色,缺了几多光谱。
如果把目光投射得更远一点,我们发现,古代西方的哲学高士们也是喜欢“清谈”的。一类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就记载了他的那位成天与人在公众场合“清谈”辩论的老师苏格拉底,最终被雅典法庭以言论有辱雅典神和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处死刑。一类如伊壁鸠鲁,喜欢在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下与人“清谈”。他蛰居在自己的花园里,既无政治抱负,也不介入城邦的公共事务与纷争。伯里克利曾谴责只求独善其身而不问政治的做法为“白痴态度”。可伊壁鸠鲁却认为快乐才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哲学只服务于至善的、生命的利益,而不必服从城邦的利益。在伊壁鸠鲁看来,个体生命的至乐与至福莫过于好友间的聪慧、有益又令人愉悦的倾心交流。哪怕是处在人生最悲苦的时刻也会成为快乐的源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伊壁鸠鲁还在深情回忆与友人之间的那一场场交谈,从而减轻日夜折磨他的病痛。
中外贤人对隐者与其所处时代现实世界的切身关联,以及隐者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有独到的观察与洞见。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写道:“在无可作为的时代,逃离人世总是正当合理的,只要逃离者并不忽略现实,而是时刻认清现实正是他必须逃离的对象。”阿伦特进而追问:“我们一旦被人世驱逐,或者从中隐退,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对人世负有义务?”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一文里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系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收入钱穆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巧了,现在有一座名为“花山隐居”的酒店正好坐落于花山脚下。暮春时节,我们一行人就入住了“花山隐居”。连续两天夜里,一直听到一种蛙鸣。我在农村长大,听惯了蛙声,但时节未到啊,有节奏的,又似乎绵长不绝的嘤鸣,这是山蛙吗?同来的田瑛先生则认为是蝉鸣,而遍寻不见后,他却认为源头是耳鸣:“昨枕湖而眠,静极。蝉鸣贯穿了整个夜晚,间以蛙鼓与鸟啼。蝉声挥之不去,它顽固地响彻耳边。搜寻源头,声音不在外界,而发自耳膜深处。原来是耳鸣。”而我以为,这是一种久远而古老的天籁回响。
住在“花山隐居”,房间没有电视,远离尘嚣,随身就带了一本《世说新语》,看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