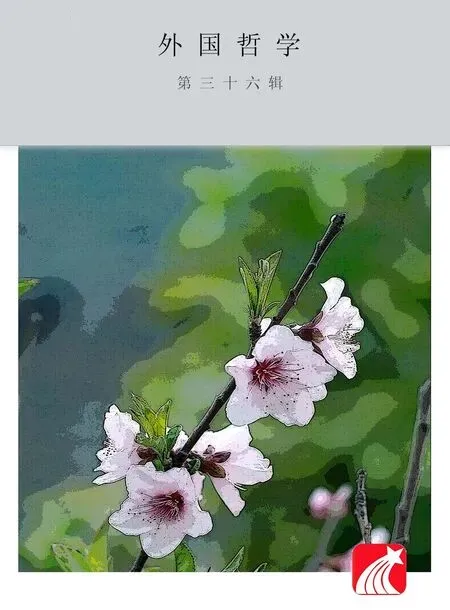洪元硕与他的大哲老爸洪谦教授
丁子江
近日得知一消息:(2010年)9月21日北京国安足球队主教练洪元硕“下课”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当上这位老兄球迷的我,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当年洪元硕是北京队的绝对主力边锋兼队长,精瘦的他个子不高,但跑速贼快,江湖人称“小快灵”。记得在球场上,球迷总是高喊“北京队8号,加油!加油!”1973年,洪元硕加入年维泗挂帅的中国国家队,担任前锋。但无论如何,我绝没有想到,这位球星与我在北大的导师之一洪谦教授竟有“瓜葛”。
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个星期天,我因要事拜访洪教授,开门的是一位穿着一套褪色旧球衣的壮年男子,看起来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此人到底是谁。当得知我的来意时,他叫了一声:“爸,有人找您!”我才明白这就是洪先生的儿子。颤颤巍巍的洪先生走了出来,介绍了一下,说道:“你们见过么?这是我儿子元硕,踢足球的。”从老先生消瘦的脸上看不出是甜笑还是苦笑。我这才将这对大哲与球星的父子关系对上了号。后来才听说,洪元硕中学时喜欢踢球,被北京队看上,但他的大学者老爸自然不同意。有次洪先生的老朋友,即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得知他要踢球,也说,要和你爸爸一样做学问,不要踢球。
后来洪元硕还是走上了足球的“不归路”,从此愈发不可收拾。他说:“如果不踢球,很快就是‘文革’到来,上山下乡,球踢不成,书也读不成,不可能像父亲那样学贯中西,所以当初的选择还是对的。”此话不假,我的另一位导师任华教授的儿子下乡,全家抱头痛哭,比别的家庭更感到一种生死离别之痛。后来任夫人过世,对任先生是又一次打击,使他陷于极度的悲伤之中,从此似乎一蹶不振,眼睛也逐渐失明。
据业内人士披露,洪元硕有着父辈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不愿趋炎附势,还有点桀骜不驯,这在足球圈里不合“规则”,有个别人就极力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因此他空有一腔抱负。好在近几年他带领青年队成绩斐然,乃至为前主教练李章洙出谋划策,得到俱乐部上层赏识,才有了老来出山、大器晚成的机会。
说来有趣,也很让人叹息。洪先生在哲学界那么有名,但在社会上的名声却远不如他那踢足球的儿子。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的所长是谁?我说了,他们不知道;可我说,他就是当时北京队8 号洪元硕的老爸,结果他们一阵亢奋,都说这下子知道了,也记住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闹得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球星的老爸手下的研究人员,但这个老爸叫什么,人们还是不知道。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领域,洪谦先生当然是泰斗之一。在改革开放后,他的学历、资格和名气曾一度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我进北大外哲所的时候,原本是由几位年富力强、学术上相当活跃的中年哲学教员,如陈启伟老师、王永江老师、张显杨老师中的某一位担任所领导。后来上面也许从国际学术与统战的角度考量,任命了洪先生为所长,熊伟先生为副所长。
记得研究生考试头天笔试结束之后,我正在闲聊。一位拄着拐杖、面容清癯、个子瘦长的老者颤颤巍巍地走进房间,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笑容可掬地鞠了个躬,然后一一同大家握手。别人怎么感受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感到了什么是礼贤下士的长者风范。那时还是百废待兴之始,受磨难的人们还没有完全重振起来,当时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洪先生还在对“文革”的后怕之中,还有夹着尾巴做人的心态,所以格外谦恭。
平心而论,洪先生当所长,对他本人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掌控的行政资源来扩大学术影响;但另一方面原来德高望重、温文尔雅、不谋其政的长者一下子卷进了各种行政俗务之中,很难会有“一碗水端平”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很可能会陷入一些无端的是非中,白白消耗了自己宝贵的哲思原创力。
由于我的导师任先生几乎双目失明,所以,实际上洪先生是我后来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另外还有周礼全先生和陈启伟先生等)。毕业之后,我留所从事研究工作,不久,由于某种需要,我当上了洪先生的临时外事助手。
其实当助手是被同事“盘算”的结果,而非洪先生作为伯乐相中了“千里马”。当时,首届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要在旅游胜地庐山召开,所以人人争着要去,但名额却极为有限。我的一篇题为《罗素人性论浅析》的论文被大会接受,于是有了参加“庐山会议”的资格。这时正好有位洪先生邀请的外国哲学家来华访问,需要有人接待。而当时,我正在为了出国而练习英语,利用业余时间在国际旅行社当导游。不知哪位好事者将此情况告知了洪先生,于是他老人家便利用所长的权力“剥夺”了我参加庐山会议的机会,命令我当这位来宾的导游。我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便无奈地答应了。这样一来,那个上庐山的名额便自然由他人顶了,以至令我至今都“耿耿于怀”。
说起来很惭愧,我这个助手挺不够档次,不能对洪先生这样的国际知名哲学家有什么学术上的协助,只不过跑跑腿,搞搞外事接待而已。其实,不仅是我,除了所里的陈启伟老师,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被洪先生真正看得上眼。孔子曰:后生可畏。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好像还没有值得洪先生感到“可畏”的后生;后来有没有,我不得而知。不过,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压力也能变成动力,如此一来,更加强了我争取出国深造、改善自己状况的决心。不过,惭愧得很,一晃二十多年下来,似乎还是不够那种档次,或许这也是命不该当“哲学家”的宿运结果吧。
在与洪先生的接触中,我也时不时能够感受到这位长者心中的某种怅惘和苍凉。某次,他让我看一张从国外寄来的相片,那上边是一栋宽大而美丽的别墅,四周长满鲜花。我不禁惊叹。这时,洪先生有些感叹地说,这是他在英国时一位同学女儿的别墅。我环视一下四周,眼前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洪先生的住宅却只是一个不大的单元,又小又挤,光线也不好,连客厅都没有。有几次我接待的外国客人想要来“洪府”做礼节性的拜访,都被我请示洪先生后婉言谢绝了。
洪先生1909年生于中国福建(原籍安徽)。20年代末他先就读于耶拿和柏林大学,1928年到维也纳学习。在那里,他以他撰写的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在石里克(M.Schlick)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在1930年到1936年石里克被暗杀这段时间,他经常参加石里克小组即维也纳学派的星期四夜晚讨论会。他无疑是参加石里克小组会议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之一。
洪先生曾回忆道:1927年他到了德国,在那里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赖欣巴哈提醒他重视石里克,他对石里克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及《普通认识论》评价很高,爱因斯坦也说石里克在这方面很有造诣。正是由于这种偶然情况,他才于1928年从柏林到维也纳去。石里克十分热情,一开始就指导他的学习。他建议洪谦首先扎扎实实地学习自然科学,认真学习数学和物理,并到卡尔纳普那里听数理逻辑。并建议洪谦暂时放弃他原来打算听的哲学课。当时他只听石里克的哲学课和魏斯曼(F.Waismann)主持的讨论课。但是他觉得石里克的讲课技术不是特别好。那时,洪先生说自己能听懂的不多,并说这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语言知识不足,但也可能是课程本身就不那么好懂。石里克在讨论班上的讲解非常出色,这和他的上课截然相反。他善于向学生提出问题,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始终很耐心,使讨论的问题得到清楚的解释。同时,他允许大家讨论的问题不一定根据他本人的著作和观点。洪先生记得,有一次他们把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哲学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学期。石里克十分尊敬罗素,既尊重他的哲学,又尊重他的人品。
洪先生说:“石里克很喜欢我,我们之间关系亲密。可以说,他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凡是他说的,我都照办。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丧失了独立性。后来我在他的《箴言》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追随别人的人,大多依赖别人’,这使我感到遗憾。我可以出入于石里克接待贵客的寓所。他时常请我到他家过节或者会见外国客人,例如艾耶尔和一位美国教授(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字),还有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费格尔,以及许多其他客人。……大约在1930年,石里克邀请我参加星期四晚上在玻尔兹曼巷举行的石里克小组会议。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原来没有机会认识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例如纽拉特(O.Neurath)、弗朗克(Ph.Frank)、门格尔(K.Menger)、哥德尔(K.Godel)、济塞(E.Zilsel)、考夫曼(F.Kaufmann)、拉达科维奇(Th.Radakovic)、奈德(H.Neider)、兰德(R.Rand)、心理学家布隆斯维克(Brunswick)、亨佩尔(Hempel),等等。参加维也纳学派会议的还有波兰人塔尔斯基(Tarski)、克韦斯蒂克(Chwistik)、雅斯科夫斯基(Jaskowski)、霍西亚松(Hosiasson)、林登鲍姆(Lindenbaum)。有牛津的艾耶尔,有都灵的吉莫纳特(Geymonat),有南美的林德曼(A.Lindemann)—他是克拉夫特教授的学生。纳格尔(E.Nagel)、赖欣巴哈有时也参加维也纳学派的会议。遗憾的是我在这些会议上没有见到过凯拉(Kaila)和蒯因(Quine)。”
有学者论述说:“在本世纪初,科学哲学伴随现代科学革命的新成果和封建王朝的衰败和垮台,从西方逐渐传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当时曾翻译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科学哲学(以及科学通论)著作。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胡明复、任鸿隽、杨杏佛,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地质学家丁文江,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王星拱等人都曾不遗余力地把批判学派的思想评介到国内,并撰写了诸多科学哲学论著。洪谦教授在40年代介绍逻辑经验论方面也有所建树。”根据考证,1938年6月1日,当时的贵阳医学院开学,除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设置,贵医还办了个“人文科”(Humanities),开设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为的是扩大医学生的视野。当时主持这一科的是留德专攻康德哲学的洪士希(洪谦)教授。在贵医院史中,洪谦博士名列教授名单之首位。这是因为贵医的科目是按人文科、基础学科、临床前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次序排列的。在当时创办人的心目中,人文科目绝非可有可无,它应该居于先行的位置。
其实,正如罗素1920年访华后,他的分析哲学在中国并没有多大影响一样,洪先生在回国后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没有使中国哲学界受到多大的影响。有学者就这样评论过:“马赫的实证论、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以及他们的现代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美国传播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了美国有发展经验论哲学的肥沃土壤。这与我国唯一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教授(1909—1992)归国后的遭遇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所以洪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中国缺乏发展经验论哲学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由于种种原因,现代西方哲学被贴上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标签,甚至大都还加上“反动”或“腐朽”两字。洪先生所代表的维也纳小组当然也在此列。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以及整个分析哲学的思想,尽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闹腾了一阵子,但其实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和有意义的重大影响。我每次回国,似乎人人言必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洪先生的那一套却始终很难掌握人心,这也许是他老人家九泉之下最感到遗憾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