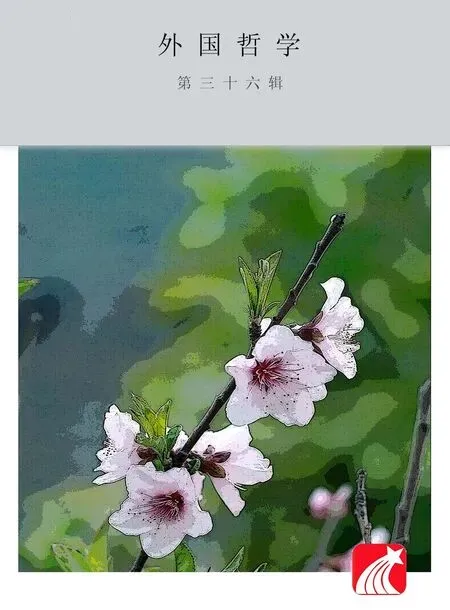洪谦先生论哲学
——纪念洪谦先生诞辰110年
尚新建
洪谦先生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始终积极推进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坚守哲学本来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对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居功至伟,深受我们后辈哲学工作者的衷心崇敬和景仰!
自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历程可谓举步维艰,跌宕起伏,历尽沧桑。时至今日,哲学学科在中国终于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数十所大学设立哲学系或哲学院(哲学学院);至少数千名哲学专业工作者从事哲学的教育与研究;每年数以百计的哲学博士毕业;国家和省部级重大哲学研究课题不断立项、在研、结项;大量汉语哲学论文、专著、译作问世;国际、国内哲学学术会议相继在中国各地召开,包括2018年8月由北京大学主办召开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到处一片如火如荼、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从世界哲学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的哲学学科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哲学家提出了什么举世瞩目的哲学命题或哲学理论?有多少成果获得世界学界的承认,有多少人能与世界哲学家平等对话?我们培养的哲学专业人才能否为世界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录用或在其中任职?答案恐怕多是负面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哲学仍未摆脱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所谓“自说自话”,指远离世界学术共同体,无视国际通行的标准,另立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围绕自设的问题组织研究和讨论,甚至能够引发一定规模的批评与回应,有问有答,有教有学,形成局部的、独特的学术团体和完整的学术产销循环链条。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在学科外表形式的庇护下关着门自娱自乐。不过,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我们不少学者竟然对这种落后局面熟视无睹,甚至沾沾自喜于眼前的成绩(和利益),其结果必然是迷失前进的方向。事实上,洪谦先生很早便提出类似警示,告诫国人必须不断反思哲学的性质,根据当代科学的发展及时调整哲学的方向,以免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借洪谦先生110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关于哲学学科及其性质的讨论,相信大有裨益。
洪谦先生1957年撰文指出:
关于国际的学术水平,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分量上能够用国际的一般学术标准来衡量。但是,我敢大胆地说,根据这些年所发表的著作或论文的质量来判断,我们的哲学水平与国际上的距离还很遥远;我们的哲学水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的教条式的解释,还周旋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思辨的游戏中间……①洪谦:《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 页。
应该承认,先生所说的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唯物论者或者唯心论者之类的辩论,现在已经过时,这无疑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哲学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仍如先生所言,“我们的哲学水平与国际上的距离还很遥远”,至今依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式的解释”和“思辨的游戏”。这里所说的“教条”与“思辨”,特指传统哲学的弊端和遗风。按照洪先生的理解,20世纪上半叶,由于分析哲学,尤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不再是一门理论科学,而成为一种活动。这种转变代表20世纪现代哲学的新趋势。传统意义的哲学隶属于科学的范畴,即便有人将其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喻作“科学之科学”或“科学之王”,但其性质仍然是科学的,因为它同科学一样,也被看作一种实际的知识体系或真理系统。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研究普遍真理,后者则研究特殊真理。①参见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18—19、26—30 页。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之所以为哲学,从本质而言,并不在于它对实际知识或真理能有所建树,仅在于它对实际知识或真理的逻辑意义能有说明,所以哲学在原则上就不是一种关于实际的科学,而是分析科学基本概念的一种逻辑的方法。”②同上书,第31 页。如果哲学原则上仍然属于科学,那不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科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因为它能说明科学理论的问题,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因此,哲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即不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体系。“哲学就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③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李德齐译,洪谦校,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 页。“哲学的任务是分别明确的思想与含混的思想,发挥语言的作用与限制语言的乱用,确定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命题,辨别真的问题与假的问题,以及创立一种精确而普遍的‘科学语言’。”④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6 页。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意义,科学才研究命题的真理性。正是从这个意义理解,哲学成为分析科学基本命题的一种逻辑的方法。
20世纪哲学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化,确实与当时科学发现的一些新方法密切相关,因为掌握这些方法,终于结束了历史上久议不决的哲学论争,以至于石里克宣称:“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①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李德齐译,洪谦校,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6 页。但是,哲学的伟大转变“并不是依靠方法本身”,而在于“看清逻辑自身的本质,这件事虽然是靠这种新方法才成为可能,是这种新方法所引起的,却发生在更深得多的层次上”。②同上书,第7 页。尽管亚里士多德很早认定逻辑是一门纯粹形式的科学,但是,他的逻辑及其理论并不能让我们看清逻辑的本质,即无从认识纯粹形式的本质。弗雷格和罗素创建数理逻辑之后,才使发现逻辑的本质成为可能。③关于弗雷格和罗素数理逻辑的新发现及其作用,参见拙文《我国哲学学科亟需激进改革的一点理由》,《外国哲学》第29 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如石里克所说:
逻辑形式弄清纯粹形式的本质,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即是说,这种陈述表达着其中所认识到的实况,而这是可以用随便哪种方式、通过随便哪种语言、应用随便哪种任意制定的记号系统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④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李德齐译,洪谦校,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7—8 页。
正是逻辑形式,使知识成为知识。换言之,“假如没有逻辑形式,不仅是一切表达或叙述无可能性,就是思想与语言也失去它的普遍的作用了”⑤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19 页。。这个发现导致两个重要结果:(1)解决传统认识论问题,终结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研究,代之以对表达和陈述的本质进行研究,即语言逻辑问题的研究;(2)消除传统的“知识的界限”问题,因为凡可以表达的问题,原则上都是可以由科学解决的。人们不能表达、不能解决的问题,并非因为认知能力有界限,而是因为它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并非真正的问题。传统哲学的问题,不少都是这类伪问题,表面上似乎符合语法规则,好像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但是一经哲学分析,便发现不过是一些空洞声音和符号的组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违背了新的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逻辑句法的深刻内在规则”①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李德齐译,洪谦校,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6 页。。于是,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失效了。
毋庸置疑,在逻辑实证主义眼里,形而上学问题理所当然地应列入失效者的清单。洪谦先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判定冯友兰先生“真正的形而上学”亦在劫难逃。冯先生洞悉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似乎承认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激烈批评②冯友兰先生明确指出:“维也纳学派所批评底形上学,严格地说,实在是坏底科学。照我们所谓科学的意义,坏底科学是应该取消底。取消坏底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贡献;不知道他们所取消底只是坏底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错误……我们是讲形上学底。但是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的批评的大部分,我们却是赞同底。他们的取消形上学的运动,在某一意义下,我们也是欢迎底。”(冯友兰:《新知言》,载《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 页),却认为自己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非但不能取消,反而“益形显露”。③参见洪谦:《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 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187—196 页。“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岿然不动,皆在于其命题是分析的,是对事实的形式的解释(形式的实际知识),诸如“山是山,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这种命题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一类命题(积极的实际知识)截然有别,因为后者需要证实有无相应的事实,如上帝是否存在,而前者则“并不肯定某些山的存在。只要‘山是山’是有意义底一句话,有山存在,固然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没有山存在,也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④冯友兰:《新知言》,载《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96—197 页。。然而,洪谦先生认为:
我们之所以称维也纳学派对于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有新的方法和途径者,即因它认为形而上学问题在哲学上的对象,并不在于某种“形而上学的客体”在实际上之有无的确定,而在于基本的形而上学命题在实际上有无意义的分析。维也纳学派认为所谓形而上学问题确为一个关于实际的问题,那么它必须从分析上而能了解其在实际上的意义,假如它根本未具有任何关于实际的意义,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只是一种如维也纳学派所谓“似是而非的问题”了。①洪谦:《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 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190 页。
凡关于实际的命题,必须表达或叙述事实,其有无意义,以证实方法为标准。“所谓证实方法者,就是指示我们对于某个命题与实际的比较手续,了解某个命题在实际上的事实根据,换句话说,就是说明某个命题在某种实际条件之下是真的,或某种实际条件之下是伪的。”因为有真伪之条件,才有实际证实的必要。倘若无论什么条件下,都不能证实其真伪,那么这一命题便没有意义,即为“似是而非的命题”。冯先生分析的形而上学命题,虽然并非“不能真或伪的命题”,却是“永真的命题”,即洪先生所谓“重复叙述的命题”(tautalogische Aussage),其真伪与一切实际无关,原则上无所谓证实方法,“自然是一些空洞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命题了”②同上书,第193 页。。因此,洪先生断言,如果说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是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胡说”,那么,冯先生分析的形而上学命题便是与实际毫不相关的一种“空话”。③参见上书,第194 页。
不过,洪先生申明,维也纳学派的确是“反形而上学”的,但是,这只是“想将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活动范围加以指示,在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加以确定”,并非“取消”形而上学。因为,尽管形而上学不再是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却仍然可以在人生哲学方面产生重要意义,“对于生活方面感情方面则具有科学所却未有的作用”。形而上学可以给人们提供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慰藉,“所以,人称形而上学为‘概念的诗歌’”④同上书,第195 页。。不难看出,洪先生对形而上学持宽容态度。这或许与他的哲学观密切相关,因为洪先生认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部分”⑤洪谦:《欧行哲学见闻》,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367 页。。相比之下,艾耶尔的态度要强硬得多。艾耶尔也把形而上学家看作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诗人,因为二者似乎都讲述没有意义的语句。但是,他特别指出,诗人的创作是为了激发人的情感,写出的语句大多具有字面意义,只是为了韵律和对偶,才会牺牲部分意义,以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形而上学家则不然,他之所以写出没有意义的语句,完全是被语法所欺骗,是推理错误导致的。因此,形而上学家的陈述未必像诗歌那样,具有美学的价值。①参见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6 页。
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激烈批评,同样遭到学界的激烈批评。作为检验实际命题是否有意义的证实方法,亦多为世人诟病。维也纳学派经历了短暂的辉煌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20世纪60年代,有哲学史家宣称:“逻辑实证主义……死了,或者,作为一个哲学运动正在死亡。”②J.A.Passmore, “Logical Positiv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5, New York:Macmillan,1967, p.56.大约同时,通过斯特劳森和蒯因等人的工作,形而上学复兴,为英美哲学主流接受,且生机勃勃,前途无量。历史的这种戏剧性变化,常常遮蔽人们的眼睛,误以为逻辑实证主义不过是哲学史的匆匆过客,或许亦是诸多哲学谬误的一例,从而忽略甚至抹杀了这种富于瑕疵的哲学运动的革命性质和积极作用。按照洪谦先生的判断,逻辑实证主义代表“现代哲学的新趋势”。此言不虚!弗雷格和罗素等人创立的数理逻辑,不仅为现代哲学提供更精确、更普遍、更形式化的技术手段,重论证,求清晰,严标准,形成一套独特的哲学方法论及其话语风格,而且引导哲学家重新确认哲学的对象及其范围,提供更广阔、更技术的方式审视和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并提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哲学问题,开拓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重新规定哲学的基本任务。逻辑实证主义正是这一现代潮流的积极推动者及其代表。它透过数理逻辑寻求“逻辑的形式”,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向语言、思想、意义及对象,主张“所谓哲学的问题,就是对于表达与叙述的本质一种逻辑反省,对于语言与概念的应用一种逻辑分析”③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19 页。。所以,哲学家应当自觉地将“哲学的分析”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分析以阐明命题“实在的”逻辑形式。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其前提以一个基本信念为基础,即: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之间有密切关联,语言才是我们与世界的交界点,“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①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5.6。;因此,阐明命题“实在的”逻辑形式,不仅能够揭示世界的基本结构及构造,而且能够解决误用语言和思想逻辑而产生的种种困惑。逻辑实证主义,是沿着这个方向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尽管最终失败了,但其批评本身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依然具有以下几点意义:(1)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蒙昧和粗糙提出质疑;(2)表现出学术的认真和诚实态度,坚持论证的严格标准;(3)关注关键细节部分,反对大而化之的笼统概括。更何况,英美哲学后来重振的形而上学(有人称之为分析的形而上学),无论其对象、论题,还是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有明显区别。历史的事实证明:曾由逻辑实证主义引领的哲学运动或哲学潮流,逐渐从少数派的革命观点转变为英美哲学界的惯常的观点,并占据统治地位。它不仅在英美世界是哲学主流,而且在20世纪末,也成为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欧陆国家的哲学主流。不仅大量的出版物呈现出社会学上的显著优势,而且其哲学话语和范式,渗入并塑造着当代的哲学实践,提升了哲学学科的专业性,成为学科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甚至成为一种学科标准。②参见Michael Beaney, “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Michael Bean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29; Hans-Johann Glock, “The Owl of Minerva: Is Analytic Philosophy Moribund?” in The Historical Turn in Analy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Erich H.Rec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326-347。
作为维也纳学派的一位成员,洪谦先生得天独厚,目光如炬,紧紧把握现代哲学发展的脉搏,力图引导中国学者跟上世界潮流。遗憾的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洪先生的告诫未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今天,国内哲学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仍与世界哲学水平有很大差距,甚至渐行渐远,背道而驰。真诚希望洪先生几十年前的教诲能够让国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