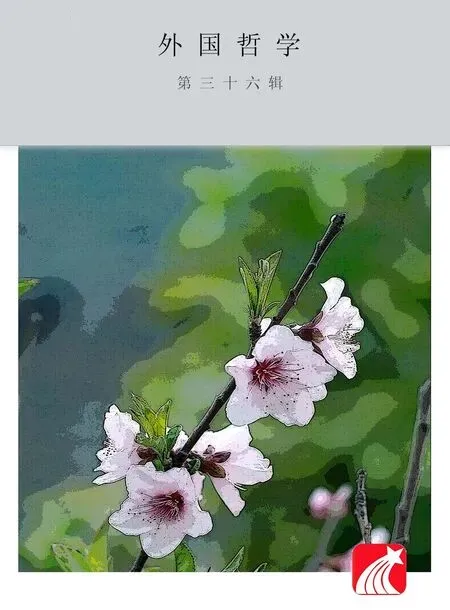政治清白 信念坚定
——回忆洪谦
梁志学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洪先生已经逝世25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是他的学生,在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时期,经常向他求教,来往甚多。有几件往事,难以忘怀,现在书写出来,作为对他的纪念。
第一,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国内的各个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大,洪先生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那时我们这些学生就知道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有些同学还看过他写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但我们当时认为这个学派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没有学生愿意追随他学习。教研室也不开课,老师们大多致力于翻译,而且来自各个大学的老师们还不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洪先生有点不耐烦,想离开这里。他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挚友王炳南(外交部前副部长)进行联系,想到外事部门工作。金岳霖(当时的系主任)和郑昕(后来的系主任)出面劝阻,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后,郑先生向我谈了这个情况,并且评论说:“他这个人政治历史清白,但不知道自己不是党员,怎么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他这个人哲学信念坚定,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批判逻辑实证主义。”
第二,随着1954年12月中国和英国达成香港问题的协议,两国关系逐渐好转,A.J.艾耶尔对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这位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吞并奥地利之前,多次访问维也纳,已经与洪先生相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洪先生赴伦敦,任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但在哲学楼西部大教室举行报告会,艾耶尔看到坐在第一排的洪先生时,不向他打招呼,洪先生也假装自己不认识艾耶尔。这次学术报告会开得不成功,因为翻译水平低,让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不过,还是按照预先的布置,报告人入场时全体鼓掌;但他离开会场时,只有一部分听众鼓掌。25年以后,洪先生赴伦敦进行学术访问,艾耶尔告诉他:“我那天一进教室就看到了你,但不敢同你讲话,怕我走了以后,有人怀疑你里通外国。”洪先生在把他的这段经历告诉我时,深深地表示,在没有思想自由的氛围中必然会让人存有这样的戒心。
第三,1955年夏季,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我被抽调到教师队伍里,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与逻辑教研室组成的学习小组的副班长,郑昕是挂名的组长。按照哲学系肃反领导小组(汪子嵩、王庆淑)的布置,我们小组要批判沈有鼎,因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曾经哀叹“世界末日到了!”进行准备的小组会邀请了一部分老师,在燕东园洪先生家里召开。在这次会上,谁也没有说沈先生在历史上有什么政治问题,只是谈了一些有趣的琐事。例如,洪先生谈到,他与沈先生于1942年从伦敦返回昆明,路过加尔各答时上街散步,后边跑来一群男孩,要给他们抱佛脚。他很害怕,躲到了商店里,沈先生则表示欢迎,结果倒在了大街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被掏光了。洪先生单独提醒我说,沈先生不关心政治,也不过是在宗教情绪的支配下说了错话,他希望我能掌握分寸。在随后召开的批判会上,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说过头的话,只是发动大家批判沈先生的错误言论。这从当时的斗争气氛看,也许显得有点温和,但从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来看,却没有出偏差。
第四,1956年7月我从研究生班毕业,原初是要留在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洪先生知道我在数学系学过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教程》,在物理系学过弗里斯《普通物理学》,而且正在学习德语,所以特别高兴;在我最后被分配到科学院哲学所时,他仍然对我表示关切,我也不时地到燕东园拜访他。我被划为“右派”,他表示痛心;在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他还想把我调回北大,而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一直担任《哲学译丛》“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栏目的责任编辑,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主任杜任之(1928年参加地下共产党)是他德国留学时的朋友,把他聘请为我们的刊物的顾问,这样,在洪先生与我之间就进而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论文,大部分都是由他推荐的,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他都对如何改进刊物的编译工作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可以说,在我们充当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国际理论战线上的哨兵时,他给予了我们必要的协助。另一方面他还吸收我参加他所领导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例如,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的编译工作,哲学所的同事们看到他这么提携我,都表示羡慕。
第五,1964年秋末,中共中央已经发表完关于中苏西贵论战的“九译”,计划下一步写出“十评”,批判赫鲁晓夫的世界观。这篇文章的第一节是批判老修正主义哲学,需要译出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好多人参加了翻译工作,上卷的统校任务交给北大哲学系王太庆,由洪谦当顾问,下卷的统校任务交给科学院哲学所王玖兴和梁存秀,由武剑西(共产国际第一任中文翻译,高教出版社社长)当顾问,他在德国时认识洪先生,他们在武汉大学时又短期在一起任教。在一次讨论翻译问题的会议上,武老发现我是洪先生的学生,就特别喜欢我,极其认真地修改了我的译稿,令我终生难忘。在这个时期,我经常将自己遇到的德文问题提出来,直接向洪先生求救,他都给予详细的回答,使我的德文水平有所提高。
第六,1966年6月《哲学译丛》停刊以前,我一直对民主德国科学院哲学所所长G.克劳斯批判地研究逻辑实证主义的成果抱有兴趣,先后读过他写的《逻辑经验主义》(1961年)、《符号学与认识论》、《词的威力》(1964年)和《狭义认识论》(1965年),我把想法告诉给了洪先生,他明确地表示,克劳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用批判的眼光肯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成就,这样的态度完全正确。为了理解这位出色的哲学家,他还从外文书店买到克劳斯与M.布尔编的《哲学辞典》。1965年春,我们发表了一批语用学家的论文,我紧接着写出《克劳斯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文,送给他提意见,他很审慎地说,此中写的语形学与语义学部分没有问题,语用学部分则难以评判,因为研究的对象太复杂。他的这种谨慎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在追本溯源,进而研读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著作时,他给过我许多指导,解答了许多难题。但说实话,在阅读M.石里克的《逻辑哲学论》和R.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时,尽管洪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而我始终未完全弄懂。
第七,1972年8月,哲学社会科学部从河南明港迁回北京,许多研究人员都想恢复荒废了的业务。我正在与薛华商讨我们该如何着手时,洪谦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告诉我,哲学系安排他与唐铖、宗白华节译马赫《感觉的分析》中那些与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关的部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参考书,这个任务已经完成,需要我承担起统改的任务。我当时感到为难,一方面觉得自己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觉得不好办:改多了,老师有意见;改少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通不过。洪先生深知我心里的想法,当即向我说:“你要大胆,不要怕我们这些老头对你有意见,同时你要细心,千万不要出纰漏。”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先改出一万字,分别送给洪先生和商务。三位老师看过以后点了头,商务看过以后表示可以出版。新年前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但在看校样时洪先生发现,他写的一篇比较翔实的译者前言不见影踪,而强加上了一篇由哲学系领导指定黄枬森写出的“译者前言”,大力强调“四人帮”所谓的“党性”原则。在当时那种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下,木已成舟,洪先生只能忍受。只有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出版这部名著的全译本(过去未译的部分是由我补齐的)时,洪先生才有可能把节译本里的那篇译者前言去掉,指明那种“党性”原则并无用处。
第八,1973年5月全国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他心里很烦闷。有一天,他约我陪他到天坛逛游。他给我讲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冯友兰写了两篇“批林批孔”的文章,经“梁效”(“四人帮”的喉舌)之手递给毛主席,得到了好评,江青还特地访问了他。洪先生对冯友兰的这种观点的转变很反感,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坚定的哲学信念,绝不能为了个人的利害而改变观点,附和某种外在的政治浪潮。我告诉他,贺麟先生在如何对待这种浪潮的问题上也有过考虑,起初怕人家说他过去提倡新儒学,现在躲到旮旯里译黑格尔不表态,在最后还是决定“你批你的,我译我的”。洪先生听过我说的,十分兴奋,当即表示“贺公的态度完全正确!”另一件事是洪先生为他的小儿子洪元硕操心。元硕当时在北京足球队里是公认的最优秀的队员,但每月工资不过40 元,在生活上不得不由家中接济,洪先生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真不知道在我去世以后,他怎么再干下去。”这么低的工资水平,真是令我感到吃惊。在东安市场南端和平餐厅吃午饭时,洪先生想到我们应当去看望武剑西,但在我们提着新买的水果到达武老的住处长椿街62号时,邻居告诉我们,他由于忍受不了批斗,早就驾鹤西游,我们只好抱着悲痛的心情离开那里。
第九,从1973年到1979年6月,我把自己的精力大都花在与同伴们合作翻译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和黑格尔《自然哲学》上。我把先译出来的“导论”都送给洪先生审阅,他给我们提过改进意见;知道我当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趣所在后,他还送给我一些德文哲学书,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费希特那种为真理而真理、为自由而自由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在这里,前一个“为”是认识真理的理论理性,后一个“为”是体现真理的实践理性,学者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沈真和我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用了4 个月时间,参照俄文译本译出了这本经典作品。这本书在商务出版于1980年,我把它赠送给洪先生,他举手称赞,说他在青年时期读过这本书,受益匪浅。由此可知,这本书为什么在中国迄今印刷了8 次。
第十,师生关系有时也会出现问题。一般来说,学生容易承认自己的差错,当老师的则不完全如此。洪先生与我的关系也发生过阻隔。1986年,他主编《逻辑经验主义》译文集,要我承担一部分任务,我实在忙不过来,只好婉言谢绝。他很不高兴,对我开始冷漠起来,将近一年没有来往。他去商务谈工作,看到武维琴、吴隽深正在审读我送去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译稿,他恍然大悟,当场就说自己对我采取冷漠态度是欠妥当的。这两位编辑把他的话传给了我,我惶恐不安,当即赴北大拜访他,说明自己过去没有把自己的忙乱情况讲清楚,洪先生却摆了摆手,表示不谈这个事情,而把话题引到评价费希特哲学的问题上,询问了我与德国费希特全集主编R.劳特交往的情况。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恢复了原状。洪先生能在那两位编辑面前责怪自己,这对我也是一种教育,让我对学生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1992年冬,我和胡文耕到友谊医院看望他,他已经病入膏肓,不省人事。我们在他面前驻足良久,脱帽敬礼以后,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病房。为了展现他的成就,范岱年和我收集了他发表的论文,编为《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我总是想到,洪先生一生的政治生活是清白的,哲学信念是坚定的,在长期的不良环境中他都不放弃自己崇奉的真理—这就是我对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