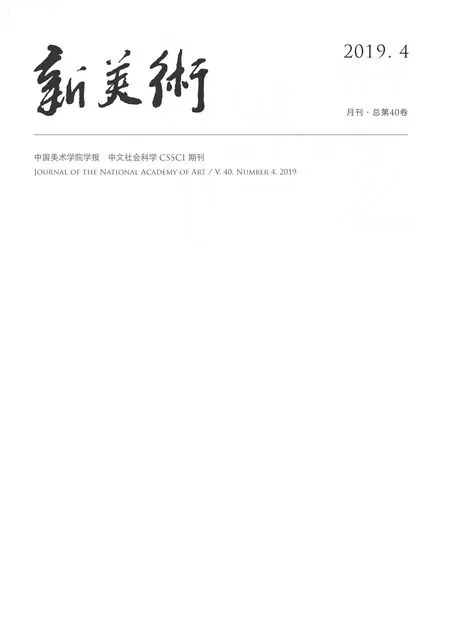中国现代设计巨匠陈之佛特展策展手记
吴光荣
三十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学的专业叫装潢设计。传统图案与三大构成课程都有学过,对图案课程的认知与理解深有体会,觉得它能够解决许多设计中的问题。在我们学习设计时,图案是必修课,最为看重的是:字体、图形、色彩,后来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多年后,我带学生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了图案课,很多同学在做装饰时都无从下手,原因是没学习过图案。在中国历史上,图案的用途极其广泛,很多场合都有,是图案保留和传播了文化。“那时若不懂图案,可能都不能称之为中国人”1与张道一老师访谈记录。。
2016年11月8日,我同杭间老师一起去慈溪陈之佛艺术馆,参加陈之佛先生诞辰120周年所举办的“历久弥新·陈之佛图案原作精品展”,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的图案原作。当时我们已有通过展览的方式系统地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的想法,并将展览纳入“中国现代设计巨匠系列”。在此期间见到了陈之佛先生的女儿、女婿陈修范、李有光两位先生,提及我们想做“陈之佛先生特展”的想法,两位先生当即表示支持。
陈之佛,初名陈本绍,16岁时更名陈之伟。22岁时去日本留学,更名为陈杰。1925年的3月底,完成学业并回国,更名为陈之佛。在今天人们的印象里,上了年纪的人认为陈之佛是位图案家,年轻一些的人认为陈之佛是位工笔花鸟画家。
2018年,恰逢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也是陈之佛赴日留学,开始近距离观察、学习日本设计100周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短短的十年间,日本军队三次踏足中国土地,这可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三次战争,让日本人对中国由崇敬而变为蔑视。2“1907年1月,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向首相西园寺公望呈送《对清政策之我见》,对于清国上下对日本的看法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向我帝国学习成为风靡清国上下之趣事,以前独从德国聘请陆军教官,现则亦从日本雇佣,我国受聘赴清国作警察、学校教官、技师者不断增加”。(引自:杨芾等著,《扶桑十旬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庚子之后,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两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一个新兴的立宪岛国,竟然打败了横跨欧亚大陆、实力超强的老牌专制强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一跃由落后变为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先进国家,这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君言立宪与国民接受新教育的长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可当以楷模,事实上也是。这便是晚清及民国初期,中国掀起赴日学习热潮的原因。陈之佛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图案,其目的是为将来以实业救国。
学成归国后的陈之佛,选择了远东最为繁华的城市上海,开启了“实业救国”的践行,建立 “尚美图案馆”并做了大量的设计服务于社会。但美好的抱负及理想并不能向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陈先生不久便离开了上海,南下去了广州,从此便投身到了教育。并于1942年至1944年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百年之后的今天,回望中国设计,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自信的因素,曾经延续五千年的从未中断的图案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却慢慢被边缘化,学术界更是缺少对图案与造物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如何来做这个展览,以怎样的角度来展示陈之佛在多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如何梳理已知相关文献,并提出我们的学术观点与方案,都取决于我们今天所持的学术立场以及所选取的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
拜访著名学者、陈之佛先生的学生——张道一先生,提出我们想做陈之佛先生的展览,就如何去做这个展览以及相关问题向先生请教询问,并聘请先生担任此次展览的学术顾问。在此期间,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着手编辑出版《陈之佛全集》,其中关于陈之佛与国立艺专的相关档案、资料,可向我们提供一些。
拜访陈修范、李有光两位先生。在慈溪时虽然有过短暂交流,但两位先生能提供些什么样的展品资料尚不清楚。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不时地将一些保存至今的相关资料、物品、教案一一呈现。有一些是复印件,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时的相关档案,包含1942年国立艺专呈报给教育部的招生简章及学校的教职员工花名册,聘任多科言任的聘书、文件,建校舍的相关程序、图纸、专家委员会名单、第一次辞职信、辞职报告等。还有一些新中国解放后陈之佛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的图案教学大纲及备课笔记,共有多个年级,可见当时的图案教学之重要。同时也发现陈之佛多是在教授图案,并未开设过工笔绘画课程。还有那张著名的陈之佛抄录1946年吴冠中公费留学试卷。
联系慈溪陈之佛艺术馆,前去拜访该馆工作人员胡迪军先生以及慈溪收藏家孙仲山先生,他们在工作之余,对陈之佛的书籍装帧设计及绘画,多有研究及收藏,有一定的数量,艺术水准均属上乘。
浙江美术馆几年前接受的陈之佛写给傅狷夫的69通信札的捐赠,以及吴冠中捐赠的绘画作品也是我们做陈之佛特展所不可缺少的。
接下来便是洽谈借展部分作品。对国内不同区域关注陈之佛先生之学术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收藏家等及官方相关机构,我们做了仔细的调查了解,掌握了一些陈之佛的相关作品信息,但能否借到手,并没有十分把握。好在有陈修范、李有光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浙江美术馆的鼎立相助,我们在两年的时间里为展览做好了准备。
另外,我还委托了我的硕士研究生、正在日本筑波大学做交换生的宋邹邹同学,多次前往东京艺术大学查找陈之佛当时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相关资料。并复制了《东京美术学校一览》(从大正十年至大正十四年,缺少大正九年),其中可以查到陈之佛在该校学习的所有课程及相关记录,从而修正了国内学界延用的“1923年回国”之说,实际应是1925年。
展览作品有了,如何来梳理文献,以及展示和空间设计等,都是需要精心策划的,我们组织团队共同讨论如何呈现陈之佛的设计、绘画及学术成就,依据已掌握的相关文献、图案、教案、信札、绘画作品等,来考虑展览板块的划分,以突出陈之佛在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往国内所做的有关陈之佛的展览,多数是绘画展览,少数是图案展览。很少有做综合整体的陈之佛展览。而我们要做的陈之佛特展,应该是第一个整体呈现陈之佛多个方面艺术成就的展览。
关于板块的划分,大家进行了多次讨论,梳理出了五个方面:陈之佛与中国图案学;陈之佛与20世纪中国设计教育;陈之佛与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与实践;陈之佛与国立艺专;陈之佛的绘画艺术。
1.陈之佛与中国图案学
该板块所展示的是陈之佛的一百幅染织图案原稿。1925年,陈之佛在上海建立了“尚美图案馆”,开启了经营设计,为染织行业设计了大量的彩绘图案稿,在尚美图案馆的几年时间里,业务很好,供不应求,但是拿不到钱。当时的上海染织行业,生意兴隆,但尚未形成花钱去买设计,与客户之间关系融洽,就像是朋友之间,请客吃饭花多少钱,别人认为无所谓,但是,设计好的图案,付多少钱一张,还没有这样的规矩。3同注1。这可能也就是尚美图案馆很难经营下去的真正原因。在这一百张的图案表现中,我们看到了陈之佛对美术工艺本质的追求。在图案美的构成中,践行了变化、统一的多种要领。由此,他对美术工艺有了较为客观的认知:“美术工艺是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实用之中使与艺术的作用抱合的工业活动”;“美术工艺品是美术和工业两者本质的融合,是使人类生活的持续同时又以人类生活的向上为目的的。”一百幅图案原稿,展示了陈之佛对图案“形式法则”的认知与贡献。
2.陈之佛与20世纪中国设计教育
此板块重点展示了陈之佛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时,给不同年级开设的图案课程教学大纲及备课笔记。在美术专科一年级第二学期图案教学大纲中,有:(一)课程目的;(二)教学时数;(三)教学大纲。在课程目的中,强调三点:1.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对于图案教学上的基本知识和技能;2.使学生获得基本图案的方法及色彩的运用;3.使学生对于图
案在教育上及实用上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
在教学时数中,排课十七周,每周四小时,共六十八小时。该教学大纲为中等师范美术专业所设,在一年级阶段,图案课两个学期都有,课程安排由浅入深,除了讲课外,留有大量的作业,并以课时进度来要求学生的作业,通常先由临摹开始。在二年级的图案课教学大纲中,出现了立体图案法,讲述了立体器物的构成与器物表面装饰,及其与图案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中国图案研究和装饰研究。
在1954年的美术系一年级图案教学大纲中,图案列入了必修课。课程目的强调了三点:一、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美感能力及创造能力。二、使学生能掌握图案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中等学校的教学服务。三、通过图案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国图案传统的伟大和优秀。这个教学大纲,显然与前面的教学大纲有所区别,且层次不同。
3.陈之佛与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与实践
这个板块中,展示了陈之佛为几家著名杂志及出版社所做的装帧设计。该板块最初的想法是还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融入世界设计思潮之中所出现的众多优秀设计,在这个文化背景中,陈之佛的设计与他人的设计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与世界设计之风有何区别等,来展现陈之佛装帧艺术的独特之处。可惜,想象的远不及现实,能说明事实的资料还是很难寻觅到的。在已展出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尚不够全面,很难反映出陈之佛较为完整的设计思想。
陈之佛回国后不久,即为《东方杂志》设计封面,直到1930年。这期间也应邀为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刊》做装帧设计,同时也在经营尚美图案馆。1928年的下半年,陈之佛离开了上海,南下到了广州,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7月,离开广州,又回到了上海。可见在这几年中,虽然不在上海,但给杂志做装帧设计,却从未中断,我们展出的杂志与书籍虽不够完整,但基本上可看出陈之佛书籍装帧的独特魅力,他在封面有限的空间里,将字体、图形、色彩融入一页之中,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在书籍的纸张、印刷形式及材料等多个方面也都有强烈的追求与实践。
4.陈之佛与国立艺专
该板块展示了一些陈之佛与国立艺专相关的文献、档案资料,基本理清了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来龙去脉。
在展出的文献中,有吕凤子写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推荐陈之佛为艺专校长的信件,也有教育部的任命文书。陈之佛接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时,应是国立艺专在抗战期间最为艰苦之时,青木关的校舍简陋拥挤、破旧不堪,临时改为上课教室光线昏暗,极不适合,便有了跟教育部申请校舍的方案。展示的档案中就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新建教室及教职员宿舍图说、施工说明、工程估价、校舍建筑委员会名单等。
陈之佛到任后,本着“求良才、课实务、除积弊”的宗旨,聘请了一批著名画家到艺专任教。展览中有民国三十一学年第二学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清册。由此可知,陈之佛的到任,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与支持,国立艺专也迎来了“抗战”西迁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
展示的档案中有“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六日,上报教育部的国立艺专招生简章”;有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时的六次辞职信中的五次辞职信;有一枚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时所使用的校徽;有陈之佛先生写给傅狷夫先生的69封信。还有一份较为特别的档案,为艺专学生自治会上报教育部的,由于校长吕凤子辞职而无人接替所引发的风波,向教育部提出对接任者的四点要求:一、在艺术界富有威望并热心于中国艺术运动者。二、对艺术教育行政有经验者。三、能聘请优良教授者。四、必须专任者。
5.陈之佛的绘画艺术
展出的绘画作品,虽然不多,但涵盖面较宽。有早年的装饰画,写意花鸟画,工笔花鸟画,还有几张尚未画完的半成品。关于陈之佛的绘画艺术,陈先生的学生,邓白先生有过客观的描述:“陈先生擅长工笔花鸟,继承了徐熙、黄荃的优良传统,直登宋、元堂奥,又广泛吸收钱选、吕纪、陆包山,恽南田诸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参以写生技法,独树一帜,创立了他那清新隽逸的艺术风格,把传统工笔花鸟画向前发展了一步。”
我们邀请了王欣老师担纲展览的空间设计,视觉设计则由吴炜晨老师操刀。关于陈之佛特展的空间想象与视觉效果,我们做了多次讨论与沟通,大家希望多找些史料,并通过阅读来了解陈之佛先生在那个年代的所有经历,以帮助我们认知陈先生。王欣老师依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抱病西行,带着一家老小,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将寓所取名为“流憩庐”的态度,展开空间设计: “以传统中国的‘大靠’‘大座’的形制出现,即‘屏山下的船形座靠’,是文人的端坐资态,是小中见大的虚拟书房:夜幕下的漂泊斗室与华彩思想的画意组合。书房,即是文心。夜幕屏风下之船书房,即抗战期间陈之佛先生在重庆的居所书房——‘流憩庐’的诗意再现。流憩,漂泊流亡中的小憩,这是在巨大困境的一种超然心态。‘流憩庐’是先生在困苦中坚持创作的生命立锥,是推进艺术教育救亡事业的案头阵地,是中国现代设计启蒙之路的诗画坐标。夜航,茫茫夜色中的航行,苦心孤诣探索不止。夜色屏风上的华章,是极限空间与时代困境下的精神华彩与创作不息。”以此来再现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感谢浙江美术馆、陈之佛艺术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艺术》杂志等诸多机构的大力支持!
感谢张道一教授担任此次展览学术顾问!
感谢李有光、陈修范、孙仲山、胡迪军诸多先生对展览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