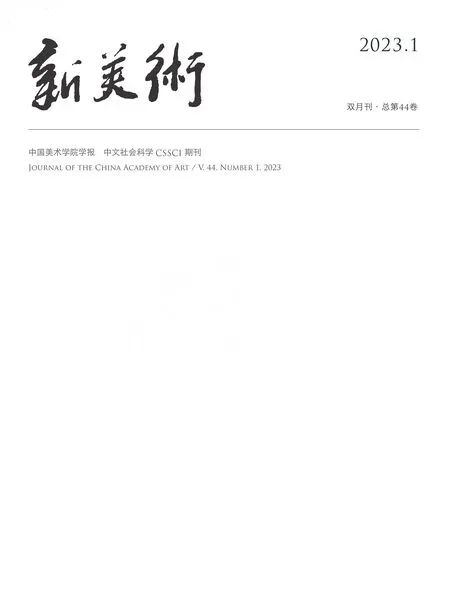陈之佛留日时期相关史料考* 以新见《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为中心
谭小飞
陈之佛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设计的拓荒者之一。陈之佛早年在东京美术学校的留学经历,构成了中国现代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节点。陈之佛一生著述丰富,在图案学、美术学多个领域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始,关于陈之佛的画集、图案作品集开始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大量美术、设计学人开始撰文介绍陈之佛的生平活动、思想和学术成就。国内除大量文章与文集之外,还有多本专著陆续出版。2020年《陈之佛全集》的出版,更是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陈之佛的早期美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图案领域,美国学者朱莉娅·安德鲁斯[Julia F.Andrews]提道:“作为中国首位职业平面设计师,陈之佛的重要性尤为突出。”1Andrews,Julia F.and Kuiyi Shen.A Century in Crisis: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Solo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1998,p.185.可见,对于陈之佛的重要性,中外学者基本形成一致共识。
一 起因
近年来,关于陈之佛的研究愈发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各种论文、专著、展览、文集频出。笔者在查阅陈之佛材料时,发现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点:关于陈之佛留学时间的起止。在吉田千鹤子《东京美术学校的外国留学生》、陈日红的《对〈陈之佛年表〉中留日学习图案经历的相关考证》、李华强的《设计、文化与现代性:陈之佛设计实践研究(1918—1937)》等新近成果中已经形成共识,即陈之佛于1920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1925年毕业。但在《陈之佛全集》之中,编撰者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考订为“1919年至1925年”。可见,关于陈之佛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入学时间,仍存有争议。
关于陈之佛的具体赴日时间,现有成果基本沿用了《陈之佛年表》中的表述方式,即“1918年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日本。1919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2陈修范、李有光,《陈之佛年表》,载《美术与设计》1982年第1 期,第19 页。不难看出,由于缺乏原始档案,这部分材料需要详细考证。
第二点:陈之佛留日期间的费用形式。已有成果同样沿用了《陈之佛年表》中的“官费”说法,同样缺乏史料佐证。并且,陈之佛的官费与同时期其他留学生的官费有何异同,也未能加以说明。
第三点:陈之佛留日期间的住所。住所是陈之佛能够完成学业顺利回国的重要前提。陈之佛子女编写的《陈之佛年表》中提到,陈之佛留日期间“一直住在神田区猿乐町二·一清寿馆一号房间”,这部分材料也是经不住推敲的。
第四点:陈之佛的归国时间。关于陈之佛的回国时间,现有成果主要有1923年4月、1924年、1925年3月、1925年7月四种说法。考察发现,这些观点无论在史料可信度上,还是在解释层面上,都显得不可靠。
早有研究者发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的两本《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分别为1923年和1928年版(其中,1928年陈之佛早已毕业回国,该版对本话题不具有讨论价值)。并且,《中国近代教育文献丛刊 留学教育卷04》3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件丛刊 留学教育卷04》,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还对1923年版进行了影印重刊。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发现该文本对于陈之佛留学史料的研究价值。
笔者于2020年研究陈之佛档案时发现,浙江省档案馆网站“数字档案”查询栏目有“留日学生同学录”专题,因系统录入信息中有明显错误,笔者进一步考察该档案的原始来源,查找到浙江省档案馆馆藏1920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1921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报》、1922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1924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四本重要史料。并且,在该馆《浙江大学校友录》中还发现了分别以“陈杰”和“陈之佛”名字著录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和教员校友身份。此外,笔者自藏一本1917年版《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在此基础上,结合浙江图书馆藏1923年版《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笔者发现已有成果有语焉不详、甚至讹误之处,本文通过对这部分原始档案的梳理,结合民国时期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等材料,试图修正陈之佛留日期间的相关史料。
二 陈之佛的赴日时间
谢海燕先生在《陈之佛的生平及花鸟画艺术:〈陈之佛花鸟画集〉前言》一文中,最早提到陈之佛的赴日时间为“一九一八年,陈之佛考取留日官费生。十月去日本。次年四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4谢海燕,《陈之佛的生平及花鸟画艺术:〈陈之佛花鸟画集〉前言》,载《美术与设计》1979年第2 期,第4 页。其后的成果在表述上有些许差异,但大体没有超出这个范畴。
《陈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中刊出一张陈之佛在1947年受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美术组专员时所填的履历表手稿 。5陈修范、李有光,《陈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19 页。履历表有多处涂改痕迹,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张草稿。在履历表“教育经历”一栏中,“1919—1925日本文省部东京美术学校”一行的年份和校名有多处涂改,涂改之前的“1920—1926”依稀可辨。可见,尽管出现了年份上的模糊,但陈之佛对于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六年时长是肯定的。
尽管履历表为陈之佛亲手所填,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时间就没有疑问。1919年,美术家、教育家刘海粟曾赴日考察美术现状,据刘海粟的专文《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记录,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的学制为预备科(一年)加四年本科。6刘海粟,《对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09—113 页。可见,陈之佛手填留学时间与东京美术学校的学制有明显冲突。考虑到陈之佛本人是留学活动的亲历者,结合吉田千鹤子与陈日红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1919年应该是陈之佛在日本的考前准备期,1920至1925年才是东京美术学校的学习期。陈之佛在日本的六年经历,是符合当时一般留日学生基本时需的。
1920年3月刊印的《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中,有一条陈之佛的信息介绍:
姓名:陈杰;字:之伟;年龄:25;籍贯;余姚;费别:官;学校:西洋画图案;科级:……;现住所:神田猿乐町二ノ一清寿馆;国内通信处:余姚浒山。7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姓名录》,《浙江留学生同乡录》(内部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编号:学校-474),1920年,第21 页。
需要注意的是,陈之佛的信息中,“学校”一栏为“西洋画图案”,参考同期《同乡录》内周天初(1919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的信息,该栏则标注“东京美术学校”。8同注7,第14 页。进一步查阅1921年版、1922年版和1923年版《同乡录》,陈之佛的学校信息均为“东京美术学校”。可见,直到1920年3月之前,陈之佛都尚在预备考学阶段。
《陈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对于陈之佛在东京美术学校留学时间的界定,正是依据“陈之佛手填履历表,及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寄来的档案”,考订为1919年至1925年。9同注5,第17 页。至于东京美术学校所寄档案,作者并没有在文中公布。但在吉田千鹤子依据东京美术学校档案所撰写的《东京美术学校的外国学生》文中,认为陈之佛是“大正九年(1920)4月7日临时编入图案选科第一部第一年级,同年9月11日编入第一年级。大正十四年(1925)3月毕业”。10[日]吉田千鹤子,《东京美术学校的外国学生》,韩玉志、李青唐译,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62 页。陈日红依据东京美术学校原始档案所撰的《对〈陈之佛年表〉中留日学习图案经历的相关考证》一文,同样认为是陈之佛的留学时间是1920年4月7日至1925年3月30日,历时五年。吉田千鹤子与陈日红在文中详细列出了原始档案的来源及条目原文,结合《同乡录》中陈之佛的信息记录,显然二人的时间断定更可靠。
既然陈之佛为1920年4月进入东京美术学校,那么他有无可能如谢海燕所说,1918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十月去日本?查阅《教育周报》(杭州)显示,1917、1918、1919 三年,由于浙江省留日官费生尚有余额可备选补,浙江省教育厅均有发布留日《考试留日学生》相关公文,并举行过专门考试。这表明,陈之佛有机会通过该途径考取官费留日,但1918年1月30日《教育公报》曾发布一则教育部令《指令留日学生监督新生预备限一年应照准文》:
据呈已悉,所请新补官费生预备考入高等学校期间,概以一年为限,一节尚属可行,应即照准此令。11中华民国教育部,《公牍·指令留日学生监督新生预备限一年应照准文》,载《教育报》1918年第2 期,第40 页。
原文由留日学生监督处呈报,意在将原预备期的一年和一年半两种情形,齐整划为一年,即:春季抵达日本者以次年春季为限,秋季抵达日本者以次年秋季为限,否则即行停止官费。
倘若陈之佛1918年赴日,那么次年(1919年)他将面临被官费除名的现实。因而陈之佛应该是在1919年赴日,次年(1920年4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这又可与陈之佛1947年所填履历表上的“1919—1925”六年留日时间相互印证。
三 陈之佛留日的费用形式
由于陈之佛的突出贡献,他的留学经历构成了中国近现代设计史、图案教育史上的重要节点,至于他留学的费用形式问题本已不那么重要,但考虑到中国图案教育史的完整性及陈之佛的重要性,还是有必要作详细的考订。
最早提到陈之佛官费留日的,还是前文提到的《陈之佛的生平及花鸟画艺术:〈陈之佛花鸟画集〉前言》一文,其后,陈之佛家属的《陈之佛年表》《陈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均采用这一表述;吉田千鹤子从东京美术学校的原始档案中考察的结果同样为官费;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后,《申报》为统计留日学生受灾情况,刊载了《留日学生最近情形之调查》系列报道,其中有“姓名:陈杰(陈之佛);学校:美术;费:官;受灾情形:无恙 ”。12《留日学生最近情形之调查》,载《申报》,1923年10月10日第十四版,第四张。可见,陈之佛官费留日无疑。
吉田千鹤子的考察结果,仅能表明陈之佛在东京美术学校期间享受官费。根据谢海燕、陈修范、李有光的观点,陈之佛是带着官费赴日的,也就是说,陈之佛在预备期起就享受官费待遇。考察《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极少发现留日学生在预备期就享受官费待遇。
陈之佛的友人章克标,也曾于1918年赴日留学,《浙江公报》1918年11月11日发布的指令中,有令浙江省教育厅核准章克标自费留学的材料。13指令原文为:“浙江省长公署指令第10661 号,令教育厅:呈一件呈送海宁吴敩、章克标等,自费留学日本填送留学书表请核准给文由”。参见:《浙江教育公报》1918年11月11日第2381 号,第5 页。章克标在《九十自述》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留日学生“猎取官费”的一般做法,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自由往来,出入国境无需签证、护照,只需买到船票。1918年9月,章克标与友人同赴东京,先入预备学校,只需准备一年的学资。次年春季章克标考入东京高师,从此开始享受官费待遇。14章克标,《九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2—38 页。章克标的经历可与《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相印证,《同乡录》中刊录有大量尚在预备期的会员信息,这部分留学生均为自费。如1920年浙江诸暨籍留日学生何时慧、何乃贤二人在预备期均为自费,15同注7,第20 页。考入东京高师后,费用也变为“公”。16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录》,《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23年,第13—14 页。这种方式是当时官费生的常规途径。
1918年4月21日《教育周报》发布了《留日官费学生一览》,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报告给浙江省教育厅的名单,共有一百零六名留日学生获得浙江省1918年官费资格。17浙江省教育厅,《留日官费学生一览》,载《教育周报》1918年第199 期,第16 页。这部分留学生需要自备预备期费用,被日本高等学校录取后,可通过留日学生监督处获得官费资格。1918年5月7日,《浙江公报》第2197 期发布了《浙江省教育厅布告第三号:为应考留学日本官费生报名及考试日期由》,布告内容是为选拔留日官费生,“据留日学生监督处册报,浙江留日官费生尚有余额可备选补”。18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布告第三号:为应考留学日本官费生报名及考试日期由》,载《浙江公报》1988第2197期,第8—10页。通过该考试选拔的官费生被为“选补生”意为补充该年留日学生之余额,是带着官费待遇进入预备期的。
与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呈报的《留日官费学生一览》中的官费生不同,据1920 版《同乡录》中的记载,陈之佛预备期已经是官费,显然是选补生。根据前文提到的教育部于1918年1月30日发布的《指令留日学生监督新生预备限一年应照准文》,这类新补官费生需在一年内考入日本高等学校,才能继续享受官费,否则将面临取消待遇。
四 陈之佛留日期间的住所
《陈之佛年表》的辑录表示:“(陈之佛)在日期间一直住在神田区猿乐町二·一清寿馆一号房间。”直到2020年《陈之佛全集》的出版,仍保持这一说法。
陈之佛留日期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莫过于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地震加之引发火灾和海啸,导致房屋损毁和人员伤亡,屠杀朝鲜人事件的扩大化更使局势动荡,受此影响,大量留日学生随后归国。
前文提到,在《留日学生最近情形之调查》中,陈之佛的受灾情况为“无恙”。查阅其他居住神田区的留日学生,多有财务、行李全烧,甚至生死不明,陈之佛何以如此幸运?查阅《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1920年、1921年版中,陈之佛留日期间的住所都在神田区猿乐町二ノ一清寿馆;1922年版《同乡录》中,陈之佛的地址已经改为下谷区真岛町一番中华学舍。19浙江留日同乡会,《会员录》,《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内部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编号:学校-475),1922年,第19 页。比较两区在地震中的受灾情况,可见端倪。
《申报》1923年9月系列专题《日本震灾之调查》,报导了当时日本的震灾损毁详细状况,现摘取神田区和下谷区的部分资料以作对比。
区分: 神田区 下谷区
全面积: 一九九三 三二七一
烧毁面积: 一八七一 一五六〇
未烧面积: 〇一二三 一七一一
烧失步合: 九四 四八20《日本震灾之调查》,载《申报》1923年9月22日第六版,第二张。
从烧毁面积来看,下谷区损毁几近一半,而神田区几乎全无幸免。据《申报》1923年9月6日《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四)记录了东京具体烧毁区域:
“神田区”全烧,……“下谷区”:二长町、竹町、御徒町、西町、南北稻荷町、东町、西黑右门町、南大门町、仲町、长音町、山伏町、阪元町、中入谷町、丰住町、金杉町、龙泉寺町、日本堤、三轮及夹在此间数街,全烧。21《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四)》,载《申报》1923年9月6日第七版,第二张。
材料显示,神田区全烧,在下谷区烧毁区域中未见真岛町。可见,陈之佛从神田区搬到下谷区真岛町,才是能够幸免于震灾的关键。陈之佛的一次住所搬迁,对于设计史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但对该话题的纠偏,可能是他能够顺利回国的前提。
五 陈之佛的回国时间
陈之佛的回国时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陈之佛全集》卷十六《年表》中,尽管陈之佛的毕业时间从1923年改为1925年,但对陈之佛1923年4月之后在国内活动年表辑录,基本没有改动,可将该观点归纳为“陈之佛1923年4月回国”;谢海燕先生在《陈之佛的生平及花鸟画艺术:〈陈之佛花鸟画集〉前言》一文中,提到“一九二四年陈之佛回国”;李华强在《设计、文化与现代性:陈之佛设计实践研究(1918—1937)》一文中认为,陈之佛是在1925年3月毕业之后归国;蔡仕伟在《陈之佛书刊装帧探源与发展考略》一文中,通过考察官报和航运记录,认为陈之佛是1925年7月回国。
可见,目前主要存有1923年4月、1924年、1925年3月和1925年7月四种观点。并且,极少有研究成果出示了有效的史料档案(有证据表明,陈之佛早在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之前就返回国内并从事美术活动,这里所说的回国时间与其毕业时间不可混淆)。理清陈之佛具体何时回国,不仅对于陈之佛早期美术活动的考察,乃至于对中国现代设计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关于陈之佛留日期间在中日之间的短期往返情况,我在拙作《陈之佛留日期间的回国时间问题—兼陈之佛早期美术活动再考察(1920—1925)》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考察,文中还对以上四个时间版本作了相应考证,在此不复赘述。本节主要考察陈之佛正式回国从事美术活动的时间,借此对拙作进一步修正。
限于材料,拙文原先的考证结果认为,陈之佛的回国时间应该在1923年9月至1924年8月之间。从材料来看,这应该是目前最可靠的。但就结果而言,时间范围仍过于宽泛,需要进一步缩小、明确。
1920年、1921年、1922年、1923年版的四本《同乡录》中,陈之佛均作为浙江留日学生会员出现,1924年版的《同乡录》中,不再出现陈之佛的名字(陈杰)。22参见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内部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1920年(编号:学校-474)、1922年(编号:学校-476)、1924年(编号:学校477);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报》(内部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编号:学校-475),1921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23年。1924年1月距离陈之佛的毕业时间尚有一年有余,这意味着,在1924年1月《同乡录》统计会员信息时,陈之佛已经退去位于下谷区真岛町一番中华学社的租住房,并返回中国。
至于陈之佛离开日本的具体时间,仅凭现有材料难以考订。已有材料表明,大地震发生时(1923年9月1日)陈之佛在日本无疑。事实上,直到1923年10月10日《申报》发表《留日学生最近情形之调查》之前,陈之佛还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未回者,尚有二百余人,以官费生为多,皆系五个月以上未领官费者,积欠店账,已多欲归不得。”23《留日学生回国代表之谈话》,载《申报》1923年9月20日第十三版,第四张。
依据《同乡录》中的现有材料能够确定的陈之佛归国时间大体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之间,比此前的“1923年9月至1924年8月”缩进了八个月。尽管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再进一步详细,但它仍是目前最贴近的(笔者系统查阅了在此期间上海与长崎、东京之间的航运记录,关于陈之佛的回国时间,目前尚未发现价值的材料)。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陈之佛之所以能够提早一年有余回国,一方面是与地震的影响有关。“(地震)直接袭击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枢部门,从而使这些部门一度陷入完全瘫痪状态。”24[日]有泽广巳编,《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鲍显铭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 页。另一方面,还受惠于当时“日本留学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管理制度松,平时上课与否也不检查;学科考试严,毕业考试更难。25沈殿成,《中国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47 页。1925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许幸之,在一次访谈中也提道:“那时学校(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创作可以国内做了寄回学校,审批合格就可以毕业。”26沈欣生,《沈西苓在日本留学时及回国后的情况:访许幸之教授》,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德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德清文史资料第六辑:现代德清名人》,内部资料,1997年,第163 页。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创作执行制度,也反映出当时日本留教育学的特点。 陈之佛回国时间的重新考订,将会进一步对此期间其他史料的发掘形成助力。
六 余论
对于设计史、设计教育史来说,陈之佛留日期间的史料研究是一个细微的话题,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代接受现代设计教育的设计家和教育家,陈之佛的求学经历又是绕不开的话题。对这段历史的澄清,显然是必要且迫切的。
由于缺乏系统的考察,现有成果中,对于陈之佛的赴日时间、留学费用形式、留日期间的住所以及归国时间等问题的表述,还是存有诸多不实之处。本文通过对五本《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的考察,结合部分已有档案文献,对以上四点进一步廓清。陈之佛1919年以官费“选补生”身份赴日,并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之间回国,是对中国现代设计发端时期的再梳理。通过以上材料的考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文的考察虽然仅涉及陈之佛早年留日期间的几个重要事实,但对于设计史研究中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不无启示。一方面,已有成果中对于史料的运用,包括陈之佛手填履历表,是兼顾自传与口述特点的,经年日久,口述者记忆发生偏差等原因,导致口述材料的可信度降低,通常都会与史实发生偏差,需要与档案材料进行相互佐证;另一方面,设计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提出一些理论框架,而是需要加快基础材料的挖掘、鉴别和考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审慎地提出理论模式,这需要大批志同道合的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陈之佛赴日时间,现只能根据1920年版《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中的记录进行逻辑推理,有待新史料的印证;陈之佛的归国时间,想必也是有据可循的,遗憾的是,限于当下材料,目前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时间段作为增补,更期待新材料的纠正。
本文对于四本《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的参考,根据浙江省档案馆的管理规定,档案材料查阅全程禁止拍照,仅能通过手抄转录,这也是文中无法插入档案原文图片,不能让读者直观阅读史料的原因,留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