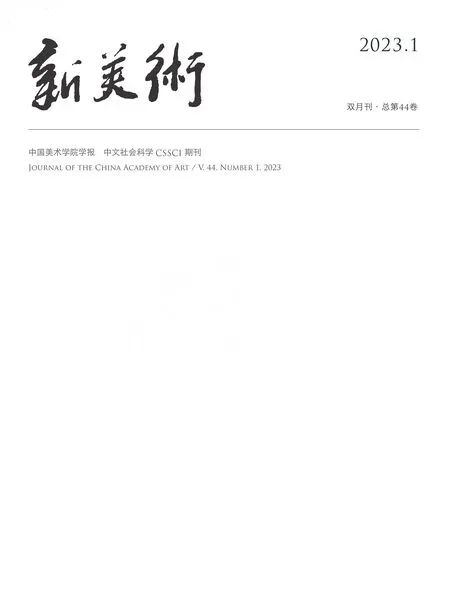通向社会重建的教育 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核心脉络分析
任晓栋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活动与教育事业关系密切。但相较于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同时代的教育家而言,他并不算一个典型的职业教育家。甚至教育事业本不是他投身社会活动的原初目的,只是在致力于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走上了教育道路。
梁漱溟的办学实践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集中于从执教北大到创建“勉仁学系”这一阶段。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探索和建立期,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在此历史语境下,“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的问题;对教育问题的讨论和实践背后,实则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
因此,教育的核心问题——人之塑造,在此时常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体塑造的问题,藉此转化为通过人的塑造来实现社会改造与国族振兴。“教育救国”的思潮亦由之兴起。“人之塑造”是所有教育问题的出发点,而在“教育救国”或以教育实现社会改造的历史情境中,这一问题通常被转化为“立人”以“立国”的问题。亦即,如何通过人的塑造来导向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开辟。
这也是梁漱溟一生致力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在梁漱溟的社会改造道路中,不仅这两个问题是互通与归流的,而且更以“人生问题”的化解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这是“梁漱溟式”社会改造道路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关键性意义与作用得以突显。进一步说,在“梁漱溟式”的社会改造道路中,一方面,作为社会改造途径的教育,通过“立人”以达致“立国”与社会发展,这是一条由“人生问题”导向“社会问题”的道路。另一方面,“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又表现为教育的“内”与“外”两个方面,前者关乎精神世界的塑造与安身立命的问题,后者则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构建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梁漱溟而言,教育的问题,既是人之塑造的问题,也是社会重建的问题。
一 基于中西比较的基本教育观
1921年底,梁漱溟应邀赴山西讲演,发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集中讨论教育问题。梁漱溟认为,东西教育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源于其文化类型和文化特点的不同。整体上说,中西方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在教育传统上,中国人偏重情意的教育,而西方人偏重知识的教育;进一步说,“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二者“各有所得,各有所失”:
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他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志的教育所要用的功夫—其功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虚情志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1梁漱溟,《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5 页。
从教育的视角来看,这种“失”与“得”主要基于知识教育和情意教育的分野而来,发展至极致,则带来西方文化因一味“向外逐求”引致冲突战乱与精神危机,中国文化则因知识教育的欠缺而致使“科学”与“民主”的缺失。“科学”与“民主”的欠缺,也是梁漱溟认为“社会问题”产生的关键。然而,尽管知识教育对于现实生活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并且“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的一端”,2同注1 ,第3 页。但梁漱溟藉由中西教育根本特质的比较,仍然认为偏重“内在”或者说“向里用力”的情意教育更为根本,认为这是着眼于生活本身和人之塑造本身的。
在这里,他实际上将问题导向了教育类型(知识教育与情意教育)背后的教育特质,而这直接关联于文化特质。可以说,在梁漱溟的语境中,教育所作用的“情志”,从根本上可溯源至决定文化路向的“意欲”,甚至亦可视为教育维度中的“意欲”问题。故而,他将“情志”视为生活本身,而将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的“知”视为生活的工具。可以说,在这种中西教育特质的比较中,实际上潜藏着“内”与“外”的两分视角或两重结构。这不仅与其中西文化路向的“向里”与“向外”之分一脉相承,而且还蕴含着对教育“体”“用”之分的趋向。
这一点,对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历程有着长远影响,且贯穿始终。一方面,随着他对文化哲学与中西文化特质思考的发展,逐渐将“向里用力”的情志教育之内涵落脚于“理性”3梁漱溟对“理性”的定义与强调理智的“理性”并不相同,是将理智、情感与道德统合在内,强调其作为人之本质的特征,即以其所定义的“理性”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上,以“理性”为教育之“体”,视之为教育的核心要旨,其贯彻始终的“精神陶炼”课程或“朝会”即为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他视“知”的教育为“用”,但对此亦有“内”“外”区分。人之“固有智慧”的启牖,与情志教育的功夫相近,归于“向里用力”的“理性”部分;而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归于“外在”的“生活工具”部分,故而尤其强调知识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需求相契合,甚至在乡建时期常直接以当地需求为知识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梁漱溟在教育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亦集中于知识教育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教育观层面将“生活本身”和“生活工具”之别,发展为情志教育和知识教育的“体”“用”两分观念相关联。也正是从“生活工具”之“用”的角度出发,他在中西教育的比较中,常强调以西方知识教育之所长补中国教育之所短:
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4同注1 ,第4 页。
中国此刻的自然科学,是来自西方的,原来没有什么科学,总都好凭个人当下的手腕与心思,太不注重知识……所以中国人不相信科学,也就没有科学,只是一种艺术的精神……中国教育的太不重知,无可讳言。所以现在我们应当对于以前的短处有一种觉悟,以后对于知识应当注重。好在现在学校多仿西法,这一方面还没有什么忽略。5同注1 ,第260 页。
在此,梁漱溟对知识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梁漱溟而言,知识教育的重要之处在于补情意教育之缺失。在“内”“外”或“体”“用”二分的结构中,作为“外”的一面的知识教育,仍需回转于内,需有一个由外而内、由物入心的过程。与之相应,“内”的一面的情志教育,作用于个体生命和生活本身,激发其“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亦会收效于外。也就是说,在这“内”“外”二分的观念中,更重要的是还蕴含着一层“内”“外”贯通的意义。如其所言,“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他的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6同注1 ,第277 页。具体而言:
创造可大别为两种:一是成己,一是成物。成己就是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成物就是对于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例如一种东西发明或功业等。这是粗略的分法。细研究起来,如一个艺术家,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算是成己呢,算是成物呢?从他自己天才的开展锻炼一面说,算是成己;但同时他又给社会和文化上以好的贡献了,应属成物。再如德性,亦独非其个体生命一种成功;而同时对于社会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贡献也很大。还有那有大功于世的人,自然算是成物;但同时亦成就了他生命的伟大,而是成己。7同注1 ,第276—277 页。
在这里,梁漱溟用“成己”“成物”之意来阐释教育中“内”“外”贯通的意义。而中西教育各自问题的产生,便在于“内”“外”之不通:过偏情志教育、只在“向里用力”而致排斥知识、科学缺失;惟重知识教育、一味“向外逐求”而致情志教育、心灵涵养的缺失。因此,“成己”以“成物”,便是在“体-用”“内-外”关系的教育结构中,超越其二分区隔、二元对立困扰的关键。进一步说,在教育中“内”“外”贯通的实现,对梁漱溟的整体思想架构以及“两大问题”解决之道的建构,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在“内”“外”贯通的意义上,因心灵事业与社会事业相通,“人生问题”才得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创造自己”也是导向“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的。
可以说,在中西教育根本特质的比较中,梁漱溟的教育观由之呈现出一种对照式的“内-外”“体-用”二分结构。以作用于“内”、着意于生活本身的情意教育为根本,以作用于“外”、着力于生活工具的知识教育为“用”。并且,以“成己成物”的关系导向“内”“外”贯通,从而超越“体-用”“内-外”二分结构中潜在的二元对立问题。而这种在教育道路中“内”“外”贯通的实现,亦回应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使“人生问题”得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
二 作为社会改造途径的教育
对于梁漱溟及其同时代的教育家而言,教育问题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他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常建立在对“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的思考上。由此,在从事教育的历程中,梁漱溟及同时代的教育家,都面临着两大问题:其一,西方文化道路以及因之而生的现代教育体系,对应于中国社会问题之解决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其二,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因之而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加以安置和转化。
承前所述,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与中西教育的比较中,将这两个问题转化为“知识教育”和“情意教育”二者关系的处理问题。亦即,西方近现代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的差异与融合问题。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实则是中西文化特质的不同,以及由之而来的文化发展路向的不同。
梁漱溟将文化视为生活的整体,并始终坚持“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而教育和文化的共同基础在于“人生态度”。即梁漱溟所认为的,决定文化发展路向的“意欲”。因此,对于梁漱溟而言,教育的问题实则包含着相互贯通的两个层面:其一,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其二,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是由“意欲”即“人生态度”联结贯通在一起的。
故而,在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中,其核心在于:人生态度的塑造。就个人而言,“人生态度”关涉人之塑造的问题,导向“人何以为人”的经典命题;就社会而言,决定文化路向的“人生态度”,通向文化重塑与社会改造的问题,亦即中国的救亡复兴和现代转型的时代命题。与此同时,“人生态度”的塑造问题,亦牵引出“内倾”与“外倾”两重面向:于“内倾”一面,面对的是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于“外倾”一面,面对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及其“外在化”、客观化的问题。换言之,梁漱溟以“人生态度”(即“意欲”)的塑造,贯通其一生致力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因此,作用于“人生态度”塑造的教育,不仅成为“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归流的关键,更是“人生问题”得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基础的关键。
从“人生态度”塑造这一条核心线索展开,梁漱溟的整体教育思想,进一步呈现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逐次推进的方面。
(一)“孔颜之乐”与“人生问题”
梁漱溟认为,“人生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这既有中西文化碰撞所导致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的崩塌,也有西方文化一味“向外逐求”而引致其自身的“意义危机”。两厢夹击之下,无论是秉持“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倡导“全盘西化”,都在反思中产生自我怀疑和价值危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对此,梁漱溟试图以中国人文传统中同样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孔颜之乐”来应对。
“孔颜之乐”亦称“孔颜乐处”,代表了儒家一种理想化的人生道路。“孔颜之乐”来自《论语》,意指孔子、颜回以求道为乐,而不以生活清贫为苦。梁漱溟提出“孔颜之乐”的命题,是针对人生的“苦”“乐”问题而言,既有其自身的省悟,也有教育的价值导向:希望以“孔颜乐处”应对时人追名逐利又因欲求不满而产生的“苦”,或是因现实困境、社会局势而产生的“人生苦闷”问题;并以“孔颜的人生”为理想,导向一种超越功利、“人生向上”的人生态度。如其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说,“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
在面对“人生问题”的教育中,“孔颜之乐”的问题,常被转化为道德教育的问题,用以强调中国人文教育传统中注重精神价值、追求道德完善的教育理想。这固然是梁漱溟倡导“孔颜乐处”的重要缘由。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省悟“孔颜之乐”的问题,是从研读《明儒学案》开始的,或者说是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如其所言,“宋明学者虽都想求孔子的人生,亦各有所得,然惟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心斋先生以乐为教,而作事出处甚有圣人的样子;皆可注意处也”。
那么,从“泰州学派”来看“孔颜之乐”,有何种独到之处?唐君毅曾提出,“泰州之学之精神,在直面对吾人一身之生活生命之事中讲学……然言以心安身,则重在心之向在此身上事,而非重在心之向于其自己。”这里指出了泰州学派较之其他阳明学派,对人之安身立命问题的新发展,即对“吾人一身之生活生命之事”或“身上事”的重视。这也是梁漱溟所倡导的人生态度。
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即为化解“人生问题”,但有“内求”与“外求”两种面向。从“内求”的一面而言,即为调适自身态度以适应环境,也是梁漱溟所总结的中国文化的传统路向。但这一传统路向,在与西方文化相遭遇时,带来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文化的失败。因此,梁漱溟以“泰州学派”的“孔颜之乐”来应对安身立命问题时,实则是在“内求”的道德涵养之外,又引入了“外求”的一面。8梁漱溟认为,泰州学派既“救朱子之失”,又弥补了其他阳明学派疏忽“照看外边一面”的缺陷,即“补其照看外边一路”。而“内求”与“外求”两个面向的统合,导向了一种新的“孔颜之乐”:道德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与“向外逐求”的“事功”的统一。换言之,即为“孔颜乐处”与“生活生命之事”的融合,亦即以“孔颜之乐”的态度来面对“事功”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种经由泰州学派生发而来的“孔颜之乐”,是一种“人生向上”的积极态度。这既是承继了儒家精神中“刚”性一面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调和中西文化各自优势后的人生道路。这也正是应对彼时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人生问题”的重要途径。
由此,从对安身立命问题的省悟出发,梁漱溟将“照看外边一面”补入了通常“内求”的“人生问题”中,以道德理想与“身上事”的融合,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贯通起来。
(二)“向里用力”的文化路向与“社会问题”
在梁漱溟的“两大问题”中,“人生问题”与社会剧变、文明冲突时代里个人的安身立命息息相关;而“社会问题”则关涉中国在严重社会危机下的救亡与复兴,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这两个问题,同样也有着“向里”与“向外”的不同面向。而就彼时中国最急切的“社会问题”而言,其解决须得在“向外”这一面向中求得出路。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危机源于“文化失调”。当近代中国面对“向外逐求”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以“向里用力”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遇了全面失败。在此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失败,关键在于无法孕生出“科学”与“民主”,而这正是西方文化之所长。这种文化失败是根植于文化特质和文化路向中的。故而,在此情境下,泰州学派补入“照看外边一面”的文化道路,虽可回应“人生问题”,但仍然不能通向彼时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
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文化改造,其关键在于:如何让“向里用力”的文化真正发展出其“向外”的一面。进一步说,一方面,需要将对“身上事”的重视,由原本“向里”的安身立命的目的,转而“向外”成为对知识和智慧的“逐求”;另一方面,将对“人生态度”的强调,由原本“向里”的人格塑造的目的,转而“向外”发展为公共意识和组织团体的塑造。此二者是梁漱溟基于“科学”与“民主”这两点生发而来,将其转化为知识创造与团体塑造的问题,而这正是他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根本性解决方案。9关于文化道路的“内”与“外”的问题,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从“内圣外王”的传统出发,认为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路并不成立,而试图建构起西方民主制度导向下的新“内圣外王”之路,即由“内圣”开出制度的“新外王”。
那么,当这一方案落实到教育中时,便转化为两个不同面向的教育:基于发展“科学”而来的导向知识创造的教育,以及由“民主”目标而来的导向社会主体塑造的教育。即为,“知识教育”和“民众教育”。前者主要依托于系统化的学校教育,要求教育的系统性和创造性,梁漱溟亦在中西教育比较中提出,这是西方教育之所长,须以此来补中国传统教育在知识教育上的欠缺。如其所言,“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因此“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的一端”。10同注1 ,第3 页。而后者则着力于社会主体塑造,是面向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求其普及度和对社会主体的适应性,在当时情境下表现为突破学校体制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在乡建时期,将其转化为面向中国最广大农民群体的乡村教育。
然而,这两个面向的教育,从教育目标到学校的社会角色,均不相同。甚至在“社会问题”的不同语境中,二者还会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向。与此同时,将二者置于现代教育转型的视野下,知识教育和民众教育两个教育面向背后,又隐伏着教育的精英路线(培养知识精英)与平民路线(塑造现代国民)的分野。由之而来的,则是知识阶层与社会大众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当梁漱溟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时,需面对的是:如何处理知识阶层和社会大众的关系。这些问题,正是梁漱溟在以教育应对“社会问题”时所产生的困扰。也是当“向里用力”的中国文化面对社会与国家的现代转型,而不得不开出其“向外”一面时,所需处理的问题。更是当教育从安身立命的心灵事业出发,通向社会改造、国家振兴的社会事业时,所面对的内在困难。
(三)“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归流
对于梁漱溟而言,教育是使“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得以归流的关键,由此提出应将教育置于社会之“领导地位”,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途径。“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缮改正,固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所有革命,就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1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3—434 页。
梁漱溟认为,教育“尽其功用”“即可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即为解决“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就“内求”的心灵事业而言,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就“外求”的社会事业而言,解决改造文化以改造社会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此二者所牵涉的实为文化路向的不同,要处理的是如何使“向里用力”的中国文化开出其“向外”的一面。故而,这“内求”与“外求”路向的调和或兼顾,就不得不进一步上溯至比决定文化路向的“意欲”更为根本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经典命题。
对此,梁漱溟在儒家“四端之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生命中的“创造”本能。不仅视其为超越道德与智识、情意与智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且认为,这是人能联结、贯通于宇宙大生命的根本,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他在吸纳伯格森、罗素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以生命哲学的角度阐发孔子的教育思想,并结合杜威的教学哲学,提出了建基于“生命观”的教育主张:追求激发生命内在创造力的“活”的教育。继而,以生命观统摄教育观,藉此得以贯通“向里”与“向外”的两重面向:人之个体生命的创造,以及社会生命的创造。故而可以说,从作为人之本质的创造本能出发,以生命观统摄教育观,是梁漱溟贯通“内求”与“外求”、从“人生问题”导向“社会问题”并使二者归流的关键。
在建基于生命观的教育视角下,一方面教育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创造,使人类的生命活泼舒畅、奋进翻新,继而通达于宇宙大生命“无已开展、创造不已”的活泼之势;另一方面,教育使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相联结,使人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亦创造社会。如梁漱溟所言,“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它的功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1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6 页。“我们是想启发每个人的生命力量,结合而成一个大生命力量。这个结合,顺其自然之势,自必从小范围的乡村着手。我们先把乡村结合成为一大生命力量,继续扩充,发挥光大,必会成为更大范围的生命力量”。13《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07 页。
这两个方面(即从个体生命出发,完成自我的创造与社会的创造)教育的合流,是将教育从文化塑造层面回归其本原——人之塑造的问题中。进一步说,这也是由儒家“成己成物”教育理念生发而来的塑造“大我”的教育主张: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乃至洞彻一己与天地万物共有之大生命。
这种通向“大我”的教育,于“己”或“自我”出发,一面可无限延展以通达于天地万物,一面可层层外推以扩展至国族社会。而这两重面向又分别通向两个维度: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在精神世界层面上,以教育塑造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相贯通的“大我”,这是通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自发挺立起来的“我”。在生活世界层面上,以教育塑造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相贯通的“大我”,是作为社会中人、处于“群己关系”中的“我”,也是“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的社会性“大我”。14关于“大我”的问题,梁漱溟并未对其概念有专门的提出和阐释,而是蕴含在他的文化观和教育观中。胡适则曾在他的“社会不朽论”中提出“大我”概念,但二人的指向并不相同。胡适的“大我”意为社会集体,认为“无数的‘小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放大,便成了‘大我’”,是由“小我”组成的“大我”。而梁漱溟的“大我”是由“已”之无限突破、延展而来。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路线及其思维逻辑。
梁漱溟正是藉由这“大我”的教育理想,从教育的根本——“人之塑造”的目标出发,试图从源头调和兼容“向里用力”与“向外逐求”两种文化路向,建立由“人生问题”导向“社会问题”、由心灵事业通往社会事业的内在机制。
总体而言,对于梁漱溟来说,教育是一项从“心灵”走向“社会”的事业,在彼时国族振兴、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中,更是作为社会改造与社会重建的重要途径。并且,其中交织着两组不同层面且互相影响的关系:其一,“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在教育中的联结与归流;其二,现代国家的建立与理想社会构建。这是两组有着强烈内部张力的关系。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刻关切,梁漱溟急切希望解决一个问题:何以使中国摆脱危局并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他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实为一个关乎社会整体性重建的宏大命题,不仅直接指向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结构体系两大层面;而且与作为其思想体系根基的“文明发展三路向”理论相关联,从而超越了“救亡-启蒙”之路甚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换言之,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归流的背后,有着一重超越于救国和建国的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
梁漱溟眼中的理想社会,是“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均得以圆满化解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即走上了一条以“人生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解决之基础的道路。这意味着,通向社会改造的教育,需从根源处着手,将重心落于“内在化”的人生态度的塑造上,继而将其引向“外在化”的生活世界的塑造。这是一个从“人心”到“人生”“内”与“外”贯通的过程,是一条以文化重建导向社会重建的道路,也是一条带着儒家色彩的“孔子的道路”。
在这条由“内”至“外”的道路中,隐伏着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传统。或者说,这条由“人生问题”导向“社会问题”的道路,其“内”“外”贯通的逻辑机制,与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传统路径是相仿的。然而,梁漱溟所面对和致力解决的“社会问题”,与传统儒家所面对的“事功”问题已截然不同。那么,这条着眼于“人生态度”、从心灵事业出发的教育道路,何以导向以“内在的进益”而“收效于外”的社会重建?
这是梁漱溟以“人生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基础,以及处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归流时,所面对的困难。而在这一困难的背后,潜藏着复兴文明发展道路与化解社会危机或建立现代国家,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差异及其调和的问题。与此同时,始自孔子的通向“大我”塑造的教育,源自“士君子”之教的圣贤理想,实为一条精英化的教育路线。那么,当梁漱溟将这条起自传统中国的精英教育之路,引入中国现代转型期的平民教育中时,便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在以塑造社会主体为目标的教育中,如何处理君子人格与现代国民之间的差异?又如何处理圣贤理想与救亡建国、伦理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困难始终潜藏在梁漱溟的教育实践及其所导向的社会改造之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