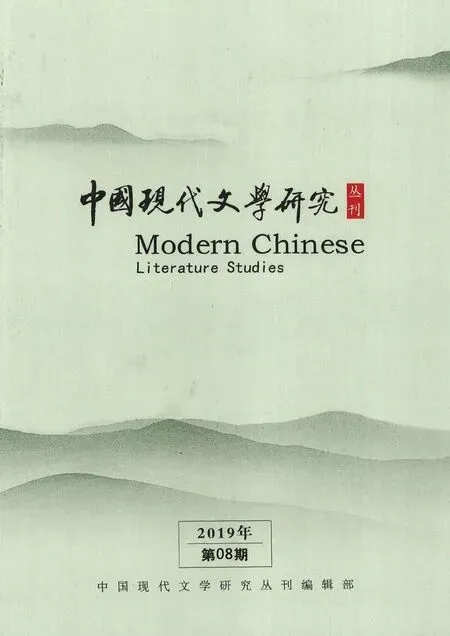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方法※
郭冰茹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以及近些年逐渐显现的文体融合的创作趋势,促使研究界将“叙事文学”视为认识文学的一种“知识类型”。“叙事文学”的提出打破了文学原有的文体边界,有助于创新文学研究的维度,并有效克服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危机,从而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进入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
严格地说,“叙事文学”并非新的概念,但当我们将其视为文学的一种“知识类型”时,它就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甚至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意义。“知识类型”是现代心理学提出的对知识的分类,文学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和表达,属于陈述性知识的范畴,然而如何陈述,如何看待陈述直接关联着文学内部对文体的认识。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文体”是指借助叙事方式和语言选择而形成的意义形态和美学效果,文体呈现的方式之一是作品的体裁。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关于文学的知识分类,便会发现“叙事文学”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学的新视角,关注“叙事文学”势必打破文学原有的文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既定的“知识类型”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束缚,从而创新文学研究的维度,有效克服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危机。
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创作的新变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概念、观念和阅读经验,这需要文学批评提出新的知识分类,并做出新的阐释。“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也已存在,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会饮记》在相当程度上革新了我们对散文的理解;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流浪地球》将物理学的知识经验化之后,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麦家的系列“特情小说”以绵密的写实和严整的逻辑推理建构出一个虚构世界;莫言的《一斗阁笔记》在汪曾祺之后再生笔记小说的风采;李洱的《应物兄》则以知识的名义重构了小说的叙事格局。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文体边界内讨论文学创作、文学的叙事问题,势必与这些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创作实际产生隔膜。
如果我们悬置既定的文体分类,将“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方法来考察文学创作,就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叙事文学”如何整合分体研究中的理论资源;二是在批评实践层面,跨文体的文本实践如何呈现“叙事文学”的多样性。
一
文学内部的“知识类型”或者说知识分类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观念、文学研究以及创作实践发展演变的结果。西学东渐后,知识的更新带来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漫长的中国文学史逐渐由“杂文学”演化成“纯文学”,从而形成了新的文学秩序。换言之,将文学文本分为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这四种基本的文体类型,是一种现代的知识类型对中国传统“杂文学”的重构。而将“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则是对原有知识分类的调整,并在“叙事”的层面上消解了既定的文体界限,形成新的文体融合的知识体系。
“新文学”确立以来,文体的四分法重构了中国文学的版图,新文学作家对小说的“现代性”预设令小说处于文学版图的中心。作为“叙事文学”之一种,对小说的看重也意味着突出了“叙事文学”的重要性。但文体四分法同时也将“叙事文学”这一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分割了。文体的边界成了文学研究的门户,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只专注于某一种文体,而忽视对文学“叙事”的整体研究。事实上,文学的“叙事”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文体中,而为了更有效地“叙事”,文体的跨界现象在创作中并不少见,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新闻小说、散文诗等概念的提出,即是对此类现象的概括和描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文体跨界的现象,是因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虽各有各的体制,但彼此之间的边界却是流动而开放的,即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只要具备叙事的功能,就都存在如何叙事的问题。
就散文而言,其最初只是一个与韵文和骈文相对的,关于语言表达形式的概念,即便是在完成了“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观念转变之后,关于“现代散文”仍然没有清晰的界定。周作人提出“美文”的概念是从外国文学说起的,“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他认为“有很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去表达,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并且进一步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①。在周作人看来,现代散文受外国的影响比较小,反而与明清小品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有学者在论及明清小品时认为,“它们通常是非虚构的,不过有些作品却具有高度想象力。小品通常从头到尾都是散文,但掺杂韵文的情况也不少见。所有小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形式的非正式性”②。明清小品呈现出的文体的“非正式性”以及“美文”“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的条件,显示出散文这一文体边界的不确定性,边界的不确定性反映的正是该文体形式的不确定。比如,在通常的散文研究中,日记、书信、游记等并没有被囊括其中;报告文学曾是散文中的一种,但由于其介于新闻报道与小说之间的文体特点,逐渐从散文中分离,成为独立的一类;谈及杂文,则不得不先论证杂文的文学性,等等。换言之,当散文被等同于美文小品时,散文中的叙事、说理和抒情等元素也相应地被狭窄化了。
散文文体边界的不断变化也是多年来散文研究无法形成系统理论的重要原因。散文研究的困境一方面与周作人所说的“艺术性”的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与散文中叙事、说理、抒情三者如何恰当融合有关。1990年代兴起的“文化大散文”以篇幅长、题材大、内涵厚重革新了现代散文的叙事方式,这种以历史记忆、民族精神、知识分子命运和人的困境等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新的散文样式,打破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边界。“文化大散文”除了改变美文小品的“短叙事”,确立起“长叙事”的叙述形式外,也让历史事件和人文景观作为一种“知识”进入文本,从而确立起论说的品质,当这些知识与作者在文化语境中的经验相融合,当作者从个人经验出发而对历史发出感慨,便使“文化大散文”有了“感性”与“知性”兼备的特点,并进一步丰富了散文的文体特性。
要讨论“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能做诗”的“长叙事”,则必须提及近些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文学”,“非虚构写作”具有无可比拟的文体开放性,“当它与文学‘嫁接’时,产生的是诸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常见文类;当它向新闻靠近时,则会呈现出类似深度报道、特稿和特写的艺术风貌;而当它与社会人类学相关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田野调查、口述报告和民族志研究意义上的作品。由此,旅行笔记、个人日记、历史散文、社会调查、深度报道,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都可构成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内容”③。
显然,面对当下众多被冠以“非虚构写作”的文本,面对那些不断溢出既定文体边界的叙事文本,使用沿用已久的文体分类法,借助既定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分类原则,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二
相较于散文,小说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当散文因其纪实性被视为一种“非虚构”的文体时(这里我们暂且忽略关于散文也可以虚构的理论主张),小说则因其想象力被看作一种“虚构”的文体。如果为小说追根溯源,回到小说生成的文学传统中去清理小说的叙事特点,则有助于我们考察叙事文学中“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也有助于认识散文和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联系。
文学中的“叙事传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论题。在通常意义上,叙事传统分为史传传统、小说传统和民间文艺传统,这种“知识类型”意义上的划分实际上已经搁置了文体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史传是中国小说的母体,那么中国小说的发展就经历一个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转变,而在此过程中,散文体式一直是小说的基本文体形式。今天我们固然能够在“虚构”的小说中将逐渐演变的叙事传统加以区分,但事实上,不同的叙事传统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详细地论述了小说与史传之间的关系,他说:“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它的发展有分明的轨迹:神话——史诗——传奇——小说。中国小说在它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中国确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孕育了小说。”④并进一步分析了史传中所包含的小说的文体因素,即: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认为“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不论是在处理巨大题材的时空上,还是在叙事结构和方式上,还是在语言运用的技巧上,都为小说艺术准备了条件”⑤。换言之,两者在文体上并不存在一条绝对的边界,而他们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区别是,史传是实录,而小说是虚构。即如金圣叹评说《史记》为“以文运事”,而《水浒传》则是“因文生事”。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虚实问题一直是界定小说文体的主要标准。即便在唐传奇流行了几百年后,明代胡应麟仍把小说归为史部或者子部,认为近实者为小说,近虚者非小说;清代纪昀仍坚持小说必须忠实事实的真实。这种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对“小说”的界定,反映出其与史传之间的关联,也说明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小说自身叙事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不断背离史家“实录”原则的唐传奇的出现,已经标志着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真正脱离了史传母体,获得了文体的自觉。所以,石昌渝总结说:“传统观念瞧不起小说,就在它视小说为无稽之言;而小说家却偏偏要与史传认宗叙谱,在叙述的时候总要标榜故事和人物是生活中实有,作品中毫无夸饰的成分。当小说宣布自己是虚构的,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时,小说才是彻底摆脱了附庸史传的自卑心理,正所谓‘史统散而小说兴’。”⑥换言之,当“实录”的束缚解除之后,“虚构”的小说才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关乎对“实录”的理解。史传传统中的“实录”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叙事方式的“实录”,一是作为写作态度的“实录”。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完成了“实录”向“虚构”的转变,从而实现自身的文体自觉和文体独立;但史传的“实录”精神仍然作用于小说创作,尤其是新文学确立以后,史传的写实精神与西方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相吻合,这在“人生写实派”的短篇小说和反映社会全景,追求宏阔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新文学发展至今,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当代小说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时也都贯通了实录与虚构的精神。1980年代曾经出现一种被称为“纪实小说”的文体,它所呈现出来的纪实与虚构的融合特征对当下的文学书写和文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如果我们将纪实与虚构的融合视为对小说文体的研究路径,那么所谓散文化的小说,或者小说的散文化表达的就是散文和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融合。长期以来,研究界在讨论散文化小说或者小说的散文化特征时,往往侧重“抒情传统”在小说中的呈现,尤为关注那些重在造境而淡化情节的中短篇小说。当我们强调这些文本的意境、诗意和抒情特征,或者认为作家是在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时,实际是在方法层面而非本体层面讨论散文与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融合,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认为散文并不像小说那样讲故事,散文化的小说只是小说对散文叙事方式的借用。然而,散文一开始就是讲故事的,周作人在讲散文发展的顺序时说:“散文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⑦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是散文讲故事的经典文本。当我们在“叙事文学”的框架中讨论这些现象时,我们可以说虚构的小说可以像纪实的散文那样叙事。而在散文式的叙事中,抒情、诗意、意境等不仅影响叙事,还是叙事的构成元素。正是这种叙事上的融合,才使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既被视为小说又被当作散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本是散文却被视为小说,而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被看作是散文的小说化呈现。
讨论“实录”与“虚构”的贯通融合既是在承认文体分界的前提下,强调文体之间的联系,也是想强调不同叙事传统之间的联系,在“叙事文学”的总体框架中,既讨论不同文体之间的边界与融合,也讨论现代小说对古典文学叙事传统的继承和扬弃。将“叙事文学”视为一种“知识类型”,一种研究方法,正是因为它是在文体分类基础上的再整合,它可以是小说的,也可以是散文的;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或者是彼此融合的。而创作中不断出现的跨文体写作也为“叙事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文本实践的样本。
三
跨文体写作正是在“叙事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实现的,就创作实践而言,“叙事文学”所呈现出的文体融合也是为了缓解叙事艺术的危机。
韩少功是极具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马桥词典》出版后,韩少功谈到某种模式或者成规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束缚,他说:“我以前写小说常常不太满意,一进入到情节,就受模式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到一种感知成规的控制,一种传统小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那种模式中推进,这就受了遮蔽,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而要摆脱这种控制,韩少功选择融合,或者他所说的“打通”,“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⑧。如果知识体系的更新总会伴随着某种观念、模式、成规的更新,那么任何一种关于叙事的定义、分类都可能形成某种遮蔽,而新的叙事方式的探索则是为了打破原有方式的限制,从而形成叙事艺术创新的循环。这成为“叙事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得以产生的学理基础。
韩少功意识到的这种叙事艺术的危机,涉及对小说本体的认识,“以前认为,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叙事都是按时间顺序推进,更传统一点,是一种因果链式的线型结构。但我对这种叙事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小说发展已几百年了,这种平面叙事的推进,人们可以在固定的模式里寻找新的人物典型,设计新的情节,开掘很多新的生活面……,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感受方式的重复感”⑨。而要改变这种平面叙事,就要改变既往的叙事方式,用韩少功的话说,是建立与从前的叙事方式“不同的维度”。换言之,是改变以往通过核心事件展示人物命运的单向度描写,找到“每个人物,每个细节与整个大世界的同构关系”。
《马桥词典》对小说文体的改变除了尝试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与“整个大世界”建立一种“同构关系”之外,还将各种知识融入其中,知识在文本中不仅是认识人物的视角,也是叙事的重要内容。在《马桥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的介入对小说文体产生的影响,而知识融入与小说创作的关系也是我们讨论“叙事文学”时需要留意的问题之一。李洱的新作《应物兄》可以说将小说创作中的知识介入发挥到了极致,据不完全统计,小说中引经据典的中外典籍五百多部,涉及儒学、史学、生物学、美学、古典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作家通过对知识的叙述,呈现出看待当下社会的总体性视角,而读者通过对知识的接受,获得了与以往阅读小说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知识的介入扩充了小说的容量,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重新看待小说的文体特征。
知识的介入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叙事文学中知识与生活经验的关系。韩少功的《暗示》是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暗示》的文体属性在出版时已有过争论,它的确和我们熟悉的小说不一样,而不一样的部分是韩少功在写作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文体置换”,知识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进入了小说文本,而关于知识的叙述和讨论在篇幅上远远超过写故事和人物的部分。韩少功在《暗示》的前言中已经像批评家那样解读了自己的创作,他在写完《马桥词典》之后,就想通过写作来讨论一个话题,即:在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能否存在,又会怎样存在。“《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而眼下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我无意于理论,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⑩如果“具象”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那么“读解框架”便是关于“具象”的知识呈现,两者的结合显现出的文本结构便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陈述一些隐秘信息的常例,包括场景、表情、面容、服装、仪式等等事物怎样对我们说话。接下去,我愿意与读者共同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记忆、感觉、情感、性格以及命运;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教育、政治、经济、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传统。最后,作为一个必不可少也最难完成的部分,我将回过头来探讨一下语言与具象怎样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⑪这段文字与其说是小说的前言,不如说更像学术论文中交代研究框架的绪论,在这篇前言中,作者的问题、方法、目标和价值判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论述系统,而且落实在文本实践中。
这看上去是将小说写成了“理论”,但《暗示》还是将“理论”写成了小说,并且最终完成了“文体置换”。韩少功说《暗示》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具象”不仅与抽象的知识相关联,并且在言与象的互动关系中尝试确立起处理知识与生活经验关系的维度。在通常意义上,知识的传播和推演需要征引文献,《暗示》中被视为“理论”的部分按照学术规范也需要文献索引,但韩少功认为文献的自我繁殖无异于知识的逆行退化,而知识应该是对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总结。“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⑫换言之,当知识成为叙事的内容,携带着作者经验加工的信息,知识本身才具有生命力;而当知识进入叙事时,只有将其与生活经验相关联,文体内部的论证和叙事才能融为一体,论述和叙述才能“合而为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或许“文体融合”比“文体置换”更为恰当。
四
近年来为我们讨论“叙事文学”提供新鲜经验的另一位作家是批评家李敬泽。如果说韩少功的文本实践是在小说文体中融入其他文体元素,促成了小说文体的革新,李敬泽的文本实践则融合了文学的叙事、哲学的思辨来讲述那些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生活本身的故事。这些文本丰富了散文的表现力,也使李敬泽成为一位具有先锋性的散文家。新时期以来,散文如何创新一直是个重要问题,李敬泽的探索因此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散文在“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绚烂多彩的表现,呈现了现代散文在意义和形式上的多种可能性。朱自清谈论“五四”散文的那段著名论述在散文研究中被广为征引:“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⑬朱自清用了若干不同的概念论述了现代散文的表现手法、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李敬泽散文的一个背景。
李敬泽近几年的文本实践呈现出丰富的文体探索性。《青鸟故事集》被认为可以是散文、评论,也可以是考据、思辨,还可以是幻想性的小说;《会饮记》则是散文、随笔、小说,都像又都不像,被称为是一部介于虚构和非虚构、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跨界的文体。而出版界对这些著作的推介语也从侧面反映出作家的这种文体探索性。比如《青鸟故事集》的推荐语是: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作家中的考古者;《咏而归》的推荐语是:读经典领古人之风,从知识中见精神,从传统中得到智慧;《会饮记》的推荐语是:酒神与诸子的慷慨与低回,十二种文学生活场景和内心戏剧,当代智力生活和精神社交的秘密地图;《会议室与山丘》的推荐语是:谈笑风生,深思明辨;谈文学,也是谈生活;把评论写成美文,在批评中呈现性情。在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文本清理出若干关键词,比如美文、思辨、知识、生活、文学、考古、博物、性情、智慧、评论、家国天下、春水春风……我们无法按照某种规则排列这些关键词,因为当这些关键词出现时,曾经关于散文的规则就已经被打破了。
《青鸟故事集》是2000年出版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的修订版。相对于我们现在谈论的“叙事文学”,这是一本早熟的书,同时也是一本被忽视的书。书中的诸篇问世时,它的气息就和当时的散文迥异。彼时,“文化大散文”正处于僵硬的状态,曾经给散文文体带来活力的历史、知识和“长叙事”也已经被格式化了。而这本书则呈现出时间和空间向度上辽阔的延展性,正如李敬泽在跋中所说:“这本书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展开。”⑭李敬泽的博学和丰沛的想象力给辽阔的时空安插了无数细节,让历史的长卷有了肌理,而他自己也超越时空的界限,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事相遇。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是现代知识的产物,也是李敬泽不受拘束的个性使然。李敬泽在这里找到了和他的文学批评一样驾轻就熟的表达方式。
正是由于重新确立的时空的维度,李敬泽才能在纵横开阖的大结构中或叙事,或想象,或议论,或抒情。比如《〈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由日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谈起,带出中国的那个潘仁美、杨家将之外的宋朝,又由周作人对清少纳言的解读,引出李商隐的《杂纂》之《不相称》条:“穷波斯,病医生,瘦人相扑,肥大新妇。”李商隐的文字极为简单,但李敬泽从《太平广记》中搜出《独异志》,将一个“不相称”的穷波斯人临死之前以珍珠相酬的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又续上李勉与波斯人的故事。文章的波澜并不止于此,李敬泽由波斯人说到胡人,由胡人的珍珠说到唐朝宫廷。这样看似不相干却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故事,既显示了李敬泽文史知识的丰富,也突出了他对事物的独特理解:“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知识的介入在李敬泽笔下不是学术随笔的形式,而是叙事方式。在文章的结尾,李敬泽如此叙述:“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京都,贫病交侵,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⑮
《青鸟故事中》收录的《飞鸟的谱系》也是我们在分析“叙事文学”时值得讨论的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李敬泽首先还原了1840年8月17日北京圆明园中道光皇帝批阅表章的一个场景,而引出夷人、英国和汉语的翻译等,并由此谈及1836年10月广州《中国丛报》上刊登的一则短讯,说的是福建巡抚的差官前些天押解来了一名印度水手。随后,作者说:“如果是写小说,我就会选择这个印度水手的主观视角,我会用他那双乌黑、洁净的眼睛注视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很多,到处都是人,他们长得都一样……”⑯这段话看似讲故事,但谈的却是一个叙事学的理论问题,即“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也就是说,李敬泽提醒读者注意小说叙事和散文叙事对视角的甄别和选择,并在随后的叙述中演示了散文视角和小说视角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叙事形态。这种将两种不同的叙事视角并置于同一文本中的讲述方法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阅读体验,同时文体的融合也满足了作家讲述的欲望。
《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著作给读者留下的另一个鲜明的印象是李敬泽对细节的处理。如果没有细节,就无法讨论叙事,而对细节的选择则反映了作家发现世界和组织叙事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些细节的充分展示,才让李敬泽的散文叙事步入出神入化之境。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李敬泽以他在三峡的邮轮上阅读布罗代尔的细节开始,借助布罗代尔对欧洲15世纪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谈论,进入五百年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丰富的细节中,呈现人类的“历史”。
李敬泽借助那些可以将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细节,实现了穿行其中的可能。“在时间的上游,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但对我来说,它们仍然在,它们暗自构成了现在。”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他如此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或者创作手法:“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撰写这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驳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欲望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⑰“幻想”让杂树生花,让历史和现实的细节灵动,也让知识在文本中由抽象而具象。不仅《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同样可作如是解释。由“幻想”连缀起的各种细节成为李敬泽对历史、现实、生活、梦想的再叙述,成为他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批评家的李敬泽以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依然能从他的文本中看到批评家的影子,虽然他的批评风格与学院派的批评有很大的差别。他的艺术感悟、判断方式和修辞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中国的文章传统。在各种细节、感受、幻想、叙述突破了散文的文体边界时,散文作为一种“叙事文学”也获得了新意。
我们的文学传统早已为“叙事文学”提供了融合多种文体的叙事经验,韩少功、李敬泽等作家的跨文体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中国的文章传统,将“叙事文学”视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或者研究方法,是在尊重文体之间“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重视文本的内部构成和文体间的相互融合。当然,这种观察视角并非是要消解我们业已形成的关于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而是在回应当下文学创作的同时,尝试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进入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
注释:
① ⑦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刘运峰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19~120页。
② 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大中国文学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③ 徐刚:《虚构性的质疑与写作的民主化》,《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④ ⑤ ⑥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65、83页。
⑧ ⑨ 韩少功:《叙事艺术的危机》,《小说选刊》1996年第7期。
⑩ ⑪ ⑫ 韩少功:《暗示·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⑬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⑭ ⑰ 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跋》,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360~361页。
⑮ 李敬泽:《〈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青鸟故事集》,第2、10页。
⑯ 李敬泽:《飞鸟的谱系》,《青鸟故事集》,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