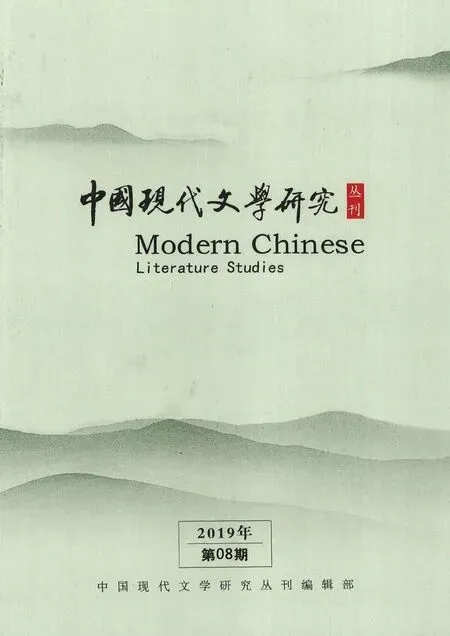废名的晚年心态与《废名小说选》
刘新林
内容提要:《废名小说选》是废名生前唯一一部小说选集,它呈现了废名晚年作为文艺“志愿兵”和文学家两种形象的交织。作为文艺“志愿兵”,废名试图通过选择篇目和修改语言来修正过去的形象,但文学家的自觉又使修改不彻底。由于重视乡土题材和语言经验,最终使选本呈现出淳朴、自然、健康的美和富有青春朝气的文学风貌。这影响了此后的作品选本和作家研究。
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废名对政治的态度日渐积极。1948年11月7日,废名出席了北京大学文艺团体“方向社”召开的主题为“今日文学的方向”的座谈会,一同出席会议的有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袁可嘉、汪曾祺等北大师生。在会上,废名的发言引来大笑。他说文学家应该指导自己同时指导别人而不应受别人指导,没有文学家会来开接受指导的会。废名自认为已经不是文学家,所以才来开会。是不是文学家,接不接受指导,在当时看来并不是句玩笑话。沈从文对此非常严肃,竟要和废名争论。沈从文提出文学虽然受政治的限制,能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修正政治呢?即是说文学在宣传政治之外,能否有自己的出路。废名认为,这对于“大文学家”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大文学家”是天才、豪杰和圣贤的合一,圣贤也从来没有这个问题。他又举了屈原和杜甫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有忠君之余仍能成为一代文豪的。在他看来,“大文学家”完全可以接受政治的影响。①争论虽不了了之,但却预示着“今日文学的方向”。
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这年春天,废名读到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并写下长文《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以下简称《欢喜的话》)。虽然这篇文章有很强的论辩色彩和劝谏意图,但服膺共产党和欢迎新社会的到来是主调。废名在文中自认为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学习毛著并用数万字的长文表达的是“一个小学生的喜悦”——“我一向的一点儿疑惑一天都解决了”②。手稿扉页上还写着“献给中国共产党”。
抗美援朝初期,北京大学号召学生参军入伍。废名的学生白榕在散文里记过这么一件事。当时学生响应号召志愿参军入伍,被批准的同学胸前佩戴光荣花,绕场一周向师生告别。这时,废名站立在“民主墙”喜报前,“亲手将一幅上面工整题写题名《向小草鞠躬》短诗的大红喜报,贴在墙上。……不仅如此,他还一直伫立在喜报前面,每当一位佩红花的同学走过,他果真都深深一鞠躬……”③。这应不是夸张。冯健男也曾在散文中说废名赞成他参加南下工作团。④废名对共产党用训练党员的办法办教育,深以为然。废名在一个大会上甚至扬言要到埃及去做一名志愿兵抵抗英法侵略。⑤废名身体力行。1951年,他参加了江西吉安专区的土改。从解放前思想上主动向党靠拢,到解放后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废名很有一个受教育的“志愿兵”心态。
废名的“志愿兵”心态也体现在他所从事的文艺领域。废名调往东北后,最初从事的是杜甫研究。谈到杜甫研究的缘起,“我是从一个问题引来的,……他的《前出塞九首》明明是歌颂一个兵士,明明是写一个兵士的传记,过去我一般地读过去了,现在令我对之深思,我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毛主席的《讲话》对我的教育,我能得到一个判断,杜甫是写兵的。因为‘写兵’已经是美学上的一个术语,我从感情上接受了,所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就起了作用”⑥。谈到1958年以后的新民歌研究,“我再说一遍,自从采风运动以后,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此我自己并不梦想做作家,我一点遗憾没有,我相信我能作科学研究。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我有无限的欢欣”⑦。而之后的美学研究,部分原因是听了周扬的报告,因而想做一个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的“志愿兵”⑧。如果说解放前写的《欢喜的话》只是“志愿兵”心态下的习作,那么杜甫研究、新民歌研究和美学研究则应视为深思熟虑后努力经营的学术研究。解放后,显然废名更看重文学家以外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的文艺“志愿兵”身份。
废名是不是真不在乎文学家的身份呢?也不尽然。到江西参加土改,除了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也有为写小说做准备的考虑——南下途中曾对沈从文言及此事。⑨据一同南下的乐黛云回忆⑩,废名起初兴奋不已,一路上同她讲故乡农民的种种,由衷地为农民获得土地而激动。抗战时期,废名蛰居故乡八九年,同农民打过许多交道,后来他认为农民有“最大的力量”,“他们向来是做民族复兴的工作的”⑪,和那一段生活经历分不开。抗战结束后,废名写了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详细地表达了对农民的意见。此番参加土改,废名有备而来。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土改深入,废名的热情逐渐冷却。他对眼前发生的一些现象感到不解。乐黛云说他很少说话,很少出屋子,也不再讲农民的趣事。乐黛云回来,他就讲因果轮回,讲人死后灵魂长在,讲不要轻易否定那些自己并不明白、也无法确证其乌有的事,讲他见过鬼魂。后来,他也没有写出任何小说。到了1957年,废名又热情高涨起来。废名在《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要订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写一部长篇小说,第二个五年写又一部长篇小说”⑫。这两个计划也只是计划。
做文学家固然很难,做文艺“志愿兵”也并非容易。尽管废名一再要求进步,却难以摘除“落后分子”的帽子。先是北京大学的课程被取消,到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便从北京大学调到了东北人民大学。到东北后,不久患上眼疾,一只眼睛完全瞎掉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废名仍旧坚持学习、工作,改造自己。“当时党的政策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断加强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看的书很多。古今中外都有,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中国古典哲学及文学方面的书一直在看,从未放弃,如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六朝文及晚唐诗,屈原、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诗等等,还有游国恩、林庚、钱钟书、苏雪林等人的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时还用英文朗诵莎士比亚的戏剧片段。毛主席及鲁迅的著作通读了一遍,重点篇章看了几遍,而且作笔记。他当时在学校讲鲁迅、杜甫、美学等课程,讲义写了一遍又一遍,一本又一本,几乎都能成书。他看书写字不能低头伏案,而是把书或稿纸放在特制的木架上,昂着头一只眼睛看书写字,非常吃力。”⑬冯思纯所说的包括五六十年代的整个情形,其努力和艰辛程度可以想见。
自以为进步却得不到认可,难免会发牢骚。那时给冯健男写信,废名颇有些不平之鸣。他说学校不重视他的工作,把他送去审阅的稿子《跟青年谈鲁迅》扔弃一旁,落上厚厚灰尘都没人理睬。废名一气之下将稿子寄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想来,废名偏居东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在文艺和教育事业上勤奋工作,却并不开心。整风大鸣大放时,废名就说了些牢骚话。“我对高教部、文化部也有意见。五二年把我从北京调到这里来,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下面不了解我这个人,高教部、文化部、作家协会总应该了解我。你们把我扔了,下面还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解放之初,我很有写作热情,如果把我组织起来,恐怕可以写出不少东西。”⑭解放前虽是落后分子,解放后要求进步的呀!他埋怨党和政府没有团结他,使他的一腔热情付诸东流。
废名是在这种不被理解、不被重视、被冷落的情形中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的编选选集的邀请的。
二
废名何时接到出版社的编选邀请,尚不可考。不过根据周作人和沈从文的情况,推测大致在1957年1月间。周作人1957年1月9日日记云:“楼适夷、张梦麟来访,谈译书事。”1月14日周致信松枝茂夫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可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⑮1957年1月9日沈从文致信沈云麓云:“这里文学出版社想把我的小说印个选本,大致可印廿万多字,希望能在三月中选出来付印。”⑯可知在1957年1月9日和14日这两天,周作人和沈从文不约而同记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来访或约稿的事实。至于废名,未见有日记或书信提及。不过,废名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坦言接到出版社来信,且落款“1957年4月24日,废名记”。可知当时小说选已编好。如编辑部1月上中旬发信邀请,推测废名收信当在1月中下旬。
如此看来,从编选、修改到序言写作,废名大约用了四个月时间。最终短篇选了十篇,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共十五章选三章,长篇小说《桥》共四十三章选十九章,全书字数约十二万字。这与《沈从文小说选集》二十九万字相比,算苛刻的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废名并未选短篇代表作《竹林的故事》,且在序言中对此未置一词,令人生疑。《竹林的故事》为何会被放弃?废名编选的标准是什么?
所选篇目有以下特点。第一,从时间上看,编选的范围仅是已出版的小说集或长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和《枣》,以及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这些都是1932年以前的作品。第二,从题材上看,短篇多为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如《张先生与张太太》《文学者》《晌午》《卜居》和《李教授》等,皆未入选。此外,废名在序言里提到了编选标准。废名说,重看了五个小说集,“乃又记得自己原来是很热心政治的人,好比这里选的《讲究的信封》《追悼会》,都可以看得出一些来。即《莫须有先生传》里也还留有我对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怒,这个愤怒至今提起犹如昨日事!”⑰毋庸置疑,内容上“进步”与否是编选的标准之一。而《浣衣母》《桃园》《菱荡》《小五放牛》《毛儿的爸爸》《四火》和《文公庙》这些短篇小说入选,乃是因为语言“惊异”。对于《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取其有反映生活的,取其有青春朝气的,取其内容不太沓杂的,取其语言方面有可供借鉴的”⑱。故而废名编选的标准大致可以理解为内容“进步”和语言“惊异”两方面。
代表作一般代表的是作者的形象,可《竹林的故事》并不“进步”。这主要源自鲁迅对《竹林的故事》的评价。“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⑲“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和长期实践的文艺“志愿兵”的形象自然相去万里。况且,鲁迅的评价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中,几乎完全照录。⑳这是废名不愿见到的。为了规避形象联想的可能,于是像《柚子》《阿妹》《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这样的能“理出我的哀愁”的小说都被放弃了。废名是不是多虑了呢?至少沈从文不仅选了城市题材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烟斗》,也选了代表作《边城》。事实上,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消逝在公众视野中,废名早就被人遗忘了。1956年《人民日报》副刊改版时,胡乔木要求编辑部向废名约稿,可编辑部的年轻人根本没听说过废名,更别说是否还有人知道他调到东北了。㉑
通过排除某些篇目以求改变固有的形象,在《桥》的编选中也有所表现。《桥》的主要问题不在字词句——故而语言上的修改较少,而在于主人公小林的形象,或者说小林所代表的废名的形象。废名十年造《桥》,朱光潜概括《桥》的写作特点:“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小说家须把自我沉没到人物性格里面去,让作者过人物的生活,而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小林、琴子、细竹三个主要人物都没有明显的个性,他们都是参禅悟道的废名先生。”㉒这种沉湎自我的写法不仅“主观”“不容易懂”,更被人批评为“厌世”“悲观”和热衷于表现“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㉓。《桥》下篇中的《沙滩》《杨柳》《黄昏》《灯笼》《箫》《诗》和《故事》等多章的弃选,均可视为对不健康的形象的抛弃。
被排除的篇目自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被选中的篇目是否就完美无缺呢?事实上,语言晦涩始终是废名编选时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语言过于晦涩,读者读不懂,重建形象又从何谈起呢?此外,废名说要贡献给读者的经验是“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㉔。可“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既形成小说文体之特异,也带来行文晦涩的问题。这岂不更矛盾?在解决“晦涩”与展示“不肯浪费语言”的经验之间,废名会如何调整呢?
废名的语言是非典型的书面语,白话中掺杂文言字词,甚至直接嵌入诗词名句,古怪拗口;又有典型的口语化特征,出现不少乡音乡谈。这些是语言“晦涩”的原因。除了调整脱字衍字别字以外,废名对语言的修改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书面词汇普通化、方言词汇普通化和方言句法普通化。长篇选章修改较少,诸短篇均有修改,《浣衣母》修改得最多、最典型。以下扼要说明。
所谓书面词汇普通化,指将一些生僻的文言、书面词汇和个人生造的词汇替换为日常普通用词。如将“咒诅”改为“诅咒”,“利害”改为“厉害”,“睄一睄”改为“瞧一瞧”,“母子”改为“母女”,“不是从前的”改为“不像从前”,“未曾经验的安逸”改为“未曾经历过的安逸”。以上所举例均出自《浣衣母》。除《浣衣母》外,较典型的还有:“睄睄”改为“瞧瞧”,“喫饭”改为“吃饭”(《讲究的信封》);“演台”改为“讲台”,“演词”改为“演讲词”(《追悼会》);等等。㉕
所谓方言词汇普通化,指将难解的黄梅方言用词替换为日常普通用词。如“现得”改为“显得”,“鹊子”改为“雀子”,“头毛”改成“头发”,“真于”改为“终于”。以上所举例均出自《浣衣母》。除《浣衣母》外,较典型的还有:“台上说话的掉了一个人”改为“台上说话的换了一个人”(《追悼会》);“一晌”改为“一向”,“不现”改为“不显”(《桃园》);“蹭”改为“蹲”(《小五放牛》《四火》);“著急”改为“着急”,“现得”改为“显得”(《莫须有先生下乡》);等等。㉖
所谓方言句法普通化,指将方言句法修改为日常通用句法。在一般的差比句中,由介词介引的比较对象常置于谓词之前。但在黄梅方言中,也有将比较对象后置的情况。废名将《浣衣母》中的“至少也不差比孩子的母亲”改为“至少也不比孩子的母亲差”,就属于对差比句方言句法的修改。这种句法在废名小说中也不是只此一例,像“发财也不差比做官”“一年长大一年”(《柚子》)和“狮子的影子大过他的身子”(《狮子的影子》)都属于这种情况。此外,也修改黄梅方言里的某些特殊格式。在《莫须有先生下乡》一节中,赶驴的对莫须有先生说:“拿在手上不不方便吗?”据相关方言研究㉗,两个“不”连用是黄梅方言的特殊格式,前一个“不”表反问,意为“岂不”。但读来非常拗口。不懂黄梅方言的人极易将其误认为衍字。为免误解,废名直接把一个“不”字删去了。㉘
除字词句的修改外,废名还删除了某些晦涩的句子。这些句子集中在《桥》。涉及四章六处,分别是:
仿佛霎时间面对了Eternity。(《清明》)
又真是一个Silence。(《今天下雨》)
她这一做时,琴子也在那里现身说法,她曾经在一本书册上看见一幅印度雕像,此刻不是记起而是自己忘形了,俨然花前合掌。
妙境庄严。(《桥》)
好像已经学道成功的人,凡事不足以随便惊喜,雷声而渊默。(《桃林》)
说不出道理的难受,简直的无容身之地,想到退避。(《桃林》)
细竹,我感得悲哀得很。
说得很镇静。
这个桃子一点也不酸。(《桃林》)
这六处属于意思已尽而作者以为意犹未尽的话。用废名自己的话说,反映的是“个人脑海的深处”,是“主观”的、“不容易懂”的。
大体来说,废名对语言的修改分为两部分:一是就语言规范化所作的修改,二是对引起晦涩的句子的删除。共同的效果是使语言干净、流畅、易懂。不过,也没有做到完全通俗易懂。相比于1958年以后推崇语言大众化,其态度可谓保守。我们仍能从《废名小说选》中找到大量文白夹杂的语句和难懂的方言句法。如写梦话,“非非凡想,装点我的昼寝门面。但你们不晓得,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并不若你们戏底下令人栽困也”㉙。“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是语言中的阳春白雪,而“栽困”俚俗至极。两者合在一处,相当陌生化。写莫须有先生同赶驴的谈话:
“赶驴的汉子,你难道不看见吗?那位瞎子先生多么从从容容呵,我爱他那个态度。”
“我不看见!我不看见我不也是瞎子吗?——王八旦草的!我看你往那里走!”㉚
这里展现了方言中“不”的另一种用法,表示“没有”。像这样的句法和诗词文句与方言俚语嵌合并置的现象,几乎构成了《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体。《莫须有先生传》的“特异”之一便是语言,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是“情生文,文生情”,语言如流水一般,来去无主脑。废名若下苦力修改,《莫须有先生传》所谓“文情互生”的小说新格式怕也不复存在。相同的情况也存在于《桥》中。这就构成了修改的限度。有一处修改更可说明问题,《桃园》中描述杀场的湿冷,有一句“你不会记问草,虽则是湿的就是白天里极目而绿的草,——你只再看一看黄草屋!”在初版本中,编辑将“记问”误改为“询问”。《桃园》再版后,另一位编辑仍旧将“记问”改为“询问”。废名因此发了通牢骚,抱怨编辑没有尊重作者的语言。编选《废名小说选》时,废名又将“记问”改了回来。从编辑角度上说,“询问”比“记问”直观、易解。但在废名看来,编辑对语言不够用心。㉛这个例子说明尽管废名在规范语言和解决晦涩等方面下了功夫,但在语言“特异”的层面仍作了保留。
废名修改语言的初衷是解决晦涩,进而为转变形象做铺垫。保持修改的限度,则暗示废名仍然珍视早年“不肯浪费语言”的经验。换言之,废名对旧作的编选和修改为我们呈现了两种形象的交织。当作为文艺“志愿兵”的废名想要通过编选旧作修正过去的形象,他发现固然可以在内容上对篇目进行取舍,但语言上的修正则无法真正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修改或尽量少的修改源于文学家废名的语言自觉。作为文学家,废名可能从未有过完全修正语言的想法。他更得意自己的语言。这样说来,文艺“志愿兵”的心态并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家废名的心灵世界。
总之,经过选择放弃代表作《竹林的故事》等篇目,《废名小说选》集中呈现了乡土题材的作品,试图扫除“厌世”“悲观”和“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的倾向,使选本呈现出淳朴、自然、健康的美和富有青春朝气的文学风貌。废名对语言所作的有限度的修改,也无疑使语言更易懂、更流畅、更干净。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废名在序言里也说编选后让自己“有些高兴”,似乎别人眼中不健康的文学家形象经《废名小说选》而被扭转过来了。
三
现实情形更为复杂。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废名小说选》依然受到批判。《废名小说选》被认为是毒草,是资产阶级的白旗。“还有一些人将《废名小说选》序文中‘我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反映现实,能够反映现实,自己的政治觉悟就一定逐步提高,提高到共产党人一样’这段话专门拿出来进行批判,认为这段话的实质是拒绝思想改造,完全是胡风的文艺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㉜。“文化大革命”初,有人贴废名的大字报,说废名反对毛泽东思想。废名返回家后,立即抱起著作送到工作组,请工作组转交省委,望省委主持公道,看看他究竟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直到废名去世,人们并不清楚或不认可废名为编选选集所做的种种努力。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废名小说选》随着废名一齐在文学史中消失了。
新时期以后,《废名小说选》才显出意义,不仅为新时期以来的作品选集的编选提供参照,也影响了废名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废名小说选〉序》成为研究者参考的经典文本。
1980年代初,废名侄子冯健男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选废名作品。冯健男编《冯文炳选集》于1985年3月出版,是一部集小说、诗歌、散文和论文四方面的合集。小说编选方面深受《废名小说选》的影响。冯在《编后记》中说:“在编选时,尊重了《废名小说选》的用心和劳绩,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充。废名1957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自选小说时,对自己过去的创作要求太严格了,只选了薄薄的一本,在早期小说中,竟然连《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这样有声誉有影响的作品也没有选入,最后写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也没有选。现在的这个选集,保留了《废名小说选》的全部作品,从《竹林的故事》和《桃园》里增选了七个短篇小说,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选进了五篇。”㉝除增选七个短篇外——五个乡土题材作品,编选《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时并未做任何改动。此外,经过对比发现,《冯文炳选集》以《废名小说选》(或手校本)为底本,所选篇章未经任何处理,完全保留了《废名小说选》的原貌。200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废名选集》在选目和底本选择上受《废名小说选》的影响。这部选集同样是一部集小说、诗歌、散文和论文四方面的合集。㉞小说方面的选目,《废名小说选》中的短篇全部入选,另增添《柚子》《阿妹》《火神庙的和尚》《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五个乡土题材的短篇,《莫须有先生传》的节选章节和《废名小说选》一致,《桥》的节选章节只删除了《狮子的影子》和《碑》,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未入选。经对比可知,《废名选集》小说篇目所使用的底本是《废名小说选》(或手校本)。这样的选本有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中杰编《田园小说》和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晓东编《废名作品新编》。总的说来,这些选本集中展示了废名在乡土题材和语言上的贡献,在一定时期内都发生了影响。特别是冯健男编《冯文炳选集》,作为新时期以来的第一部选集,呈现的废名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废名小说选》。
废名的形象建构离不开选本,也离不开学术研究。新时期以后,对废名的评价开始脱离鲁迅的批评,转而重视废名在《废名小说选》中所做的努力——乡土题材和语言方面的贡献。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开先河。《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废名的评价,既沿袭了鲁迅的说法,但也认为《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尚有某些进步倾向”㉟。这种评价实际上尊重了废名晚年对自己一分为二的看法,也是对《〈废名小说选〉序》的认可。但还未对题材和语言的价值做出正面评价。杨义的论文《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㊱则在《废名小说选》的基础上将乡土题材和语言的价值深化到文学风格的层面。杨义的主要论断是废名的作品是“承继陶潜传统的田园风味的小说”。这一论断来源于废名对自我的评价:“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杨义选择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废名小说选》中已选的《浣衣母》《桃园》《菱荡》和《桥》等乡土题材小说——包括《竹林的故事》《河上柳》等少数被弃选的短篇,强化了废名在乡土题材领域的贡献。与此相应,论文对《张先生和张太太》《李教授》等知识分子题材作品没有正面涉及。这种论述策略,也正是废名编选《废名小说选》的策略。杨义非常重视废名的语言贡献。论文对《〈废名小说选〉序》的五次引用,有三次涉及语言,并以此说明废名特色的“田园风味的小说”离不开诗一般的语言,说明“废名的独树一帜不能不说是他语言清美的胜利”。论文收入198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时,杨义将原有的论断一分为二:“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和“静美朴讷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将废名在乡土题材和语言上的贡献更加风格化地展现出来了。
1985年以后,《桥》《桃园》和《莫须有先生传》等初版或再版本先后影印出版,囊括了五部小说集的李葆琰编《废名选集》也于1988年出版。到了1990年代初,人们对废名的创作情况能够做出相对宏观的判断。吴中杰为《田园小说》写的序言,便以废名的思想发展情况勾勒出小说风格的变化。浏览其选目,便能看出田园风格的层次性。而其序言,一方面展示了废名作为田园小说家较为丰富立体的一面,另一方面更凸显了乡土题材和语言的价值。㊲新世纪以后,废名的文学家形象进一步经典化——对乡土题材和语言的重视到了几近痴狂的程度。吴晓东在这方面用力尤甚。他以传统评点的方式细读《桥》,并以微观诗学的方式研读《桥》。㊳采用传统评点的方式鉴赏小说,自有先例;运用解读诗的方式解读小说,罕见其匹。这就如同废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语言的价值得到空前重视。经过两代学人的研究,废名作为田园小说家和“文体家”的形象逐渐立体起来。
废名晚年努力呈现的另一种形象的研究则要晚得多。2010年,《废名年谱》的作者陈建军借助废名晚年的手稿完成其博士论文《论废名的学术研究》——晚年部分只完成一半。王风编《废名集》出版后,废名晚年学术研究著作得以全面呈现。这也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废名晚年思想转变的研究。㊴这些研究的时间基点在1949年,重点考察的文本是《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则兴味索然。这当然有许多种原因。一个基本的认识可能是认为废名的学术姿态大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考虑到废名主动向政治靠拢时有一个做“大文学家”的初衷——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文学家的形象不断被挤压,文艺“志愿兵”的形象不断膨胀,其学术活动的意义不一定是单向度的。《废名小说选》便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文艺“志愿兵”和文学家两种形象的交织。或许这就是一次所谓“大文学家”的实践吧。
注释:
① 载1948年11月14日《大公报·星期文艺》107期,转引自《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8~3397页。
② ⑥ ⑦ ⑧ ⑪ ⑫ ㉛ 《废名集》,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4、3364~3365、3371、3280、1942、3281、727页。
③ 白榕:《花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④ 冯健男:《我的叔父废名》,接力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⑤ ⑰ ⑰ ㉔ ㉙ ㉚ 废名:《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2、146、157页。
⑨ ⑯ ㉓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20、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137、150页。
⑩ 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万象》2003年第1期。
⑬ ㉜ 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关于废名晚年遭受批判的情况,可参见陈隄《东北人民大学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文艺报》1958年8月11日第15期;万庄《在教学改革中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日。
⑭ 沛德:《迎接大放大鸣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文艺报》1957年第11期。转引自《废名集》第六卷,第3399页。
⑮ 止庵:《〈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跋》,《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小川利康、止庵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322页。
⑲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⑳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02~103页。
㉑ 姜德明:《文苑漫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蓝翎:《静观默想》,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㉒ 孟实:《桥》,1937年7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
㉕ 《竹林的故事》对校的是1927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桃园》对校的是1930年10月开明书店三版,《枣》对校的是1931年10月开明书店版,《桥》对校的是1932年4月开明书店版,《莫须有先生传》对校的是1932年12月开明书店初版。参考王风编《废名集》。
㉖ 关于方言词汇分析得益于王定国的《黄梅方言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㉗ 汪化云、夏元明:《废名小说中的黄梅方言成分》,《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㉘ 再版本《莫须有先生传》已将此句做过修正,删去了“不”字。据王风编《废名集》可知,作者自留手校初版本亦改动了此处。《废名小说选》保留了改动后的面貌。
㉝ 冯健男编《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㉞ 岳洪治编《废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㉟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页。
㊱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收录于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时,略有增补。
㊲ 吴中杰:《田园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㊳ 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㊴ 钱理群:《1949:废名上书》,《书城》2014年10月号;冷霜:《建国前后废名思想的转变——以〈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