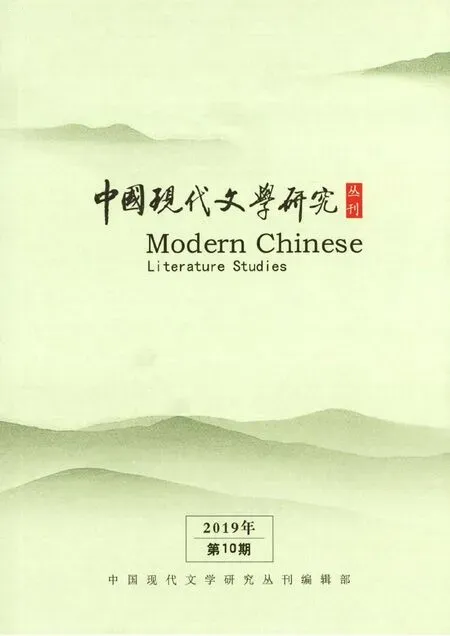重构当代散文的写作伦理
——以彭学明的《娘》为例
刘 艳
内容提要:彭学明(土家族)的经典散文文本《娘》近期再版,作家精心增补了七万字,让《娘》这个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文本,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度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这部作品,不只是以对娘深入心髓的感情,来记录娘怎样在漫长而艰辛的人生泥淖当中舐犊情深拉扯养大了“我”,以她单薄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蓝天;在散文书写方面,也是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散文流行或者说追求大散文——文化大散文的一种不自觉的、有益的反拨,还是对近年来一些作家以近乎小说虚构的方式来对待散文写作的一种有益的反拨。在非虚构叙事散文的写作路径里,有《娘》这样能够兼具丰沛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文本、散文文本。彭学明的《娘》,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当代散文的写作伦理。
2018年7月,彭学明的散文《娘》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再版,作家精心增补了七万字,让《娘》这个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文本,再度以焕然面貌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这部作品,以对娘深入心髓的感情,来记录娘怎样在漫长而艰辛的人生泥淖当中舐犊情深拉扯养大了“我”,以她单薄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蓝天,作家发自内心深处地倾诉:“娘,一块坚如磐石的寒玉,以月的清辉把我镀亮,以天的胸怀把我接纳,以海的深情把我养育。”“若有来生,我还是娘的儿子,匍匐在娘的脚下,亲吻娘的前世今生。”①《娘》这部作品,还在散文的书写方面,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是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散文流行或者说追求大散文——文化大散文的一种不自觉的但却是极为有益的反拨,也是对近年来一些作家以近乎小说虚构的方式来对待散文写作的一种有益的反拨,让我们看到在非虚构叙事散文的写作路径里,有《娘》这样能够在文学的层面表达出的入骨入髓的深情,有《娘》这样不需要爬梳史料和史料转述,依然坚持在“记述的”和“艺术性的”中国散文文体传统里写作,就能够收获具备丰赡的精神空间与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的散文文本。
有学者曾经讲过:“当代散文在‘文化大散文’这一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日益青睐历史重述与文化感慨,从而渐渐遗忘了‘记述’的传统。散文正在成为‘纸上的文学’,正在丧失和生活现场、大地细节、故土记忆之间的基本联系。”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申“一种值得重视的散文写作伦理:必须再一次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使作家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从而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记述,找回散文写作中生命的秘密通道和心灵的丰富维度”。在彭学明的《娘》中,看不到散文“正在成为‘纸上的文学’”之虞,作家有着丰厚的生活实感,与湘西大地生于斯长于斯的绵密的情牵魂系和湘西风土物事人情种种的细节,在对娘的深厚感情记述和回忆当中,也复活了作家的故土记忆……《娘》这部堪称华彩的当代散文作品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散文,一定是找‘心’、寻‘命’并使灵魂扎根的散文”②。而且在《娘》这里,清晰可见沈从文的写作在当代的血脉传承。亦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确切说是散文一脉的抒情传统在当代的赓续和扩展。
一 还原贴近事物、细节、常识和现场的写作
有学者认为,散文在中国,有一位最佳的形象代言人——庄子。理由是:“我们说庄子是天生的散文家,不仅仅因为他的文章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尤因其间文与人的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庄文的境界,在于胸襟。其为人也,绝真率性、自由无碍。这种性情,正是散文内在天然的品格,而庄子其人与散文的品格,恰似天作之合,浑然如一,他得散文的风流与真谛最多,绝不是偶然的。”而李贽的“童心说”,讲存心纯朴的可贵,不妨将它当成一篇散文基本理论的好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不作伪,不矫饰,“修辞立其诚”④。有无童心、赤子之心,是古往今来散文以此而立分高下。很难得的是,通过彭学明的《娘》,几乎可以看得到生活与现实中的那个有着真率性情的彭学明。《娘》中有一个绝真率性、自由无碍的“我”,一个能够不伪饰、真实地坦露内心真实感情抑或是想法的“我”。因着人与文或者现实与艺术的疏离关系,有的人现实中名节有亏或者为人深诡,但作品依然可以呈现清新自然乃至莹亮剔透之气,也就是说,文不一定如其人。但是彭学明的《娘》,让人真切体会到什么叫作“修辞立其诚”和拥有着最初一念之本心般“童心”的彭学明。《娘》的第一节,就是娘背着我,进了寨子,要问已经离婚的爹索要儿子的伙食费。不仅整节写得充满真情实感,而且也引出了娘身世的坎坷。不仅没有要到儿子的抚养费,娘和爹的不得已的离异,也让人读得心里纠结。“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娘经历了数次婚姻,通过后面的回溯、倒叙补叙手法,讲到了母亲曾和史伯父生下了大姐,这个大姐的婚姻并不幸福,却在后来的生活中照顾了瘫痪在床一段时间的娘,并且与娘一起支持“我”念书。娘与爹离异后,一次短暂的婚姻,生下了妹,而这个妹妹与“我”,有着长期一起生活的兄妹深情,与娘一起支持“我”上学、复读、上大学。为了保护“我”和家人,妹还迫不得已嫁给了一个又穷又恶的男人,尝尽生活的苦头。娘与继父的几年生活,也是受尽寨子里人尤其生产队长的欺辱,娘用她那单薄弱小的身躯,极力护佑着“我”。一个女子,离异再嫁这么多次,必然会受人歧视和欺辱……即便是被娘深爱和保护着的“我”,也曾不理解娘的难处,不理解娘的苦心和娘的艰辛。虽然,在“我”眼里,娘是美的:
每天,娘都会去瀑布边洗脸、洗菜。飞金溅玉的瀑布,把滴滴水珠摔成水粉,洒在娘的身上,飘进娘的肺腑。两个潭,一深一浅。深的,绿得发稠,有如墨玉。浅的,波光潋滟。阳光的芒刺刺进里面时,一波一闪的,碎成无数金银片和针尖尖。有时候,会有一架彩虹从潭里架起来,把娘弯在一弯彩虹里。娘在彩虹里站着漂洗衣服、蹲着择洗菜叶的身影,就成了远山远水最为宁静动人的风景画。画框里,娘是朴素而美丽的仙人。⑤
在“我”的眼里,娘是美的,但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笔触。更多时候,是年幼的“我”对娘的各种不理解,甚至在心里竟然认为自己和妹妹被小伙伴排斥、不能融入集体,以为自己的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全是娘造成的。那么多的曲解、误会和隐隐的“敌意”投射到娘的身上。湘西有名的“赶仗”,又称“撵肉”或打猎,是全寨全村的一场狂欢和盛宴——上山赶仗见者有份,但生产队长不仅不给应得的肉,还欺辱娘和我们兄妹,在汉英大婶娘主持公道下,又捡起肉,递给娘,娘拒绝了这份近乎施舍般的给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我却感到灰溜溜的,就像小狗夹着尾巴逃跑一样。”“从此,‘我’不再去看赶仗,更不会去看分肉。”“赶仗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疤和痛。”“因为赶仗时,中弹倒下的不是一头野猪,而是我的尊严,以及人性中最丑陋的人情与世故。”(64页)《娘》的第四节,继父的儿子要比跳房梁和摔抱鸭子,是预谋好的,目的其实是“想把我害死”。“我”不仅不知情,还中了他的、他们的圈套,是娘救下了“我”,而且:“当娘得知我没有骨气地讨好伙伴时,更是生气,又把我绑在柜子上狠狠打了一顿。娘讲:人从小就要有硬骨头,你骨头软,我把你打硬起来!”(32-33页)
绝真率性,袒露“我”的应该有和不应该有的率真性情,以及娘为人的刚正不阿,等等,是《娘》典型的艺术特征。而从另一个维度来说,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大散文”——“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⑥《娘》又形成了一种自觉反拨。当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一度成为散文的写作方向时,彭学明的《娘》,告诉我们当代散文的写作伦理,不只是要还原人的真率性情——母子情深和怎样表达这份母子情深,可能是为我们长久所忽略了的;而且,《娘》有意无意中,其实是在尝试一种贴近事物、细节、常识和现场的写作。《娘》所表达的娘对我、我对娘的感情,不是通过简单的抒情,更不是通过历史的追思和缅怀来实现的。《娘》的书写,回到了当年的“生活现场”,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场”,让读者产生仿佛见证者一样的身临其境之感、真实感。虽然作为散文,只能记述,不可以像小说叙事那样随意虚构。但彭学明写作《娘》,很多的记叙、记述的段落,写得层峦叠嶂甚至惊心动魄,时有悬念……因了这些,《娘》这个散文的文本可读性很强,很多段落引人入胜。可能是由于作家自身土家族少数民族血缘和湘西地域文化气息、人文气息的熏染,读者会觉得写作者在《娘》里,是充分打开了他所有的感官——听觉、味觉、嗅觉,等等,作家是用比我们寻常人细腻、敏锐许多的感受力来写作的。
二 散文“记述的”写作伦理重构:贴近人物叙述
汪曾祺在《小说笔谈》(1982)中有一个小节的标题就是“叙事与抒情”,他说:“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这是他的“汪氏文体”的典型特征,独树一帜,其后几乎无人再能相及。汪曾祺的小说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同传统小说纯散文的语言不同,与郁达夫的个人自叙传式散文化小说也不同,倒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并直接师承废名和沈从文尤其是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诗化小说一脉。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常常难以区分,这其实也说明在中国文学大的抒情传统里,除了是否虚构叙事这一小说和散文固有的界分,其实小说和散文在写作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彭学明的《娘》,颇有沈从文写作的遗韵,既有沈从文散文的韵致,也有沈从文小说的韵致——当然,沈从文小说本身就是散文化的,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汪曾祺先生亦然。
而在《两栖杂述》(1982)里,汪曾祺说:“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从沈从文和汪曾祺那里绵延而来的“要贴到人物来写”——贴近人物叙述,其实可以为当代散文写作所借鉴,不啻为当代散文写作伦理得以重构的重要一径。在彭学明《娘》中,作家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采用了贴近人物叙述的写作方式,方才产生了如此真实和感情充沛的散文书写。《娘》的第一节,看似平平常常的记述,其实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是用“贴近人物叙述”的方式来写的。爹是如何地怕着他的叔父婶娘,而与娘生了感情的嫌隙以致必须分开,爹本心里对娘和“我”的情难舍,爹的叔父婶娘和族人如何鼓动爹强留下“我”,而娘如何有骨气地连爹的饭都“不喰”(不吃)……再比如,湘西人讲话“米有”(没有),等等,这样的方言土语的嵌入,在《娘》中有很多。每个人的话,不仅保留了每个人物的视角和每个人物的特点,而且很多时候直接保留了方言的用字、用词和说话的习惯,这就将情景和情境的真实感,一下子烘托出来了。试看这一段:
爹就极不情愿地放了我。泪,也伤感地流了。
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背了我就跑。
爹喊:你莫跑!你实在要走,喰了饭再走!
娘边跑边答:不敢喰你的饭!我怕卡犟根!
爹就装了一碗饭端着在后面追。边追边喊:你不喰,带到路上喰!
娘边答边跑:我不喰,我不是跟你要饭喰来的!
爹就站了,不动。呆呆地望着娘背着我跑远。
娘越跑越快,一跑,就是十六年。⑦
在这一页的脚注里,作家还注明了:“卡犟根:夹脖子。”如此的情景、情境的还原能力,不能说不是靠贴近人物叙述来实现的。贴近人物叙述,就要用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手段,与小说叙事采用转换性人物视角或者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是可以互相取镜的。《娘》的第四节,写到继父的儿子和小伙伴们如何作诡害“我”,“我”如何傻乎乎地想通过自伤来取悦他们,如果没有儿童的、叙事视角,这一节不会写得那么真实感人,甚至让人心生一种好似身在当时现场般的紧张感。
三 写给母亲和生活的叙事抒情诗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本质》当中,那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是说连小说都要像散文,像诗,那就更不要说散文本身了。好的散文,更加应该是写给生活的叙事抒情诗。
重视风土人情、风物的描写,其实是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创作时就开始形成了。比如1946年的《鸡鸭名家》和《落魄》等,都是闲庭信步般讲一通风俗,而且风俗有时还和风景混在一起,“似乎是风俗就是风景,风景包括风俗,风景也成了风俗的一部分,然后才淡淡地扯出小说中必须要有的人物来”。大写风俗,当然是沈从文小说的传统,在沈从文之前则更多是存在于像周作人散文之类的非小说文类之中。汪曾祺将其引入小说,“风物和人物同成重要的叙事主体,而且以风景带人物,风物有压倒人物之势”⑧。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当中,都如此地重视风土人情、风物的描写。而以写出生活的感性和智性见长的散文,更需要风景物事人情方面的写作能力。《娘》让我们看到了它怎样在风物的描写当中,复活散文本该有的知性和感性。赶仗(打猎)、娘为挽回继父的心而一手炮制了nia nia药——少数民族的一种下蛊、下“情蛊”的方式,等等。尽管娘带着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可是谁又能否认呢?《娘》依然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多彩的湘西风土和物事人情的画卷。很多景致描写的自然嵌入,很是给人一种如沈从文所描画出的湘西的画境和情致。
我们看《边城》的开篇,仅仅几段文字,便把读者带入了水边的故事,显现的是船上水上的背影,以及水边船上才有的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显示出沈从文虽则是在写小说,却能用最简练素朴的文字,三言两语,文字闪转腾挪中,诗情画意般的情境、意境,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⑨
再看彭学明《娘》中:
油坊很大,有十来栋木房子那么大。我们住的仅仅是油坊一角。油榨、油锤、油碾,都静静地躺在那里,用一地常年都不会散去的油香欢迎我们。
娘带着我们砍了很多土墙树条子,把油坊一角围起来,一个远离上布尺的新家就有了。远离上布尺的新家,虽然显得有点孤零,但却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山与水的交接处,在油坊的裙角边,当峡高谷深的石壁上,有一线瀑布飞流直下时,青山被整齐地翻开,像披满了青枝绿叶的书。那飞流直下的瀑布,就是夹在书中的一根丝线。几架筒车,沿着瀑布和小溪,在悠闲而辛勤地劳作。既有些散漫,又有些老态,更有些安详。筒车劳作的样子,像老人摇着蒲扇的样子,一晃一摇,风就来了;一晃一摇,水就来了。⑩
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边城》,与近年的彭学明《娘》,隔着世纪的长河,如此情韵相合、精神气韵一脉传承,向我们展示着湘西诗情画意般的景致。而又有那么多能够打开作者自己的各种感官、各种知觉,进而打开读者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等种种感官知觉的段落,《娘》将还原贴近事物、细节、常识和现场的写作,几乎做到了极致。这样的片段和段落,在彭学明《娘》里,不胜枚举:
一群一群的山鸟,从林中飞出来,落在灌木丛中,偷吃各种野果。鸟最喜欢的是八月瓜。八月瓜是山里的一种野果,因为农历八月成熟,所以叫八月瓜。八月瓜是藤本植物上结的一种果实,有香蕉长,比香蕉大,有香蕉的两三个大,味道也比香蕉甜美很多倍。一串串的八月瓜吊在藤子上时,像一串串风铃在摇响。八月瓜熟时,会从上至下裂开一道缝,慢慢地,缝越来越大,完全炸开。里面的果肉雪白雪白的,像一根圆圆的冰棒,甜入心脾。鸟们就会成群结队地飞落到八月瓜上啄里面的果肉。吃饱喝足后,鸟们就会落在油坊四周的林梢和空地上,散步、嬉戏、鸣唱。满眼的绿色里,都是飞来蹿去的鸟儿。常有一只两只的松鼠,警觉地溜来,在油坊里“翻箱倒柜”,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箭一样地射出,蹿上一棵又一棵的树。野兔显然比松鼠疲沓,慢悠悠的样子,像迷路的孩子,既有点惊慌害怕,又有点茫然迟钝。面对这样的鸟雀和小动物,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我砍了竹子,破成竹块,弯成弓箭,做成猎套,套鸟。把猎套放在林地丢几粒食物,总能套上三两只的斑鸠、画眉和野鸡。千山鸟不绝的雪天,我和妹在雪地上撒一把稻草,丢一爪稻谷,引诱鸟雀。我们在撒有稻草和稻谷的地方,支一个筛灰篮,用一根绳子套住支起筛灰篮的那个支点,把绳子牵进屋里,躲着。一旦觅食的鸟雀钻进筛灰篮,我和妹把绳子一拉,支点一倒,筛灰篮扑通一声盖在地上,几只、十来只的鸟就成了“篮中之鳖”。那种快乐不是一顿美味可以言表的。也许,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⑪
彭学明土家族的血缘和湘西山山水水养育他、带给他的精神气质,似乎能让他比我们这些久被现代生活磨钝了感觉知觉的人,而另外别具一种能力。通过《娘》,彭学明在他的生命、他的写作,与故乡湘西之间,似乎建立起一个能够在生命层面互相感知和同呼吸共心跳的隐秘通道。彭学明与湘西这里的山鸟、与这里别具地域特色的植物,与这里的松鼠、野兔以及雪天雪地里的斑鸠、画眉和野鸡等,都能建立起生命的秘密通道。他的眼睛、鼻子、耳朵等的感官,都能向故乡湘西的风景物事人情打开……彭学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能够接近山林,接近飞瀑、岩鹰,接近春华秋实的野花野果的感官世界。继父的儿子和他几个亲戚的孩子,一下一下地往下猛拽满是棘刺的羊屎泡树枝,刺一排一排地扎进了“我”的脑袋。而“我”为了多抢一点果实给娘和妹,竟然是:“我不知道鲜血早已把我的头、脸和脖子都染遍了,不知道鲜血早已被深秋的冷风凝固成斑块了。我已经痛麻木了。”当“一个血人裹着一阵深秋的寒风滚进家门时”,娘只能以大哭、拔刺来面对,而娘想找出害儿子的凶谋,换来的竟然是继父族人和继父的踢打……阅读这些文字,让读者如在其境,棘刺就如扎进了自己的脑袋和皮肤,会产生一种如亲身经受一样的痛感。
读彭学明的《娘》,既有读小说故事时候那样的情节引人入胜之感,又仿佛展卷了一幅多彩的湘西风土物事人情的舒徐有致的画卷。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曾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娘》这个散文文本,是以情真意切,也即“情”和“真”见长,文字所写的景色山水和动物、植物,等等,都是活的,是能够与我们心灵相通的,自然产生“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初刊本第三则)的美学效果——将“我”物化,或者说淡化“我”的观物——以物观物,即为无我之境。散文写作,能够打开人的各种感官知觉,写得富有生命敞开之感,又不失自信从容和内蕴的情趣,似乎可以追溯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现代散文的源流那里。但是要注意的是,《娘》并不是“Essay”——随感或者短论式的散文写法,不是以漫议、漫谈的浅显笔调,去谈论似小实大的问题或道理。《娘》中,也读不出如周作人那种“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有着涩味的散文境界。《娘》在适合阅读、令读者畅通所有感官知觉来体会和享受散文所提供的情境、意境等方面,倒是与以上现代散文名家们可以遥相应和、气韵相通的,更是与沈从文有着隐隐的、隔代的呼应和传承关系。
不能不格外一提的是,《娘》里面,即使在记述娘在艰苦艰辛年代怎样将“我”和妹妹抚育成人,也依然不失积极明快的笔触,这是作家、“我”和娘等人物身上自带的精神力量。而在一些轻逸的笔触里,并不失一种“重”的力道。也就是说,《娘》在骨子里是重的。《娘》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很重,有时候重得让人心里百般纠结,种种难以释怀……而这文字背后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背后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彭学明的《娘》,切切实实以打动人心的散文写作,重构了当代散文的写作伦理。“情”与“真”,都是这项重构里重要的维度。
注释:
①⑤⑦⑩⑪彭学明:《娘》,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封底语,第78~79、8、78、79~80页。
②③⑥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④参见李洁非《散文散谈——从古到今》,《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⑧参见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⑨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8,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