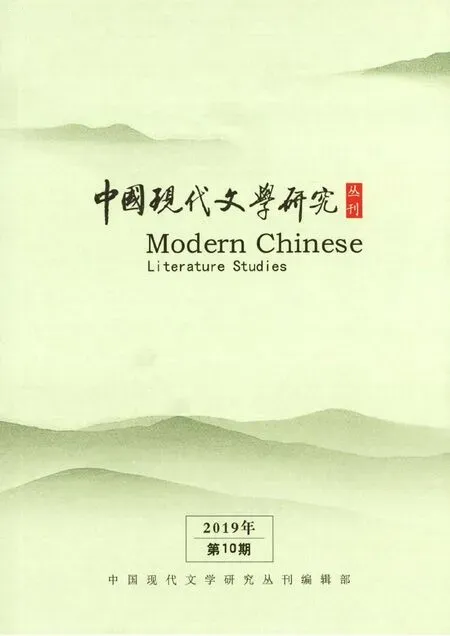《青蛙骑手》的历史考察与艺术探析※
——兼及“民族形式”与“文艺审美共同体”讨论
周燕芬 李斌
内容提要:“青蛙骑手”因其口传性质而生成了多种“类型故事”,长久、广泛地流传于我国少数民族间。1956年萧崇素将其整理出版,1960年老舍改编成儿童歌剧,随后多种外文译本以及连环画出现。口传版的图腾、宗教、文化密码,萧崇素版与老舍版的时代印记及美学增殖,都使得这一开放性的文本更为丰富而立体。《青蛙骑手》的整理、改编、译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文艺“民族化”实践的重要成果,也属于当代民族文艺审美共同体建构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老舍根据“藏族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儿童歌剧《青蛙骑手》刊载于《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它是老舍后期创作中又一篇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贫苦夫妻向神祈祷后终于生下孩子,但孩子却长着青蛙的面目,形容丑陋。父亲想丢弃他,而母亲不忍,决定将他养大。待青蛙成年后,却没人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成年的青蛙主动向官寨大头人的三个女儿求婚,并以自己的“神力”迫使大头人屈服,最终获得小女儿的青睐,两人成婚。在每年的赛马会上,一位英俊健壮的少年总以精彩的骑术使得许多年轻女子对他产生爱慕,但无人知道这位英雄少年的名姓。妻子回到家后,发现那位英俊骑手竟是自己的丈夫。这则故事篇幅不长,但情节一波三折,生动感人,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以及独特的民族风味,读来赏心悦目。
一 口传“青蛙骑手”故事探源
萧崇素在其整理的《青蛙骑手》一书中写道:“‘青蛙骑手’是藏族人民幸福的化身,也是藏族人民力量的化身。”①因而老舍也称其为“藏族民间故事”。但据考证,“青蛙骑手”所流传的地区并不只是藏族地区。有资料记载,它“主要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流传”②。另一些资料则显示,《青蛙骑手》在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间同样广泛流传。分布在云南西北部怒江和独龙江峡谷,以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洛等地的独龙族中历来就有《姑娘与青蛙》的故事:
独龙族的《姑娘与青蛙》说的是一个女子怀孕了,一天,突然从她的膝盖上跳下了一只青蛙。青蛙长大以后要娶媳妇,母亲说:“傻孩子,谁愿意给你做媳妇呢?”青蛙说:“那我自己去找吧。”青蛙在一户人家门前看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正在织布,就到她家求婚。姑娘的父亲见求婚的是只青蛙,就说:“你如果能笑,我就把姑娘嫁给你。”青蛙听了哈哈大笑,震动了房子。姑娘的父亲又请青蛙哭,青蛙哭得洪水遍地,房子也给淹了一半。后来只好把女儿嫁给青蛙。姑娘和青蛙结婚以后,每次和婆婆劳动回家,都有浓香的饭菜做好了等着他们。婆媳感到奇怪,一次她俩出门后躲在户外偷看,原来青蛙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帮她们做饭。她俩要求青蛙不再变回去,青蛙答应了。从此,三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②
四川的羌族地区也同样有青蛙与姑娘的故事流传:
羌族……《青蛙花》的故事,描述猎人杨打枪的三女不嫌青蛙貌丑,同意和青蛙成亲后,过着美满富裕的日子。大女得知产生嫉妒,趁三妹回家探亲时,巧言哄骗三妹,狠心地把三妹推下水井淹死。大女穿上三妹衣服,装成三妹模样去跟青蛙小伙过活。而被害死的三女变成小鸟,变成花椒树,变成梳子与大姐斗争,使大女原形败露而遭舍弃,最后三女死而复生又与青蛙小伙生活在一起。④
此外,云南西北德昂族中的《青蛙与绣花姑娘》⑤,藏族民间故事集中的《海螺姑娘》,都与“青蛙骑手”的故事结构和情节十分相近。《海螺姑娘》中同样是三姐妹金姑娘、银姑娘、海螺姑娘中的海螺姑娘,爱上了又老又脏的乞丐,最后才得知老乞丐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贡泽拉”,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⑥另有材料记载,广泛流传在西双版纳布朗山区的一则神话《岩洛卜我》中,“人王岩洛卜我是一只癞蛤蟆……岩洛卜我上天打仗时,把癞蛤蟆的皮脱在家里,被他妻子烧掉了,所以永远变成了人”,“在另一个故事里,蛤蟆也被当作帮助弱小共同战胜强敌的英雄”。⑦显而易见,与“青蛙骑手”相似的民间故事应广泛流传于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藏族、羌族、独龙族、德昂族、布朗族)间,而因其口传性质,以及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不同,出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但还不仅如此,以“青蛙丈夫”为原型的“异文故事”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如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族群中也有流传。⑧这则故事的广为传播和接受,似乎可以从以下几点作出解释:首先,它表达了普通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具有普遍性价值;其次,对真挚爱情和人性至善的赞美是这一民间故事的核心主题,读来十分感人;再次,情节丰富,一波三折,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可读性较强;最后,《青蛙骑手》有着较为明显的宗教文化内涵和地域民族特色,体现出先民对“蛙”的生殖崇拜⑨和原始图腾⑩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富的原始文明密码。
二 萧崇素《青蛙骑手》历史考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搜集运动中,四川籍作家萧崇素⑪将这一口传民间故事整理为汉文字,并由重庆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5月出版。与上述以口耳相传方式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故事“青蛙骑手”相比,经萧崇素整理的《青蛙骑手》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变化。首先,在独龙族和羌族流传的“版本”中,女孩的父亲是普通农人或猎人,而萧崇素整理的《青蛙骑手》中,三个女儿的父亲是住着碉楼和宫殿的“错尾”;此外,萧崇素版的《青蛙骑手》增加了青蛙祈求西方天神答应他“三个愿望”的情节。这些细微的变化,很容易为人所忽略。但若回归历史语境进行考察,其中深意则十分耐人寻味。故事中,风烛残年的老夫妇准备将青蛙放进池塘时,青蛙开口说道:
爸爸呀,妈妈呀!不要把我丢了,也不要把我放在泥塘里吧!我是人生的,让我和人一起长大吧!我长大,我要使我们这地变样子,使我们穷人变样子!⑫
幼小的青蛙自知他担荷着使“地变样子”、使“穷人变样子”的使命。“扶危济贫”或“劫富济贫”是世界许多民族都存在的一种朴素正义观,但在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诉求成为“革命”的原发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在“工农兵”文学中有难以计数的表达与强化。无法确证,萧崇素在整理时是否有“移花接木”的主观意识,但上述变化无疑与彼时的文学潮流十分吻合。而且,当妻子烧掉了丈夫的青蛙皮使他濒临死去时,骑手让妻子去西天找到神,并让神答应三件事,这样他将不会死去。青蛙说:
我不是普通人,我是“撒尔加尔神”的化身,等我长到力量够了的时候,我就要起来替百姓做事。要使人世间再看不见有钱人糟蹋穷苦人;要使人世间再看不见做官的人压迫百姓;要使我们这地方有条路到北京,北京有条路到这里,让汉人给我们庄稼,我们给汉人以骑术。⑬
在临死之时,他仍不忘自己身为“救世者”的三个重任,故事由此透射出的阶级意识和国家意志无法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述话语明显隐含了三种关系,“有钱人”和“穷苦人”的对立、“做官的”和“百姓”的对立、“我们”(藏族)和“汉人”的团结融通。如果将“有钱人”置换成地主或资产阶级,那么“穷苦人”即可用无产阶级替代;而如果“做官的”可以理解成“封建统治者”,那么“百姓”正是“人民”。青蛙骑手的这两个愿望便可用人们熟知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替换。故事的结尾,这一肩负拯救穷人使命的骑手死去了。间接杀死骑手的竟是妻子的父亲,他因阻挠女儿去西天获取“神”的应允而导致青蛙骑手错过了活下去的时机。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似乎切中了彼时常见的“阶级敌人”阻挠、破坏革命的文学主题。换言之,一个致力于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青年,在革命道路中遭遇了阶级敌人的阻挠迫害,最终不幸牺牲,这正是左翼文学中常有的故事类型。故事最后甚至以颇具“启蒙”意味的话语写道:“晓得这神的吩咐的,只有非常少、非常少的人。剩下的人一直认为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一切都是神早安排定了的。”⑭此时,死去的青蛙骑手,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而“革命”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升华,具备了神话般的崇高精神。上引段落中,“我们”和“汉人”的互通有无,则毋庸置疑地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民族团结这一国家意志的突出表达。
如此看来,萧崇素整理的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或多或少打上了20世纪左翼文学的印记,也直接反映出此时文艺实践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但需要强调的是,萧崇素“整理”中的“改编”虽若隐若现地透射出革命年代的话语逻辑,但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一民间故事的原初风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的爱情和人性书写,传奇和浪漫色彩,以及较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风物描写,都使得这部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得独特而丰富。其后老舍慧眼独具地将其改编为儿童歌剧,紧接着多种外文版《青蛙骑手》(英、法、德、俄、日、意大利、藏、朝、乌尔都、阿拉伯、孟加拉文等)出版以及连环画、动画片问世,都证明了这一民间故事强大的文学生命力。
三 老舍《青蛙骑手》艺术探析
儿童歌剧《青蛙骑手》共有六场,由1500余行“唱词”组成,尾字隔行押韵,句间多有对偶,读来朗朗上口。以下面一段对话为例:
.三姐:青蛙郎啊,你莫哇哇地哭,
也莫笑哈哈!
我愿随你去,
请你递过手中的花!
我宁愿舍去几头牛,
决不许你早出嫁!
蛙儿:她是一朵自由自在的花,
.她要出嫁就出嫁!
大姐刁钻二姐坏,
请你留着两个小夜叉!
三姐呀,我爱你容颜美,
不假脂粉秀如花,
我更爱你的性格儿好,
不耻嫁到苦人家。
头人:住口!没有我的话,
看谁胆敢自己找婆家!
你的命儿苦,
劈柴磨面用处大。
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花,
咱们携手回家去,
乐坏了我的慈善老爹妈!(鲜花)
咱们走!
三姐:走!走!我愿跟你走!
这里呀是我的监牢不是家!
你的好话打动我的心,
我就渴望不分贫富,不受欺压!⑮
可以看出,即便在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六十年代,老舍仍展现出了不一般的艺术才华与智慧。歌剧《青蛙骑手》较少沾染“大跃进”时代流行的浮夸风气,同时还保留着这位著名“京派作家”的独特风味,读来意蕴醇厚。在1956年创作了经典话剧《茶馆》之后,老舍所改编的《青蛙骑手》在1960年的中国文坛不失为一件艺术佳作。他在“一些说明”中谈道:
剧本与萧崇素同志整理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些出入:
1.原故事中,三姐妹都是头人的女儿,剧本中把三姐改为义女,以便适于嫁给青蛙骑手。
2.在原故事里,蛙皮是三姐给毁的,剧中改为被头人劫去,好多些冲突。
3.最大的改动是故事的结局。原来是青蛙骑手死去,三姐在他的坟前变成一块石头。在故事形成的年代,这样的结局是很自然的。改编时,我把悲剧变为喜剧;青蛙骑手濒死,被三姐救活。
4.此外还另有些小的改动,都是为使故事更集中、人物更鲜明些,即不一一说明。⑯
一方面,原本的民间故事以情节为主而人物形象模糊,但儿童歌剧通过对话使得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具体表现在头人、大姐、二姐等人物塑造上。歌剧“第二场”头人的大女儿、二女儿出场,她们互相打趣,各自矜夸,娇贵恣睢,因久住闺中、闲极无趣而时时盼望有人前来求婚,两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形象跃然纸上。但青蛙到来后,她们的“真相”显露出来。头人无奈答应将大姐许配给青蛙时,大姐说:“门当户对我应早出嫁,不等你催,我骑上快马飞奔婆家!我可是不能把这鲜花一大朵,不插花瓶,却在粪上插”,她将青蛙称作“绿脸小怪物”,拿起杯子掷向他。二姐说:“青蛙,青蛙,放弃贪心吧,我永远永远不会将你嫁!”大姐、二姐年轻漂亮的容貌下隐藏着一颗世故而刻毒的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姐。她是头人的义女,干粗重家务,家庭地位与奴婢相差无几,但却美丽、大方、善良、真挚、勤劳、淳朴、平等待人。由此,原民间故事中作为陪衬的大姐、二姐形象在老舍笔下变得立体而鲜活。
另一方面,老舍通过三姐与青蛙骑手的爱情故事突出了女性解放与婚姻自主的现代爱情观。在萧崇素整理版本中,头人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先后在跟随青蛙回家途中,欲设法杀死青蛙而逃脱。幸免于难的青蛙虽然觉得她们心狠手辣,但仍让她们返回头人家中。而在老舍的剧本中,青蛙与头人的小女儿结婚,完全遵从了她的主观意愿。青蛙说:“她是一朵自由自在的花,她要出嫁就出嫁!”三姐回答:“我愿跟你走!这里呀是我的监牢不是家!”可以看出,她有明确和自觉地逃出“封建大家庭”,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意识。“五四”文学中女性解放与婚姻自主的现代女性观、爱情观在老舍的《青蛙骑手》中得以复见,这与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女性通过走向“集体”和“革命”而实现自我解放的表达殊异。
此外,将“悲剧”改为“喜剧”,将烧掉青蛙皮的“三姐”改成“头人”,也明显合乎时代的规范性。而“在原故事里,蛙皮是三姐给毁的,剧中改为被头人劫去,好多些冲突”。这一改变同样值得探究,前文提到,“头人”某种程度上是“地主”“富农”“封建统治者”的代称,而“青蛙骑手”则是“革命者”或“无产者”的化身,“头人”烧掉了“骑手”的蛙皮,无疑使得作品中“阶级矛盾”的表现更为突出,“阶级仇恨”的表达也更加强化。而歌剧的“第六场”,四组“群众”的登场更强化了其时代特征:
群众一组:(低唱)作人难!作人难!下有头人上有天!
群众二组:(低唱)天降灾,涝与旱,头人依旧要粮、钱!
群众三组:(低唱)头人莫轻犯,宁可得罪天!天神无刀剑,头人有皮鞭!
群众四组:(低唱)今朝又何事?传唤到门前?家无隔夜粟,身无一文钱!⑰(后面顺延)
这一场景无疑折射出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的影子,而他们脱口而出的“天降灾,涝与旱,头人依旧要粮、钱!”与“家无隔夜粟,身无一文钱!”读来也耐人寻味。总之,萧崇素与老舍的改编都使得这一民间故事打上了革命叙事的印痕,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此较为明显地凸显出来,但口传故事的内核与样貌仍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
四 文艺“民族化”与“审美共同体”建构
历史地看,萧崇素版和老舍版《青蛙骑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195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文学整理运动即已开始,“当时发表、出版的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民间诗歌,有藏族等民族的抒情短诗,以及《嘎达梅林》(蒙古族)、《阿诗玛》(彝族)、《阿细的先基》(彝族)、《召树屯》(傣族)、《逃婚调》(僳僳族)等史诗和叙事诗。在1957年,《人民文学》选刊了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汉译情诗”⑱。此外还有《格萨尔传》《蒙古秘史》《青史演义》《藏族民间故事》《泽玛姬》《草原红花》《纳西族民歌选》《中国少数民族歌谣》《中国民间故事选》等等,品类繁多,内容丰富。而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少数民族诗歌再度被人重视。如此看来,《青蛙骑手》的整理、改编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包括《青蛙骑手》在内,彼时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改善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题材、主题单一化,丰富彼时文艺的思想和审美内涵,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新时期”至今,这项工作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少数民族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老舍所言:“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这种互相学习与影响,对我国各民族文学的成长与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⑲
若进一步考察,少数民族文艺的发掘和整理,是“五四”新文学以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追求的具体表现之一。1960年8月第三次“文代会”召开,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仍然是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茅盾在此次大会发言中的“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一部分强调:“两千多年来我们的优良传统……不是把发展民族形式和借鉴并吸收外来影响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的。”“民族化就是批判地继承旧传统和创造新传统的问题”,“民族化、群众化和个人风格不是对立的”,因为“个人风格必须站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上。但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不一定都有个人风格”⑳。因此要努力创造民族化、大众化和个人风格有机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文艺上“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茅盾此文中有关“民族形式”的论述,至今看来也不乏洞见,它一方面回应了将“民族化”与“传统”“外国”并行对立的错误观念,一方面又纠正了“全盘欧化”和“自我封闭”的认知误区,同时又指出了融会贯通和“再创造”的“民族化”方向。正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脉络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译介才得以迅速发展。《青蛙骑手》的发掘、改编与译介,正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探索方向下的艺术结晶。这则涉及原始图腾、宗教文明、民族习俗的民间故事长久地流传于少数民族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它的发掘无疑是继承传统和民间的典范;而根据这则故事改编而成的儿童歌剧、连环画、动画片等艺术形式,则属于民族艺术形式的创新发展;它的汉、英、法、德、俄、日、意大利语等多种译本的出现,则证明了优秀的“民族化”文艺作品国际传播与接受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此外,满族作家老舍在1960年8月第三次“文代会”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告中》同样强调,“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为了丰富我国的文学宝库,我们必须搜集、整理古典和民间的文学作品”,并遵循“推陈出新”的方针,“采取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向各民族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民间文学学习”㉑。他又特别提醒,在发掘、搜集、整理、翻译、改编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故事时,“不赞同对民族遗产随意加以粗暴的删改。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在整理和翻译中不恰当地修改原著”㉒。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不尽相同,蒙古族、维族、藏族、回族、彝族、白族、傣族等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或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或以民族文字的形式,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其中许多作品历久弥新,饱含艺术生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上述种种差异,各民族文艺在宗教、伦理、情感、思想、主题、题材、风格、审美形式等各方面有着明显区别,甚至互相抵牾、难以融通。针对这一事实,在发掘少数民族文艺作品时,还应重视文艺的通约性和共同美。而诸如文学艺术中对真、善、美的思考,对假、恶、丑的揭示,对爱情、亲情、友情的呼唤,对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的体认,对自然、宇宙和理想世界的描绘与想象等等,都使得优秀的艺术作品具备可通约的美学质地。总而言之,在充分尊重和考虑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同时,最大可能地寻找民族文艺间的通约性和共同美,在“和而不同”的总体思维中努力构建民族文艺审美共同体。从这一角度看,一方面《青蛙骑手》的整理与改编大体尊重了民间故事的原初风貌,它所展现的文明密码、宗教思想、尚武文化、赛马习俗以及自然风物等,充满异域情调,读来引人入胜;另一方面《青蛙骑手》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可通约性的美学质地,使得它具备了翻译为多种语言,改编成童话剧、连环画、动画片及其他衍生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因而这则看似短小的民间故事不仅穿越了历史,而且跨越了民族和地区,至今仍不失艺术魅力。
最后,由《青蛙骑手》而及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议题,几乎贯穿了“五四”新文学至今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尤其体现出当代文学如何在扬弃和发展古典、民间资源的基础上,开创出“新传统”这一总体性的文化规划和文化愿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再到21世纪的“传统热”,这条线索背后除了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推动外,也隐含了文学/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自觉走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返“古典”和寻找“古希腊”,中国“五四”以来人文思潮中的回返传统,都象征了中西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历史命题的展开。因此,考察《青蛙骑手》以及文学史上其他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改编和译介,对于反思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历史,构建理想的民族文艺审美共同体,带动中国文化的总体性发展,都提供着有价值的经验和有意义的启示。
注释:
①⑫⑬⑭萧崇素整理《青蛙骑手》,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版权页,第2、15、19页。
②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7页。
③⑤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126页。
④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页。
⑥陈石峻搜集整理《泽玛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2~78页。
⑦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编《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上册),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1983年版,第21页。
⑧林继富:《“青蛙丈夫”型故事研究》,见林继富《民间叙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⑨唐海宏、蒲向明:《藏彝走廊“青蛙娶妻”型故事的情节生成和文化意义》,见邱雷生主编《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论文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163页。
⑩蛙为仰韶文化四大图腾之一。广西壮族解放前仍保留了蛙(壮族称“蚂拐”)图腾崇拜残余。一些人认为,左江岩画上的蛙为蛙图腾神。凉山彝族古籍《勒俄特依》记述彝族曾有三种蛙类图腾:(1)癞蛤蟆;(2)红田鸡(生活于稻田或溪边的一种蛙类);(3)小青蛙。解放前新平鲁魁山彝族普姓也以癞蛤蟆为图腾。云南普米族亦曾以蛙为图腾,称蛙为“波底阿扣”,意为“蛙舅”。珞巴族和布朗族也有以蛙为图腾的氏族。见何星亮《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6~137页。
⑪萧崇素(1905—2002),四川安县人。1929年参加上海左翼戏剧活动,历任重庆《新蜀报》主笔,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常务监事,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编著作品有:《抗战文摘》(重庆抗战文摘社)、《小播音员:抗美援朝快板剧》(成都市文联出版社1950年版)、《假货郎:川剧》(川西文联说唱报社1951年版)、《青蛙骑手》(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山兔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sbal ba rta pavi sgrung》(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56年版)、《bod la yod bavi gtam dpe bsgrungs:藏族寓言故事》(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6、1957年版)、《骑虎勇士:彝族民间传说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年版)、《五色海的传说:藏族长篇民间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萧崇素民族民间文学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必胜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6年版)等。
⑮⑯⑱老舍:《青蛙骑手》,《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⑰这一点,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给《青蛙骑手》的审稿意见中也可看出,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中写道:“值班编辑崔道怡首先肯定剧作‘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然后写下阅读感受:‘作为剧作家老舍,能够运用各种样式,无论巨细大小,紧密配合政治人物。没去西藏生活,就来改编西藏民间故事,这种精神是可敬的。’编辑部主任杜麦青感到作品中存在一些不足:‘主题和情节有些不太协调,对话流畅通俗,但也有不少陈旧别扭的地方。’副主编陈白尘主张留用,但请作者进行一些修改。主编张天翼审看后,也作出同样的意见:‘从这一类的主题来说,即使不改,亦可以发。当然,能改一下更好。’”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2016年1月第五次印刷),第131页。
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⑳㉒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合刊)。
㉑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