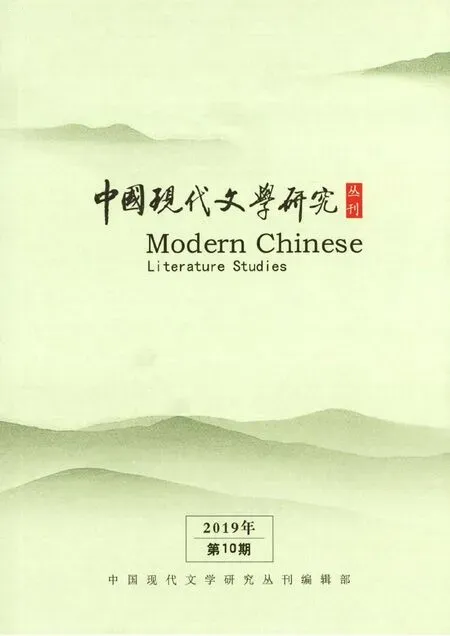社会革命思想中的“革命文学”论
——以早期共产党人为中心的考察
张 晶
内容提要:1924年左右出现的“革命文学”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笔下,他们从文学的革命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出发,对文学中的“靡靡之音”“无病呻吟”和“吟风弄月”展开了批判,将“革命文学”归诸“革命的感情”特别是“革命家”,并强调“革命文学”在革命动员之中的作用。这些讨论既是此前中国共产党人与“东方文化派”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论争的延续,也是共产党人社会革命思想的必然产物。它们预示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发生的必然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乃至中国革命的特质都有所裨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文学”的关系,已为文学史家所注意。如在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著者在论述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时,将其“渊源”“追溯到1923年前后”:“那时,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蒋光慈就提出过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1924年还出现过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春雷社。”①不过,1923年前后所出现的“革命文学”主张并不只是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先声,它的发生几乎没有受到苏俄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一波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出现于新文化运动落潮之际,而且恰恰由共产党人提出,也不是巧合,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革命思想的必然产物,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②乃至中国革命的特质都有所裨益。
一
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国青年》周刊上,该周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先后由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等人主编。1924年4月18日,《中国青年》出版第27期“泰戈尔特号”,其中刊发了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董亦湘四人的文章,就此时刚刚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及中国社会的反响展开了分析与批判。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所写的文章是《太戈尔来华后的中国青年》,他在其中宣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所需要的思想是联合被压迫民族共起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而独立的思想。决用不着太戈尔那种懦怯的逃藏在灵的世界中去享乐的文学和思想,不但我们中国用不着,即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用不着。”②这也是“革命的文学”概念首次在《中国青年》中被明确使用。应该说,文学家泰戈尔来华激发了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思考。此前,早期共产党人已经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进行了持续的批判,而与“东方文化派”关系密切甚至被该派作为旗帜的泰戈尔的到来则将这一批判引向了文学领域。
共产党人谈论“革命文学”同时也是出于读者的缘故,恽代英和萧楚女在《中国青年》上首次谈到“革命文学”都是在答读者问中。1924年5月,读者王秋心致信恽代英,就后者在上海大学演讲中“教人不要做小说诗歌”之论展开讨论,他虽然“承认小说诗歌是有产阶级的游戏”,但是同时指出这仅仅是“对于那些为个人娱乐无裨于实用的,讴歌恋爱,赞美自然及其他一切无病呻吟的文学而言”的,“革命的文学”——“那些观察社会最真确,同情于人生最深切,富于刺激性反抗性的文学”则不在此列。王秋心进而指出,“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以文学感人,比普通文字感人尤深!而鼓吹革命及改造社会等事业,文学更是利器”。恽代英在答复中认可了王秋心关于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的说法,并由此将“革命文学”逆推至“革命的感情”并进而归诸“革命家”:“我相信最要紧的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情感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④可以看出,恽代英和读者在思考“革命文学”时的角度是不尽相同的,他更倾向于把“革命文学”看成是革命的自然产物,而非如读者那样试图以“革命的文学”去助成革命的事业。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上始终对文学讨论兴趣不大。
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有读者致信《中国青年》,表达了与王秋心类似的意见。这位署名“悚祥”的读者指出,《中国青年》上“太少了文学的作品”,而“小说诗歌,在改造运动中,也是很重要的”。萧楚女在答复中称,《中国青年》刊载文学作品少,一是限于篇幅,二是因为“纯粹的供人欣赏的文艺”与刊物的“使命”——宣传“怎样去改造中国的实际‘动作’”不符。尽管萧楚女承诺以后刊物要“更加注意”“‘革命文学’的问题”,多发表些“革命的文艺”⑤,但是刊物实际上后来仍然变化不大。这其实正如萧楚女所说,是由刊物的“使命”所决定的,《中国青年》最关心的仍然是青年从事实际反抗运动的经验及其教训。
文学,至少是当时的文学在《中国青年》中经常是被排斥或批评的对象。恽代英曾经发问,“大家都会做‘风啊’‘月啊’的‘新文学’,便可以救国么”,并进而指出“最要紧的是研究社会科学”。⑥陈独秀在谈到译书问题时,也表现出了重社会科学而轻文学的倾向,“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似[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⑦。对当时文学最为集中的批评来自署名“济川”的《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文章选自作者致恽代英、林育南书信中的一部分,可能正因为是私人信件的缘故,其中的批评毫无掩饰、避讳之处,无论是当时两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创作,还是翻译文学中的“欧化语句”,抑或恽代英戏称为“变相的闺怨诗”的新诗,都让作者不满。不过,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与恽代英恰异其趣的结论,文学正因为如此的沦落,“真是现时代而且是现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这种急需的文学便是迥异于当时文学的另一种文学,即“富刺激性的文学,不是那些歌舞升平,讲自然,谈情爱,安富尊荣不知人间痛苦事的文学”。从作者列举的理想诗人——“Black的雄伟,Byron的态[悲]哀,Heine的缠绵,Wilde的俏丽”⑧来看,他对文学的理解还是相当有见地的,并没有仅仅将其当作革命宣传的工具。
无独有偶,邓中夏也感叹“现在中国的文艺界是糟到透顶了”,同时批评了“为艺术而求艺术”和“为人生而求艺术”。他吁求的是“社会化的文学家”,“极力经营社会化的作品,为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尽力”。在同一篇文章中,邓中夏还批评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出发点也是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恽代英所提倡的“社会科学”也应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而非狭义的社会科学。曾有读者来信质疑恽代英“以为只有社会科学能够救国”,“未免立论太偏”,恽代英辩解说,“我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⑨。因此,恽代英所谓的“社会科学”更像是“社会”与“科学”二词的叠加,“科学”代表方法,而“社会”则是其落脚点。更准确地说,其归宿在于实际的“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并由此质疑一切旁观式的研究。进而言之,“社会科学”是与此时反复出现在共产党人包括恽代英本人笔下的“到民间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邓中夏的“社会化的文学家”无疑也具有同样的内涵。
共产党人也是从这种特别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文学的,并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与其说他们是在“社会科学”/“文学”的对照中看待文学,毋宁说他们将“文学”置于实践的坐标中去衡量其价值。这一点从李求实《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研究文学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哪一种急要?”“现在这种文学运动,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有效力么?”⑩恽代英反对青年“从事于无目的的学问美术”⑪,邓中夏断言“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⑫,都与这种实践的尺度有关。正因为如此,《中国青年》才宣称,即使是“那些讴歌爱与光明的文学家,还是应当受我们毫不容情的反对”⑬。如果说“革命文学”不同于之前文学的特质正是其实践性和阶级性,那么早期共产党人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显然更侧重于其实践性的一面。
与恽代英、萧楚女相比,张闻天、沈泽民、蒋光慈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更亲近于文学,他们都有作家的一面甚至以文学为志业。张闻天在《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中写道:“那末我们到底应该用那一种方法去鼓励民众使他们共同起来干革命的政治运动呢?……我想单单说中国民族性的优良或是单单用历史地理的教授去鼓励民众是不中用的。……我们还要革命的文学(包括国民文学,激昂慷慨的国歌,革命英雄的传记)来打动我们的感情,鼓起我们的热血,使我们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中华民国,发生无穷的希望,使我们对于她的建设发生无穷的努力。”⑭张闻天是从思想领域的斗争角度注意到“革命的文学”的重要性的,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甚嚣尘上的“复古的运动即反革命的运动”,他认为要廓清这些思想不能仅仅靠“知的一方面”的努力,还需要感情方面的涤荡。这篇文章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饱含着激情,堪称“革命的文学”的范例。张闻天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烦闷与闭塞”的“梅雨时期”,需要进入“愤怒与激昂”的“暴风雨时期”,所谓“革命的文学”即是带有“暴风雨时期”的“愤怒与激昂”特质,鼓舞民众起来革命的文学。
张闻天以“革命的文学”去涵括“暴风雨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可能是受到了沈泽民的启发,他在文章中也引用了沈泽民提倡“革命的文学”的论断。有趣的是,沈泽民也用“暴风雨时代”去形容当时的时代,不过,和沈泽民不尽相同的是,张闻天把“暴风雨时期”看成是即将到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民众去实现的;而沈泽民则把“暴风雨时代”看成是现在时,所以文学家更多的是扮演着时代的记录者角色,他们需要“替它留一个影片”,“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为了成为这样一个“综合者”和“组织者”,文学者首先需要是一个革命家,不单是具有革命的思想,还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文学”不同于郑振铎所提倡的“‘血与泪’的文学”。沈泽民不仅较早地提及了“文学的阶级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单纯的革命信仰尚不足以成就革命文学,“只是一班政治家,却不是文学家”。沈泽民也没有落入谈论“革命文学”时经常出现的文学工具论的陷阱之中,而是指出了革命与文学二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文学家只是“最真挚的人”,他只需要表达出内心真正的声音。“他必须是具有对人类的绝大的同情的人”,然而,在人类历史中,“阶级的偏见无情地将人们的心灵践踏着,很少数的人能从这里脱离出来,以成就他们的伟大”。革命即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彻底翻造中把人类——全人类——的心灵解放出来,使他们在宇宙中发挥空前的光耀!把人类从阶级的偏见中救出来,从长时间的苦作中救出来,从无知识的黑暗中救出来,涵养他们在弥漫全人类的忘我一体的社会意识中间”⑮。
与沈泽民同属春雷文学社的蒋光慈也是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之文学界》中对当时“漫溢全国”的“‘靡靡之音’的文学潮流”进行了批判,呼唤“好的批评家”和作家来“振作中国的文学界”。⑯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激烈地批评了叶绍钧、冰心等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按照蒋光慈对“革命文学”的描述——“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并不能推导出对叶绍钧、冰心作品的批评。蒋光慈的文学观看上去似乎相当宽广,一方面认可再现的文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文学家在消极方面表现社会的生活,在积极方面可以鼓动,提高,奋兴社会的情趣”;另一方面也承认表现的文学,“文学家是代表社会的情绪的(我始终是这样的主张),并且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职任”,实际上却与前文提及的大多共产党人一样,强调文学与情感的关联。因此,他对创造社作家的评价明显要高,“颓废派”作家郁达夫“的确引起我们的同情,的确能与我们同立在反对旧社会的战线上,的确高出皮条式的文学家百倍”,而《女神》的作者郭沫若则被目为“中国唯一的诗人”。⑰蒋光慈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的评价上的反差,与上文提及的济川的态度如出一辙,济川尽管不像蒋光慈这么贬褒鲜明,但是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品时也表示,“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创造上的作品大概要比较好些”⑱。这应该不是巧合,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1928年第二波的“革命文学”主张由创造社的成员发起含有某种必然性,同时体现了革命文学与浪漫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沈泽民、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多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由于《觉悟》上的作者群比《中国青年》远为驳杂,使得“革命文学”讨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展。这些讨论有的直接是承共产党人的主张而来,如王家荷的《文艺作家底责任》,其副标题便是“听沈泽民先生在苏州一师演讲‘文学与革命’后的感想”⑲。有的是思考如何建设“革命文学”的问题,如杨幼炯的《革命文学的建设》,从其立论来看,比如主张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们现在应该拿自然主义作革命文学的建设,以人生的,丑的,真切的,平浅易解的文学,去培养民众个人解放和为社会而战的勇气”,基本未脱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进化论的框架,而以自然主义为“革命文学”建设的旨归,也依稀可见陈独秀早年提倡自然主义的影子⑳。不过,其中对“靡靡之音”和“无病呻吟”的文艺作品的批评㉑,则与“革命文学”提倡者多有共鸣。有的则是对批评“革命文学”者的反批评,如许金元的《为革命文学再说几句话》,反驳了把“革命文学”产生归于之“厌故喜新的‘人之常情’”的看法㉒。许金元是1924年5月成立于杭州之江大学的文学社团悟悟社的成员,该社团的宗旨便是提倡“革命文学”。由此看来,“革命文学”主张在青年中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是整体上看,它并未在文学界引起更为广泛的讨论,特别是未能形成有规模的论战,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地扩散。
二
发生在1924年左右的这一波“革命文学”讨论,并没有就“革命文学”概念给出清晰的界定,而且只有个别共产党人如沈泽民从民众意识与阶级性的角度对“革命文学”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场讨论中,经常被提及的有三点:一是对“靡靡之音”“无病呻吟”和“吟风弄月”文学的批判;二是将“革命文学”诉诸“革命的感情”特别是“革命家”;三是强调“革命文学”的刺激性,即其鼓动受众革命热情的特性。事实上,这三者都内含于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思想之中。
“社会革命”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至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在比较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时说:“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㉓李大钊认为,社会革命是20世纪时代精神的体现,它萌发于俄国革命之中,并终将遍布世界。因此,在随后的《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把俄国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㉔。同时,他从德国一战失败中也看到了这种时代精神和世界性的革命力量,他强调,“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㉕。
可以看出,在李大钊的提法中,社会革命本身即有与政治革命对照之义,暗含着政治革命不足以改造中国的判断。实际上,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的前提。新文化运动一定程度上不谈时政问题——“批评时政,非其旨也”㉖,与其说是回避政治,不如说是回避政治革命。它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应对共和危机,背后寓含的正是对于辛亥革命这一政治革命失败经验的反思。然而,思想革命并非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它只是被当作社会全面变革的温床。因此,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带有对社会状况的普遍关切及改造的尝试,并且呈渐趋深入之势。《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第3号起设立“社会调查”栏目,陶孟和在“导言”中号召人们先“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这个“现在最切要的一个大问题”着手进行调查㉗,而始于1919年年底的“工读互助团”则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一次直接实践。从实践的角度看,1919年间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倒更像是理论与实践之争,不过,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倡导“多研究些问题”的胡适更多地仍然是指向对“问题”的理论探讨,而同情于“主义”的李大钊则出于社会改造实践的需求。㉘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其落脚点是整理国故。陈独秀也反对空谈主义,不过他的着眼点却与胡适迥然不同。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陈独秀批评“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其着眼点却在“实际的努力”。㉙
“问题与主义”之争预示着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新文化运动的实践品质和全面变革诉求更多地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并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其集中体现便是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中,“社会革命”即是其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共产党人此时并不排斥政治革命,正如《共产党》月刊上所宣称的,“我们并不反对政治革命,只是不满意于单纯的政治革命;因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立脚在经济革命上面,革命成功之后,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制度一切设施,都必然仍旧立脚在资本主义上面;无论何人组织政府,都必然和前政府一样受资本家支配,采用资本主义”㉚。也就是说,政治革命需要作为社会整体变革的一个部门,才能发挥效用,因此,这种政治革命也就不同于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变革。施存统在思考中国社会革命的方法时认为,社会革命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缓进的方法,一种是急进的方法。前一种方法就是丢开政治,专门向社会上去活动,等到社会上的多数人信从了那种主义,然后才起来干革命,从此把政府永远废除。后一种方法,乃是一面向社会上去活动,一面又向政治上去活动,有了少数人信从了那种主义,即乘机而起,将政权拿到手中,借政治的优越权来完成革命”。他的结论是,“我们要在支那干社会革命,必须要从社会上政治上两方面并进,否则断断无效”㉛。
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思想也建立在对辛亥革命以降一系列社会改造实践反思的基础上。“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而社会革命则是“由下而上的彻底的革命”,“把革命的真义和需要,连续不断地向民众宣传,务使民众了解,做到那‘革命民众化,民众革命化’”。㉜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才把革命看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刘仁静所说的,“中国的革命是一长期的运动”,它不排斥军事运动,但要广阔得多。㉝恽代英也曾纠正青年对于革命的误解——以为“用手枪炸弹以从事暗杀”便是革命,他强调,“革命是一种有组织的积极的行动,决不是浪漫的消极的行动”,“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整顿革命党,向农工平民宣传革命党的主义,把他们吸引而组织到革命的旗帜下面”。㉞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将“宣传主义”与“组织工人”作为当时的两种工作之一。㉟1924年,当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时,他们普遍发现国民党在宣传与组织工作方面的欠缺,即革命缺少群众根基。李大钊指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柢]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㊱。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重心被确定为“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㊲。相似地,恽代英也洞察了国民党革命工作中的失误,是“以前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㊳。邓中夏则断言,“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㊴。
创刊于1923年10月的《中国青年》一开始便把动员与组织青年作为自身的使命,它在“发刊辞”中宣称,“《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㊵。这里的“活动”指的便是实际的社会改造活动和革命运动。紧随“发刊辞”之后,刊载的是陈独秀的《青年们应该怎样做!》,其中批评了青年的几种现状:或被教会教育磨灭了“性灵与爱国心”,或视教育如科举进身之阶,或“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或沉湎于个人奋斗、“生活和恋爱问题”。㊶这篇文章可以视作《中国青年》的一个总纲,教会教育、东方文化派都是刊物后来主要的批驳对象,而当时的文学则被看作让青年沉溺于个人世界的一个表现,附带着也受到了批判。
这些批判都旨在肃清思想界的混乱局面,让青年走出狭小的个人世界。刘仁静在《青年运动与革命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中国是急切需要一浩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以解除人民的一切痛苦,中国的解放与自由唯此革命运动是赖”。为了达成这一革命运动,首先需要消除当时思想界的多重消极影响——“老庄的虚无主义,孔教的折中主义,佛教的寂静主义都是勾结着西洋类似的学说在那里复活,都是在那里争夺青年们的灵魂”㊷。共产党人对既有文学的评判,也是认为它局限于个人生活层面。萧楚女在答复读者时甚至说,“至于文学一门,我向来自己不很抬举他。我以为把他作为私人生活上一种欣赏的享受,和课余去公园以遣倦一样看待则可;若当一件事业做则不可”㊸。总体来看,共产党人并不反对文学,而是要求一种有益于革命动员的文学。正如《中国青年》的“编者”在答复读者提出的增载文艺作品的要求时所说,“我们虽登载过几篇似乎反对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决不反对文艺,我们只是反对那些无聊的诗歌小说。因为现在的青年,有许多事要做,这种‘吟风弄月’的恶习,断然应加以排斥,没有提倡的道理。——我们所希望的,是要能激励国民的文艺作品”㊹。
随着早期共产党人投入到组织民众和革命宣传工作之中,他们逐渐发现文艺的重要性,并愈发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恽代英早在平民教育实践中就发现,做群众工作时,“感情的动人,比理性的力量还大得多”㊺。他进而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㊻。从情感上看,“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主因”,恰恰在于“农民不知渴望革命,甚至厌恶革命”。㊼因此,采用文学艺术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就不只是承担着大众化的任务,同时也需要化大众,唤醒大众的主体意识,走上反抗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也就是说,文艺需要同时兼有思想革命的使命,甚至以后者作为其主要目的。1925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收到读者王卓如的来信,提出在农民运动中应该注意“编印充满革命精神的浅显读物‘清醒他们的思想’”,同时“投合农民艺术上的要求,练习一种歌调,把革命纳入其中,去满足他们艺术上的要求,顺便输入革命的思想”。恽代英为此文作了按语,同意其中的建议,并表示“编读物亦好,演说亦好,唱大鼓亦好,都可以使农民声入心通,引他们发生革命的要求”㊽。
正是通过感情这一中介,文学与革命发生了关联。前文曾经提及,包括恽代英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都认可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过来看,则文学具有非比寻常的感化力量。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同样强调革命情感对于革命者的重要性。比如林育南就把“革命情感的修养”看作是革命青年的“第一步工夫”㊾;张闻天也认为,“感化人决不单是头脑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伟大的人格”,即“人格的美化和纯化”㊿。从这一前提出发,张闻天将人格视作社会改造的根本,“人格高尚了,一切什么主义都能实行”。这样,呼唤革命文学,以激发民众革命的感情,便是革命动员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正如邓中夏所言,“我们承认人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承认革命固是因生活压迫而不能不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但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
“革命的情感”以及“革命家”最终成为早期共产党人讨论“革命文学”时的落脚点,这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对于“革命人”的强调,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与1928年的“革命文学”思潮相比,1924年左右的这场“革命文学”讨论是在几乎未受到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发生的。正如沈泽民在为蒋光慈的诗歌作的按语中所说,此时国人对苏俄新的文学动态知之甚少:“革命以来的俄国,关于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事情,我们时常听见说起;关于文学美术方面的新发展,我们听见的就很少了;至于劳农俄国的新精神,新的心灵生活是怎样的,我们虽然都渴想晓得一点,可是更无从接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反思“革命文学”产生的条件:与其说它是外来文学理论影响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生于中国的现实与革命之中,是共产党人社会革命思想的必然产物。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49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7页。
③亦湘:《太戈尔来华后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1924年第27期。
④参见读者王秋心致恽代英的信及后者的回复,《中国青年》1924年第31期。
⑤参见读者悚祥来信及萧楚女的回复,《中国青年》1924年第36期。
⑥代英:《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1923年第2期。
⑦实庵(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中国青年》1923年第2期。
⑧济川:《今日中国的文学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按:“济川”应当是覃济川(1900 —1927),早期中国共产党员。
⑨参见“通讯”栏读者正厂与恽代英关于“学术救国”的讨论,《中国青年》1924年第28期。
⑩秋士(李求实):《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
⑪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学宣言》,《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⑫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1923年第7期。
⑬参见《中国青年》向青年提出的研究题目,《中国青年》1925年第68期。
⑭张闻天:《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1924年第4卷第12期。
⑮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
⑯蒋光慈:《现代中国的文学界》,《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147页。
⑰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154页。
⑱济川:《今日中国的文学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
⑲王家荷:《文艺作家底责任——听沈泽民先生在苏州一师讲〈文学与革命〉后的感想》,《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27日。
⑳陈独秀对自然主义的盛赞,可参见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3号。
㉑杨幼炯:《革命文学的建设——与悟悟社诸君一个商榷》,《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15日。
㉒许金元:《为革命文学再说几句话——第一百二十九期〈文学〉上一篇杂谈的读后感》,《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12日。
㉓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㉔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59页。
㉕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63页。
㉖参见“通信”栏“记者”回复读者王庸工的信,《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㉗陶履恭:《社会调查》,《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3号。
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主要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的《问题与主义》,均可参见《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345页。
㉙独秀:《随感录(九八) 主义与努力》,《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号。
㉚参见《共产党》月刊刊首“短言”,《共产党》1921年第3号。
㉛CT(施存统):《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1921年第5号。
㉜剑霞:《第一步工作应该是什么?》,《中国青年》1924年第42期。
㉝敬云(刘仁静):《中国革命之前途》,《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
㉞参见代英《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中国青年》1924年第22期;读者黄光东的质疑及恽代英的答复,参见代英《手枪炸弹与革命》,《中国青年》1924年第25期。
㉟李达:《党的一大前后》,《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㊱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09页。
㊲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页。
㊳但一(恽代英):《评国民党政纲》(上),《中国青年》1924年第18期。
㊴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中国青年》1923年第8期。
㊵《发刊辞》,《中国青年》1923年第1期。
㊶实庵(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1923年第1期。
㊷敬云(刘仁静):《青年运动与革命运动》,《中国青年》1923年第6期。
㊸参见萧楚女就“脱离家庭及拒婚问题”给读者燕日章的答复,《中国青年》1924年第33期。
㊹《编者的话》,《中国青年》1923年第10期。
㊺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文集》(上),第191页。
㊻恽代英:《论社会主义》,《恽代英文集》(上),第250页。
㊼代英:《农村运动》,《中国青年》1924年第37期。
㊽参见恽代英为《一个小学教师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所作的按语,《中国青年》1925年第70期。
㊾林根(林育南):《青年的革命修养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45期。
㊿张闻天:《谈无抵抗主义的两封信》,《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