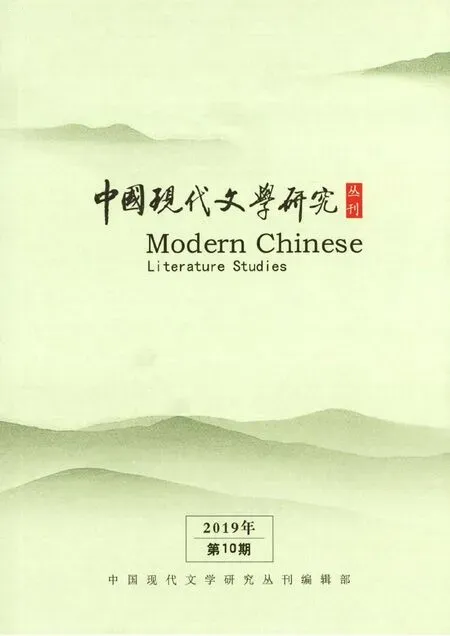丰盈的人生与极致的叙事
——论《人生海海》
季 进
内容提要:麦家新作《人生海海》充满了人性与命运、偶然与必然、孤独与英难、记忆与铭记的纠葛,不可揣摩的人性与命运仍是他关注的重心,环环相扣的悬疑设置依然得心应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贯穿始终,但小说叙事又是多声部的“我”的接力与故事的接力,以文本外的个人记忆创造了文本内的个人记忆,从而使个人记忆在文本中经他人之口繁衍更新与自我和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世界。麦家深挖“记忆”的两大面向——精准与含糊,这种对立是麦家的叙事策略,也是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的互动呈现,将“记忆”推向更深入的“铭记”的层面。麦家将“回忆”上升为“铭记”,把人生的丰盈繁复推向了极致,《人生海海》终将成为麦家创作历程中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一
麦家新作的出版,距其上一部长篇《刀尖》(2011)的出版已经有八年之久。从《解密》到《暗算》,从《风声》到《风语》,再到《刀尖》,麦家在谍战或密码世界中埋头深耕,以一种冷静精细又饱含力量的叙述姿态,不断书写缜密的情热、疲惫的亢奋、隐秘的伟大,把这类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些书名,也与麦家其人形成了一种彼此建构、黏着成长的状态。
对于猝不及防、蜂拥而来的声名,麦家当然是感恩与感叹的,毕竟他的写作曾经伴随了太多的坎坷与周折。但是,巨大的声名也衍生出一个尴尬的局面,不少阅读者与研究者都轻忽地将其作品归到了类型小说的定式想象之中,却忽略了作者更为用心的小说文本的深层意蕴——人性的解码。小说中的谍战迷宫或密码世界,确实充分显示了麦家对故事本身与叙事行为所具有的强大的掌控力,但也让我们感知到了他对刻画与成全一种孤独、崇高、悲怆的精神力的执着。麦家笔下的容金珍(《解密》)、安在天(《暗算》)、顾晓梦(《风声》)等诸多英雄,多半有着超人的智慧或过人的胆识,阴差阳错走进了神秘的行业,从事着抽离出正常人际关系的“地下工作”。不论是解密、听风还是捕风,似乎都并置了有法可循的数理逻辑与失控玄奥的自然规律,在杂糅了国族、战争、权力、生命、感情的宏大背景下,观照主人公内在的面向如何实现与外互动,如何呈现出一种奇诡的状态。他们身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房间或封闭的环境中,却又亲身经历并制造着外面的一切,甚至激发出某种超人的精神,与外面的世界实现遥远的共鸣,悄然扭转外面的现实。麦家作品中的能量与野心,不断地将我们引向对人性、对生命、对信仰、对精神的思考。
细读麦家的小说,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文本背后一个淡到透光但纹理鲜明的麦家的影子。正如所有严肃作家一样,麦家的写作姿态是一贯的,在如何写作以及通过写作传达什么的问题上,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求。这一追求的边界或许模糊多变,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明确清晰的,那就是人性的解码与追问。用麦家自己的话说,他小说中的密码只是噱头,真正的密码是人的内心。几十年的生活、写作与思想经验让麦家可以更高效、更坦诚、更深刻地表达他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的思考。麦家这八年不是在冬眠,而是在蛰伏,在延续一种内在的力量,酝酿一种全新的呈现。果然,麦家刚刚推出的长篇新作《人生海海》以细密的叙事,讲述了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传奇故事,人性与命运、偶然与必然、孤独与英难、记忆与铭记,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本世界。这部新作与此前的作品既有联系,更有突破。破而后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脱离了谍战或密码题材的麦家新作,就像一本掩去了作家姓名的小说,然而,捧读之下,可以发现这部新作依然闪耀着光芒,麦家小说的内核一以贯之。这或许也再次证明了麦家此前的作品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类型小说,某种意义上,麦家以自己的新作,也把自己从过去简单化的“分类”中“救赎”了出来。
二
《人生海海》由三个部分构成,彼此照应,环环相扣,细密精致,自成一体。三个部分以叙述者“我”从孩童到中年的浮沉成长加以串联,叙述了“上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周围人各不相同的命运。小说塑造了上校、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等独具个性的人物,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从抗战到“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下的历史纵深。每个人都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神秘的命运之手提着线,牢牢牵引所有人的命运。即使强悍、传奇如上校,也难逃历史的播弄、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操纵,最终复归孩童,一切清零。
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都是作者用心用力之处。麦家的设计与处理似乎都可以假借本雅明“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的观点来加以解读。本雅明把“讲故事”视为自史诗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经验与记忆的塑造方式。故事与讲故事者,讲故事者与听故事者,都通过记忆中的相似经验整合到了一个“讲故事”的话语实践之中。“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①小说中不论是叙述者“我”,还是老保长,抑或是林阿姨,都承担了讲述一个时间跨度颇大的故事的艰巨任务,而“我”以外的人所讲述的故事,最后不但变成“我”与诸位听者共有的人生经验,也成为故事的语料,从而使得“我”可以不断地复述故事,于是每个人所讲的故事都成为“我”所讲的故事(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小说中的“我”,具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这就是环绕于讲故事者的无可比拟的气息的底蕴,……在讲故事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②
小说颇为大胆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但小说叙事其实是多声部的“我”的接力与故事的接力。麦家在处理第一人称叙事上颇为老到,干净清晰的指示词与叙事者的串联使得小说有着全局性的视野,一环套一环,张力丰沛,层层起伏。小说的三大部分以叙述者“我”的成长为线,共二十章、一百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交代“我”的年纪时,文本模仿记忆,呈现出一种由模糊至清晰的变化。第八节时“我”五岁,而在通往第九节的两页纸中,文本提示上校的奇人奇事和与“我”家的羁绊,“我”见证了上校如何救下吃农药寻死的小爷爷,也见证了小爷爷如何一步步恢复健康,自己也从五岁到七岁再变成了十一岁。而在十一节中,叙述者“我”又回溯到了九岁,到了十八节,又跟着时间流转过上了十四周岁生日,十四岁的第一次失眠之后,记忆叙事中的“我”便一年一年地顺序成长。故事的整体流向水到渠成,而数字在增长的时候却因为连贯的事件与线索变得暧昧,尽管可疑,却又准确无误。这样的处理也可见作家一番苦心。正是因为在回忆时,有了理性的指导与照顾读者的考量,“我”这样抱有“讲故事”的目标的叙述者才会尽量理出一条好懂的故事线,故而须得在记忆中重建逻辑,在故事的连贯与事件的真实之间调停,同时,又流露出一些孩童回忆的模糊与跳跃。随着故事的推进,叙述者日益长大,记忆模式也更为清晰可靠,也就鲜少再以直接提及具体年岁辅助叙事。
听故事的人终要成为讲故事的人,而换了一张嘴说出来的故事并非简单的经验累积与传递,讲故事的人的复述,已经整合叠加了记忆中的相似经验,从而改造了故事,在故事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小说中几个讲故事的角色,年纪、背景、思维模式不一,各有一套语言系统,择取的视角、策略也大不相同。一个故事在众人间口口相传,转为下一个说故事的人的经验,用新的语言模式再说出来,效果、意味、影响也自有变化。麦家在各具个性的讲故事的人之间不断切换口吻、更改说话习惯,这些讲故事的人,又相互补充,颇为出彩。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关联颇大,却也见证了孩童与少年的分野。第一部分正如“我”对自己的形容一样,像“一只黄嘴鸟,藏不住话”(《人生海海》),尤以短句居多,甚至有定论的意味,直率坦诚,充满表达欲,抓住人一股脑地说个不停,还有些孩子气的霸道。“我”列举与描述时往往不吝篇幅,二字、三字、四字短语从来是成群出没,节律感十足,读来格外爽辣。不过短句与短章节的设计,容易使得文本节奏偏快,此时麦家显出了技巧上的敏锐掌控,往往以写长时段的事件加以平衡。到第二部时,“我”已是少年,所以文本不但从排篇布局上益加醇熟,“我”的感官也越发敏感,对感官的关注与描述的渴望也愈发强烈、自觉,思考也趋向深入。
三
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并未“为破而破”,那些不可揣摩的人性与命运仍是他关注的重心,那种环环相扣、紧张纠心的悬疑设置依然得心应手,甚至有的地方与《日本佬》《汉泉耶稣》等旧作也是声气相通。为了证明上校的清白,老保长选择对爷爷说出一段惊悚的上海往事,也解答了为何他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痛恨上校,反倒在其被迫害时挺身而出,为其辩白。老保长讲故事的安排,不单添置了悬疑元素,也让老保长带领听者亲身重现“讲故事”的话语实践。老保长讲述的思路屡次被打断,故事游离时也反复被拨正,偷听的“我”和直面讲述者的听者(爷爷)都充满着对故事的焦急与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与老保长被回忆调动起的“兴奋”的共同作用,使老保长这个“讲故事的人”的形象在这段酝酿良久的叙事中获得呈现,烘托气氛,制造悬念,几乎是驾轻就熟。老保长重温着身临其境的感官挑逗,讲述了一段自己如何卷入上校的人生世界的故事。上校为了完成任务,与“女鬼佬”(日本女人)们进行情色交易,在阴鸷浮夸的情欲里咬住高尚光明的意念,也指向了肉体欢愉背后被悬吊的身份痛苦。
此前叙述者“我”偷听小瞎子逼供上校,虽然没有听到关键部分便险被发现,仓皇溜走,但他在忘情的状态下无限想象了听到的部分,化归为自身的经验,或者说一种并未得到却有了基点以供想象的经验,从而唤起了少年的欲念。“即使他不赶我觉得也该走了,因为蚊虫实在太多,咬得我浑身痒。刚才我不敢挠,回家的路上我使劲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挠得手臂上、脚关节上都是红疱子和血印子。睡觉时爷爷发现我身上这些红疙瘩,连忙拿来杨梅酒给我擦身子,一边数,总共数出二十七块红疙瘩,简直遍体鳞伤啊。”(《人生海海》)麦家此节的处理十分有味道,少年不懂得被唤起欲念的感受,态度模糊而羞赧,拒绝直面欲念,却又沉溺诱惑,只好给自己找借口,将红肿与瘙痒归咎于讨厌的蚊虫。在麦家有意无意的叙述中,蚊虫伤肿不妨视为一种自我对外界的裸露,也是少年欲念经验想象的表征,而这些成为借口的伤口很快便引出了“强加”在父亲与上校之间的情欲。
上校的腹部被疑似川岛芳子的日本女人文了一行字,这行字是串联起上校、上校后来的妻子林阿姨、小瞎子、“我”一家命运沉浮、荣辱悲欢的重要线索,也是读者跟随叙述者不断追索、欲罢不能的悬念。那行刺在上校肚皮上的字作为其一生无处诉说的屈辱的源头,在被刺上的同时便已挑衅、反转了上校的自尊。“女鬼佬”在他的肚皮上用针刺字,以精细的针头,讽刺着上校的男性力量和自尊。上校的肉身体会到了穿刺的屈辱,此时身体的痛苦是卑微的、复杂的,要靠意志和理想的支撑才能忍辱负重,暂且忘记创伤。但是,时间并没有冲淡上校的屈辱,相反,上校的记忆却不可思议地变得明晰与深刻。刺字的记忆,成为上校必须承受的精准的羞辱,这又与上校高超的医疗能力相映照,上校有一套金子打造的手术工具,也正是凭借着精准的手法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小瞎子的造谣、上校为了封口对小瞎子的惩罚,还是爷爷对小瞎子“以毒攻毒”的炮制,无一不是“精准作案”,越是要消解掩饰那行字,却越是让那行字变得无比扎眼。麦家几乎没有对上校的心理世界进行正面的揭示与铺陈,而这行字却让整个小说变得惊心动魄,实在是深谙讲述故事之道,“使一个故事能深刻嵌入记忆的,莫过于拒斥心理分析的简洁凝练。讲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听者也越是愿意日后某时向别人重述这故事”②。
刺在肉体上的字和它所裹挟的痛楚、羞辱是上校无法忘却的,而这些来路即是罪孽的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又将“我”的整个家族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带来了根植于心的耻辱,制造了无法忘却的记忆。“大哥是去了秦坞,一个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人生海海》)叙述者“我”的经历与父亲被打为右派的童年麦家颇为相似,在此意义上,麦家似乎成了距离文本最近的那个“讲故事的人”,以文本外的个人记忆创造了文本内的个人记忆,从而使个人记忆在文本中经他人之口繁衍更新与自我和解。当然,小说并不满足于讲述个人记忆,也并不是想炮制一部家族秘史,其野心在于借由个人记忆,展现人性晦暗、人生多舛与命运背后的力量。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再到改革开放,麦家的纵向用笔映出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记忆与呈现,而第三部分叙述者“我”作为海外华人的归来,又带来了从本土延伸至海外再反观本土的新视角。
四
麦家紧扣“记忆”,深挖“记忆”的两大面向——精准与含糊,这种对立是麦家的叙事策略,也是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的互动呈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暧昧的中间地带,有着多重的切换与拉扯,从而将“记忆”推向更深入的“铭记”的层面。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中,读者可以极为直观地感受到“我”的情感的波折。“我”的情感及其表现非常鲜明,非爱即恨,夸张爽直,不加掩饰,在大哭与大笑之间切换,起伏巨大。但与此同时,“我”的情感又颇为混沌,混沌之处在于,“我”无法厘清情绪的缘由,也无法很好地将其描述和传达。于是,在无法厘清自我感情变化的来龙去脉的状态下,“我”反而更受情绪支配,呈现出一种任其自然的“尽情”的孩童状态。“我”的情感表现的精准与含糊的状态,似乎也存在于“我”的处世立场上,“我”对待一切事物总是立场鲜明,而缘由又是稀里糊涂。小说有相当篇幅的故事发生于“文革”期间,“我”对于事态的看法总是深受他人摇摆,一旦受到挑唆,便全情投入地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在反复更新的事实面前,又一次又一次地被操纵、被颠覆,同时,从外部与内部夹击的错位的震撼不断强化了“我”的羞耻感。“我”在第一、二部分中面对羞耻,哀号着不知如何忘却羞耻的记忆,却也无法与之和解。记忆同时保有着精准与含混的特质,仿佛滑动在光谱之上无所捕捉,无法忘却也无法厘清。文本内的人显得无能为力,不断叩问命运变化背后的隐秘力量,文本外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贯通文本内外时,麦家讲述故事时有意安排了两股声音的接力,面向历史纵深的同时又聚焦当下,传达了作家对当下现实的焦虑与思考。第一、二部分充满了“爷爷说”,这当然是麦家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我”作为一个“稀里糊涂”地在特殊环境里成长的乡村孩童,自然无法精准地传达出作家想适时点拨的评论性话语,故而需要一位知识结构复杂、生活经历丰富、占据家庭高地的老者出面。“爷爷说”不仅强化了“我”易受影响的这一面,而且与第三部分代替“爷爷说”的“报纸上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报纸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源代替了传统的“爷爷”,而信息的获得仿佛愈加权威,也更为规训化了。叙述者“我”从认知朦胧、价值摇摆、感情鲜明的乡村童年来到大城市里的中年,却也遇到了成人/城人危机。此时我们或许可以说,麦家在有意识地塑造一个“我”,巧妙隐晦地诉说“我们”,纪录片似的再现(按此思路去象征地理解文本,记忆精准的含糊也可理解为摄影技术如实呈现低清晰度的画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如何失去自我、如何被左右,也疑惑着新中国从赤着脚的乡村童年到而今的成人/城人时代,又该如何处理当下。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宏阔的、更为广义的“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作为小说的标题,直到第三部分才浮出水面。这个闽南语词汇的语意及其用意到底所指为何?这个悬置一直到小说后面快结束时,才得到彻底的揭晓。“人生海海”一直被有意压抑的意义——或者说以“叙事”方式不断诠释的意义,不是由上校、爷爷、父亲、老保长点明的,而是由次要人物“我”的前妻说出来的,前妻在文本中也仅仅与主人公有着单一的关系。由这个与他人关系最游离的人物提出“人生海海”,麦家似乎在寻找一道遥远而亲密的边界,从那里包抄,借由“我”来勾连遍布全书的各式人物命运沉浮的众声部。小说看似在追寻上校一生的踪迹,进行着非谍战式的暗算与解密,讲述一个忍辱负重的英雄的传奇故事,其实也可说是以“我”(或是上文提出的“我们”)为中心的回忆与反思。“我”把上校、老保长、林阿姨、“我们”家的故事凝成了长篇回忆,创作的过程就是累积个体的故事,又通过那道遥远而亲密的边界将故事交织,将“回忆”上升为“铭记”,把人生的丰盈繁复推向了极致。而读者在一气呵成的阅读过程中,与这些故事歌哭与共,不断体验着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诚如斯坦纳所说,“阅读是行动方式。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象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麦家在描写“我”的童年遭遇时也倾注了不少私人情感,比较集中地引入了故乡与童年记忆,相似的经历与记忆的有机安排,并非暴露秘辛,而是通过小说书写这个时真时假、亦真亦假的机会卸下过往的光环或负累,自我剖白,以环环相扣的故事,与广大的读者一起,进行一场治愈表演的自我和解。“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人生海海》)经历了这一切,却依然热爱生活,勇敢地活下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也才是“人生海海”的真谛之所在。帕慕克说,“每个作者写的每一本书,都代表着他自己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人的小说,可以看做他精神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⑤,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麦家以后的小说创作走向何方,我相信,这部《人生海海》终将成为麦家创作历程中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注释:
①②③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118、102页。
④乔治·斯坦纳:《人文素养》,《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⑤《奥尔罕·帕慕克》,方柏林译,见《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