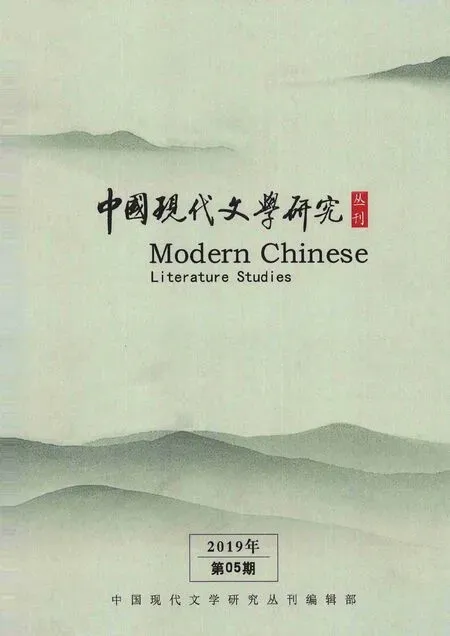“缺席的散文”和一个散文家的档案
——周晓枫论
项 静
内容提要:本文把周晓枫的散文创作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写作的传统中,分析解读了周晓枫散文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她对散文写作传统的对话意识和反叛精神,进而论述当代散文在话语空间、对象的延展度、形式嬗变和自由属性上对时代承担的文学责任,以及这一文体面临的挑战和生长空间。
一
古代散文是相对于韵文和骈文而言的,较早是指更具活力的诸子百家之文。现代文学肇始阶段,朱自清即明确提出现代散文“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文散文,或称抒情散文,或称小品文”。张国俊在《中国艺术散文论稿》总结当代散文的概念基本是“从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当代散文并没有对现代时期有所突破和嬗变,是对现代散文概念的继承”。当代散文继续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和形式,与诗歌、小说、戏剧并举,分为广义的散文和狭义的散文。狭义的散文特指抒情散文,广义的则包括报告文学、杂文、随笔、游记、特写等。自现代以来,散文不断开拓写作的边界、题材,也在历史和文学的发展中接受各种新的内涵和形式的嬗变,当然也生产着自己的问题。范美玲的《从“十七年”到1980年代的散文创作嬗变》概括出“十七年”散文的特色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体规范之下,重视细节的真实和典型化手法的运用,重视散文意境的营造和追求抒情的崇高化;而1980年代的散文创作则跟整体文学氛围同步,寻求艺术方式的突破与创新,弱化语言形式的技巧性,将小说、诗歌、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融入散文的创作。李雪梅《中国现当代散文本质特征论》一文翔实地追溯现当代散文发展过程中,加诸散文本身的各种论争和命名,比如现代时期的“美文说”“性灵说”“工具说”,当代以来的“诗化说”“形散而神不散”“真情实感”“文化”“内向”,等等。
在现当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概况中去看当代散文家周晓枫的创作,就能够理解她对散文文体固执的认同,无论她的写作方式多么复杂,其“内在支撑和整合的方式是散文本质”。自古至今,散文所建立起来的谱系图就像彗星狭长的尾巴,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为自己划定的版图中,已经照亮和辐射了足够的空间,其话语空间、对象的延展度、形式嬗变的要求,跟其他写作样式并无区别,关乎个人染乎世情,是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学形式。同时,散文写作的自由属性使它在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时代,携带着秘密的火种——它带来谨慎的同时又有冒险的快感,周晓枫说自己热爱散文这个文体就是因为它宝贵的自由精神,“我繁育无数散文中的‘我’,像披光的树叶不断翻动着它们的侧影和虫斑”。唯有自由精神提供创造的可能,散文本应该承担更多形式创新的责任,今日散文的弱势本质上是具体写作者把散文逼进了狭窄之地,并习惯性地在舒适地带徘徊,从而在一个具有对话空间的体裁上纷纷滑落。
周晓枫较早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始于1990年代后期,1990年代的文学失去了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整体上的高昂与缤纷绚丽,但在局部仍然演进着创造的火花,散文界关于“大散文”与“艺术散文”的论争,“小女人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等命名的迭出,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对旧形式旧思维的改写。但近年来已经很少有诸如散文“怎样写”和“写什么”的论争,同时也缺少必要的命名、对抗和拒绝,散文写作总体上走向随意流淌的自然状态,加上新媒体又拓展了写作的边界,这是一个写作能量获得充分释放的年代。似乎每个写作者、每种类型的散文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和受众群,给写作者和读者都造成仿佛自言自语写到地老天荒都可以的幻觉。这是一个需要对散文收束和聚焦的时刻,也有对写作者的幻觉进行清理的必要,恰如周晓枫那个刻薄的讽刺,许多当代散文就是“化装在散文里的个人赞美诗。他们修饰出光可鉴人其实根本无法辨识出原型的自我形象”。
二
在散文备受质疑的时代,周晓枫是散文华丽家族的使者,她在作品中“把戏剧结构、诗性语言、小说技巧和随笔智慧融入实践……习惯在散文里维护中性立场,既非绝对小说,又非绝对散文,像雌雄同体令人迷惑”。除此之外,语言的雍容丰瞻,鲜活的个人经验、敏锐的体察,精神探索和文体试验,饱满、激情和挑衅使得现当代散文中大行其道的浅显的“美和诗意”“抒情”“叙事”“中正雅致”等范儿变得略微可疑,给人一种走进散文的“新时代”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让我们重新体味到散文的显赫的存在感。
周晓枫散文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社会评价。在销售市场上周晓枫的散文无法跟很多明星散文家相比,她经常自嘲作品是“票房毒药”,但另一方面她的散文却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比如来自评论家们的认可,“周晓枫的语言是最好的书面语,水晶钻石,自带魔性”(李敬泽),“中国散文写作里罕见、完成度非常高的作家”(汪惠仁),“散文家中的散文家”(张莉),等等。周晓枫还斩获了散文界的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奖、朱自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官方和媒体各类大大小小的奖项。从评论家的盛赞和获奖情况来看,周晓枫的散文写作在评论家和媒体的视野里一直存在,并不存在“被忽视”这种作家经常臆想的问题,她的问题存在于散文内部。
周晓枫的写作一开始就带着反叛的气质,恰如张莉一篇文章的名字是“起义的灵魂”。1998年《大家》杂志顺应文学的内部需求提出“新散文”的概念,“倡导注重散文文体的自觉探索,注重审美经验的独到发现的写法”,并推出周晓枫、张锐锋、庞培、于坚、钟鸣等一批带有冲击力的作家作品,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以真挚、痛切的女性经验令人印象深刻。稍后的2004年周晓枫主编了散文集《7个人的背叛——冲击传统散文的声音》,依然保持对传统散文宣战的姿态。在习以为常的散文标准里,她的散文必然是不合群的,这可能意味着对普通读者一定程度的拒绝。比如她的散文几乎每一篇都是篇幅较长的精心设计的专业性写作或者说职业性写作,少则四五千字,多数是万字长文,《离歌》更是五万字的篇幅。著名散文家秦牧认为“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一切篇幅较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畴”。周晓枫很少发表短小随意的写作,每一篇都带着工匠手工劳作的痕迹和专业写作者的自觉意识,步步为营,靠着理性的设计和语言的力量扎实前行,绝不是一时一地灵感、心绪和臆想引发的灿烂火星和美丽霞光。
1997年年末开始写作的《收藏》,书的副标题是《时光的魔法书》,整部作品带着魔法和工业社会的属性,借由童年记忆和摇晃的时光,在日渐理性主义的今日回望中,锻造出生活越来越膨胀的光影,他们由于自己的身形和固执持续的言说,脱离了原生的语境,自成一个混杂了经验、想象和议论的世界——“这是在想象中开始的回忆,记忆的参照系数和想象的设计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使我重新成为孩童,满怀好奇,开始打量。”
《病床》一文里写到医院的病床,由于作者的母亲是医生,医院对于她来说是一个熟悉之地,这给她带来了较多的审视和感受的机会。在对医院的立体式叙述和打量中,唤起的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记忆,还有缓缓升起的对世界的清冷认识:医院与死亡保持着危险的暧昧关系,手术是体面而正义的暴力事件,愈合只完成于伤口之上,而被拯救的人则不再完整,身体是神设下的谜局,太平间是另一个世界狭窄的进口,细节是记忆的索引,而记忆是整个生命的索引。《大地》写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久远的公共记忆是一个时间窗口,是一个脱节的或者说被提炼出来的场景,里面有很多琐碎、简单、残破,对今天没有启示对未来也不见得有提示的意义,但毫无疑问它们留下了深刻的刻痕。地震冲破了人们的日常尊严,流出简陋的内衬,人们表露出惊骇、担忧以及种种防范和抵抗,家园近在咫尺却不敢回去,而孩子们则表现出难得的自由和解放感,不用回到被大人们束缚的日常生活,终日游戏到深夜,像漫长的节日。这篇散文在周晓枫的作品中属于相对简洁明了的作品,以患病的爷爷作为所有其他生活的对照,爷爷毫无恐惧地回到楼上睡觉,他无法分辨世界的危害、他人的嘲笑和善意,而这些却让他得以在那个悬在众人头上的恐惧中脱身,自在而有尊严地度过了地震期。
在内容上作家潜心创造了内在大体的统一性,比如医院和地震的氛围,辅之以对时间的详细打量和立体性的叙事围剿,呈现出写作者主观性内心生长的云图和丰赡的生活勾连能力,超越了日常生活本身的轮廓和体积。这本书中还有《烟火》与孩子幻觉的眼睛,《铁轨》里火车的工业主义诗情、联想的激情、生命的流转与变迁,《票证》与昨日的虚像,《旧物》与丰富令人震惊的寓言主题,《词语》与虚荣心和微小的罪行,等等。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眉梢的哀愁、鼻翼的眼泪,作为写作对象本身非常重要,但在同一幅度里常年重复性摇摆,是导向无意义的走廊。周晓枫把日常抒情和散文和蔼可亲的部分,分割在散文的不同章节之中,避免过度集中引起的不适和虚假感,又能够串联进自己的新语法中,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三
周作人在1930年对于文学有一种失望情绪,自认为对于真与达的文学无法实现,但还有一种思路可以到达文学,“文章还是可以写,想写,关键只在这一点,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吧,只怕此事亦大难,还须得试试来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草木虫鱼是对纯文学的一种解救,是对人的文学的有益补充,另外又是具有较多空间和书写自由的题材。
周晓枫对于动物题材的书写,与周作人的思路具有类似性,大概也是要“认真去写一篇文章”,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包含了一种职业和专业的态度在里面。周晓枫《斑纹》序言中提到纳塔莉·安吉尔的《野兽之美》,这本书内容中有关动物的部分是她唯一敢于接近并且体验到阅读享乐的科普类读物,她又提及著名散文作家苇岸的写作,他温暖而高贵的抒写给她带来了启发。
《斑纹》一篇写有斑纹的动物们,作者首先给这类动物们以整体性的“嫌恶”和“指摘”:“密布全身的鳞片组成斑斓的图案,一条蛇,夸耀用心险恶的美。”而后以个人经验去陈述对于蛇的生理性恐惧与避忌,也科普了蛇的特征,它们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世界对于它们来说线条和轮廓是模糊的,只有无所不在的斑驳,它们没有听觉,世界是绝对的寂静。由此蛇与尘土为伍,它们偷袭洗劫其他动物的巢穴,吞食鸟类的蛋卵,使得它们成为与阴谋、危险、罪恶有关的象征,它们似乎拥有冷酷而贪婪的心。由蛇蟒到蛇蝎美人,再到其他斑纹类动物鲑鱼、斑马、老虎、豹子、猫、鹰凖、长颈鹿、蝴蝶,等等,穿插它们的习俗和故事,拎清它们之间善恶秘密接壤,最远的善将是最早被消灭的生存法则。接着由生活中接触到的蝴蝶标本制作者,回到人类的世界,标本制作者的激情,令人感叹人类的狂想可以抢夺上帝的社稷。此文最后是抒情,斑纹无处不在,就像我们有意修饰并损害的生活,每个人都终身隐秘地镌刻着各自记忆的斑纹,爱与恨的斑纹。而在神的视野里,人类也是一些斑点。
从这篇散文来看,周晓枫的散文依然保留着传统散文的一些“套路”,如感情的升华,但是她对着力点更加严苛,从大自然的秩序(神)到人类的寓言和生理感应,从对上帝社稷的理解和认识到对上帝的僭越,最后还能再次回到神的视野,反观人类世界的渺小。在不同空间和表现对象之间不厌其烦地反复和折回,并以各种寓言故事、经验知识和恰当的抒情议论去勾连填充不同对象之间的空间。
如果说《斑纹》比较集中,那么《聋天使》一篇则可以窥见周晓枫的万花筒风格,看到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自由转换。《聋天使》开端是对养蚕的描摹,按照蚕种生长的顺序,详细编织它们生命所辐射的图谱,交代了它们成长中的危险,只吃桑叶的单一食谱,恪守如一的啃食习惯,数度蜕皮以至成熟吐丝,隐没在自己织就的屏障之内。稍后是两个人的疾病史,由于采集桑叶,“我”结识了进京治疗耳朵的聋男孩小盐,寄宿在亲戚家,接受医院的系列检查和化验,安静地像个永远不会被读出声的句号,是一个无辜者不幸的故事。化脓性中耳炎不可逆转地修改了他的世界,在疾病面前,人体是脆弱的维护系统。病人含着委屈与无效抗议的哭声,小盐自始至终的沉默,还有对比之下自己所遭受的几次微弱的肉体历练,都让“我”迷惑于疾病和残疾的意义。
文章突然转入写作的话题,由中耳炎销毁任何美化的可能,而生发出“频繁使用痛苦的审美意味,原因恰恰在于,使用者不疼;一个真正痛着的人不抒情,如同残疾孩子久居沉默”。由蚕的一生而慨然叹息:“作家的能量,取决于他对困难、苦难乃至灾难的消化……蚕不停咀嚼,在聋掉的世界里专注消化眼前的桑叶,它将忠诚于素材之后的使命。”写作的本质与蚕的相似性,“每当形成和适应了某种表达风格,我就明白,必须再次从这种惯性保护里驱逐自己,重新,脆弱地裸露,像蚕除掉旧衣,像易于变脏的木头不断刨掉表层,露出新鲜的花纹”。
《聋天使》可以感觉到周晓枫散文中强硬的作者主体,她抛弃了“语文的教养”,“唯美得虚弱的教养”,她的理性思维和组织架构能力,让作品的所有枝叶都牢牢掌控在作家的手中,即使是写动物和童年的散文,其主体意象也没有随意流淌和闲笔信步的可能性,伸缩收支都在作家的把握之中。即使是作品中“我”的孱弱和敏感,都在繁复的言辞锤炼中成为一种凸出意志和焦点形象。作家的议论倾向和思辨性,对于单纯叙事的冲击,对于简单抒情的不信任,使得周晓枫成为一个打破假象的写作者,她的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模糊的“平等”“正义”“爱”“真诚”的社会图景,这些词汇串联起一个高悬的“道德谱系”,杂陈了信仰、神话、故事、动物、人类等造物的存在。另外,周晓枫谈起写作来有一股飞蛾扑火的气势,她说:“我希望自己,有胆量以耻为荣。”“我感到自身的邪恶,并由此欣喜。”以耻为荣,因邪恶而欣喜,剔除了散文所谓“艺术”的衣装,无限地具体地解放了进入写作的自我和生活。
四
埃德蒙·威尔逊谈及文学的转变,“法郎士那一代的力量,来自对社会事务的广泛知识,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兴趣,与民意的直接接触,以及通过文学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而到了瓦莱里的时代,孤独的挣扎、真诚的内省,才是文学的力量之源”。我们很难在两种文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也无法迅速指认哪一个是更好的文学,确凿无疑的是不同的文学趣味和真实发生的改变。周晓枫的散文以及1990年代以来有辨识度的当代散文大都是以“孤独的挣扎”和“真诚的内省”作为文学之源的。从《聋天使》《病床》《收藏》《墓衣》等篇章里对社会的暗讽与审视,精神考古式的对人物和事件的追索,到面对他人死亡的自我诘问,挣扎和内省的文学气质已经成为鲜明的个人标志。2015年年初长篇散文《离歌》发表,2017年即领衔《收获》上半年非虚构长篇散文排行榜首位,备受评委和读者好评。这固然是一次转变,但在她个人的写作里,也是水到渠成。
《离歌》从万花筒的散文写作中跳脱出来,以聚焦的方式,以低姿态的叙述方式讲述一个生命的陨落。吕永林把《离歌》看作作家对亡魂进行的“一次单方面的精神考古”。《离歌》的开头像一篇推理小说,首先宣布了屠苏的死亡,一个曾经以为是“发白齿豁,依然鸡犬相闻、肝胆相照”,结果二十年来几乎没有联络的朋友。屠苏的死亡,他的妻子小夜的主动告知,逼迫“我”重新勾勒他的前世今生。他毕业于显赫的学府北京大学,曾经的小城高考状元,在“我”记忆中是一个智商超群、温良淳厚、细腻体贴、聪颖、博学、专注的写作者,受到扎实的学术系统训练,加之阅读涉猎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凡的见识,是“我”的精神指引。在不可名状的男女微妙情感龃龉中两人告别,屠苏放弃理想主义的玄谈,务实地去专注生活,结婚生子,成为彼此的记忆和怀念。
嗣后的离婚、事业坎坷等都是遥远的传闻。死亡让故事重新开始,“我”带着好奇和疑惑,重新走进屠苏的生活,跟随屠苏的骨灰回到故乡,发现了另一个屠苏。慌不择食地选择进入“体制绞肉机”,不善于复杂的情感和社会关系,作为薪资微薄的小公务员,在北京的汪洋中注定了失败者的悲剧结局。在内心的失败和受挫中,屠苏选了最初人生高光时刻(高中时代)的暗恋对象小夜,小夜以虚构的远景(有钱、有背景、生孙子等)打动了屠苏及其家庭。在狂热的经不起严密推敲的生活臆想中,屠苏和小夜选择了撕毁道德和伦理,对前妻的负情,也包含他对自己以及一家老小的寡恩薄义,“屠苏凝聚终身之力,也还不起父母恩情,只好抹杀和忘却。他背不动整个家族的大包袱,余力只够背起一个体量比常人还轻的小夜。所以,他对屠家所有人采取回避的办法。屠苏回避他的处境,渐渐,他回避他的良心。他说服自己,他给予家族的光荣,已将全部债务偿还”。这一切的背后是北京生活的坚硬现实:房价物价与一个小公务员的微薄薪资之间的必赢的搏斗。屠苏依然在挣扎,四十岁高龄跨界去考教育学博士,由于工作本身繁重,他必须像高考学生那样刻苦,抓紧每分每秒,夜以继日地苦读,最后他死于劳累。
《离歌》最初刊载于2015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卷首言:“本期始,将开设‘思想者说’的新栏目,旨在召唤文学与当代思想对话的能力,记录当代人的思想境遇与情感结构。”《离歌》从“屠苏”之死切入个人和时代的痛处,是一个纤毫毕现的标本,打开了灰暗世界的褶皱和内里,也打开了一条理解世界的道路,平实中蕴藏着沉默和悲鸣。同时作品又没有放过“我”和周围的观察者、围观者们,实现了自我充分的田野化和反观,“我”对写回忆屠苏这篇文章的道德优越感和为自己寻找借口,可能跟小夜的行为一样自私而残忍,“像在被污染的河里;一条鱼指责另一条鱼”。“我”对跨越阶层和出身的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们的粗野庆祝也释然和理解,自己的清高冷淡,不过是籍贯和出身保障了它们的存在。
相对于万花筒风格的散文,《离歌》“作散文”的姿态减弱了,因为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里尔克说,“一件艺术品是好的,只要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在这样的根源里就含有对它的评判:别无他途”。从私人经验来说,《离歌》是告别和清理;从公共热情来讲,它逼近的方式接近了时代生活黑暗悲怆的内核。《离歌》的发表,使得一个陌生的散文文本进入了周晓枫个人写作的历史,也进入了当代“散文写作”的历史,并成为一个重要的路标,带来的不仅仅是被呈现世界的深入、丰满和辽阔,还是叙事艺术边界的变动融合的沸声,《离歌》不是之前散文中常见的对小说艺术具体手法比如蒙太奇、意识流的借鉴,而是全面深入的融合,称呼它为散文、非虚构或者小说都不是越界之举。
五
自我往往都是被他者或者敌人所塑造的,周晓枫的写作正是在对抗中完成了自己的“独特”,而她也对此心知肚明。没有谁比她更了解自己创作的价值和意图,也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在当代散文写作的空间里,谈论周晓枫这样具有文体自觉和理论能力的作家是非常困难的。要么,继续重复她个人和众多论者已经反复阐述的对于书面语的爱好,对形容词的重视,女性立场和表述,风格化的叙事,创造性的文体,跨文体,等等,要么就被她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所说服,接下来的言辞就有流于溢美的危险。周晓枫是一个非常会表述自己的艺术主张的作家,比如《关于写作》一篇,可以看作她对自己散文写作的自问自答,也可能是对潜在质疑者的回答,方方面面都妥帖而逻辑自洽。
不仅仅是在散文写作过程中,她紧锣密鼓建立起文本的壮丽城堡,在自我意识上她也是铜墙铁壁的作家,自我阐释和自我建筑得牢固踏实,看得清形势,从容不迫而内心坚定。即使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你也很难找到这种作家的缺点,因为你所认为的缺憾在彼处正是作家写作的起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阅读当代散文时候的一个共同问题,你所操持的那一套语言恰恰是写作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陷阱,写作者都特别会为自己建造安全的防护堤,而在这个防护堤内,并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
同样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里尔克说:“谁若是要真实的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的种种问题。”散文应该是生存者对生活问题的担当,也是个体面对日常世界一草一木无分轩轾的接纳,包括超越私人世界的问题和写作的问题。当代散文写作的责任,仅仅建立自己的姿势还不够,需要以写作的实绩去完成生活问题的担当。里尔克说,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怎样生活,都在不知不觉地为它准备;每个真实的生活都比那些虚假的、以艺术为号召的职业跟艺术更为接近,它们炫耀一种近似的艺术,实际上却否定了、损伤了艺术的存在。
与其跟一个腐朽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的近期散文传统缠斗,不如放弃这个视野;与其借鉴小说的方式方法,不如放眼历史、思想、政治等的方式,毕竟即使艺术上的本地人也总爱“把他所看到的一切运用在他自己或是他的需要上边”,但是“人对于周围的事物看得是多么不清楚,常常必得从远方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周围的真面目”。
在当代散文写作者中,自觉的文体实验者和精神探求者已经涌现,比如近年来陆续在当代期刊杂志中出现的张承志、李敬泽、阿来、陈福民的散文专栏,还有一直躬耕于散文写作的李修文、李娟、贾行者等的新作,他们在散文随笔中创造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和对“重”的承担,并在写作中具体化物质化了带有我们时代气息的“重”。周晓枫当然属于最优秀的散文家群体,读者们寄予她的期望就是对当代散文的期望,她理应是冲锋陷阵的写作者,首先希望她冲破自己的那座城,再奏一曲《离歌》,再现融合的沸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