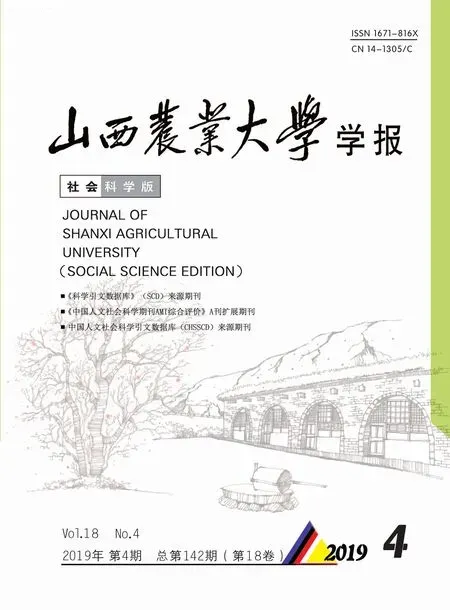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周春芳,苏群,常雪
(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4;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历经近40年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后,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社会一个庞大且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7 747万人,其中女性占33.6%。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和户籍改革力度的加大,农民工通过职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化,最终完成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高质量的就业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则是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关键。然而,由于生物学差异、社会性别分工以及个体资源禀赋的差异,女性就业质量低于男性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普遍现象,尤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而言。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与男性的差距,决定了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因而也是决定我国人口城镇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因而,本研究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考察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变化及其性别差异。欲回答:职业流动是否促进了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呈现怎样的变化?其作用机理是什么?以上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从社会性别视角制定城镇化政策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
研究表明,在参加工作的前10年,工资增长的40%可以归因于职业流动[1]。职业流动是非熟练工人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多次的职业流动不仅有利于农民工职业的向上流动[2],还有助于提高流动者的工资水平[3]。与男性相比,职业的性别隔离使得女性大多集中在工资收入低、职业培训机会少及福利待遇差的“女性职业”[4],其在职务等级、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等方面远不如男性[5];女性更容易因怀孕、生育、照看幼儿中断工作,因而其工作经验较男性少,加上雇主的性别歧视,女性重返职场后的报酬和晋升机会明显低于获得同等教育的男性[6]。只有当女性的能力高于男性竞争者,以至于其能力能弥补其因家庭因素可能导致的工作中断时,雇主才会给予女性晋升机会[7]。同时,随着工龄增长及跳槽次数的增多,性别间工资差距快速拉大。研究表明,在进入职场的头10年,女性小时工资为男性的94.8%,随后下降到84.9 %,其中跳槽对男性工资增长的贡献率为32. 9%,是女性的4倍左右[8];且职业流动模式和职业流动回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两性收入增长的差异[9],其中家庭原因的主动流动、单位原因的被动流动分别降低了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10]。
以上文献十分具有启发性,但其仅仅涉及了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尽管工资是一个相对较好、更直接测度就业的工具,但对就业状况的测度还应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雇佣和晋职机会等指标,而现有文献对此的关注明显不够。为此,本研究引入了就业质量的概念,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指标,不仅包括工作报酬的提高,还有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职业地位的提升等。以往研究往往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而事实上,在历经近40年的人口流动后,农民工群体的同质性被打破,其内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统一的身份类属难以掩盖群体内部出现分化和差异的事实[11]。在农民工就业质量离散度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仅采用基于均值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存在较大偏差。与均值分解相比,分位数回归与分解不仅能够全面刻画整个收入分布上的工资性别差距,且不易受异常值的干扰,分解结果更加稳健[12]。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可以将工资分布的变动表示为以各自变量的特征效应和不可解释的系数效应,进而计算出就业质量性别差距的形成机理,因而较其他分位数分解法更具优势。基于此,本研究利用CHIP2009和CHIP2013数据,采用FFL分解法,考察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性别差异及其异质性,厘清其作用机理,以期得到一些普遍性的结论,为我国城镇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理论分析、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一)理论分析
作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形式,职业流动及其后果长期以来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形成了诸多理论。职业匹配理论[13]认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披露,当劳动者发现外部工资水平高于其现有工资水平时,就会主动寻找工资水平较高的其他就业机会。因而,职业流动可以促进劳动者收入增长。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本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由在职培训及“干中学”形成的专用人力资本,认为专用人力资本具有不可转移的特点,因而职业流动会导致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的丧失,致使劳动者生产率下降,且流动者不能享受到职业内的工资增长和内部职位的提升,因而会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与男性相比,女性先天的生理特征以及感性、温柔的性格特质使其在家庭生产中更具优势,尤其是在生养、教育孩子方面,因而其更容易因家庭中断工作,导致职业流动过程中其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较男性低,因而雇主更喜欢雇佣被认为“生产效率更高”的男性,且给男性提供较多的晋升机会。此外,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致使女性等弱势群体在职业流动中遭遇额外的制度成本,所以她们只能流动到职业声望较低的岗位上,因而其就业质量低于男性。综上所述,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社会性别分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可能是两性间收入差距随职业流动扩大的重要原因。该结论构成了本研究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
(二)就业质量的内涵与测算
就业质量是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自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之后,欧洲基金会提出了“工作和就业质量”指标,主要包括工作报酬、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以及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和谐,体现了工作稳定性、工作场所的尊严及个人发展。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从工作报酬和职业地位、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3个维度,构建了以月工资收入、职业声望、周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现工作的从业年限等5个方面的8个指标,用以反映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状况。其中,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是就业质量的核心,周工作时间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逆向指标,社会保障提高了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现职业就业年限反映了就业的稳定性。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量化是一个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各原始指标包含的信息可能有重复,即各指标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复杂的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并提取公因子,然后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解决了人为赋权的主观性。计算过程如下:(1)为了增强可比性,用物价指数对2013年的月工资收入进行了调整。(2)数据标准化:对于除工作时间外的其他7个正向指标,直接对其进行标准化;周工作时间采用了1减去标准化后的周工作时间。(3)数据的KMO检验结果显示,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参与情况的KMO值均在0.6~0.8之间,综合KMO值为0.8086,证明了因子分析的适用性。(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降维,提取公因子,并计算各因子得分。(5)以旋转后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就业质量的综合得分。
(三)自变量的选择
职业流动。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变量,职业流动的内涵及其测度尚未达成一致。大多学者用是否转换工作、转换工作次数、流动比率或某一类流动等指标来探讨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然而,是否转换工作、转换工作次数均与外出务工年限有较强的关系,一般来讲,外出年限较长者,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转换工作的次数也可能较多。为增强可比性,本研究引入了职业流动周期的概念,该指标为工作年限与换工作次数的比值,指一定时间内劳动力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的平均时间[14],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越高。同时,与行业间流动相比,行业内流动有利于农民工社会资本、专用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该类流动容易引致就业质量的向上流动,因而本研究引入了是否行业内流动;此外,国有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及外资企业具有更好的薪酬、职业培训和社保体系,因而流入这类所有制性质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相对较高,为此本研究引入了个体私营企业流向非私营企业。
家庭负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家庭生产的比较优势,使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为了便于照料家庭,女性往往会阶段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也致使其以工作经验和由培训形成的专用人力资本较男性少,加速了通用人力资本的折旧,这必然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鉴于母亲对子女健康成长的不可替代性,本研究以“家中是否有6岁以下儿童”作为家庭负担的测度指标。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较高者生产效率更高,且其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更强,因而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往往较低。一方面,由于子女效用的不同,父母往往将有限的经济资源投资于男孩,造成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另一方面,流动女性以工作经验和由培训形成的专用人力资本较男性少。本研究把人力资本界定为以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通用人力资本、以务工年限为代表的专用人力资本、以身体健康为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
其他变量。引入职业流动渠道、地区等控制变量。职业流动渠道用亲友渠道就业来衡量,通过该渠道找到当前工作=1,其他=0;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而本研究引入了地区变量。此外,为了解决就业质量与职业流动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初始工作质量。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仅以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3个指标,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周工作时间的标准化为1-标准化后的周工作时间),然后采用平均加权法计算初始工作质量的综合得分。
(四)数据描述
本研究将农民工界定为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员,研究范围限定在年龄为16~65岁、在业的、曾有职业流动行为的农民工,删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获得可用样本4231个,其中男性2700个,女性1531个。

表1 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行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流动次数来看,自外出务工经商以来,女性农民工平均流动1.91次,为男性农民工的72.9%,但由于务工年限不同,流动次数不具有可比性,为此本研究引入了职业流动周期。现有数据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时间间隔为6.43年,比女性农民工长2个月,说明男性农民工的稳定性稍高于女性。从职业流动的方向来看,由个体、私营企业流入国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等非私营单位的女性占5.2%,仅为男性的66%;从行业流向来看,女性在行业内流动的比例为35.8%,高出男性0.4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其中,以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通用人力资本为男性的95.2%,而以务工经商年限为代表的专用人力资本仅为男性的85%,这与女性更容易因家庭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她们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和由培训形成的专用人力资本较男性少有关。由于性别间年龄的差异不大,女性身体健康状况略低于男性,且其依靠亲友渠道获取工作的比例略高,而家庭特征、地区变量的性别差异不明显。

表2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变化及其性别差异情况
注:初始就业质量为因子分析法计算的综合得分,负值代表低于平均水平
就业质量提升的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女性农民工初职的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及工作稳定性分别为男性的97.5%、86%和95.2%,女性就业质量的综合得分为-0.054,明显低于男性(0.030)。经过劳动力市场的再次职业流动,农民工就业质量有所提高。其中,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分别为初职的1.08倍、2.36倍和1.63倍。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月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提升了7%、144%、72%,女性农民工分别为 11%、121%和46%,男性农民工现职就业质量明显高于女性。从具体指标来看,女性现职的职业声望与男性基本持平,但其月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分别为男性的78%和81%,明显低于初职的同类指标,说明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流动扩大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而女性农民工享有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分别为男性的98.68%、83.64%和99.55%。
二、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首先考察了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在此基础上,检验了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影响。
(一)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即FFL分解法。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利用重置权重函数,使自变量在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中服从同分布,以此为基础进行RIF回归。Qτ分位数的RIF方程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Qτ为 F(Y)分布的分位数函数,fY(·)为Y的边际密度函数。


其中,[Qτ(Yu)-Qτ(Yc)]表示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特征变量不同而带来的差异,可表述为特征效应,属于可以被个人特征差异解释的“合理部分”;[Qτ(Yc)-Qt(Yγ)]为收益率不同带来的差异,即系数效应,属于不可解释部分,也被称为“歧视”部分。与其他分位数分解法相比,FFL分解法可以将就业质量分布的变动表示为以自变量为基础的特征效应和系数效应,计算出各自变量对总差距的影响大小。
(二)职业流动是否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各分位数上,职业流动周期、个体私营到非私营、行业内流动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大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职业流动促进了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结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职业流动周期、个体私营到非私营、行业内流动的回归系数依次增加,说明职业流动的回报率随就业质量的提升而增加。其中,在90分位数上,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周期的回归系数为0.0116,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别为10分位数、50分位数的10.54倍和4.3倍;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周期的回归系数0.0235,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别为10分位数、50分位数的78.33倍和12.37倍;说明职业流动周期越长,越有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而频繁的工作转换容易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尤其是对较高就业质量的农民工来讲,其频繁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较高。一般来讲,较长的职业流动周期,可以实现工作年限向工作经验累积效应的转化,且有利于提高雇主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因此获得较大提高,终将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同时,由个体私营到非私营的所有制间的流动,其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同样呈现随分位数水平提高而增加的趋势,说明农民工由个体、私营企业向国有、外资企业的流动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对于较高就业质量的农民工而言,这与国有、外资等非私营企业拥有较为完善的薪酬、培训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关。此外,与行业间流动相比,行业内流动更能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表现为行业内流动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中高分位数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较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行业内流动大多是水平流动,尚不能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而在中高端的劳动力市场中,行业内流动更有利于农民工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叠加,进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
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由表3可知,在10分位数上的女性农民工样本中,职业流动周期、个体私营企业到非私营企业、行业内流动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职业流动对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其可以显著促进同分位数上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在50分位数上,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高于女性,其中职业流动周期、是否行业内流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同分位数上女性农民工的1.42倍和4.8倍,而个体私营到非私营的流动对50分位数上女性农民工的回报率较高。但在90分位数上,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高于同分位数上的男性,其中职业流动周期、个体私营到非私营、行业内流动的回报率分别为男性农民工的2.02倍、1.63倍和1.03倍。说明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对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不同,且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

表3 不同分位数条件下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RIF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内为误差项。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受教育程度、外出年限、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人力资本较高者容易获得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且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受教育程度、外出年限、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越大,说明人力资本回报率随就业质量的提高而增加。两个群体中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随分位数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表明高层次劳动力中有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其中,女性农民工在10和90分位数上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男性的2.5倍和1.1倍,50分位数上两者基本相当,表明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验证了提高女性尤其是低收入女性教育投资对缩小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在各分位数上,务工年限及其平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说明务工年限与就业质量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原因在于:农民工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初期,劳动熟练程度和技能的提高促进了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工作质量随之提高;但由于人力资本再投资不足,一旦其掌握了基本的工作技能,劳动生产率随工作经验增加缓慢或不再增加。就其分布来看,外出务工年限及其平方的回归系数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加,但其对90分位数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女性农民工的回报率略低于男性。健康状况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明显,除90分位数上的男性农民工外,其他均为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其他变量来看,6岁以下孩子数对10分位数上女性农民工的回归系数为-0.0144,说明6岁以下孩子数每增加1个,就业质量分布底端的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将下降0.0144,但其对各分位数上男性农民工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负担不会影响男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这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的结果。以亲友为主的职业流动渠道,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不明显,这与老乡和亲友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较强有关。地区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就业于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高于中西部地区;除90分位数外,年份虚拟变量对男性、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2013年中低分位数上的农民工就业质量较2008年有所提高,但高分位数上就业质量的变化不明显。
(三)职业流动是否扩大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
FFL分解结果显示(表4和图1),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在75分位数上达到峰值,说明中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较大。从造成性别差异的因素来看,在10和25分位数上,特征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56.69%和54.17%,说明在中低分位数上,特征效应(可解释部分)是造成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就业质量差异的主因,但其贡献率随分位数的提高而下降;而在50~90分位数上,系数效应的贡献率均在50%以上,说明在中高分位数上,系数效应是造成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其贡献率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加。说明随着就业质量的提高,女性农民工所遭受的性别歧视程度增强,高端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农民工的歧视最大(见图2)。
从分解结果来看,在各分位数上(75分位数除外),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贡献率(特征效应+系数效应/总差异)均为正值,说明职业流动扩大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其中90分位数上职业流动的贡献率最高,表明职业流动对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扩大效应最为明显。从各自变量来看,在10和25分位数上,职业流动周期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28.77%和51.42%,高于个体私营企业到非私营企业、行业内流动的贡献率;而在50和75分位数上,行业内流动的贡献率分别为18.87%和58.73%,高于其他两个变量;而在90分位数上,变换工作频率的贡献率最高,行业内流动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其缩小了该分位数上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距。以上表明,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对不同分位数上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影响存在差异。
工作经验是特征效应的重要构成,尤其是在50及以下的分位数上,其在10、25和50分位数的特征效应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9.33%、82.77%和85.12%,表明中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工作经验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这可能与该层次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其抚育孩子和照料老人的机会成本较低,更容易因家庭生产而离开劳动力市场有关。加之特征效应是中低分位数上性别差异的重要构成,因而可以说,女性农民工相对较少的工作经验是造成中低分位数上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健康状况是农民工系数效应的重要构成,尤其是在75分位数上,其在系数效应中占比248.9%,说明中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女性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其回报率均低于男性,扩大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因此,在中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以健康为主要构成的系数效应(性别歧视)扩大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

表4 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RIF分解结果

图1 就业质量性别差异变动趋势

图2 特征效应与系数效应的变动趁势
从其他变量看,以6岁以下孩子数为代表的家庭照料负担也是扩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于中低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而言,在10分位数和25分位数上,其对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7.53%和23.58%,这与该群体家庭生产的机会成本较低有关。此外,年份虚拟变量在25和50分位数上的贡献率为正值,说明与2008年相比,2013年中低分位数上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有所扩大,而在其他分位数上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2013年中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有所缩小。
三、结论
以上研究表明,对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样本,职业流动促进了其就业质量的提高;但职业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大,因而导致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而扩大;同时,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及其对性别差异的扩大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从其作用机理来看,在50以下的分位数水平上,以工作经验为主要构成的特征效应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要因素,而在75和90分位数上,系数效应(性别歧视)造成了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不断扩大。
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是职业流动、以工作经验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和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职业流动起到了媒介作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以及女性在家庭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其承担了较多的家庭责任,她们倾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幼儿抚养、子女教育、老人照料等家务活动中,因而女性更容易因家庭生产而中断工作,这一方面导致职业流动过程中其累积的工作经验较男性少,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家庭和雇主对其进行教育、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使女性农民工陷入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少——就业质量低——家务负担多——人力资本投资少”的恶性循环。此外,传统性别观念赋予男性“以事业为重”、女性“以家庭为重”的社会角色,加上劳动力市场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对女性职业发展社会支持的缺乏,弱化了女性对职业发展的偏好,可能导致其在事业上更偏好稳定等[15]。同时,男性与女性与生俱来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如CHIP2008问卷中有关农民工心理特征和心理健康的测度数据表明①,从个体的精力集中度到困难处理方式再到幸福感,女性农民工的得分均低于男性,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计算结果显示,男性心理素质综合得分为0.029,女性仅为-0.096,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重要原因。
因而,提高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两性职业协调发展,以大力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必须打破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少——就业质量低”间的恶性循环。基于此,应清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消除市场分割,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尤其是低收入女性的教育投入,降低其接受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其受教育程度;结合女性特点,加强农村女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女性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观念,倡导两性平等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制定关于促进两性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女性农民工的保护,禁止聘用过程的性别歧视,为女性职业发展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大力发展保育事业、养老事业和家庭服务事业,将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鼓励实行弹性就业制度,尤其是对处于孕哺期的女性农民工,帮助她们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以促进我国“以人为本”城镇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① 由于2013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心理健康的测度指标,因而本文未引入心理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