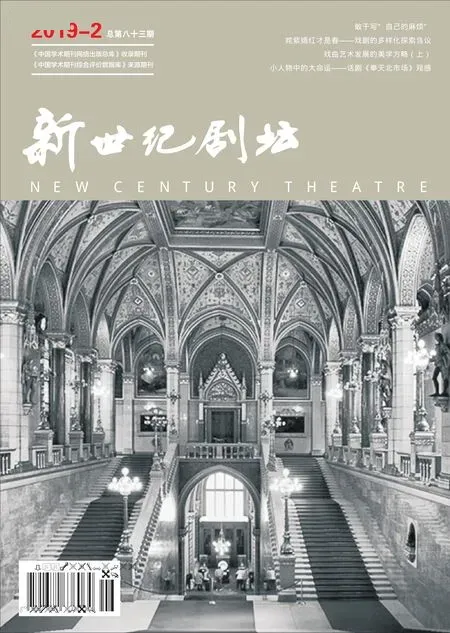从小说到戏剧
——王安忆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改编研究
王雨晴
文学名著被搬上戏剧舞台并不罕见,因为名著可为剧本的文学性提供先天保障,名著的影响力更为戏剧增添商业价值。“张爱玲热”现象的出现表明其作品的文学性与影响力在影、视、剧等领域的影响。张爱玲小说改编为话剧的作品有1987年陈冠中和2005年毛俊辉分别导演的《倾城之恋》、2004年林奕华执导的《半生缘》、2007年田沁鑫导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书影
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张爱玲后又一人”的王安忆将张爱玲最负盛名的小说《金锁记》改编为话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安忆说,“戏剧是文学的宝塔尖,一个作家没写过戏剧总是不完整的”,因此她开始了戏剧的初次尝试。“《金锁记》是我最初想要改编的作品,因为我很喜欢戏,很想找一个对象来做一个戏,就像文本上的游戏一样的。”[1]王安忆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好的一部小说,并且从戏剧性、体量来讲,都非常适合改编成多幕剧,这是她选择《金锁记》的原因。王安忆虽把这称为游戏,但三次易稿可见她对作品的珍视。2004年,由黄蜀芹执导,话剧《金锁记》于上海话剧中心首演,演出后却反响平平。2009年,导演许鞍华——曾经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半生缘》搬上大银幕的电影导演与香港焦媛实验剧团合作,将台词改为粤语,增加诗意和陌生化,同时运用电影手法,将声光电技术灵活运用到舞台中,再次将王安忆改编的话剧《金锁记》呈现给观众。王安忆评价道:“黄蜀芹的版本写实,许鞍华的版本则更写意。”
从小说到话剧的一大跨越就是对“舞台”的把握,但本文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剧本的改编,即从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为王安忆的《金锁记》的过程。王安忆通过剪裁增补情节和外化人物性格,使《金锁记》的基调从“苍凉”变为“明亮”,在背靠原著与忠于自我间找到平衡。任何作品皆有得失两面,从中发掘改编创作的启示才是意义所在。
一、创作观之反转:从“苍凉”的张爱玲到“明亮”的王安忆
身处“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的时代下的张爱玲,早在18岁写作的散文《天才梦》里就以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同时也预示出她作品的底色。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张爱玲是用冷眼看人世的悲观主义者,她的性格尖锐而“刻薄”,以至于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对立起来,从而走向虚无。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多是世俗的人用世俗的眼光过着世俗的人生,但张爱玲本人却是脱俗的,她用华靡的文章写出的是人生素朴的底子。
《金锁记》被傅雷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更是将其赞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由时年23岁的张爱玲在1943年创作于上海。在不足四万字的中篇体量里,张爱玲将三十年的故事写出三生三世之感,讲述了主人公曹七巧嫁给残疾的落魄豪门子弟,在金钱枷锁与情欲焚烧之中,逐渐异化为扭曲变态的恶魔的女性悲剧。曹七巧的悲剧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戕害,在更深层次上又暴露出金钱欲望将人性异化的残酷。话剧却将色调由“苍凉”变为“明亮”,王安忆说,“到最后,整个演出和《金锁记》原来的气质完全不一样,它变得非常响亮,很热烈。”[3]话剧《金锁记》采用开放式结构,共两幕各三场戏,按照时间顺序上演七巧个人的悲剧及其一手造成的长安的悲剧。王安忆改编《金锁记》时年过半百,与张爱玲23岁时的爱憎分明不同,王安忆有着中年人的温厚宽容。王安忆不尖锐也不“刻薄”,她是温柔且慈悲的。王安忆说自己喜欢“朗朗乾坤的东西”,因此她把张爱玲冷冽森然的笔调弱化,增添了些许光亮。
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王德威教授,他在看过王安忆的《长恨歌》后发表文章《张爱玲后又一人》,从此王安忆便和张爱玲“牵扯上”了。但王安忆本人对此总是断然否定。“我有很多否定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和她的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4]张爱玲对她的时代是绝望的,“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5]而作为“共和国儿女”的王安忆并不会认为时代有多么坏,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比较容易妥协,比较乐观主义或犬儒主义,“我会顺应我所在的环境,我比张爱玲好商量。”[6]王安忆绝非张爱玲的传人。王安忆将小说比作“心灵世界”,着眼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将日常生活作为起点,意在挖掘人生意义,直奔人类的心灵深处,这范围要比女性、上海、市俗更大,使其作品的内涵丰富广阔。而张爱玲的世界很小,小到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世俗生活,经过对男男女女爱恨情仇剖析,走向荒谬无奈的虚无。她能把人性写得无比深刻,只有悲剧才能承担起人性刻骨的苍凉。张爱玲的世界观注定了作品的“苍凉”与虚无,王安忆的作品则充满“明亮”和饱满的生命气息。

话剧《金锁记》剧照
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复杂多样,时代背景、成长经历、性格特质、理想信念等等不胜枚举。因此,二人对《金锁记》的看法亦有所不同。“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7]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极端病态的,正因此才极端觉悟,这便透出极端苍凉之感,得以在人心中留下更深长的回味。而王安忆却从曹七巧的报复中看出了悲壮,“我觉得曹七巧的报复在《金锁记》中非常悲壮”[8]。悲壮带给人一种刺激性和冲击力,能强烈的抨击人心,终究是灼热的,而苍凉则是一种令人愈想愈瑟瑟发抖的挥之不去的余味。冷眼看世界的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也是苍凉的,而热眼看世界的王安忆却为《金锁记》增添一抹明亮之色。冷与热、绝望与希望、苍凉与明亮,这既是二人的不同,也是小说与话剧的不同。
二、剧本之再造:从内敛的小说到外化的话剧
王安忆把这次改编看作是练习“写作‘强烈’”,认为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藏着的推到表面”。的确,张爱玲的意识流手法为小说布下谜团,故事的情节和线索、人物的情感思想和语言、结构和风格皆是内敛含蓄的。王安忆承担起解谜的任务,通过增减情节线索、暴露人物性格、强化戏剧冲突的改编,将张爱玲隐藏起来的情绪外化,把谜底呈现给观众。
(一)增删情节,线索简明
王安忆在故事线索上做了几个加减法。首先制造出一个非常外化的情节——姜季泽盗取宣德炉被曹七巧识破,七巧出于对季泽的感情选择隐瞒,这里二人的感情暧昧模糊,当季泽在分家产时将此事栽赃给七巧,七巧才惊觉季泽的虚情假意。这个情节把七巧与季泽的感情由暧昧转为荒谬,背叛感破灭了七巧曾经对季泽怀抱的幻想,季泽虚伪自私的一面暴露无疑。“等于说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了一个激化的处理。”[9]于是小说中暧昧的暗示在话剧里浮出水面。
其次是一个减法,王安忆把长白的整条线索减去。原著中长白这条线刻画出七巧一步一步走向疯狂变态。七巧对儿子长白的感情有种恐怖的亵渎,为留住身边唯一的男人,她变着法哄长白抽鸦片,彻夜同床逼儿子说出与儿媳的私事,再大肆添油加醋到处宣扬。在她日益恶劣残忍的折磨下,最终逼死两任儿媳。据王安忆说,删去这条线一是出于空间和时间的考虑,很难安排那么多线。于是话剧只留七巧和季泽、七巧和长安两条主线,这使情节更加集中。二是出于王安忆个人的考虑,“我个人和张爱玲有些地方不太相和,可能我是共和国的人了,喜欢那种朗朗乾坤的东西,觉不觉得她有时候挺森然,挺暧昧的。”[10]王安忆同情曹七巧的命运,所以不愿用“这么阴毒的表现”。因此,删去长白的戏使话剧剪去过多线索的枝蔓,从而保证主线突出、冲突明确。

话剧《金锁记》剧照
三是把长安的戏加长。话剧把第二幕的故事集中到长安身上,围绕长安与童世舫从相识相恋到最终被拆散展开。王安忆把小说简略的一句“他们继续来往了一些时”扩为一场戏,改变小说中二人“很少说话”,增加对白,使长安与童世舫的恋爱过程完整丰满,从而加强观众对七巧恶言恶语拆散二人的同情和愤怒,以及强化七巧残忍变态的人物形象。原著则围绕七巧对长安的影响展开,从长安十三四岁写起,以七巧灌输长安提防男人、强迫长安裹脚、因一条褥单导致长安退学、耽搁长安的婚事、唆使长安抽鸦片等,勾勒出曹七巧的恶母形象。话剧把长安的成长经历分散在回忆中,在戏剧情节高度集中的前提下,做到与原著的细节保持一致,保证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可以说,补充长安的情节使话剧比小说更完整详细。
此外,王安忆还填补了几处细节。安排代替新郎的姜季泽把七巧背上台,“卖弄着健康和力气”的姜季泽令七巧“满意”,这与七巧揭开盖头后的“不解而害怕”形成对比,既埋下七巧对丈夫二爷的怨,也种下七巧对三爷季泽的情。另外,王安忆根据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把分家后七巧和长安的家安排在一个小学校的楼上,因此话剧中出现三处读书声,王安忆表示希望用小孩子的读书声冲淡一点戏剧冲突的紧张感。可以看出王安忆对细节的重视。
(二)暴露性格,内心外化
曹七巧是《金锁记》的灵魂人物。张爱玲把曹七巧视为她笔下唯一“彻底的人”。王安忆将曹七巧的“彻底性”归因于“原始性”,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张爱玲所有的小说人物里,曹七巧是一个最原始的人”。这一原始性通过情欲表现出来,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小说》中指出“情欲”在《金锁记》的重要作用。曹七巧和张爱玲笔下的其它人物一样经历社会的教化,但她的独特之处在于未经教化磨灭的情欲的原始力量。王安忆抓住了这一点,极力展现七巧对季泽的追求,把小说中似有若无、忽远忽近的暧昧,变为步步紧逼、夸张露骨的求爱。小说里七巧对季泽的感情是因对死人一般的丈夫的恨之后抓住的一根稻草,话剧则因季泽背七巧入府这一细节的补充,使七巧对季泽的一见钟情先于对丈夫的恨意,这一点可以从七巧对季泽说出“谁让你背我的呢?你背我进这姜家的门,我就是你的人了!”看出。于是七巧的情欲从深处被挖掘到舞台上。
姜季泽是七巧情欲的寄托,却将这情欲无情熄灭。小说里季泽虽曾动过心,但头脑始终清醒,“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季泽对七巧的撩拨和调情更多出于一个花花公子的惯性,轻佻、虚伪但不至于可恨。王安忆则铺设宣德炉一案暴露出季泽的无赖,在季泽虚情假意哄七巧卖田时,彻底断绝七巧的一丝痴望。王安忆把小说中七巧的心中所想变成台词,这是话剧的特点,这一改变虽对七巧百转千回的细腻心思有所削弱,却增强了戏剧冲突的张力。
长安是七巧情欲幻灭后复仇的对象。母亲残酷的压迫令长安将牺牲视作习惯,甚至自我催眠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更残忍的是长安耳濡目染七巧的行事作派,“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王安忆终究比张爱玲仁慈,她保留了长安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光明的向往。王安忆写了一场只有长安和童世舫两个人的戏,这是她在这部话剧里打开的一丝光亮。两个年轻人内心纠结、挣扎、矛盾,最后终于坚定相拥,其中不乏令人松一口气的幽默。比起小说里童世舫内心将求婚看作他割舍自由送上的一份厚礼,话剧里二人的台词将内心剖白,使二人的感情更为真诚纯粹。
(三)高潮迭起,风格改变
张爱玲曾说“人生总是在走向下坡路”,小说的基调仿佛如出一辙。曹七巧逐渐沦为金钱奴隶、丧失人性、湮灭灵魂的一生,留下苍凉的余烬。小说首句“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与尾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寥寥几笔“月”的意象,勾勒出苍凉的色调,可嗅出一丝《红楼梦》的余韵。并非真刀真枪明目张胆的冲突碰撞,而是绵里藏针笑里藏刀的隐隐作痛。合上小说,这悲剧令人唏嘘,却唯有苦涩无奈。反观话剧落下帷幕之时则令人心潮澎拜,胸中似有愤激之怒火熊熊燃烧。正如王安忆所说,《金锁记》变得非常响亮与热烈。一方面,戏剧冲突尖锐,几乎每场戏都有高潮,令人时刻保持紧张感;另一方面,以七巧和长安双双精神失常为结尾,使矛盾冲突到达顶点,制造出震撼感和冲击力。此外,受演员表演、舞台设置、服装道具等多种因素影响,话剧的最终呈现经过各环节的诠释难免与原作偏离。王安忆曾说自己出于私心希望能给整个故事增添一抹亮色,因此她的《金锁记》是透着一丝光亮的。小说虽给人暗无天日的绝望,仿佛在地狱深处被黑暗吞噬,但话剧却尚存一丝希望,于黑暗中投射一束微弱但明亮的光。于是,小说敛笔营造的苍凉无奈的氛围,被王安忆袒露外化的改编所冲淡,在绝对的冷色中掺入暖调,调和出一种微亮渐暖的风格。
三、改编《金锁记》得失与启示:背靠原著,忠于自我
在某些方面,改编比原创的难度更大,且戏剧更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小说家王安忆初涉戏剧的“游戏”结果是得失兼具的。
首先,对于体裁的改编是成功的。在王安忆看来,从小说到戏剧的挑战在于,“写小说是在一个单纯的时间流程里面写,……我们可以自由地调度,调度到任何空间、任何时间,在文字这个境界里面它是很自由的。戏剧却没有这样的自由。第一,时间和空间都是受制约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你所有的故事和情节以及人物都只能用一个方式来交代,就是对话。”[11]这刚好体现出体裁转换上的成功。一方面,小说可以借用艺术手段营造出细节与复杂的想象空间,但戏剧必须凭借舞台上实实在在的演出打动观众。特别是张爱玲运用蒙太奇、象征、心理分析等多种艺术手法,为《金锁记》开拓无限想象空间,这为改编增加了难度。王安忆化虚为实,按照时间线索重新编排时序,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剪裁加工,使话剧情节线索明晰、戏剧冲突尖锐、人物形象饱满。另一方面,小说与戏剧的差异在于,小说重叙述,戏剧重展现。小说文本是叙述者的话语,而戏剧叙事的主要方式是台词,即故事中人物的话语。王安忆将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改为台词,基本做到合情合理、不过分突兀。
其次,对于人物变化层次的展现是失败的。作为张爱玲笔下最复杂的人物,曹七巧这一角色的舞台塑造是话剧呈现的最大难关。张爱玲的语言技巧是耐人寻味的关键,在看似无心的白描语言中,曹七巧一步一步走向变态疯狂的深渊,小说的悲剧性层层深入,令人不禁颤栗。曹七巧“因极端病态而极端觉悟”,其中体现着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即由阴骘到跋扈、由控制到宣泄、由抱怨到绝望。小说里的曹七巧的变化既可恨又可怜,话剧则无法令人对其心生怜悯。原因在于王安忆忽略了变化过程的层次,使结尾处高潮成为悲剧的最强音。另外,话剧中饰演曹七巧的演员只表现出一气呵成的张扬与刻薄,原因既有演员表演的不足,也有台词设计的欠缺。
除此之外,对于戏剧节奏的把握有得有失。小说阅读和观看舞台演出在接受方式上的差异决定节奏的重要性,读者可随意控制阅读速度、顺序、断续等,观众则只能一气呵成地被舞台引导,可见恰如其分的节奏调度是戏剧成功的一大关键。张爱玲的叙事节奏得益于暗示、蒙太奇、心理分析等技法的运用,详略得当又韵味无穷。然而“月亮”“镜子”“酸梅汤”等意象暗示出的想象空间,镜中人的转换等电影化描写手法,在话剧舞台上是很难实现的。对于时空变换的展现,王安忆通过服饰变化试图反映出家道中落和时代变迁,设置阳台上的佣人小双,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交代情节变化,既方便了幕与幕之间的分隔与补充交代细节,又淡化了紧张感,使节奏张弛有度。然而,对于长安与童世舫的戏份的增添,在互表心意的过程中台词略显重复拖沓,使话剧节奏由紧张突入缓和,虽有“让观众松一口气”的考虑,但从话剧整体节奏来看却是弊大于利的。
综上所述,话剧的二度创作是比较成功的。改编之大忌是完全照搬原著,如果人们对小说和话剧产生完全一致的感受,便会失去二度创作的意义。再创作不能失去自我,这是王安忆对改编的态度。王安忆的改编既抓住原著精髓,又融入个人阐释。从浅层批判金钱与情欲对灵魂的扭曲,到深层揭秘女性人格悲剧,最后延伸到人类生存困境,这是不变的主题内核。变化在于,王安忆基于个人理解和他人回忆,增删故事情节,暴露人物内心,改换风格色调,使话剧体现出王安忆的个人创作特质,并非将小说原原本本地搬上舞台,从而为话剧《金锁记》注入新的生命力。
结 语
文学与戏剧的双向运动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戏剧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普遍存在脱离原著精神、缺乏内涵创新、迎合大众牺牲文学性等缺失。王安忆改编《金锁记》的过程为小说的舞台移植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改编作品应在背靠原著的基础上,注入改编者的灵魂,并扩大作品的阐释空间。同时,小说改编为戏剧要注意适应性,一是如何能将小说特有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戏剧中,二是如何选择适合改编的作品。王安忆曾说,“当我们在诠释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好在张爱玲的东西有那么多的空间,够我们走得很远。”[12]好的作品,一定是经得起反复咀嚼的。
注释
[1][3][9][10][12]王安忆.改编《金锁记》[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60-63
[2][5][7]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1-113
[4][6][8][11]王安忆.张爱玲之于我[J].书城,2010(02):5-13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