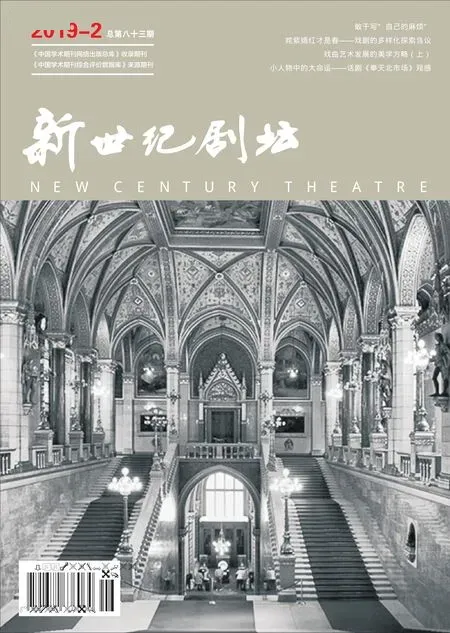《老枪》:一个人的战争
李保平
一场世纪大战,一座艺术题材的宝库。今天,二战题材影片无疑已成为战争片一个单独的子类。在这个概念下涌现出像《卡萨布兰卡》《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维雷将军》《乱世忠魂》《雁南飞》《伊万的童年》《遥远的桥》《桂河大桥》《巴顿将军》《缅甸的竖琴》《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拯救大兵瑞恩》等一大批优秀影片。
法国影片《老枪》与描写群体性战争的二战片相比,可称得上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热爱家庭的医生丈夫,为了给妻子和女儿复仇,只身消灭了一群溃败中占领乡下古堡的德国鬼子。
本片题材内容的第一个特点是,把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缩小到一个家庭内部,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场战争;本片题材内容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一场巨大的家庭变故,放在战争即将结束,曙光初露的尾声部分,它的悲剧冲击力尤为强烈。
这一切选择,显出了导演罗伯特·安利可别出心裁的构思。
家庭价值与个体清算
从“一个人的战争”的故事设计中,观众可以看到法国人的价值观和其独特的行为方式。他的爱与恨,都是通过个人化的感受体现出来。强盗动了桌上的其他奶酪,他也许还能忍受,但是一旦动了他的奶酪,他的愤怒就不可遏制。男主角胥利安是一个老实厚道的法国医生,热爱家庭,当幸福美满的家庭被德军摧毁后,他决定采取个人的方式复仇。
本片在家庭价值与个体清算之间的对照中展开,家庭价值展现为人物的心理戏,它通过闪回进行;个体清算展现为人物的动作戏,它通过现实进行。家庭价值提供了人物行动的动力,个体清算反衬出人物对家庭价值的维护与热爱。
冷静的战斗与温馨的家庭追忆交织,本片从人性与反人性较量的角度,讲述了1944年德国纳粹战败的前夜,凶残地杀害了一个法国医生的妻子和女儿,导致丈夫奋起复仇的故事。它站在捍卫家庭价值的立场,控诉了法西斯主义丧心病狂的罪恶,表达了忠诚的丈夫对逝去家人无限深情的眷恋。
现实与过去交叉对比体现在丈夫在复仇的过程中触景生情,回想起昔日一家人幸福的时光,使他的现实复仇行动,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张力。回忆的温馨气氛越浓烈,冷酷的现实对家庭价值的破坏力越令人心碎,激发起观众对复仇者的深切同情。
景深长镜头的意蕴
一家人骑车郊游的场景,构成了首尾相照的主题画面,隽永而独特的片头和片尾采用同一个意境优美的景深长镜头:绿意葱茏的乡间公路,两侧是高大的树木,伴随着柔和、缓慢的钢琴音调,主题音乐轻声而悠扬地响起,妻子克拉拉和女儿骑着单车从画面下方出现,随后,丈夫胥利安骑车和跳跃的爱犬玛赛尔一起从后面赶上来,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欢乐气氛溢满整个画面。

电影《老枪》剧照
深焦距镜头拍摄的单镜头显示,一家三口处在运动当中,此时此刻的状态被持续拉长,始终停留在一个原点,生动地表达了拍摄主体对一个幸福家庭欢乐时刻的眷顾和挽留,确定了影片维护家庭价值的温暖基调,反衬出战争的损毁力,强化了主题的深意。
这个长镜头经过深焦距镜头的处理,相当于运动型的定格:一个温暖家庭定格在永恒的时刻,仿佛是对充满了爱的家庭的礼赞。这个镜头在段落后期,分别切换为妻子和女儿的近景,最后切换并定格在男主角胥利安的身上,暗示他是这个家庭中感受的主体。
这个景深长镜头出现在片头和片尾,既显现出故事开头完美家庭的喜剧性,又反衬出故事结尾家庭破碎的悲剧性,一样的画面,不同的况味体验。
枪声带出的恐怖
影片第一个场景显现胥利安的家里,妻子克拉拉对着镜子化妆,转过身和床上的爱犬玛赛尔亲热,突然,安详和平的家庭气氛,被窗外一声枪响打破,女儿吓得哭喊着破门而入,扑进母亲克拉拉的怀里。

电影《老枪》剧照
第一个镜头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一开始确立了高调的家庭价值,从明亮欢快的高调骤然转为第二幅画面的蓝色、黑色的低调,从画面的光线亮度对比上,揭示出战争对家庭价值隐形的暴力侵犯。
由于枪声的因素,第二个镜头导入外景,从家庭温馨的内景切到夜幕笼罩的街头,这是一个插入性的环境交代:摇镜头跟随两辆保安队汽车驶过画面,从前景吊在电线杆上的第一具法国人尸体摇到第二个尸体,显示暴力的残酷幅度——不限于单个的个体,而是带有成批性的处决性质。从后面的叙事中,观众会看到——这两辆汽车的出现,不仅制造出一种高压式的恐怖气氛,而且还具有叙事的功能。同时,一队德国巡逻队从右边入画,使这幅环境画面的直观恐怖气氛处于集中的饱和度。
两组运动的物体——汽车和巡逻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入画,也反映出导演对称性的场面调度。
情节驱动力:来自保安队的威胁
影片第二个场景显现胥利安在医院里,枪声同样是这一环境下的串联因素,他站在窗口抽烟。家和医院——这两个环境是他生命中两个重要的支点。
保安队冲进病房,找到了负伤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
“我不问政治,我就知道看病,不把病人留下,我就去找缪勒医生。”胥利安抗议道,“丹迪尔先生,战争还没有结束,你要不是医生的话,早送你去秘密警察那儿枪毙了,”保安队长盯着他,“我注意你好久了,你有家庭——妻子和女儿,为了她们的好,小心点。”
不问政治,表明男主角竭力保持中立的立场,敌人把他看得更清楚,要么是他们的同盟,要么是对手,战争没有中间地带的政治。
实际上,他保持不了中立,当保安队把病人带走时,他还是激烈地反对,搬出了德国军医缪勒的保护牌。
保安队长的反击戳中了医生的软肋,提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来自保安队的威胁促使他下决心把妻女转移到乡下的古堡。由此,敌人的威胁成为影片情节发展的驱动力。
给保安队长配音的杨文元是第一代配音演员,曾在中国早期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为城堡上的守卫配过音。他的音色浑厚、低沉,不属于那种亮度很高的音区,他在配音行当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因其独特的音色,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缪勒军医的存在价值
缪勒军医在片中出现两次,一次是间接出现胥利安的话语里,一次是出现在医院楼梯上。准确说,这个人物实际出现过一次。
楼梯口包含一个语义丰满的场面调度,保安队抬着负伤的抵抗组织成员下楼,缪勒军医率领护士们上楼。
“先让那些受伤的德国军官撤退,”缪勒的画外音。
“是,大夫。”
“现在全线崩溃,我们得赶紧转移,”缪勒说,“见鬼,这些家伙又来了。”
胥利安跟到楼梯上,“别让他们抓人,缪勒。”
“丹迪尔先生,我有125名德国军官要撤退,还不知道往哪儿撤呢,再说,这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你那儿有没有磺胺?”
“没有,一点没有。”
画外传来枪声。
“再过一个两个月,你们就自由了。说不定,你们会有盘尼西林。可是我们……哼。”
胥利安转身回到走廊,助手向他请示,如何处理因为炸火车负重伤的抵抗组织成员,他命令把他转移到地下室。
“他伤重不能动。”
“他伤重不能动,你怎么想的?”胥利安情绪变得格外激动,“再来抓人他就完了,我们也跑不了,你快去办吧。”
让缪勒军医在这里出现一箭双雕:一个是借助他交代战场局势的真实变化,作为尽职的医生,他忙得自顾不暇;二是塑造一个正直的德国人对维希政府走狗们的憎恶,以及对德国民族前途的担忧。而胥利安情绪突然发作,说明保安队的威胁在他的内心发生了作用——这是他即将对家人采取转移行动的情绪预备。
缪勒军医这个角色看似微不足道,台词不过三四句,但这一形象却处于天平的另一端,成为矫正影片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让音色纯正厚重的乔榛为这一角色配音,实为加分之举,巩固了这一正面形象的定位。
影片为什么要有缪勒军医?
复仇是本片的中心情节,整个影片的行动部分都由复仇的火焰构成。维护家庭价值是本片的伦理出发点,它是复仇的强烈动因。然而,影片不想因为复仇情节,陷入无节制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一个个次要人物——德国军医的形象,平衡了战争时期的民族矛盾,换句话说,胥利安与古堡内德国鬼子之间的矛盾,不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矛盾,而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矛盾。保安队的暴戾,意味着这种矛盾在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同样存在。缪勒军医和保安队——这两组人物表意符号,纠正了民族战争影片中常常处理不好的人物结构上的偏差,避免用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人性的深刻主题制约着复仇的动作主题,使本片超越了复仇动作片的格局,回归于健康而理性的人性表达的轨道。
医生的天职:仇恨的另一翼
在人物结构上平衡了以民族矛盾区分正派与反派之后,影片还在胥利安的生命中显明了一种向度,宣告他本性中并没有仇恨的基因。导演特意为他设置了一个段落,他刚给一个按照我们的语法称为汉奸的人做完手术,吩咐助手,如果当晚这个保安队员还不小便,就安排给他导尿,
“你们看着吧,这个保安队再过一个月他准能好,真是一个怪物。”
“等他病好了就该枪毙了,”助手说。
“这有可能。”
“像他这号人哪,你就是枪毙了他,也不亏待他,”弗朗索瓦插了一句。
明知道保安队员罪大恶极,却没有撒手不管,出于医生的天职,胥利安仍要救死扶伤,哪怕他病好了,再去接受法律的制裁。敌人是敌人,病人是病人,当两种身份汇集在一个人身上时,考验着一个医生的操守和人道情怀。201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更好的世界》中塑造了一名医生,他救活了三名被恶霸开膛破肚的孕妇。一天,这名恶霸腿部负伤,作为医生,他没有将其拒之门外,可是当这个恶霸嘲笑被别的恶霸开膛破肚、不治身亡的妇女时,他把这名恶霸拖出病房,看着愤怒的群众围上来把他打死。前一个行为,他坚守了医生的天职,后一个行为,他站在了个人的道义立场。
发生在胥利安身上的这个段落,在本片中同样具有矫正的意义,作为一名医生,他救治了一个明天将要被公审的敌人;作为一个丈夫,他没有放过一个苟延残喘的禽兽,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人性与正义并行不悖,他的复仇不是出于本性的恶欲,而是对罪行的公正审判。审判彰显着上帝的公义。
着墨不多而细节深刻的母亲形象
胥利安的母亲在片中虽着墨不多,但言为心声——她的话语所传达的浓浓的爱意,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母亲印象。胥利安准备把全家都动员到乡下,可母亲以年纪大为由坚持留下。为刻画这位老母亲的性格,影片专门设计了一场母子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是我所看过的最独特的表达母子之爱的对话。我想,它一定来自主创者对生活真实的积累和观察。儿子看书,母亲安静地守候在他身旁,一边拆着披巾——
母亲:“克拉拉不在,你冷清吗?”
胥利安:“你留下是为了我。”
母亲:“知道吗?我爱你爸爸,爱了多少年——30年。每当给你开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他也爱看书,奇怪——你爸爸是个小个儿,怎么生出你这么大个子?”
这段台词表演把一位母亲细致的体贴和对儿子执著的爱的羞涩感,表达得格外动情,尤其是对这种爱的描述具有触动人心的历史感,这种从丈夫过渡到儿子的爱的延续,融合了深厚的母爱,无法定义却暖人肺腑。当老配音演员赵慎之说到“每当给你开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时,那种浓稠的化解不开的深情厚意,披上了梦幻迷离的语调,将一个岁月不能消磨的法国式的浪漫情怀呈现在观众眼前。赵慎之在为不同民族、不同性格的老年妇女角色配音方面真是首屈一指!
从道具的角度,老枪、镜子、古堡、火焰喷射器在本片中具有鲜明的表意符号特征。
复仇的工具——“老枪”的选择,代表独特而深远的家族传统。影片在胥利安打开子弹盒子的时刻,插入一段意识流的闪回:父亲端起猎枪向奔跑的野猪射击,和童年的胥利安一起走到野猪的尸体前,展示猎枪的威力:“你瞧——胥利安,这才叫双筒猎枪呢。”具有沧桑而华丽音色的第一代配音演员富润生在片中只有这一句台词。摒弃常规武器,而单单选择家族传承的猎枪,表明了男主角向德寇复仇的性质以及它的家族涵义。

电影《老枪》剧照
镜子在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作为古堡内一道隐形的屏障和主要的情节道具,既是男女主角幸福婚姻生活的见证,又是主角窥视敌人动静的窗口——同时把内外两个场景连接起来。胥利安靠在教堂墙壁上,触景生情地回忆起礼拜天坐在信众中间的克拉拉向他回眸的一刻——“到我老了恐怕你看也不看我一眼了”。声音闪回把他带回到过去夫妻俩在古堡镜子前面的对话:
胥利安:“你怎么这么说——胡说,我不会的。”
克拉拉:“你呀——隔着墙偷看我不算。”
胥利安(从镜子后面走出来):“嘿,你真敢胡说,亏你说得出口。为了看你睡觉我天天不睡觉。”
克拉拉:“撒谎。”
胥利安:“怎么撒谎?”
克拉拉:“有时候也睡。”
胥利安:“对,有时候也睡。”
克拉拉:“那么……”
胥利安:“原谅我吧。”
克拉拉:“我要不原谅呢?哈……”
夫妻之间还能像恋爱时期一样进行亲昵的调情,证明两个人婚姻生活如胶似漆般地美满,弥足珍贵。丈夫在妻子睡觉时舍不得睡去,当然,他承认——他有时候也会睡,但重要的是,他不等她说完,马上请求她的原谅。为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配音的毕克紧贴人物的内心节奏,表达一个丈夫对于妻子的宠爱。这段对话传达的是除当事人之外谁都无法体会的甜蜜感受。
这是丁建华为著名影星罗密·施耐德第一次配音,1988年她在译制片《茜茜公主》中再次让施耐德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本片中,丁建华持续而爽朗的笑声,不仅表现出女主角克拉拉富于感染力的性格魅力,而且从侧面反衬出男主角痛失亲人后的心碎。
胥利安透过镜子,看见德寇搬出他家的私人放映机,白桌布上投放出妻子克拉拉迷人的微笑——画面闪回,切到舞会场景:他坐在下面,看着妻子克拉拉与昔日英俊的情人一块跳舞,一个女人走过来,问他怎么老不跳?
他回答:“我不会跳舞。”
“真遗憾。”
“我也没办法。”
“我们玩别的?”
“我不会玩。”
——这是一个忠贞不贰的丈夫。
他回到楼上,女儿看出父母感情之间出现了问题,他问女儿为什么不高兴?
女儿:“妈妈干嘛不要你了?”
胥利安:“啊,这个说来话长啦,因为她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很漂亮,她爱上了他就跟他一起走啦——就这样。这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妈妈快活,我也快活,因为我有你。你妈妈——你爱不爱她?”
女儿:“好得像姐妹一样。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影片不仅表现夫妻间的爱情,也表现两个人的情感在时间中的微妙变化——表现性格可爱的妻子一时的感情迷失,和一个丈夫出于爱的本质而体现出的包容。“我们都是你的女儿”——在女儿旁观的视角里,显现出男主角在家庭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和宽阔的胸襟。
在另一段闪回中,胥利安从古堡镜子前面转过身来,对好友弗朗索瓦抱怨道:
“克拉拉怎么搞的?总得先讲一下吧,真是。”
“也许她不愿意夜里开车,天亮会到的。”
“现在已经天亮了,已经天亮了呀,天亮了……”
“瞧你急的,现在才五点半,天还没亮呢,你别抠字眼了。”
“说的也对,嘿,弗朗索瓦。”
“什么?”
“她是个活跃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你知道,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匆忙的,我怕她有天会离开我。俗话说,好景不长啊。”
“哦,不,你是太爱她了。”
心急是因为爱,甚至跑到客观时间的前面;担心也是因为爱,怕性格活跃的妻子和这良辰美景一闪即逝。毕克把握人物的心理分寸,先是一时着急的抱怨,继而是对自己不讲道理的自嘲,语气带着轻微的调侃,声调逐渐小了下去,最后转为一种深沉,从情绪的转折上,表达出痴情的丈夫对一位可爱的妻子的深深隐忧。
古堡具有家庭的象征意义。双方战斗在胥利安购置的乡间古堡中展开,意味着复仇者在自己的家里与非法的入侵者进行搏斗。请王者在茅屋前止步,更别提豺狼来了有猎枪。家被侵占了,主人的反击显示了不可侵犯的正当性。
影片采用对位的形式,在最后的复仇行动中,他使用了德寇的火焰喷射器。敌人用火焰喷射器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子,他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最后一个企图自杀的敌人,体现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公义的律法原则。
闪回叙述与动作叙述的相互交叉
影片前三分之一部分是常规的现实叙述,完全采用客观情节。从胥利安开车回村,目睹妻女在古堡中被杀的现场为分界,回忆式的主观情节成为情节的主导,心理现实和行为现实,闪回叙述与动作叙述交叉进行。
第一段闪回叙述是想象式的闪回叙述,丈夫在想象中还原妻子和女儿被德寇杀害的全过程,开始时的慢动作显现出人物想象的主观色彩。与其它回忆性的闪回叙述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的闪回叙述形式。
从此刻开始,在结构上,影片剪辑采用了两组闪回叙述和两组行动叙述——双线交叉的叙事。第一组闪回叙述,在复仇的准备过程中,男主角回忆夫妻在镜子前面的调情、克拉拉的忧伤时刻、她的情感出轨,夫妻俩在女儿获奖典礼上迟到、在杀猪节上妻子欢乐的场面。
克拉拉的忧伤时刻在男主角擦枪的过程中插入:妻子在古堡前点燃营火,亲朋好友一起喝酒跳舞,胥利安在地窖里找到妻子,发现她一个人躲在下面哭:
胥利安:“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克拉拉:“没有,怎么说呢?”
胥利安:“你不愿意说?是谁得罪你啦?”
克拉拉:“不不,不,不不。”
胥利安:“那么……”
克拉拉:“怎么说呢?我突然心里难过。”
胥利安:“干嘛要难过,啊?”
克拉拉:“不知道,我怕。”
胥利安:“你怕什么?”
克拉拉:“不知道。就……就……就这样不高兴了。现在过去,对,过去了。也许是刚才喝多了点,我,有点兴奋了,会这样吗?嗯?”
胥利安:“对,也许会。”
克拉拉:“懂吗?”
影片在这里似乎想传达克拉拉突然而至的忧伤是一种超验的感觉,她对后来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死亡事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预感,这是其一。其二,她除了性格热烈外向,富于感染力外,还是一个生性敏感的女孩,突出她小动物般惹人怜爱的一面。这双重的性情禀赋,使观众对男主角复仇的预期充满了理解。
这段台词分别表现出丈夫的宽厚和妻子的感性。在配音角色的搭配上,毕克和丁建华的“声音造型”符合这对老配少夫妻的组合,一个声音充满慈父般的厚道、低沉、宽容,一个声音洋溢着欢快、热情、爽朗的律动。在这部影片里,毕克和丁建华都表现出各自的声音可塑性,毕克的顿音和男主角忠厚的性格相匹配,丁建华那种萌萌的充满浪漫梦幻般飘逸的音色,随着人物的规定而调整,变成一种外向的勇敢与奔放热烈。
杀猪节上,克拉拉顽皮地挥舞着砍刀,整组画面充斥着明亮的高调,没有其他对话和音响,只有欢快的手风琴作为主旋律贯穿其中。
行动前闪回叙述结束,转入一系列的行动叙述:井口射杀打水的士兵、德军吉普车跌下旱桥、德寇在古堡内展开追捕、胥利安和跟踪他的德寇进行搏斗、谢绝游击队的劝说、射击悬崖上的德寇。射杀前,插入克拉拉的一个声音闪回:“胥利安,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要生个儿子就叫他戴维特吧。”然后射击。
行动后闪回叙述包括两个人初次见面、做爱和求婚。然后,进入下一组行动叙述:党卫军队长打死开小差的士兵、水淹两名德国鬼子、发现火焰喷射器、游击队搭建旱桥、火焰喷射器烧死企图自杀的党卫军队长。
两组闪回叙述,两组行动叙述,心理戏与动作戏,交叉推进。主观情节的心理戏构成这部影片的核心——它展示了生活之魅。日常生活的快乐体验,成为“一个人的战争“的勇气来源。这些萦绕在男主角头脑中的碎片式的记忆都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因为战争和灾难将这些日常的记忆激活放大,变成了个人性的永久丰碑。
失语的恍惚勾回主题画面
一切结束了。
镜头从燃烧的古堡拉开,一辆汽车划过画面从桥上驶过。车内,好友弗朗索瓦扶着方向盘,旁边坐着男主角胥利安。
胥利安:“那狗怎么样?玛赛尔,那玛赛尔。”
弗朗索瓦:“胥利安……”
胥利安:“啊,克拉拉把它带走啦,你来吃饭吗?”
(车子在路边停下)
胥利安:“你怎么啦?”
弗朗索瓦:“你要愿意,我在医院里找个人替我,我来陪你几天吧……”
胥利安:“那太好啦!克拉拉最欢迎你来啦!”
弗朗索瓦:“胥利安……”
胥利安:“怎么?”
弗朗索瓦:这个……
胥利安:“怎么啦?我?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男主角自问自答的失语,表明他的精神处于恍惚,他还以为克拉拉生动地活着,生活照常进行,当好友表示要陪他几天时,他还深陷在意识的误区里,直到他看见好友神色难过的样子,才似有所悟,发现自己出了问题。
毕克的声音把握着情绪变化的节奏,忽然高兴,忽然抑郁,带出一种抑制的创伤,精准地传达出人物精神状态的迟钝和恍惚。主演菲利普·诺瓦雷脸上的表情微微漾动,镜片下面眼角渐渐潮湿,接着眼神骤然发光,仿佛过去幸福的时光正从远处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