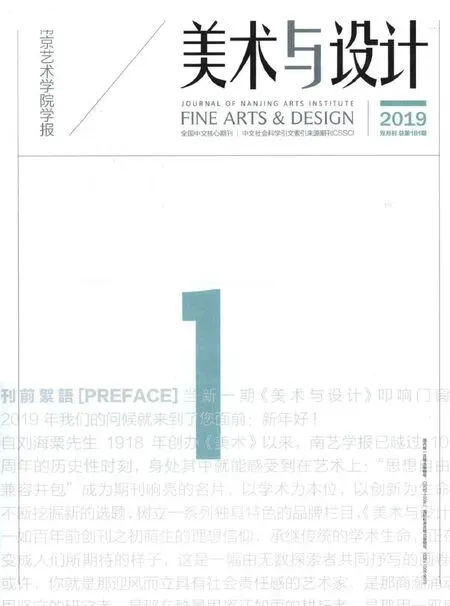西画东渐的历史先声
——油画传入中国本土的三个路径
曾希圣(贵州大学 艺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油画传入我国的历史起点,一般认为始于明代中叶。但真正作为一个美术学科,被有意识地主动引进和移植,却是在“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之后的民国时代。迄今为止,不过一个多世纪。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衰弱的清帝国大门。印证了西方文明的强盛和张扬,也折射出满清王朝的屈辱与悲哀。正因如此,才激发起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沉痛反省和变法图强的精神,并由此引发了维新派倡扬科学、革除时弊、镜鉴西方、推行科举等一系列改良主张。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守护传统文化过程中体现出拿来主义的思想。油画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成了中国艺术家追慕探寻的学科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战火频仍,西方艺术在引入中国初期,没有得到适时有效的传播与持续的对接,中国油画的萌芽与发轫轨迹实难清晰呈现。
回顾中国油画的蹒跚学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王朝艳羡西方、仰慕列强的好奇心理和政体衰败的落后国情。
据史料考证,西画东渐的历史轨迹,主要有三条基本路径:

图1 王致诚《达瓦齐像》清末
一、西方传教士的引入
作为西方绘画的主力品种,油画经由基督教向世界扩展传布来到东方,于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来自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被认为是最早携带西画(主要是基督像及圣母像)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其后有西方画家郎世宁(意大利传教士)、王致诚(法国传教士)等在清廷供职。这些入住宫廷的洋人,身为御用画师,拿着皇帝的俸禄,主要受命绘制天子龙颜及贵妃尊容。为迎合清室皇族趣味,传教士画家在绘画风格上只能有所妥协,他们必须有意识削弱西画的明暗对比和焦点透视,避开东方文化中犯忌的所谓“阴阳脸”,并兼顾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用细腻的类似于工笔重彩的渲染,避免笔触的暴露,致使传教士在宫中创作的作品,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点。(见图1)
大清宫廷御用的外籍传教士画师,不过是为皇亲国戚效力而作画,他们的创作活动完全被束缚在朝堂之上,豢养于宫阙之中,无法自由开放地向外推介与传播。宫廷传教士画师对西画在中国民间的启蒙与培植,几乎产生不了多大作用与影响。
与之相对应的是,沪上一些外来传教士慈善组织,则直接面向中国社会,体恤底层,关注民众。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在主教郎怀仁的支持下,曾于19世纪中叶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设立“土山湾孤儿图画院”(即后来的“土山湾画馆”),他们一边为信徒们传经布道,一边教收养的孤儿学习绘画,并授予他们素描、水彩、油画、雕塑以及透视学、解剖学等西画基础知识,培养了百余名生徒(图2),其中个别优异者还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后来的国立上海油画院,就是由土山湾画馆一个名叫周湘的海归生徒所创办。类似这种反哺乡梓的案例,在传教士培养的学生中,时有发生,不一而足。上海油画院,揭开了中国人自己进行油画教学的序幕。所以,“徐悲鸿在1942年说,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1]

图2 1914年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教学课堂
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及西方传教士的足迹,不仅出现在中国的皇城宫廷和沿海都市,即便有些边远偏僻、贫困落后的内陆山区,也在一定层面上受到西方宗教、文化及科学的感召或洗礼。我们可以从中国各地遗留下来的基督教堂或天主教堂得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西方传教士在异国他乡传教布道,不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人生风险。被称为“庚子事变”的义和团拳民,在清廷皇权争斗激化的内讧关头,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纵火烧毁教堂、教徒屋舍,大肆杀戮教士家人,给投身中华大地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灭顶之灾。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其最终结局,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二、商埠口岸的通商往来
史料记载,自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起,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是当时洋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随后,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亦称“十三洋行”)为中心的西方商贾集中地和自由商业贸易区。西方商船舶来的洋货中,就包含有西洋画及其印刷品。
善于摹绘、仿制的中国民间画师,通过这种商埠往来,很快便学会了用西画的材料和技法,来描绘东方故国的人文及风情,于是,广州外销画便应运而生。作为彼时南中国最时髦的手工艺品,清代的这些外销画所体现出来的东方神韵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人的好奇心理和异国趣味。在摄影术尚未发明之前,外销画就像明信片一样,描绘了中国的世俗生活、名人巨贾、城郭楼台、自然风光等,备受外籍商旅、海员所青睐,成为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一种观光纪念品。
如此看来,商埠口岸的通商往来,既是彼时西洋绘画进入中国的一条路径,也是中国清代外销画流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这些最早以西画媒材、技法模仿绘制的外销画,因大量流出,国内很少得见。现多藏于欧美、日本及港澳等地博物馆或艺术馆,被境外称为“中国风物的手绘照片”。
这类以商业利益为最终目的,经由沿海口岸间的贸易往来互通,暨商旅文化交融现象,记载持续了近百年时间。中国习学西画的民间艺人,技能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因市场所需,民间画坊内的师徒传艺,也随之应运而生,乃至一度趋于活跃,甚至有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与扩散的态势。
这些经由民间渠道培养出来的油画家自由放任,与上述宫廷引进的传教士为迎合皇家趣味而将西画风格中国化的讨好举动相较,其艺术面貌明显趋于商业化和市场化,幅面多不太大,画风也少见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干扰。“在‘外销画’大多数无名画家的作品中,如果说还不同程度地残存着传统的痕迹,那也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无意识保留。”[2]53这种状况与“中西合璧”的宫廷油画形成有趣的对照,即欧洲油画的基本风格似乎得到了更为真切的植入与保留。现藏于香港艺术馆的《啉呱自画像》(关乔昌1853年)作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为我们留下了西画东渐最接近西洋原貌的经典范本。(图3)

图3 关乔昌《啉呱自画像》1853.香港艺术馆藏
三、中国留学生的主动移植
上述以传教为目的,抑或以商贸为契机的涉外通道,不论是宫廷御用引进,还是民间自发流入,严格说来都不具备应有的专业标准或必要的学术水平。真正主动、自觉研习西画,或是将油画技法及理论移植中国,并在我国发扬光大者,主要还是通过留学西欧以及东洋的大批归国留学生。
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率先出国学习西画者,是广东人李铁夫(1869-1952),他于1887年(清光绪13年)得亲属之助,入读加拿大英属阿灵顿美术学院,后又转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1908年,入威廉·切斯画室深造。“成为中国人最早攻读油画艺术的先驱,堪称悟到西方油画技术真谛的第一人。”[3]1930年,李铁夫归国后隐居香港,1935年,在香港举办首次个展。二战时期,香港沦陷,李铁夫避居乡下友人家中。1949年,李铁夫回到广东,“欣然接受了华南文联副主席和华南文艺学院教授的职位”。[4]
李铁夫之后,有江苏的李毅士、天津的李叔同、广东的冯钢百等三人于1903-1906年间相继赴日本、英国、墨西哥等国留学。李毅士最早赴日本,后于1903年转英国半工半读,曾在格拉斯格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李叔同于1905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美术学校黑田清辉门下学习油画。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首创室外风景写生和人体写生课程,是我国正规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冯钢百1906年到墨西哥皇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后又到美国,师从罗伯特·亨利专攻油画肖像。[3]
以上四人是中国最早奔赴海外学习西洋绘画最具影响力的开山鼻祖。“从象征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学术层面上传播油画的真正先驱,是中国油画从含糊向明确阶段转换的开始……”。[5]
总体说来,“在1911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变心态构成了普遍的空气。”[2]59晚清至民国年间成长起来的国中学人,出境留学蔚然成风。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股令人瞩目的开放潮流,兴起于20世纪的上半叶。仅美术学科而论,赴西欧留学或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就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张道藩、杨秀涛、庞熏琹、常书鸿、颜文樑、吴作人、唐一禾、赵无极、吴冠中等(图4);与此同时,赴日本留学的有:陈抱一、卫天霖、倪贻德、阳太阳、宋步云、黄新波、王式廓等。这些留学生除极个别留在海外,大部分学成后都回归母国,报效乡梓,成为西画移植中土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彼时留学生回国后的最好归宿,就是各地的艺术学府或专业社团。于是,有学校的城市,他们就积极加盟从教;没有学校的城市,他们就努力创办学堂(图5)。这些归国留学生以学府社团为阵地,以教育培训为手段,一边创作,一边教学,全面强化了西画在我国的传播与研习。史学家刘新在《中国油画百年图史1840-1949》第二章第一节中,把“留学”和“办学”,喻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西方油画在中国本土的起动与翱翔现象,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留学生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把西画的种子播撒于华夏大地,使中国油画迅速成长为几乎可以与传统中国画分庭抗礼的一个画种。可见,这些早期留学生,对西方油画在中华大地上的孕育和发展,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图4 1933年留法学生合影于巴黎

图5 创建于1912年上海美专
结 语
上述三条路径,各有建树,互为补充,为“西画东渐”的历史线索勾勒出立体式场景。我们于此得窥油画在中华大地萌芽生发的契机与前兆。
过去油画史学界一直把西画的引入和移植,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它对推动我国新文艺的发展,对促进传统中国画的革新、改造等,都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可是,从以上时间节点来看,这种引入与移植,其实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五四”不过是对这种新文化的延续倡导而已。另外,在西画舶来的过程或路径上,其初始阶段一般多是处于混沌无序、章法紊乱,甚至时有时无、断断续续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归国以后,情况才逐步有所好转。
值得庆幸的是,西方油画在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一步步孕育了中国油画的成长与独立,油画作为一个绘画种类,在中国总算扎下了根,形成了土壤,结出了硕果。时至今日,终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队伍,已奠定起坚实的基础,并展现出东方民族所特具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