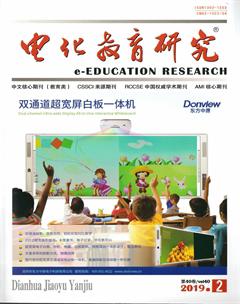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研究
叶新东 仇星月 封文静
[摘 要] 技术应用于语言学习一直是语言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热点。研究从语言的自主性和社会性入手,思考技术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通过对虚拟现实技术特征与发展的解析和对最新实证研究案例的分析,构建出了一个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这个模型从技术支持、理论支持、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四个方面重构了技术支持下的语言学习研究,试图为语言学习的新技术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框架,带来新的思考。
[关键词] 虚拟现实; 语言学习; 生态模型; 技术应用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叶新东(1976—),男,浙江温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媒体新技术与教育研究。E-mail:yxd@wzu.edu.cn。
一、引 言
语言学习研究最早是以语言的构成要素作为研究起点的。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语言教育运动的开展,外语首次成为中小学课程,在教育理论丰富的同时,语言如何去教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1]。但随着学习科学的发展,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实际上学习者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独一无二的语言体系,因此,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学习者个体,学习者的自主性受到重视[2]。此外,由于受社会文化理论等新理论的影响,语言学习的社会属性也开始深入人心。然而语言的实际应用与一般的语言学习相比,蕴含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语言的社会性和自主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目前,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应用开始走向成熟,为如何提升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自主性和社会性带来新的思路。
Holec在1981年提出“学习者自主性”时,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常规学习途径逐渐掌握的[3]。学习者自主性强调的是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的独立存在(Independence)以及与外部因素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4]。对于社会性而言,Atkinson提出,语言是社会实践,是社会成就,也是社会工具。人们通过语言来传达、建构和表现思想、感受、行为、身份甚至是简单的存在等[5]。但当语言的使用不是基于社会环境时,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语言学习中,技术不能仅仅作为语言学习的辅助工具,而是要让它成为促进语言能力发展的技术化环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正朝着信息化的方向持续发展,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移动终端辅助语言学习(MALL)等领域逐渐成为世界上语言学习研究的热点。语言学习开始突破理论探讨,进入技术的实践应用层面。通过计算机网络、可移动设备进行交互,促进语言学习已成为常态。
21世纪初,国外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功能定位发生重大转变,即从学习工具/伙伴转变为实现与母语者交互、合作的虚拟环境[6]。这表明技术化环境已逐渐成为语言学习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或实现社会环境与物理环境的相关功能。而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更能够解决传统学习媒体的技术限制问题,它能产生强烈的沉浸性与存在感,这也使虚拟现实技术能与其他技术相区分,造就更为理想的技术化环境。
二、语言学习研究中的虚拟现实技术的特征
(一)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也称“沉浸式多媒体”,是一种可交互、体验、创造虚拟环境的仿真技术[7],但它与传统多媒体技术明显不同。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受计算机图形学、情感计算、传感技术等多项技术支持,用户的感官体验得到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在社交体验方面的媒体丰富度、社会存在感和自我开放度明显强于普通社交媒体[8]。
虚拟现实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往往体现沉浸性和存在感两种特征。沉浸性是虚拟现实技术的技术属性,是用户感受到被环境包围并与之相互刺激的体验[9]。而就存在感而言,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也是用户沉浸在虚拟环境中所体验的有意识的存在。尽管存在感和沉浸性是虚拟现实技术早期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但现在仍能作为衡量虚拟现实技术是否成熟和体验是否真实的标志,尤其是语言教育应用。
1. 沉浸性
沉浸性作为虚拟现实技术的重要技术指标,是客观、可测、可控的属性[10],它能影响用户的存在感。Jennett等学者认为,按照沉浸性程度可以分为:(1)参与,参与者投入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掌握如何使用、操控;(2)专注,参与者情绪直接受虚拟场景影响,淡化了外界感知和自我意识;(3)完全沉浸,完全切断了参与者对外界的感知,全身心投入到虚拟环境中[11]。可以看出,沉浸性提升的过程,实际上是用户对虚拟环境的存在感增强以及对外界感知减弱的过程,虚拟现实技术正是利用这种特点给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画面真实度、图像帧速率、声音环绕度、触觉反馈程度、虚拟身体表征(能否看到自己的虚拟身体及其完整性)和身体参与度等都与沉浸性呈正相关[12]。因此,就虚拟现实技术本身而言,合理的利用其技术特征刺激并增强用户的感官、知觉,是提升用户存在感的有效措施。
2. 存在感
简单讲,存在感就是一种参与者存在于虚拟环境中的感受,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临场感,最基本的感受,可简单描述为“置身于此”的感觉;(2)共存感,一种心理上的交互,能感知他人并能體会他人对自己的感知;(3)社会存在感,突出交互性,定义为互动过程中他人参与的显著度和人际关系的显著度[13]。有研究表明,社会存在感最能给用户带来环境体验的满足感,而且社会存在感强度的高低与社会交互的真实度、丰富度等呈正相关[14]。所以,要把提升交互指标作为加强用户存在感的重要手段。
对语言学习而言,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丰富且真实的交互情景是突出社会存在感的关键,存在感会影响语言的输入、内化和输出。语言学习环境的构成应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一方面,物理环境要经过还原、仿建现实应用情景作为产生存在感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环境要通过在物理环境中构建社会构成要素、实现社会功能,进而形成虚拟化社会空间。
(二)虚拟现实技术的分类与应用
本研究认为,通过对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等级和所属设备载体进行比较,可以将其划分为桌面式虚拟现实技术、洞穴式虚拟现实技术和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这也是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三个发展阶段。
1. 桌面式虚拟现实技术(Desktop VR)
桌面式虚拟现实技术是将计算机等图形显示设备作为技术载体,利用鼠标、手柄等控制设备在计算机所构成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由于桌面式虚拟现实系统具有低沉浸度,易导致体验性不佳,真实感匮乏。所以,有必要通过设置丰富的社会角色体验来提升学习者的社会存在感。在外语学习研究中,桌面式虚拟现实系统的应用相对成熟,多是基于Second Life、Open Simulator和MMORPGs等软件进行开发。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大型项目,典型的包括欧盟的VILL@GE项目、美国的Language lab等。国内尚处在简单虚拟场景的构建层面。
2. 洞穴式虚拟现实技术(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
洞穴式虚拟现实系统通常是在一个封闭房间内利用投影设备将虚拟场景画面覆盖到周围墙屏中实现的。用户会配备立体快门眼镜和操纵手柄等设备用于交互。该系统将用户封闭在房间内,避免了外界的干扰,因此,具有高度沉浸性。由于造价昂贵和空间受限,它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难以应用。研究者一般仅实现洞穴式虚拟现实的部分技术功能,构建出类洞穴式(CAVE-like)虚拟现实环境。这在一般研究中较为常见,但是在降低技术成本的同时,也会导致体验感的削弱。
3. 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Head Mounted Displays)
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现在已走向成熟,与其他种类的虚拟现实技术相比,它能将用户对自我身体和外界环境的感知分离,全身心投入到虚拟世界中,对环境产生深度感知。使用者需要佩戴沉浸式的输出设备和追踪装置等,确保其身体运动和环境反馈之间的精确匹配[15]。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类型较多,功能、成本、沉浸性等也有较大差距。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已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多项应用研究,并通过实验证实了其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和可行性,但它在语言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
三、虚拟现实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
实证研究回顾
近六年内,研究者已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语言学习的实证研究作出努力。本研究对20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汇总(见表1)。其中,利用桌面虚拟现实技术作支持的研究占16篇,利用类洞穴式(CAVE-like)和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作支持的研究各占2篇。我们把支持级别作为汇总表的重要指标,依据实验时长,被试人数,社会环境、社会角色和学习策略的丰富度,实验结果与实验假设的符合程度来确定对应用效果的支持程度。语言学习研究的三要素也作为重要的评判内容,依据以下标准:(1)社会环境,交互行为的丰富程度和环境的真实程度;(2)社会角色,社会交互的自由度和可供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种类;(3)语言学习策略,策略应用的适用程度和丰富程度。
桌面式虚拟现实技术目前仍然是相关实验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技术,它已相对成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Lan Y J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优势,他用可靠的实验结果证实虚拟现实技术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果呈现较高的支持程度[18,23,25,28-29]。类洞穴式虚拟现实系统应用的典型案例是Chang Benjamin等人利用大型的交互式显示屏构建了一个类洞穴式的虚拟现实环境,学生在这个环境中进行了八周的学习,感受到了真实情境所带来的沟通压力,促使他们进行语言交流,多数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取得成功,实现或超越了预期目标[32]。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Cheng通过与桌面虚拟现实系统对比,证实了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Oculus Rift)可以提供最为理想的交互体验,产生真实的存在感,更有助于语言学习的开展[34]。
总的来看,虚拟环境的独特优势可以激发与影响学习者动机、自我效能感等,多数实验结果表明,受训后学习者在各项语言能力上都获得显著提高。这些研究对社会环境和策略应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缺乏社会角色的使用。语言学习应给学习者提供充分的角色扮演的机会,这样有利于从社会视角实现语言使用,提升学习的代入感、真實感。虚拟现实技术在语言教育中的良好应用价值已被证实,但沉浸感更强的洞穴式和头戴式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还很有限。这意味着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在语言学习研究中的应用空间很大。同时,头戴式虚拟现实系统已进入技术成熟期,它在语言学习中的广泛应用有着很大可能性。
四、虚拟现实环境下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
(一)模型提出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是受秦丽莉提出的“‘生态化任务型语言教学模式”的启发提出的[36]。它从技术支持、理论支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了模型重构,如图1所示。模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让学习者在不同级别的情景中不断交流合作,持续反馈评价和逐步实现学习目标,真正实现从语言学习的浅水区向深水区的安全过渡。
图1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
(二)模型构建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以语言学习的终极目标为导向,通过技术与理论的支撑,摒弃了限于形式上重复操练的学习方式,试图在更接近生活的实境中解决语言学习问题。希望从微观上创造一个角色更加多样、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学习者体验更加丰富的练习情景,用于语言学习。对语言学习者来说,从课堂走向社会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虚拟到真实、从个体到群体的层级转换,是一个由浅到深的发展过程。
1. 技术层面
该模型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其他技术形式相区分并给出明确定位,它用于还原真实应用情景和提供理想学习场所,兼具了其他技术的优势特点,体现出对语言学习技术的优势整合,并能利用独特的想象性、构造性,让语言学习中环境、角色和策略的应用更具表现力。根据Hargie的泳池理论,如果将语言真实应用环境看作是泳池的“深水区”,那么传统课堂中的语言学习就像是在“戏水池”中练习游泳[37]。受到传统学习环境限制,学习者从简单交互里所习得的知识难以迁移到更复杂的交互情境中,这将导致学习者只能在“戏水池里学游泳”,难以在真实情景的“深水区”中施展技能。而虚拟现实技术恰好能为学习者创建一个介于课堂模拟环境与真实社会语境之间的“浅水区”,有助于学习者过渡到“危险的深水区”。虚拟现实技术将为教育提供崭新的理念,将认识世界、感知世界、构建知识紧密融合,产生的教学效果将高于原知识价值效果,真正体现技术为教育服务的思想[38]。尽管虚拟现实技术为语言学习带来了理想的环境,但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必须加以限制,以求在教育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达到均衡。
2. 宏观层面
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个性化教育新需求下,语言学习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增强社会交互意识。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独立于课堂内外的自主学习能力应成为学习者掌握一门语言的关键;但作为学习发展共同体的一员,学习者参与社会互动的效果直接关乎语言学习的质量[39]。语言学家克拉申曾在 “输入假说”论中指出:情景(Context)能促进语言输入被理解[40]。因此,我们把情景作为语言学习活动的开展单元,而情景是反映现实中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缩影”,是相关现实情境受技术虚拟化处理后的结果。在这里的每一个学习单元都是对真实社会语境的微观重现,它对实际交互情景进行了复杂度、真实度的压缩。但随着语言学习的深入,学习单元中情景的真实性会不断增加,情景中的社会角色类型、社会关系复杂度、社会活动丰富度、环境真实程度等社会指标会得到增加,最终与真实社会语境相接轨。这种学习形式保障了学习者时刻拥有真实的社会存在感,建立层级式的语言学习情景有利于促进学习的顺利迁移。
情景的最后一个层级会把语言学习扩展到真实的社会语境中,表现出语言学习的动态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学习者在社会性和自主性两方面能力的并行发展,最终实现从“虚拟练习”到“现实应用”的超越。首先,对学习者逐步掌握语言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进行划分,将其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从产生语言学习意识,到积极参与、自适应调节、自主创设学习活动,最后实现从虚拟到现实的超越。社会性层面的能力主要是按照学习者的社会参与度划分,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意识和交互程度逐渐加强的过程,涉及互动、参与、会话、融入和向实际应用的转型。
3.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是宏观层面要求的具体实现,反映情景单元内的活动开展情况。模型中的角色可以按两种方式划分。根据参与者角色可分为:教师、学生、虚拟角色和母语者,其中,虚拟角色是对教师、学生和母语者行为的仿真模拟,母语者参与的意义在于建立使用目的语的实践条件并进行串联学习。从活动作用的角度又能划分成:指导者和学伴两类。此外,尽管活动开展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但本模型不摒弃教师对学习者的监督和指导作用,重视学习者之间的指导与陪伴。教师的职责重在激发学生自主参与和提供即时的反馈纠正,而学生的职责除自身的学习与发展外,还要在共同体中体现出多样角色,包括指导者、陪伴者。角色之间还存在三种交互形式,即师生间、生生间和学生与母语者之间的交互。为了让虚拟环境更接近真实,我们追求三个“复杂”:复杂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社会交互与复杂的社会环境。
(1)复杂的社会关系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互动的社交过程,它超越了学校的范畴,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所以,当个体融入学习共同体中参与社会交互活动,便被赋予了社会角色。在该模型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在学习中拥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作为社群成员在学习活动里发生交互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化的学习空间。在虚拟学习环境中,虚拟化身是社会交互的媒介,它也是学习者的身份、行为等在虚拟现实中的投射[41]。由于学习者是虚拟化的存在,能避免接触实际应用场景,减小了目的语交互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削弱了情感滤网对个体的作用,有利于触发学习热情[42]。在虚拟环境中,学习者作为社会角色,必须要考虑到社会心理需求,同时,也要让学习者拥有一定的自主权[43]。当学习者能同时具备社会责任感与自我责任感时,才能让学习活动有意义进行。严格来讲,虚拟角色的使用是通过体验替代自身的角色来达到构建与调节语言的目标[44]。这是因为知识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通过与他人的連接和协作而发生的社会过程。在严肃游戏(Serious Game)研究中,已有学者利用角色扮演游戏开展语言教学,研究结果表明,虚拟条件下的协作式的语言学习活动能支持知识共构,激发学习动机,可促进高层次的学习[45]。
(2)复杂的社会交互
首先,在技术上,虚拟现实技术与其他新媒体技术相比能带来更具扩展力的交互体验。它建立在现实中的交互隐喻之上,除了能进行基本的文本交互、语音交互、手势交互、触觉交互等,甚至还能做到多种交互技术的结合,实现多通道交互[46]。多种交互手段并存使语言学习增加了肢体语言、表情语言等非语言线索,不仅避免了过去的语音交互技术过于单一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让学习者体验到更佳的社会存在感。此外,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可控制代表自我的虚拟角色对环境持续探索、体验并不断与环境中的虚拟对象和其他学习者产生交互,这种自由、可调控的学习机制本身就能为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学习自主权。社会交互重要性已在实证研究中受到重视。Pasfield-Neofitou等人利用虚拟现实创建了一个充满中国文化特点的环境,并设计了一系列汉语口语学习任务,学习者要通过探索环境线索并与虚拟角色进行交互来完成相应的任务[47]。此类语言学习方法让学习者以虚拟化身为中介,在丰富的交互中促进语言的内化并掌握语言的运用,由此实现从虚拟到现实的迁移。
(3)复杂的社会环境
语言学习会发生于一个真实与虚拟叠加的环境中,这里的一切均取材于现实,但又具备“超现实”的特点。而模型中的每个情景都是对目的语语境的真实刻画,它充满了语言学习应具有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相对于传统的语言学习,虚拟现实技术除了能够高度还原真实的社会语境,还能把语言符号具象成图形、图像,甚至表现出语境中想象性、创造性的一面。此外,学习者以“虚拟化身”为中介,在情景中社会角色会被赋予,使学习者成为虚拟环境的构成要素。这种复杂的社会构成无疑为语言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更能带动学习动机和持久性。Donato认为,最直接有利的策略方式是他们最难以抗拒的策略方式,即积极的社会使用[48]。因此,除了物理环境,不受控制的社会交互环境是语言学习环境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当社会活动一旦被确立,语言交互就会变得不可预测。这时就需要选用协作、合作、竞争的策略,增强学习的目的性和学生之间的凝聚力,把环境对学习的促进作用做到最大化。在Chen等人的实证研究中,任务型的学习活动使得学习者间的依存性变得紧密,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通过设置符合学习者发展的任务活动,营造与目的语应用相适应的丰富社交场景,以及获取教师的即时反馈与指导,学习者能够在交互和协作中完成复杂的学习目标[49]。
4. 理论层面
本模型把实践社区理论与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温格的实践社区理论认为,当前的学习内涵在哲学层面已经发生改变,学习不再是个体单独的事情,而是团体的社会交互活动。学习不仅仅是获得新技能的过程,也是一条群体中共同实践的社会路径[50]。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成熟的个体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外部语言的内化,当然也可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促进语言能力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的提高[51]。在语言学习中,支架一般是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帮助学习者提升到潜在水平,促进语言的内化[52]。一旦个体掌握了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让这种语言系统化、内部化,最终成为内部语言。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学习活动被视为是社会活动的符号过程,语言结构和功能的认知是在语言的社会性使用中得到发展的。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虚拟现实技术促进语言学习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我们认为语言学习是终身的过程,它离不开技术的使用。而想用技术促进语言学习,就必须首先解决理论如何融入实践与研究的难题。只有解决了这一根本性问题,才能保证后续设计、开发过程的正确性。本研究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学习者创设高度沉浸感和存在感的目的语言环境。虚拟现实技术凭借自身的技术特性会让这种关系得到加强,形成一种适用于语言学习的社会空间。因此,我们提供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期望为语言学习实践应用研究提供参照,并能够真正为当前的语言学习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庄会彬. 反思与借鉴:英美国家第二语言教学法百年流变(1914—2013)[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2(1):22-33.
[2] 顾世民,赵玉峰. 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回顾与思考——国外研究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2015(5):41-49.
[3] HOLEC H. 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Pergamon Press,1981.
[4] LITTLE D. Developing learner autonomy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a social-interactive view of learning and three fundamental pedagogical principles[J].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1999,38:77-88.
[5] ATKINSON D. Toward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2,86(4):525-545.
[6] SCHWIENHORST K. Why virtual,why environments? Implementing virtual reality concepts in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J]. Sage publications,Inc. 2002,33(2):196-209.
[7] 何聚厚,梁瑞娜,肖鑫,等. 基于沉浸式虛拟现实系统的学习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 电化教育研究,2018(3):75-81.
[8] BOWMAN D A,MCMAHAN R P. Virtual reality:how much immersion is enough?[J]. Computer,2007,40(7):36-43.
[9] WITMER B G,SINGER M J. Measuring pres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s:a presence questionnaire[J]. Presence,1998,7(3):225-240.
[10] WANG Y F,PETRINA S,FENG F. VILLAGE——Virtual immersive language learning and gaming environment:immersion and presence[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5,48(2):431-450.
[11] JENNETT C,COX A L,CAIRNS P,et al. Measuring and defining the experience of immersion in g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2008,66(9):641-661.
[12] SANCHEZ-VIVES M,SLATER M. From presence to consciousness through virtual reality[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05,6(4):332-9.
[13] BULU S T. Place presence,social presence,co-presence,and satisfaction in virtual world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2,58(1):154-161.
[14] NOWAK K L,BIOCCA F. The effect of the agency and anthropomorphism on users' sense of telepresence,copresence,and social pres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s[J]. Presence,2014,12(5):481-494.
[15] 高媛,劉德建,黄真真,等. 虚拟现实技术促进学习的核心要素及其挑战[J]. 电化教育研究,2016(10):77-87.
[16] BERNS A,GONZALEZ-PARDO A,CAMACHO D. Game-like language learning in 3-D virtual environm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3,60(1):210-220.
[17] HENDERSON M,HUANG H,GRANT S,L HENDERSON. The impact of Chinese language lessons in a virtual world on university students' self-efficacy beliefs[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3):400-419.
[18] LAN Y J,KAN Y H,HSIAO I Y T,et al. Designing interaction tasks in second life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3,29(2):184-202.
[19] CANTO S,JAUREGI K,HUUB V D B. Integrat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hrough video-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world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s:is there an added value?[J]. Recall,2013,25(1):105-121.
[20] HSIAO I Y T,KAO C L,TSAI Y C,et al. Creating a virtual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second life[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Washington DC:IEEE,2016:520-522.
[21] CHEN Y L . The effects of virtual re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student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development[J].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2016,25(4):637-646.
[22] CHEN C C. The crossroad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task-based instruction,and 3D multi-user virtual learning in second life[J]. Computer & education,2016,102:152-171.
[23] HSIAO I Y T,LAN Y J,KAO C L,et al. Visualization analytics for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in virtual world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17,20(2):161-175.
[24] ZHENG D,BISCHOFF M,GILLILAND B. Vocabulary learning in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context and action before word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2015,63(5):771-790.
[25] LAN Y J,KAN Y H,SUNG Y T,et al. Oral-performance language tasks for CSL beginners in second life[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2016,20(3):60-79.
[26] NATASHA L,JEONG-BAE S. Facilitati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with second life and skype[J]. Recall,2017,29(2):200-218.
[27] CHIANG T H C,HUANG C S J,LIOU H H,et al. Student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using second life[J].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Learning,2014,6(1):1-17.
[28] LAN Y J. Contextual EFL learning in a 3D virtual environment[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2015,19(192):16-31.
[29] LAN Y J,FANG S Y,LEGAULT J,et a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vocabulary:context of learning effect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2015,63(5):671-690.
[30] GARRIDO-I?譙IGO P,RODR?魱GUE-MORENO F. The reality of virtual worlds: pros and cons of their applica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2015,23(4):453-470.
[31] HASSANI K,NAHIV A,AHMADI 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lligent virtual environment for improv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2016,24(1):252-271.
[32] CHANG B,SHELDON L,SI M,et al.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s[C]// Proceeding of 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 USA,2012:1-9.
[33] SI M. A virtual space for children to meet and practice Chinese[J]. Internation journal of ar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15,2(2):271-290.
[34] CHENG A,YANG L,ANDERSEN E. Teach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virtual reality game[C]//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New York:ACM,2017:541-549.
[35] MADINI A A,ALSHAIKHI D. Virtual reality for teaching ESP vocabulary:a myth or a possi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2017,5(2):111.
[36] 秦麗莉, 戴炜栋. 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的“生态化”任务型语言教学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41-46.
[37] HARGIE O D W,DICKSOND A,TITTMAR H G. MINI-teaching:an extension of the microteaching format[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1978,4(2):113-118.
[38] 李小平,张琳,赵丰年,等.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下混合形态教学设计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17(7):20-25.
[39] 魏玉燕. 促进学习者自主性:外语教学新概念[J]. 外语界,2002(3):8-14.
[40] KRAHNKE K J.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Tesol quarterly,2012,17(2):300-305.
[41] WANG A,DEUTSCHMANN M,STEINVALL A. Towards a model for mapping participation:exploring factors affecting participation in a telecollaborative learning scenario in second life[J]. Jalt call journal,2013,9(1):3-22.
[42] KIRSCHNER P A. The sociability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02,5(1):8-22.
[43] NAJEEB S S R. Learner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3,70(11):1238-1242.
[44] VILLANI D,GATTI E,TRIBERTI S,et al. Exploration of virtual body-representation in adolescence:the role of age and sex in avatar customization[J]. Springerplus,2016,5(1):1-13.
[45] OKSANEN K.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sociability in a collaborative serious game[J]. Simulation & gaming,2013,44(6):767-793.
[46] 張凤军, 戴国忠,彭晓兰. 虚拟现实的人机交互综述[J].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6(12):23-48.
[47] PASFIELD-NEOFITOU S,HUANG H,GRANT S. Lost in second life:virtual embodi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via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2015,63(5):1-18.
[48] DONATO R,MCCORMICK D.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the role of mediation[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4,78(4):453-464.
[49] CHEN C C. The crossroad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task-based instruction,and 3D multi-user virtual learning in second life[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6,102:152-171.
[50]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meaning and identit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1] THORNE S L,LANTOLF J P.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52] LANTOLF J P. Language emergence: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J]. Applied linguistics,2006,27(4):717-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