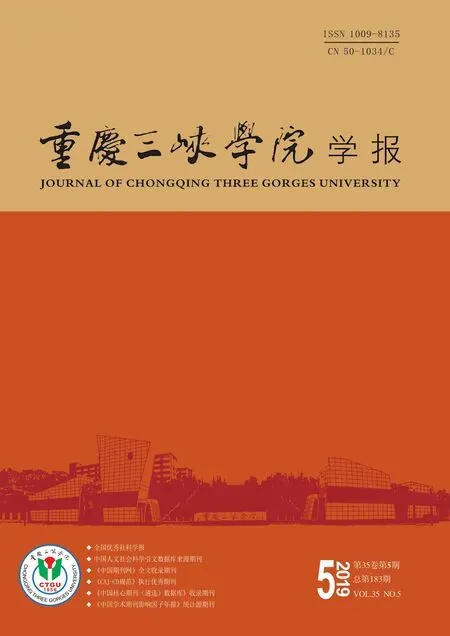章太炎“语根说”的西学渊源
杨 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1)
清末民初,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继往开来,“既为中国古代文字音韵学的发展做了总结,又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贡献中,“语根说”是其核心创见。章太炎认为,在汉语言文字演化史上,同一语根(《说文》独体字)衍生出诸多文字,这些同源字音义相互关联,属于同一语族;不同语族共同构成了汉字体系。他以音韵为线索,结合字义和字形,探考语根到语族的演变,梳理汉字的源流体系。
“语根说”贯穿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从《斯宾塞尔文集》译文(1898)和《订文》(1900)的初步思考,到《与吴君遂书》(1902)“语根”之名的提出,再到《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对“语根说”的阐释,进而发展到《新方言》(1907—1908)和《文始》(1910)对“语根说”的具体实践。
章太炎“语根说”的构想和实践有诸多因缘。其中,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启迪十分关键。在19世纪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既是专业的语言学,又被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批判地借鉴[2],并于19世纪晚期传入日本和中国[3]。那么,章太炎是如何接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他的“语根说”受哪些西方学者启发?这有迹可循么?
已故语言学家俞敏[4]认为,章太炎的“语根说”承沿了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的《言语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尤其是此书第二卷的“论语根之言”(“On the Powers of Roots”)。周法高[5]、何九盈[6]和赵振铎[7]等借鉴俞敏的论点,将其融入到语言学史著作中。万献初[8]、许良越[9]和贾洪伟[10]等探讨章太炎“语根说”的中西渊源时,沿用了以上语言学家的论点。
然而,汉学家伊丽莎白·卡斯克(Elisabeth Kaske)认为,这一论点缺乏确切依据[11]365,但并未剖析这一论点的成因。卡斯克[11]365、姜义华[12]和王诚[13]指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影响深远。他们尤其提及斯宾塞《论进境之理》(“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对章太炎“语根说”的启迪,但未作具体分析。此外,尚未有学者探讨斯宾塞《论礼仪》(“On Manners and Fashion”)中的诸多词源分析对章太炎“语根说”的启发①姜义华和王天根都曾谈及《论礼仪》对章太炎语义学的影响,然而,两位学者的侧重点并非《论礼仪》对章太炎“语根说”的启发。详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37.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J].东方丛刊,2004(2):78-92.。鉴于此,本文以章太炎的相关译作和著作为依据,分析这两种观点的理据,梳理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斯宾塞的关联,由此探考章太炎“语根说”的西学渊源,呈现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清末民初译介和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一、章太炎的“语根说”与缪勒的《言语学讲义》
俞敏先生最早提出章太炎“语根说”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渊源关系。在《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1948)中,俞敏指出:
章氏造《文始》,自言读大徐所得,夷考其渊源所自,实出于德人牟拉(Max Mueller)之《言语学讲义》②俞敏原文中的脚注:“4.M.Mue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s,6th ed.,London,1871.”。持《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后半以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言相较,承沿之迹宛然③俞敏原文中的脚注:“5.Vol.II,p.349.”。其《检论·订文篇》附录《正名杂义》云:“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语言之瘿疣”④俞敏的引文与章太炎原文稍有出入:《检论•正名杂义》原文为“神话为言语之瘿疣”,俞敏将“言语”引作“语言”。,亦即牟书中语也。牟氏常取印欧语之根,历数其各语系中之变形。章氏取之。其说转注云:“类谓声类,首谓语基”是也。[4]
引文中的“德人牟拉(Max Mueller)”和“马格斯·牟拉”即德裔英籍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缪勒是19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知名学者,在梵语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神话学等领域贡献卓越、备受争议[14]。引文提到的“语根”学说和“神话为语言之瘿疣”是缪勒学术的两个代名词,最早出现在他的两卷本《言语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⑤两卷《言语学讲义》是缪勒1861年和1863年在大不列颠皇家学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两个系列讲座的讲义集。1861—1900年间,《言语学讲义》英文版多次再版。俞敏先生参考的是1871年版。中。
在《言语学讲义》卷一第1 讲中,缪勒首次提出,“神话为语言之瘿疣”(mythology is a disease of language)[15]12。缪勒扼要指出,在语言演化过程中,字词原义被遗忘,又被后人赋予新义;新义往往是对原义的误解,这类语言误解现象是广义上的神话,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狭义上讲,神话是诸神和英雄的故事,最初也大多源于后人对前人语言的误解。到第7~9 讲时,缪勒以梵语为例探讨语根的定义、分类和演化。缪勒认为,语根是最小单位的单音节语音类型(phonetic types);梵语有大约四五百个语根(400 or 500);同一语根通过语义引申、拼写变化等方式衍生出诸多词汇;词汇纷繁多变,但大都遵循语音法则(phonetic laws),有其源流脉络[15]290-448。
在《言语学讲义》卷二中,缪勒深入阐释了“语根”学说和“神话为语言之瘿疣”。俞敏提到的“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言”即此书第7 讲“On the Powers of Roots”,尤其是这一讲有关语根“Mar”的分析(The Root Mar)[15]349。“神话为语言之瘿疣”是此书第8~12 讲的核心内容[15]368-633,“亦即牟书中语也”。俞敏发现,章太炎《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后半部分与此书“论语根之言”的思路类似。俞敏由此推断,章太炎的“语根说”源自缪勒的《言语学讲义》,关键佐证是章太炎《检论·正名杂义》引用的“神话为语言之瘿疣”也出自此书。
诚然,《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后半部分[16]和《言语学讲义》的“论语根之言”[15]349思路相近:二者都以音韵为线索,历数同一语根的诸多变形,而且《检论·正名杂义》引用了缪勒的“神话为语言之瘿疣”,此语和“论语根之言”都是《言语学讲义》的重要内容。然而,俞敏忽略了一个关键线索:章太炎引用的“神话为语言之瘿疣”并非出自《言语学讲义》,而是转引自姊崎正治(あねさきまさはる,1873—1949)的《宗教学概论》(1900)[17]。
俞敏先生治学严谨,为何忽略了这一关键线索?这主要源于《检论·正名杂义》行文的“误导”。文中,章太炎援引姊崎正治,但未指其名,而以“尝有人”代称,却在转引“神话为言语之瘿疣”时提及缪勒(马格斯牟拉):
尝有人言:表象主义,亦一病质。凡有生者,其所以生之机能,即病态所从起。人世之有精神见(现)象、社会见(现)象也,必与病质偕存。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是则然矣。抑言语者本不能与外物泯合,则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风吹,皆略以人事表象。……有表象,即有病质凭之。[18]
以上引文皆译自“尝有人”(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第四章“宗教病理学”[17]。然而,文中未注明出处。文中的措辞和标点也遮盖了这一引用关系,既消隐了“尝有人”,又凸显了缪勒(马格斯牟拉),容易给读者留下这样的错误印象:章太炎先后引用了“尝有人”的“表象主义,亦一病质”和缪勒的“神话为言语之瘿疣”两个点睛之句。因此,读者难以觉察《检论·正名杂义》对缪勒的转引。
还需留意的是,作为精通梵语和英语等多门外语、学贯中西的语言学家,俞敏既了解梵语学界泰斗缪勒的《言语学讲义》,又知晓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俞敏敏锐地发现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论语根之言”的近似。受这一发现“诱导”,俞敏自然地认为,章太炎直接引用了缪勒《言语学讲义》中的“神话为语言之瘿疣”。以此为佐证,俞敏推测,章太炎的“语根说”源于缪勒的《言语学讲义》。
若要发现章太炎对缪勒的转引,需追溯《检论·正名杂义》的版本渊源。《检论·正名杂义》(1915)是对《訄书重订本·正名杂义》(1904)的删改。后者又是对《文学说例》(1902)的修订[19]。三个版本引用“尝有人”的文段未变,但措辞稍有改动。最显著的差异是,《检论·正名杂义》隐去了姊崎正治的名字,而以“尝有人”代称;前两个版本则以“姊崎正治曰”提示引文。此外,《文学说例》标点明晰,并在引文结尾注明出处为“译姊崎氏宗教病理学”:
姊崎正治曰:“凡有生活以上,其所以生活之机能,即病态之所从起,故凡表象主义之病质,不独宗教为然,即人间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其生命必与病质俱存。马科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虽然,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其必不得不有所表象。故如言‘雨降’,言‘风吹’,皆略以人格之迹表象风雨……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译姊崎氏宗教病理学。[20]
章太炎认为,这段文字“推假借引申之起源,精矣”[20]77。他在《文学说例》中引用了这段文字,同时转引了缪勒的“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借此论述语言的“假借引申”[21]。引文对应的日语原文中,姊崎正治未标注缪勒此语的出处[17]457。此外,作为日本宗教学创始人之一,姊崎正治在《宗教学概论》中回顾了西方宗教学和神话学史。书中几次谈及缪勒,既承认缪勒对宗教学的开创性贡献,又批判缪勒局限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式[17]2,8,18,299,316,457。然而,书中并未提及缪勒《言语学讲义》的“论语根之言”①1900年1月,姊崎正治在《帝国文学》发表了《言語学派神話学を評して高木君の素尊嵐神論に及ぶ》,见《帝国文学》1900(6):13-39。此文是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讨论缪勒神话学的主要材料来源。文中第24-26页的注释表明,“神话是语言之瘿疣”这一引文出自缪勒的《比较神话学》(“Comparative Mythology”),主要分析语言的误解讹传产生神话,而非缪勒的《言语学讲义》。。由此可以推断,章太炎只是在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中偶遇缪勒的“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这一关键句,并未由此了解缪勒的《言语学讲义》。
那么,章太炎最早阐释“语根说”(1906年9月)②《论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最早阐释语根学说的文章。此文最早见于1906年9月日本秀光社印行的《国学讲习会略说》。1906年11月和12月,《论语言文字之学》分两部分刊载于《国粹学报》第24期和25期。俞敏依据的《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1910)是《论语言文字之学》后半部分的修订版。之前,是否通过其他途径接触过缪勒的《言语学讲义》?
一方面,章太炎不懂英文。尚未有证据表明章太炎与其他学者合作阅读《言语学讲义》的英文版。章太炎虽懂日文,然而,《言语学讲义》日译本于1906年12月和1907年首次出版[22],晚于章太炎最早阐释“语根说”的时间。日译本虽然分为上、下两册,但只翻译了《言语学讲义》卷一,将其分成两册出版,并未翻译第二卷,也未翻译卷二的“论语根之言”③日译本《言语学》上下2册共14章。上册包含前7章,下册包含后7章。两册只翻译了缪勒《言语学讲义》卷一。其英文原作底本为1899年版Max Müller,The Science of Language,founded on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in 1861 and 1863,Vol.I.London: Longmans,Green,and Co.,1899.。此外,未有证据表明章太炎通过日文著作而间接了解缪勒的《言语学讲义》。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学生胡以鲁于1909年开始在日本帝国大学博言科学习,较为系统地研究西方语言学。随后,胡以鲁写作《国语学草创》(1913)[23],批判地借鉴西方语言学[22]。章太炎为此书写了序言,了解书中内容。然而,章太炎的“语根说”未受此书启发。胡以鲁赴日留学前,章太炎已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阐释了“语根说”思路。
简言之,尚未有迹象表明章太炎在1906年之前直接或间接地了解缪勒《言语学讲义》的“论语根之言”。因此,仅凭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论语根之言”近似、章太炎在《正名杂义》中转引了缪勒的“神话为言语之瘿疣”,尚无以断定章太炎的“语根说”源自缪勒的《言语学讲义》。不妨说,章太炎的“语根说”与缪勒的“语根”学说思路近似:二者都以音韵为线索、历数语根的演变。还需留意的是,重视语音法则、梳理语根演变的思路并非缪勒首创。缪勒的语根学说扬弃了19世纪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15]176-367。因此,笼统而言,章太炎的“语根说”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有近似之处。那么,章太炎的“语根说”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有渊源关系么?或者说,章太炎的“语根说”受其启发么?这要从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Essays:Scientific,Political,Speculative,Vol.I,1868)[24]说起。
二、章太炎“语根说”与《斯宾塞尔文集》
斯宾塞是缪勒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社会进化学说著称。他的社会进化学说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影响深广[25]。章太炎是斯宾塞进化学说的重要译介者、批判者和借鉴者。1898年,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26]。该文集包含诸多文章,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了《论进境之理》[27]和《论礼仪》[28]两文。《论进境之理》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诸多方面论证“由一生万”[29]14(from the homogenous to the heterogeneous)进化法则的普遍性及原因。《论礼仪》主要探讨王治、神治、礼仪、习俗的共同起源和历史变迁。两文旁征博引,融汇诸多学科。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①斯宾塞引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材料时,往往不注明出处,也较为笼统。由于《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的最初发表时间分别为1857年和1854年,皆早于缪勒两卷本《言语学讲义》第一版的出版时间(1861年和1863年)。因此,两文有关语根的论述未参考缪勒的《言语学讲义》。但是,在《言语学讲义》出版之前,缪勒还发表过关于世界语言起源和民族起源的文章,被斯宾塞所知。斯宾塞在《论进境之理》原文中谈及缪勒与本森(Christian von Bunsen)有关世界语言同源的争论,意在例证语种的演化也符合“由一生万”的进化法则。是两文征引的重要素材。
《论进境之理》开篇即指出,包括语言在内的万事万物皆符合进化法则:“由一质之种,而变化至于无穷,吾于是知进境之理……语言文学工艺之成果,其始皆源于一,其后愈推至于无尽”[29]4。由“一”到“无穷”的进化法则统摄全文,反复出现。不同语境下,章太炎对这一法则的译文有所调整。在《论进境之理》承上启下的文段中,章太炎将这一法则概括为:“由一生万,是名进境”[29]14。
在“由一生万”的进化框架下,《论进境之理》论述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涉及词类演化、词汇演进等诸多方面[30]。论述词汇演进时,斯宾塞认为,语言从原始阶段的一词多义、语义模糊进化到词汇丰富、语义明晰,他进而援引历史比较语言学,意在说明任何一门语言中,词汇由不同的语族构成,每个语族内的词汇皆从同一语根(primitive root)衍生而来[30]17-18。章太炎将原文译作:
求语言之源,复有一术,凡字同而义异,义同而字异者,巵言日出,莫可名状。然就其支离,可以深求其理。人初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假借,归之一语。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射覆矣。乃不得不为之分其塗畛,而文字以孳乳。至于末世,有数字之义,祖祢一字,而莫能究其原者,非覃思小学,孰能道之?[29]10
一方面,译文中的“小学”对应原文的“philology”(历史比较语言学)。小学的常用概念“引申假借”被用于译介原始语言的一语多义,“孳乳”被用于翻译词汇的分化衍变。由此可见,章太炎翻译这段文字时,意识到小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一定程度上的对等性。如章太炎后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中所说,“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31]116。
另一方面,原文中的“primitive root”(语根)和“word families”(语族)超出了小学的概念范畴。章太炎将“primitive root”及其同义词“a common ancestry”和“a common origin”合译作“祖祢”;将“word families”及其近义词“a tribe of words”合译为“数字”:“数字之义,祖祢一字”意译了语根到语族的演进②《论进境之理》原文为“Philology early disclosed the truth that in all languages words may be grouped into families having a common ancestry.An aboriginal name applied indiscriminately to each of an extensive and ill-defined class of things or action,presently undergoes modifications by which the chief divisions of the class are expressed.These several names springing from the primitive root,themselves become the parents of other names still further modified…there is finally developed a tribe of words so heterogeneous in sound and meaning,that to the uninitiated it seems incredible that they should have had a common origin.”(p.17)。
这段译文随后出现在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订文》(1900)③章太炎的《订文》有三个版本。《 訄书重订本•订文》(1904)与《 訄书初刻本•订文》(1900)的内容相同,未作修改。《检论•订文》(1915)改动较大,虽然保留对《论进境之理》的引用,但隐去斯宾塞的名字,而以“远人”代称。中,文辞稍有改动:
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人之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缘传以为称。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固数字之义,祖祢一名,久而莫踪迹之也。[29]44-45
《订文》引用这段译文,意在说明词汇由少到多的演进,由此引出词汇多寡与社会文明的关联,并非专门探讨“语根说”。但是,《订文》对这段译文的引用至少表明,章太炎对《论进境之理》有关词汇演进的论述印象深刻,留意到“数字之义,祖祢一字(名)”的演化规律。
章太炎依据汉字特点,对“数字之义、祖祢一字”的最早阐释体现在《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中:
如立一“为”字以为根。为者,母猴也,猴喜模仿人之举止,故引申为作为,而其字变作伪矣;凡作伪者异于自然,故引申为诈伪;凡诈伪者异于真实,故引申为譌误,而其字则变作譌矣。又如立一“禺”字以为根……又如立一“”字以为根……又如立一“辡”字以为根……如上所说,“为”字、“禺”字、“乍”字、“”字、“辡”字,一字递演,变为数字。广说此类,其义无边,今姑举五事明之。[32]
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的“论语根”思路相近,这很可能源于章太炎创造性地融合了《论进境之理》的思路框架和中国的文字音韵学传统。从思路框架来看,这段引文对《论进境之理》译文的“承沿之迹宛然”:“一字递演,变为数字”既呼应了“由一生万”的进化论框架,也延续了“数字之义,祖祢一字”的思路,而且措辞极为相似。从具体例证来看,这段引文立足中国的文字音韵学,比《论进境之理》的概述更加专业,也更为具体。章太炎进而指出:“一字递演,变为数字,即所谓转注者也。”[32]73何为“转注”?章太炎沿用古人的表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32]73同时,章太炎表达了自己的新见解:“吾所谓首以声为之首也……吾所谓同意相授,数字之义,成于递衍,无疑于归根也。虽然,此转注也,而亦未尝不为假借。就最初言祇造声首之字,而一切递衍之字,皆未造成。则声首之字,兼该递演之义,是所谓转注也。”[32]73
章太炎对“转注”的解读既强调声韵,又重视“归根”。在章太炎看来,“建类一首”的“首”即“声首”(语根),“声首”兼具语音和语义;同一“声首”衍生出诸多文字,它们的字义都能溯源到“声首”的语义,这“无疑于归根也”。就具体内容而言,章太炎批判地借鉴中国文字音韵学,以音韵为线索解读“转注”。从思路框架来看,章太炎对“转注”的理解注重“数字之义”都归根于“声首”,承沿了《论进境之理》“数字之义,祖祢一字”的思路。
章太炎“语根说”与《斯宾塞尔文集》的渊源关系不仅在《订文》和《论语言文字之学》中有迹可循,还尤为明显地体现在《与吴君遂书》(1902年8月18日)中。信中,章太炎首次提出“语根”之名:
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唯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34]
写作此信时,章太炎刚刚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①1902年8月23日,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铅印出版。,已经对斯宾塞社会学持批判态度。这并非意味着章太炎完全否定斯宾塞。斯宾塞“探考异言,寻其语根”以揭示社会历史的思路,依然启发章太炎在中国“寻审语根”,修述中国通史。那么,具体如何“寻审语根”?由章太炎的书信可知,斯宾塞“寻审语根”的案例“繁博”,涉及欧洲“中古帝王”的词源追溯。根据这些线索推测,章太炎此时很可能联想到《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中的词源分析,尤其是《论礼仪》中诸多“神王”(God-King)名称的词源分析。
《论进境之理》的词义溯源主要概述了尊称和谦称的历史演化。章太炎将其译作:“凡尊崇之称,始进诸天,继进诸王,继进诸大臣,所进者皆巨人长者也……自卑之称,始于囚虏,其后臣民以施之朝觐,久则常人相酬酢,亦巵拾用之……综是数者,则风俗既成,本意亦渐失也。”[29]8-9类似的词义溯源也出现在《论礼仪》中,语序和措辞有所改动:“凡自卑尊人之称,大抵如是。东方人相与语,自斥言仆,或曰下走,而呼其友曰我公。……崇高之称,始以敬神明,旋以敬主父,卒以敬长者强者”[29]31。引文中的例证偏重同一语根的语义拓展,还不算是“一字递衍,而生数字”。但是,这些例证表明,章太炎已经留意语根的历史演变。同一语根衍生出“数字”的案例在《论礼仪》中更加“繁博”,尤其是有关“帝王”名称的词源分析与章太炎信中的“中古帝王之行事”相呼应:
礼仪始于敬神王,敬神王之称,习用至今,以施之称号,其名类繁矣。上世人类之王,其所部即以其神名之,为加尊号,曰某某之子,由此知古者以‘父’为神称,因以号生我者,又久而以称‘父’为常语,故或谓‘父’之与‘王’,其训诂相应……东方以其国君为太阳之弟,罗马则称其君曰天主……然后有曰天主教者,有曰握图録之帝王者,爵之命名,或亦自人名始,故埃及法老之称,义与王同,罗马该撒之称,义与帝同……[29]30-31
以上引文列举了“神王”(God-King)、“神”名(names of their gods)、“天体”(celestial bodies)等称谓,通过语义引申、词形变化衍生出繁多的名号,可谓“一字递衍,而生数名”。以“神”名演化为例,原始部落之王的名称源于部落之“神”的名字:在神名基础上添加表示“某某之子”的音节,以“神子”称呼部落之王①原文为The names of early kings among divers races are formed by the addition of certain syllables to the names of their gods—which certain syllables,like our Mac and Fitz,probably mean“son of”,or“descended from”—at once gives meaning to the term Father as a divine title.(Spencer,72)。既然“王”是神子,那么神是王的“父”(Father),因此“父”这一称谓也获得了神圣性。随着社会演进,“父”也被用于指普通人的父亲,与“神”的渊源关系弱化。通过词源追溯,可以揭示“父”与“王”的共同语根是“神”名。如章太炎译文所说,“‘父’之与‘王’,其训诂相应”。
《论礼仪》中类似的词源分析虽然“繁博”,也借鉴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但并非专业严谨。斯宾塞未对“语根”作出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分析语根的语音演变,而是从拼写变化和词义变迁的角度历数同一语根的分化演变。以语根演化为依据,斯宾塞论证了社会的历史变迁,尤其是礼仪制度的演变。作为关怀民族历史的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敏锐地留意到斯宾塞“探考异言、寻其语根”的思路及意义。受其启发,章太炎重新审视小学传统,既重视“寻审语根”、梳理汉字源流,又依据汉字源流揭示社会变迁,可谓是“造端至小,所证明者至大”。如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所言:
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候,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31]116
引文中,章太炎指出社会学对小学的启迪,未明确提及斯宾塞的社会学。然而,这段文字的思路呼应了章太炎1902年信中的“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所证明者至大”。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斯宾塞的社会学是章太炎革新小学、提出“语根说”的一个灵感渊源。
三、结 语
综合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言语学讲义》、章太炎“语根说”与《斯宾塞尔文集》译文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章太炎“语根说”与缪勒“论语根之言”虽有相似之处,但未见承沿之迹。章太炎“语根说”的一个西学渊源是斯宾塞的《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翻译这两篇长文是章太炎接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契机。两文有关词汇演进的论述在框架思路上启发了章太炎:“由一生万”的进化论框架和“数字之义,祖祢一字”的思路启发章太炎反思小学传统,在支离纷繁的汉字中深求其理,探考汉语言文字的源流体系。受其启发,章太炎批判地运用中国的文字音韵学,注重以音韵为线索历数语根的演变。从微观层面看,《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有关“神王”等的词源分析启发章太炎“探考异言,寻其语根”,由此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两文对章太炎“语根说”的启迪尤其体现在《订文》《与吴君遂书》《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对斯宾塞的创造性借鉴中。
今日,《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往往被视作章太炎的社会学译作,很少被语言学者关注。然而,在19世纪的西方和清末民初的中国,诸多现代学科尚处于形成期。章太炎善于从不同学科汲取灵感,由此反观自身的学术传统。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从翻译《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中捕捉到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其与社会学的关联,意识到小学的局限,探索超越小学的新思路。“语根说”是章太炎借鉴两文,突破传统小学的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创造性转化”[35]。因此,有必要适度地跨越学科边界,梳理章太炎“语根说”的缘起发展,更客观地认识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贡献。章太炎不仅通过《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译介了语根学说,而且创造性地借鉴发展了语根学说,既融汇中西,又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