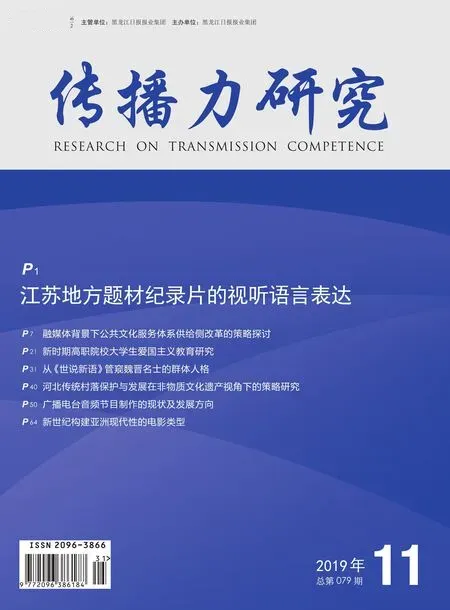跨文化交际之价值观纬度的冲突与和解
——以电影《喜福会》为例
沈咏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电影《喜福会》讲述了从中国移民至美国的家庭中,四位在中国长大由于多种原因移民至美国的母亲、与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四个女儿,由于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交际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在影片中,尽管生活在美国,自小的耳濡目染让母亲们仍保留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用心中旧有的观念去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世界。她们事事以家庭为重,认为与亲戚朋友团团圆圆才是最好的,因此才有了定期一聚的“喜福会”;顺从、保守、善于忍耐是她们从小被教育女子必须具备的“美德”,她们有意无意都想将这种价值观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这些都令成长在美国的女儿们很难接受。文化背景的差异使母女两代人在对话中有不同的理解反馈,这种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可以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来分析。
1980年,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 tede)在进行大量调查后将文化差异划分为四个维度;而后又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完善,最终确定了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气质和柔性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电影《喜福会》中母女关系之间的文化冲突恰恰体现了前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
一、“我”与“我们”
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提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描述了个人及其所在集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个人主义文化中“我”的意识盛行:从各个角度来说,个人都相对较独立于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强调“我们”的意识:个人相对于家族的脸面和集体利益,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传统社会的中国强调要压抑个体的欲望,要服从集体主义。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下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家族的利益和面子高于个体的幸福,必要时要牺牲个人成全集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四位母亲,都无一例外地孝顺、守礼、听话、恪守本分,理所当然地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次于集体利益。比如安梅的母亲被迫做了别人的姨太太,她的家人却认为这都是安梅母亲的错,认为她丢了家族的脸,将她赶出了家门。然而,当她的母亲病危时,她无视兄嫂对自己的辱骂,按照老传统从手腕上割肉给母亲做药引,希望母亲的病可以痊愈。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讲,“这种孝已深深地印在骨骼中,为此而承受的痛苦是不足道的”。受到封建“愚孝”观念的影响,母亲们普遍认为:个人的痛苦在集体、家族面前是渺小的,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难以逃脱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的母亲们,在面对下一代时也在有意无意地沿用这种传统思想去教育女儿。母亲希望女儿能够成为家族的骄傲,同时希望她们能够像自己一样听话、顺从,按照长辈的意愿行事。
然而,这种观点显然并不适合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她们更重视个人权益,追求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习惯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总想寻找自由,挣脱母亲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而活。母女两代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差异引发了种种冲突。如在影片中母亲素云一直对自己丢失在大陆的双胞胎孩子耿耿于怀,并将这一遗憾的心结全部转嫁到女儿菁美身上,致力于把女儿当成天才培养。女儿稍有不服从,母亲素云强硬地宣布:“女儿只有两种,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这个家里只容得下听话的!”女儿也不服气地反抗说:“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也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受到美国更偏向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女儿们心中“我”的意识更强,对她们而言,个人的利益和需求是第一位的。这与母亲观念中牢固的“我们”的意识,认为母亲和女儿是一家人、是一体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与母亲们心中固守的种种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集体主义观念,包括应先考虑他人再考虑自己,在饭桌上要讲究的谦虚、客气的礼仪等一系列观念都严重不符,因而产生了鲜明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跨文化冲突。
二、“我”与“你”
除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异冲突外,母女两代人观念中权利距离的理解差异也是产生跨文化交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提出的理论来看,“权力距离”指的是“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1]这种“不平等的分配”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上下级的关系之中,同时在父母和子女、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有非常鲜明的差异表现。在电影《喜福会》中,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高权力距离文化和低权利距离文化。中国的传统家庭环境下,由于父母给子女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情感到金钱都是毫无保留地全部给予,父母对孩子的经济命脉的绝对把控以及情感的全力倾注,使得父母自然而然地对孩子的生活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小到子女一次外出的许可,大到终身大事,父母对子女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相比中国的高权力距离,美国社会则更倾向于子女的独立。在子女长大成人尤其是成年以后,父母已经完成了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理所当然地应该自己从经济到精神上学会独立。对成年子女的事业、婚姻等个人问题上,美国父母会提供建议和帮助,但不会多加干涉,也很少会再去“命令”和“控制”。
这种权利距离的巨大差异,充分体现在了母亲对女儿的教育、管束中。例如,龚琳达的婚姻就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听从了父母的安排。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听从长辈的话远比子女的个体幸福和个人追求重要得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下一代永远要牢记尊重长辈、服从长辈,绝不能忤逆父母的话,否则就是不孝。这样一种绝对的高权力距离使得女儿们只想过听“你”(父母)的,没有要表达“我”(自己)的意识。因为当影片中的女儿们喊出类似于“你希望的那种女儿我永远也不当”,母亲们才会怒不可遏,认为女儿十分大逆不道,竟然敢这样违抗自己的安排。从女儿们的角度思考,在美国这种低权利距离文化耳闻目染中长大的她们远比母亲们要渴望平等,她们有明确的“你”和“我”之分。她们尊重父母,但并不能接受父母过度的不平等命令。骨子里受美国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影响,女儿们无法认同母亲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什么时候,母亲都可以管教女儿,为女儿做决定,这是为了女儿好。为人子女,就应该顺从,因而产生了种种冲突。
三、沟通的可能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影片的后半段,母亲们和女儿们逐渐从二元对立走向融合。影片本身从女儿的视角展开,以类似讲故事的方式解开了过去她所不知道的母亲们的往事,这一视角本身就是女儿在尝试了解母亲的过程。随着女儿对母亲过往的经历了解和背后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她们也开始理解和体谅自己的母亲。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最开始的排斥、过度地崇洋媚外,到接受母亲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身上与母亲共通的文化因素。与此同时,母亲们也在学会适应身处的新的文化环境,开始尝试放下一部分固有的偏执观念,从绝对崇尚集体主义到慢慢接受女儿们的个人主义观念,从要求女儿对自己绝对服从的高权力距离到尝试给女儿更多的个人空间自由,对中美文化的多种差异表现出了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在母女两代人不断的反思和理解过程中,两个文化群体之间长久存在的偏见、隔阂、排斥终于慢慢消解,母亲和女儿原本紧张的关系也在血浓于水的亲情助推下得到了缓和。
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典型、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对于现实环境下跨文化交流沟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展示出了跨文化交际中相互理解共存的可能性。通过运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对文化差异所定义的五个维度理论,我们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经典影片《喜福会》进行了分析,从而了解到: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矛盾冲突是正常的。对此我们不应该选择简单回避或者消极排斥,而应该充分尊重并努力去了解存在的文化差异,用平等、包容的心态去直面冲突,重要的是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移情,从而展开效果理想的跨文化交际,互利共存。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