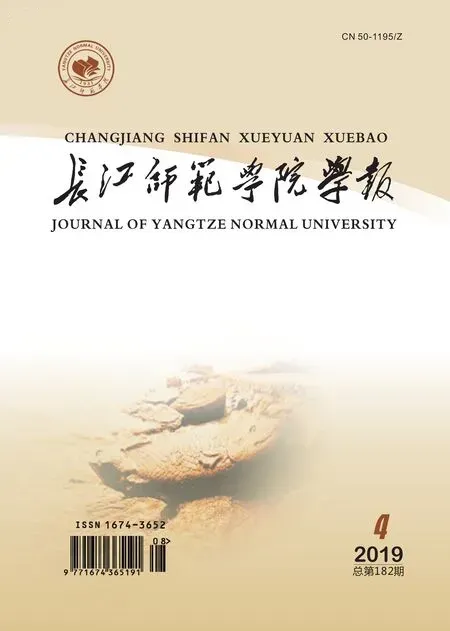城乡之间的小镇现实主义
——艾玛小说阅读札记
张雪妞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在当代作家中,艾玛是值得关注的一位。自2007年第一篇小说《米线店》发表之后,10年间艾玛佳作频出,引起了批评界注目。艾玛小说多取材于她的真实经历,这种“点燃自己”写法往往和个体经验有着紧密的连接。艾玛作为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集历史、法学专业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于一身,在写作中展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诸如城乡结构视域下的土地问题、教育问题、法律问题等。这种强烈现实指向,使艾玛小说“写什么”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论者指出的,艾玛的文学世界是“我”与涔水镇[1]。她还善于从不同视角思考、表达现实问题,尤其是历史和法学背景的融入,使她的小说具有一种抽丝剥茧般解谜破案的结构,以及层层嵌套式的叙述形式。由于诗化意境的营造,细节真实的呈现等,其小说达到了对真实性的整体把握。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进入艾玛的文学世界:首先,对于故乡的历史书写是艾玛小说的起点,由此展开对记忆中人物成长史的追寻。艾玛以涔水镇众多小人物的生计叙事为中心,结合农民、手艺人等小生产者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生选择,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小镇人复杂的情感。其次,人物善与恶的冲突集中爆发,是艾玛小说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生存境遇历史化的呈现。艾玛小说对于人物“罪与罚”的深入开掘,虽然集中于当代史的“冤案”背后个人、历史、法律、社会等多方面原因的推演,但这些问题无法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等法学或历史主题”[2]面前被轻易评判。再次,艾玛小说的意义在于,她善于写“我”的故事却不囿于个人的伤感,从而超越了个体的“我”的自言自语,而追求一种普遍性的“我们的故事”。这种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的现实态度通过节制内敛的叙述,传达出更为开阔的文学理想。
一、当代城乡结构的缩写:生计视角下的涔水镇人生
艾玛在小说《路上的涔水镇》题记写道:“故乡,我们开始和终结的地方。”[3]这可以理解为艾玛小说的力量之源。一般来说,小镇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转站,是乡土中国基层的缩影。在时间意义上,它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过去与当下的交接点,是当代政治经济变革的历史空间。小镇和小镇人进入当代文学叙事脉络,要追溯至他们对农村集体化劳动的叙述。在当代文学史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里,关于乡村的叙述和农业集体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柳青的《创业史》集中表现了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的“创业史”。这一时期的作家认为,农民通过合作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个体劳动无法获得的,因而集体化获得了穷苦农民的支持。这一叙事在合作化的历史实践中不断遭到挑战:农业集体化难以解决农民的普遍贫困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包产到户”政策实施后,集体化不再是乡土农业生产主流的叙述模式,城镇小生产者的财富叙事成为乡土文学的主流,因而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更为主流的是乡镇小生意人形象。
20世纪70年代的涔水镇,处在乡土和城市、集体化和市场化两个世界的夹缝中,艾玛深切感受到农业劳动的辛劳与收获的颠倒,“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乡人们的生活,只有田园生活诗情画意的表象,并不轻松,非但不轻松,而且十分辛苦”。“因为疾病,因为债务,或者仅仅因为歉收,因为家庭琐事,绝望很容易就将他们裹挟而去”[4]。我们会发现,艾玛揭示出农民的贫困现实与田园诗式的文学想象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对集体化农业生产劳动“创业史”的改写。《一山黄花》(2010)写生产队长老毛自参军退伍回来后,为了能让队里吃上油,带领大家集体开垦梯田种油菜,但青山的生态环境变化招来了鼠灾,饥饿的老鼠和社员争食新米,最后甚至老鼠食人。老毛这个“高大全”的带头人身上聚合了社会主义文学新人的全部美德:他不畏艰险带领青年在湖水中突击水利,儿时伙伴立秋因此身体垮掉,他深感愧疚而代为相亲帮助成家。相亲对象曹惠兰对老毛一见钟情却嫁给了立秋,婚后对老毛仍爱恨交加。失去爱情的老毛仍然勇猛果敢,在鼠灾面前无惧无畏,带领社员消灭鼠患。不同于梁生宝的是,老毛面对失去的爱情、温饱问题与生态灾难,内心极度纠结,这不仅仅是作品中抽象的人道主义表现,更是历史远景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困惑与反思。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集体尚能组织、团结饥饿的社员,社队还有“创业史”故事产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之后,“土地”在短暂地满足小生产者的致富梦想之后,就再难以产生富有诗意的气息。《浮生记》(2009)中曾经的乡土少年打谷和老毛已近中年,下一代的乡土少年新米在父亲矿难死后向毛屠夫学习杀猪,堂哥高中毕业后继续父辈的矿工生活,人们就这样带着“刀一般的刚强和观音一样的慈悲”神色继续前行。“浮生”典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恰如乡土世界中生命的静默与坚韧。
艾玛小说把这种生命的乡土底色带入到小镇人城市化的思考当中。在20世纪70年代,小镇的半城市性质给人们带来对于城市的美好想象:“也许那时年幼,并不懂得什么梦想,于是只好把离开故土当成梦想。”“(故乡人)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或许多少有些惧怕……他们把一个简单的乡村熟人社会,搬到了一个更庞大、更强势的熟人社会——城市中,以减轻城市带给他们的惶恐与无助。”[4]但是,“乡镇”这种城乡中介物决定了涔水镇人的生活,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既有传统乡土的朴质与诗意,又有现代城市化扩张带来的躁动不安与惶然失落。艾玛在小说中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
艾玛以涔水镇人的生计展开叙述,善于描写小镇人对于日常生活里的物质迷恋,以及由之生成的小镇人气质,其主要是通过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故事而展开。《路上的涔水镇》(2010)讲了三个和婚姻有关的故事:法律援助律师“我”倾听下岗女工倾诉她的离婚案,女工如愿离婚却丧失生活保障;“我”想到三十年前故乡涔水镇的婚外情案,向法学教授丈夫诉说却不被理解;乡下人梁裁缝因与军属偷情而被枪毙。前两个故事是引子,它们提醒叙述者“我”的当下生活与故乡的隐秘联系:“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涔水镇也像我一样长了两条腿,多年来一直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疾步前行,动不动就会与我不期而遇。”[3]与故乡的遭遇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史,在小说里常常表现为对人物出身的追问。不了解人物的童年,人物的完整性就难以呈现,个人成长也就很难和当代史相勾连。这种勾连在小说中有具体鲜明的物质性特征,它首先交代涔水镇人物的谋生手段,“金钱”决定了不同人物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乡下人梁裁缝因家贫和吃商品粮的供销社职工李兰珍结婚,婚后的他每天熬夜做活也敌不过票证制度下城镇户口的优越感。城镇户口优越感的显现,在小镇这个熟人社会是通过街上人的闲话传达出来的:“她们坐在裁缝铺边上的街道边扯白话,偶尔一两句是关于他的,一两句,就足以让他羞愤交加,为他的肯做,为他的乡下人身份。”[3]一再被伤自尊的裁缝后来因与军属叶红梅的婚外恋在“严打”时期被枪毙。在早先一篇小说《绿浦的新娘》(2008)中,艾玛已写出梁裁缝悲剧故事的雏形:梁裁缝的新婚妻子李兰珍去参观镇上屠夫毛二的二婚婚礼,嫁资丰厚的白嫩新娘瑶珠却原来是梁裁缝因家贫而放弃的心上人,看似出人意料的巧合却内在契合于20世纪80年代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在这一时期的乡镇,手艺人和农村小生意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的政策下追求“勤劳致富”的梦想,不少人是借助婚姻以乡下人变成镇上人而实现的。新娘婚礼上的哭泣揭示出在小镇世俗眼中的“门当户对”婚姻观中隐藏的不平等:从乡下到街上、从农民到小镇居民的身份转换之下,隐藏着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在现实生存面前悲伤无助的感情。两篇小说都以裁缝婚姻悲剧为内核,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婚姻里的两方家庭以及围绕礼俗庆典出现的小镇人物,他们带着镇上人的市井气息,这样的情感表达看似粗糙简单却隐藏着细腻敏感。
同样是写小镇婚姻故事,之后艾玛另一篇小说《菊花枕》(2010)则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化大潮下小镇逐渐丧失了吸引力,小镇和乡村中的留守者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小说以小镇上的四婆婆两代人的婚姻与爱情悬案为中心,揭示出小镇生活的安稳朴质,吸纳和消融了不可控的命运给人们造成的苦难。年迈即将老去的四婆婆执意要把菊花枕陪葬,原因是四婆婆对青年恋人的怀念。未婚夫为了政治前途被迫抛弃四婆婆,四婆婆嫁给谭木匠生下儿子德生、咏立,镇上流传着二人不是一个父亲等类流言,四婆婆在艰难处境中抚养儿子成人。流言里面藏着身世秘密,两代五口人面对秘密的不同态度呈现了不同的人生走向:四婆婆自己走过了苦难,大儿子德生是职业屠夫却又慈悲心肠,二儿子咏立困于流言选择逃避,二儿媳兰馨编造借口将丈夫的出轨行为合理化,大儿媳桂子保守着婆婆的秘密也继承了婆婆心大则安的生活态度,“德生也好、咏立也好、兰馨也好,日子都没有过到点子上。他们的心像只眼太小的筛子,什么也漏不下去,因而他们过得格外伤神费力”[5]。小镇上的生活不易,“那一天紧咬着一天的日子又未尝不是一把刀子呢”[5],从刀尖上走过的四婆婆和桂子,自有一种蛮气把薄凉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种生活态度支撑着小镇人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从乡土走到小镇,再走到城市的过程,对于进城者而言,是又一个时代的“创业史”故事。失败者在农民—工人的身份矛盾中陷入“出走—回乡—再出走”的恶性循环,而“昔日的乡村少年成为城市中坚”,也难以回避城乡问题。《小民还乡》(2010)写梁裁缝儿子小民去城市闯荡五年后回乡见闻。在小民眼里,城市是不同于涔水镇熟人社会的残酷空间,在工地提灰桶、进工厂、混社会的生活留给他的是被恶人灌强碱损伤的声带和打架斗殴遗留的伤疤,但是城市比乡村好活人的现实却吸引着乡村少年一个个走向城市。
除了物质生活条件的诱惑,城市还象征着在乡村社会遭遇不公之后,可以找到正义的理想之地。在《小强的六月天》(2009)、《小民还乡》(2010)两篇小说里,涔水镇米线店店主崔木元的哥哥小强,在青春期热血躁动时期的混混行为被镇上派出所以“公愤极大”罪名枪毙。不满于派出所长以个人威权定义“法”字怎么写的行为,崔木元坚决进城攻读法律寻求正义,但遭到了镇上人的嘲笑。小镇人的大多数已经习惯了面对一切强势力量造成的不公。艾玛继续讲述小镇人进城的故事,就是让人物完成农村—乡镇—城市空间的空间转移和身份跨越。但是,他们通过在城市求学,获得现代知识,如《白日梦》《相书生》里的知识分子何长江一样在学院里成为教授,却仍然走不出乡村生活的阴影,那些脆弱、卑微的生活印记是他们不断追问真理与现实差距的动力。
二、情与法的矛盾:当代人的“罪与罚”
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与纠缠在艾玛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罪案也往往成为作家剖析人性的重要对象。艾玛小说善于以案件为核心,审视当代人在具体历史环境中面临的情与法的矛盾冲突。只是,善与恶冲突在艾玛笔下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有着具体的阶级性、社会性内涵,它不仅贯穿于夫妻、父母子女关系当中,而且延伸到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透过艾玛的小说可以看到,那些案件中的个人悲剧,不仅仅是恋爱悲剧、家庭悲剧,还是时代悲剧。
在这些人物的悲剧故事里,生计依然是每一个人物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小说里的案件往往勾连出犯法者及其家庭与生活阶层的隐秘联系。艾玛在小说中尤为关注的是,金钱渗透到个人的身体感觉和心理层面,从而形成人们遵从的“习俗”,甚至可以让人们出卖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违法之徒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跨越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在看似自然的“习俗”之中,他们的“罪与罚”在当代社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艾玛小说中经常出现古代典故与现代案件的古今交错、以古喻今,还表现出不同代际之间的人物故事的交相叠映。通过艾玛几篇代表作的解读,可以看到她在法律正义与文学正义之间的细密思考。
《人面桃花》(2008)让读者很容易想起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意象很美的题目却和一宗少女失踪案有关,这种古典诗意与现实残忍的错愕感弥散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叙事中。故事围绕小镇上足疗店女孩小美的失踪展开,米线店老板娘桔子最有嫌疑,因小美长相像木元暗恋的少女。在小镇人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得知崔木元爱慕的少女春儿,在南方工厂打工期间手指工伤却没有得到救治而死亡,而小美出卖肉体却坚守底线被老板娘羞辱后在河边哭泣。失踪案最终无解,但揭示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镇空巢中人们面临的艰难生计与道德难题。艾玛写时代和个人的恶,也对人的道德善恶之间的亮色格外敏感。《非常爱》(2012)既可理解为爱的程度之深切,又可理解为不合常情、非同寻常的爱:律师文仲良曾因婚外情而输官司入狱,晚年出狱后的他对妻儿愧疚自责却不敢直面。妇女美和来自乡下,十年前因丈夫赶年集丢了儿子而不断奔波寻找儿子,对丈夫恨极而离婚。文仲良与保姆美和同居后同病相怜而生情,要把房产留给美和,最终满心愧疚的他却得知妻儿已经原谅自己,被生活磨损的热情最终重新燃起,“非常爱”不必再遭受道德良心的审判。
艾玛关于法律正义的思考,不仅针对当下生活现实,也带有历史的纵深感。《白鸭》(2014)分上下两部分,讲了三个“白鸭”的故事。所谓“白鸭”,乃贫者出卖性命替富者顶罪。上部讲第一个“白鸭”故事:通判大人奉命赴任C城,以观地方是否如奏报所言那样太平,细察之下发觉贱民刘流儿被父兄卖身替富者顶罪的冤案。这一案件道破了“帝国良心的秘密”,奏报文书上的物盛民安、词清讼简的公文掩饰的是水灾过后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惨状。通判大人自以为主持正义力图平反冤狱,却触犯了售卖“白鸭”获利者的利益而引起聚众哗变,最后惯于风雅的通判大人进献失传古书给圣上以求尽快回京,“眼不见为净”。下部以第三人称“他”视角讲一对夫妻的故事:他为报恩赚钱替儿时伙伴小豪顶罪入狱十年,妻杀死性侵她的继父后,母亲替她顶罪死于狱中。而小豪并没有因躲过牢狱之灾,他为养家救父卖肾后仍然挣扎在卖命糊口的困境里。看上去夫妻二人是当代“白鸭”,却原来小豪也是另一个“白鸭”。“但凡能换得了钱”的“白鸭”习俗贯通于千年历史,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资本逻辑下弱者命运的无常感。
艾玛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倾注了对于现实不公、不义的反思,并透露出理想主义知识分子遭遇的困惑。小说虽然批判了当代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但仍然企图寻找充满理解与同情世界的重建。《初雪》(2013)写了不同历史时期高校三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坚守与困惑。退休的法学教授在初雪日见到年轻法学青年,仿若看到年轻人的已逝的导师,也是自己曾经的知己般的学生,又想起自己曾经的导师。理想主义的“我”在孤独之中欣喜遇到同类:“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一个打着灯笼/能在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的人/相遇。”[6]这种期待“能在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是艾玛执着探索和追问的问题。
这一问题意识同样见于小说《诉与何人》(2013)。这一题目有着多重意涵:既可理解为情感意义上的向何人倾诉的发问,又可理解为法学意义上的控告之意[7]。小说中隐含了多个故事的交织和缠绕。小说以“我”收到一封信为开端,信这一文体在“你”“我”“他”人称转换使小说呈现出不同视角下观照现实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在显性叙事层面,是两起案件串联起三层关于“诉”说的故事:第一层故事是女读者给作家的来信,讲述自己不为人知的心事,即法学理想主义者Z在狱中自杀。第二层故事是少女小宇被迫援交杀男友案,第三层故事是作家在其小说《最后的国王》的虚构与自身现实的互相投影。在隐性叙事层面,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发问“诉与何人”,他们在无处可诉、无人可诉的困境中挣扎:少女小宇无法向父母诉说成长之困转而投向早恋男友,却为钱所迫援交而无处可诉,进而杀死男友;法学理想主义者Z为良心谴责而诉诸于法律,反而身陷囹圄;律师M的退伍伤残老兵父亲是战场上的英雄,在生活中却是失败者,内心的苦楚无处可诉;作家的理想与失落诉诸于写作的虚构王国,衰老之后的孤独与寂寞无处可诉;按摩女丽莎的欲望无处可诉……这些诉求无门的人们陷入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遥遥无望的境地:“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一再遭受侮辱与损害的无处可诉的人们如失落的国王哀叹:“我不再爱这世界/世界对我亦然。”[8]这种人与人沟通的渴望与失望的矛盾,有着契诃夫式的人与人之间内心永恒“隔阂”的影子。艾玛的超越之处在于,即便在无处可诉、无人可诉的悲凉心境中,仍然企图寻找一种人与人相遇和救赎的可能,犹如读者M和作家的现实与虚构的互相观照。
如果说法律故事的善与恶、罪与罚是艾玛对于法学正义的追问,那么她的童话寓言故事则是对于人性善恶的文学正义的思考。《歧途》(2014)以四层故事展开:作家在临近暮年想起答应儿子写一个小灰兔故事,故事中的小灰兔被人间诱惑变成人又被抛弃,作家写小灰兔故事让儿子逃回兔子纯真的世界。而兔子的纯真世界和人的残忍无情世界哪个才是真正理想的世界?“人有一样东西很珍贵,很美好,这东西叫真爱。人类的真爱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多少好兔子毁于人类的真爱!”[9]什么是真爱?在小灰兔的故事里,经不住诱惑的兔子变成了人走入了歧途,也就不能分得清人世间的话语的真假:“人的言行是不一致的。比如,他们嘴里喊着人人平等,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话不好懂,更不好说,听不懂人话事小,说不好人话才麻烦呢。”[9]在小灰兔历经人间劫难的故事里,人世间的话语是有魔力的,如何使得误入歧途的小灰兔重回理想的人世间,在这篇小说通过写这些“挽救了一颗纯真的心的故事”给孩子们看。作家并没有写出喜庆的结尾,最后儿子产生回家的幻觉,这是他对疏忽儿子困境的忏悔。写作是一种救赎,作家写童话救赎儿子的行为其实也是自我拯救。这不仅是小说中的那个写小灰兔故事的作家的理想,也是小说家艾玛的写作动力,即如何写好当代人情感结构的“罪与罚”,寻找“罪”的缘起与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中的联系。艾玛在小说中倔强地表现为对“正义”的追问,几乎每一篇有关罪案的小说都是一个法学论题。艾玛显然并不想写成法学论文和案件陈述,这种看似客观真实的写法对于法学出身的她来说并不是问题,但是艾玛小说常常故意打破这种公文式的真实,她寻找、创造文学书写形式,具有明确的的文体实验意识。文体的探索实践实则涉及一个问题:文学写作者如何以“真实感”抵达读者的内心?
三、细节与整体:现实主义如何“写真实”
艾玛小说给读者最为直观的阅读感受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重新恢复对于现实生活的整体感知能力。比如,艾玛极善于捕捉人物关系的远近亲疏,在小说中常常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器物来表达,犹如查案寻找证据一样精确、细腻、妥帖。《菊花枕》中的对于亲生父亲留下来的茶壶的喜爱与对生死的思考,是和对将逝母亲的爱以及对弟媳兰馨的怜惜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的身外物,有时就是这个人的泄密者。”[5]人与人、物与物,在艾玛小说的世界里不是呆板的罗列关系,而是有呼有应,由此引导读者去发现生活的真实性。用艾玛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追问“我们的观察力是否足够强大,强大到能洞穿现实生活的喧嚣,去发现那更为珍贵的回响”[10]?
日常生活如何发出回响,在艾玛的小说里最先表现为对熟悉的语言多义性的解谜冲动。如《路上的涔水镇》叙述者“我”在童年时代沉默寡言,但是对于大人们的言语的敏感以及汉语词汇系统的多义性好奇,使得涔水镇的表面寻常无奇的日常生活里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秘密。这种对语言的迷恋和怀疑,表现为艾玛对于语言文字与社会实践两套运作系统既统一又断裂的复杂关系的探索,由此呈现出复杂丰富的人物世界。对语言秘密的发掘在遭遇困境时,也可能面临无以言表的震惊后的失语难题。小说《失语》写自以为人生经验丰富的中年父亲反而被儿子的“歪理”教育一通,结果无话可说而造成“失语症”。“失语症”的表象之下潜藏的是现实生活里的巨变给小镇人带来的价值判断的混乱,真假难辨、善恶难分的小镇人既是被侮辱者也是被损害者,他们的词不达意或者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一种无法归罪于谁的无力感,这种伤感不只是个人的哀叹,而具有值得反思的普遍性意义。艾玛小说善于写人物群像,在“我”和涔水镇乡亲以及更多普通人的故事里,把握人物关系变动与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关联,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遗产被激活的可能性。
从这种表现细微之处整体的写法,恢复了现实主义的魅力,也克服了过于琐碎的细节描写可能造成的碎片化倾向。人物群像的塑造,使得小说中的生活世界超脱于“我”的狭小天地,走向普通人相关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营造。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哲学著作《我与你》一书中,将人生活的哲学概述为“我—它”人生和“我—你”人生:前者是人必须与及物动词联系在一起,因为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把周围万事万物视为与“我”相分离的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占有和处置这些对象和客体;后者是“我”必须栖身于“你”的世界之中,当“我”和“你”相遇,“你”必须为“我”所经验、所利用,“我”就和“你”建立了联系[11]。布伯所说这二重性,表现为如何认知个体在社会中的生计状态,通过生计关系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在“我”所经验的故事里映照出“我—你”人生的可能。布伯的哲学启示对于文学的意义在于,写作者所写的故事如何映照出读者“我—你”人生的可能,这不仅仅是要求细节真实,还要有准确认识现实整体性的能力,从而映照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爱与恨。以此观照艾玛的写作,她对城市化进程的思考以及当代人在情与法矛盾中的“罪与罚”的探索,提示了真诚的写作者要直面社会人生现实问题,把生活世界的回响带入到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