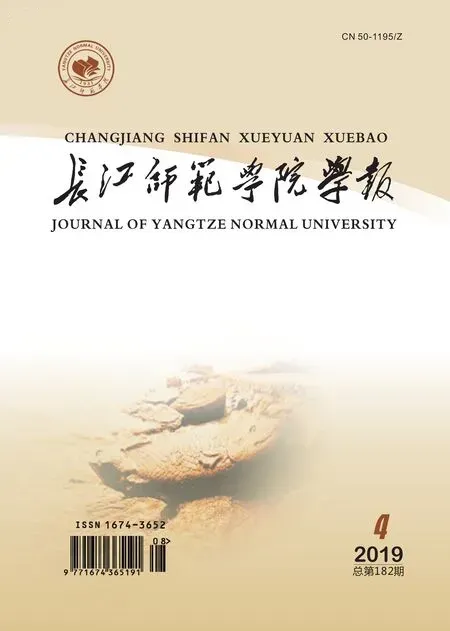试论汪曾祺的上海书写及其情感转变
孙 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引言
《矮纸集》(1996)是汪曾祺众多小说选集中比较独特的一部,因为它是汪曾祺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为背景来进行编排的创作集。在汪曾祺一生的小说创作中,写高邮、北京和昆明的居多,而上海,据他个人所说,“住过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1]195。对于汪曾祺这篇小说,及其在上海两年的经历(1946年7月—1948年2月),目前只有郜元宝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其他的研究则相对简略和零散。2017年,郜元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汪曾祺与上海的研究文章,他从手法(“间离效果”)、结构、人物描写(白描、留白)、语言(沪语)四个方面,对《星期天》进行了全面分析[2];又将“汪曾祺文学生涯和上海的关系始末”(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作了极为细致的爬梳[3];进而他又探讨了汪曾祺故里小说中的上海叙事,并从中发现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高邮与上海两地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双向互动关系[4]。可以说,郜元宝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汪曾祺研究打开了一种新思路。本文以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上海书写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与创作风格,探究其中的缘由,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照汪曾祺与现当代文学的某种内在关联。
二、1980年代回忆中的上海
1994年6月,由《钟山》杂志社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的“94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汪曾祺受邀参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汪曾祺阐发了他对城市文学的几点见解:“第一,他认为中国的城市文学仍处于萌芽状态……茅盾的《子夜》不能代表城市文学。而是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以及一些狎邪小说、妓院文学,是城市的产物。第二,城市文学必然是新潮文学,城市文学与先锋派文学紧紧相连,二者不可分开。第三,城市文学还必然带来文体上的变化。”[5]在提到城市文学的文体变化时,他还特意以小说《星期天》的最后一句来加以说明,“失眠的霓虹灯明灭在上海的夜空”只能出现在城市的语汇之中。总而言之,城市产物、先锋派文学、文体变化等构成了汪曾祺对于城市文学的总体理解。那么汪曾祺在创作中又是如何落实其城市文学的理念呢?这就需要从他所举例的《星期天》开始谈起。
《星期天》写于1983年7月,刊载于《上海文学》1983年第10期,是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篇全篇幅记叙上海的小说。通篇虽然是上海的城市书写,但却延续了其20世纪80年代写高邮、昆明等地的创作笔调,即从环境到人物的白描,再到故事的简短叙述,是典型的以20世纪80年代的笔法去写20世纪40年代往事的表现手法。
首先,汪曾祺在书写上海时所选取的时空角度是独特的。一方面,他聚焦于“致远中学”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里弄世界,从“校舍”“教学楼”到所谓“听水斋”的木板棚,虽然简单而狭小,但却成为各色人等相聚的重要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他将“星期天”别出心裁地贯穿于小说始末,除了舞会故事的那个星期天之外,在占全文三分之二的人物白描中,汪曾祺多次提及“星期天”,透过不同星期天人物的活动轨迹,看到的是各种鲜明的人物性格:校长赵宗浚的星期天,体现的就是他为人漂亮、大方,他会“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逛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或到老城隍庙去走步九曲桥,坐坐茶馆,吃两块油汆鱿鱼,喝一碗鸡鸭血汤。凡有这种活动,多半是由他花钱请客”[6]99;体育教员谢霈,在生活上是个节俭的人,但因是个棋迷,格外舍得花钱请人下棋:“一到星期天,他就请两个人来下棋,他看。有时能把上海的两位围棋国手请来……不仅预备了好茶好烟,还一定在不远一家广东馆订几个菜,等一局下完,请他们去小酌……花起钱不觉得肉痛”[6]104;再如寄住在学校里的李维廉,他的星期天“有时到叔叔家去,有时不去,躲在屋里温习功课,写信”[6]105,体现出他性格上的腼腆特质。
其次,汪曾祺通过塑造一些神秘而又传奇的小人物,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许多事都“蛮难讲”的大上海。比如一个大字不识、只会傻笑的流浪汉,竟被培养成上海滩票友中数一数二的月琴高手;又如卖小黄鱼的沈福根和首饰店学徒出身的史先生,竟成了致远中学的英文教员和史地教员;再如那个“有点神秘”的郝连都,“虽然住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子里,睡在一张破旧的小铁床上,出门时却总是西装笔挺,容光焕发,像个大明星”[6]107,从早忙到晚,与白俄结交,喜聊政治,加之热血爽朗的性格,因而在痛打美国兵之后被怀疑是共产党。总而言之,这些神秘而又颇富传奇色彩的小人物,不仅构成了小说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给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增添了几分神秘而又传奇的意味。大上海,这个风云诡谲、变化多端之地,即使是看似平常的小人物,也有着令人惊讶的非凡经历!
再次,汪曾祺透过描述这些人物的生活方式,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上海。这些生活方式既有现代的一面,比如逛公园(兆丰公园、法国公园)、看电影、泡咖啡馆(DDS、卡夫卡司)、轧马路、追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去健身房练拳击、到马场骑马;也有传统的一面,比如听戏、下围棋、拉胡琴。因而在《星期天》中,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它们显然并不是对立冲突、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交融在星期天的那幢“俱乐部”之中的。甚至在那个星期天的舞会中,人们可以品尝着“中西并蓄”的鸡尾酒(可乐兑白酒),也可以和着“雅俗杂陈”的音乐(古典、爵士、伦巴、地方流行曲),而正是这样别具魅力的城市生活气息,才使汪曾祺即使过了三十多年仍然记忆犹新。
最后,从城市文学书写的实践上来讲,汪曾祺的沪语使用是一大特色,通篇都满溢着上海话的浓重味道。比如“辰光”“铜钿”“交关舒服”“呒不啥”,这些沪语方言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说,是不能被代替的、是有劲的、是过瘾的,正因如此才更能彰显上海城市生活气息的。而结尾那句“失眠的霓虹灯明灭在上海的夜空,这里那里,静静地燃烧着”[6]112-113,更是一种具有先锋技巧的象征手法,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星期天》所描写的小人物,神秘而又颇负传奇色彩,其中叙述的故事,生动而又鲜活,他们是汪曾祺上海回忆中的那一抹抹亮点,宛如上海夜空下的霓虹灯。总而言之,汪曾祺在1983年所创作的《星期天》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凡事都“蛮难讲”的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市民生活气息的上海,更确切地说,停留在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回忆中的,是一个分外和谐的上海。
除《星期天》之外,在《读廉价书·旧书摊》(1986)和《寻常茶话》(1989)中也都有一些汪曾祺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的记叙。比如在《寻常茶话》中,他就写道:“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去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7]汪曾祺曾说:“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8]透过这些回忆性文字,可以看出,汪曾祺所书写的上海,是经过反复沉淀才最终形成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的、宛如在水晶球中的上海,却总是让人感觉缺点儿什么,也许需要重返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生活及其创作中去寻找答案。
三、上海1947:嘈杂声中的矛盾感觉
有人曾说,汪曾祺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能力和很强的一种感觉意识……比较喜欢品味自己的感觉或琢磨别人的感觉,有时候干脆就沉浸在对世界的感觉之中”[9]。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对上海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我教书,教国文,我有时极为痛苦……一种攻不破的冷淡,绝对的不关心,我看到的是些为生活销蚀模糊的老脸,不是十来岁的孩子!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整个社会。我的脚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无所攀泊,无所依据,我的脑子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我的声音失了调节,嗓子眼干燥,脸上发热。我立这里,像一棵拙劣的匠人画出来的树。用力捏碎一只粉笔,我愤怒!
但是,我自己都奇怪,一边批判着一边恨恨的叫着,忽然伤狗似的大吼一声,用力抓揪自己的头发,把手里红笔用力摔去,平常决不会有的粗野态度这时都来了;这样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有时候要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当垃圾堆中忽然发现了一点火星;即便只是一小段,三句,两句;我赶紧附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来,烧起来……自然,有时我是骗了自己,闪了一下的不是火,是一种甚么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嘲笑,使我的孤独愈益深厚。[10]
1946年9月,经李健吾介绍,汪曾祺得以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在当时的福煦路(Avenue Foch),校长高宗靖(《星期天》中校长赵宗浚的原型)曾是李健吾的学生。在这所学校里,汪曾祺负责教三个班的国文。但是从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到,汪曾祺在致远中学的教书工作并不如意,当他陷入一群无知的幼童当中,他内心的失落、苦闷以及孤独感,只能借由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表达!
黄梅天,总是那么闷。下雨。除了直接看到雨丝,你无法从别的东西上感觉到雨。声音是也有的,但那实在不能算是“雨声”。空气中极潮湿,香烟都变得软软的,抽到嘴里也没有味,但这与“雨意”这两个字的意味差得可多么远。天空淡淡漠漠,毫无感情可言。雨下到地上,就变成了水。哪里是下什么雨,“下水”而已。[11]114-115
天倒是晴了。早晴,今天一定热得很。——隔壁那个老头子咳了整整一夜。——不得了,汽车都出来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汽车!还有,那时无线电的流行歌曲,已经唱起来也!我想起那位乖戾的哲人叔本华的那一篇荒谬绝伦的文章:论嘈杂。[11]134
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6]105
工作并不如意的汪曾祺,生活也是苦闷的。《绿猫》这篇所谓的“怪”小说,正写出了汪曾祺当年茫然而又苦闷的情绪,其中透露出他对上海城市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与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星期天》大相径庭。意识流或独白等现代手法的运用在笔者看来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它与人物对话能够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人物的处境之窘迫,小说中有这样一句,“我还是敲门。剥啄一声,我心欢喜。心里一阵子暖,我这才知道我为什要来,我该来。门里至少有我一个朋友,在茫茫人海之中可以跟我谈话”[11]115,偌大的上海,“我”的心事却很难找人诉说,因而只能通过意识流或独白的方式才能得以表达。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意识流和独白,我们才得以了解20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对于上海的城市感觉:“嘈杂”是他对上海的总体印象,从早到晚的汽车声、咳嗽了整整一夜的隔壁老头儿、叫卖声、关窗声,等等,这些声音属于现代都市,都让他觉得厌恶,甚至成为打断其意识、干扰其创作灵感的因素。更不用说那《星期天》中被称赞为“很好听”的梅雨了,在汪曾祺笔下,从触觉到听觉,都是丝毫没有“雨意”的,简直就是“毫无感情”的“下水”罢了。就是这样充满嘈杂声的上海,哪里还是《星期天》中那个和谐的上海?!
我想起柏文章中提到的小院子,那时我们住在一起。想起那棵大白兰花树,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了。只有在云南那样的气候,白兰花才能长得那么大,罩满了整个一天井。开花时,在巷子里即闻到香气,如招如唤。我们常搬了一张竹椅,在花树下看书,听老姑娘念经敲磬。偶然一抬头,绿叶缝隙间一朵白云正施施流过,闲静无比……这时候!我们多半已经到了呈贡,骑马下乡了。道路都在栗树园中穿过,马奔驶于阔大的绿叶之下,草头全是露,风真轻快。我们大声呼喝,震动群山。村边或有个早起老人,或穿鲜红颜色女孩子,闻声回首,目送我们过去。此乐至不可忘。——一说,也十年了,好快!——而这里,就是汽车!汽车又一辆一辆地开出来了。[11]131
乡村生活的景观化描写,有时只不过是大都市体验的投射性产物。嘈杂的上海使得汪曾祺对昆明的往昔生活充满了眷恋之情,眷恋那个“平凡之地”的“平凡生活”。实际上,汪曾祺在昆明的生活并不比在上海好过,他先后居住在民强巷和若园巷两处,尤其是“在民强巷的生活,真是落拓到了极点”:房租是经常拖欠;睡在一尺多宽的条几上,因邻窗,隔壁鸭子的叫声吵得无法入睡;四季“都是拥絮而眠”;没钱吃饭时,或不起床,或把字典卖掉[12]。但辛酸的昆明生活在汪曾祺处于上海之时,竟变得格外恬静而又美好;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汪曾祺再次踏上作为第二故土的昆明之时,在曾经的居住之地近在跟前之时,他竟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想去了。因而,在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笔下的昆明,并非那个现实中的昆明,它常常成为其上海都市体验后的一种近似于乌托邦式的投射,这种投射只有放在作家上海城市体验的背景中,才能够显现出某种特别的意味,这是一种对城市绝望后燃起的把乡村景观化的希望!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当时知识分子共有的矛盾感觉,汪曾祺也不例外。他在《牙疼》(1947)中这样写道:“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13]通过这样一种“冷嘲”的方式,汪曾祺表达出了上海生活的无意义,上海这座充满可能的大都市显然没有让他展现出自身的价值,既然汪曾祺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是如此地不尽如人意,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留在那里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段文字中看出些眉目:
他(黄永玉——笔者注)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地刻几年。我直觉地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14]4
在去上海之前,汪曾祺的家人曾给他在家乡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但是被他拒绝了。城市与乡村,对于从事文学写作的汪曾祺来说区别甚大,即使在大都市中是“狗一样的生活”,也绝不会妥协回乡村发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汪曾祺的内心深处,在城乡生活的抉择问题上充满了矛盾,而且肯定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远非信中所表现的那样潇洒。不管怎样,正是抱着这份梦想与坚持,形单影只的汪曾祺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上海。
四、现代体验与当代重塑:文学史视野下的跨年代书写
直到此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出,汪曾祺对上海的城市书写,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与创作风格:一种是在20世纪40年代写当时的际遇,他对上海这座大都市,流露出一种虽厌恶但不得不留下的情绪,因而在其创作中,一方面是将昆明作了景观化的描写,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生活的冷嘲;另一种则是20世纪80年代写20世纪40年代,时隔三十多年,上海这座大都市,经过沉淀,在其回忆式书写中,变换成了分外和谐的模样。究竟是什么缘由导致汪曾祺的上海书写会如此迥然不同呢?如何从文学史的脉络中去理解汪曾祺的这种转变呢?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一)“冷嘲”与无法规避的现代性体验
汪曾祺在《两栖杂述》中曾写道: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他要求我)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15]
众所周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一种从文格到人格的全面影响。汪曾祺曾在《沈从文的寂寞》《一个乡下人对现代文明的抗议》等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绝望、对于愤世嫉俗、对于玩世不恭,他最为反对,“千万不要冷嘲”便成为了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嘱咐。然而,即便是沈从文自己,当其身处于上海之时(1928—1931),也和汪曾祺一样是二十多岁,“千万不要冷嘲”也是很难做到的。在那个阶段他与程朱溪、王际真等人的通信中,沈从文认为“上海住下来不好,离开了也觉得不好”[16],多次表达自己的性格在这里变得乖张、爱生气,他认为自己身处在一个无聊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甚至动不动就会有一番“冷嘲”。由此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沈从文同样是个尚未做到“千万不要冷嘲”的年轻人,而这种通过“冷嘲”的方式所表达出的矛盾感觉,简直与20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如出一辙!
相比沈从文,汪曾祺40年代在上海的际遇则更为凄苦。他连作为“文化工人”的“职业作家”都不是,更不用说什么“天才作家”“多产作家”了。加之当时上海时局的动荡、生活的颠簸,以及那个“乌烟瘴气”“胡闹”[14]2的上海文艺界对他的排斥与轻视,使汪曾祺在上海的两年,无论生活还是创作,其实并不舒展自在。生活上的落魄与创作上的不顺利,使得他对上海、对文坛,甚至对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但又不得不有一种依恋性的牵连,因疏离与依恋而产生的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感觉,同样在汪曾祺这个青年人身上。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对上海的矛盾感觉,这种在创作中所采用的“冷嘲”方式,是包含着特别意味的,这是一种无法规避的现代性体验的产物。在马歇尔·伯曼看来:“现代生活就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17]13“事实上,这种爱恨交织的自相矛盾的嘲讽,结果是人们对待现代城市的主要态度之一……说话者愈是强烈地谴责这座城市,他就愈是生动逼真地让它再现出来,使得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愈是让自己脱离它,他就愈深地与它融合在一起,他离开它就不能生活这一点就愈是清楚。”[17]262因而,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上海书写中的矛盾感觉与“冷嘲”手法,才不至于片面地否定其中的感伤情绪与悲观色彩。我们也应该更深刻地理解到,汪曾祺在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中所产生的矛盾感觉,是其最为即时地、也是最为真实地面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情绪反应。这些作品放置在汪曾祺一生的创作中,也是难以复制的存在,这种具有现代特质的矛盾感觉被剔除干净,却是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回忆式书写的一种遗憾。
(二)当代城市意识与“和谐”的美学情感
即便如此,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书写也并非是虚假的,它同样显露着逼真。在这逼真之中,汪曾祺注入了两种呈现其个人风格的元素,一是当代意识,一是美学观念。在汪曾祺的创作理念中,小说从根本上说就是回忆式的。汪曾祺在这种回忆式书写中,有意识地添加“当代意识”元素,使过去的往事带有当下的精神内核。1983年所创作的《星期天》也是如此,虽然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但从其创作背景上来看,却极富当代意味。
汪曾祺创作《星期天》的时段,正值全国开展城市化建设之际,文学当然也是紧跟着时代的脚步。1983年8月21日至30日,由天津、北京、河北三省(市)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部)发起的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在北戴河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就城市文学的命题、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就某些问题展开了争鸣”[18],最为重要的是,城市文学的内涵在此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来,即“凡以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都可称为城市文学”。此次笔会是有着轰动效应和导向意义的文学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新时期城市文学开始兴起,自觉的城市文学研究由此形成;另一方面,它对城市文学的发展远景及其与现代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有着极高的期待与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多数作家仍以传统的农村意识来观察城市,而以城市意识来艺术地表现城市的创作则十分匮乏。事实上,城市文学的产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成为文学发展贴合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从城市文学的意义上来观照汪曾祺的《星期天》,才能发现其产生并不突兀。虽然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但这是一篇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在汪曾祺的创作中,旧貌常因这种当代意识焕发出新颜。
除此之外,汪曾祺曾指出,和谐是其创作上的追求,这正是一种“美学感情的需要”[19]:在他看来,和谐的美学感情,并非是要原生态地呈现过去,而是需要将过去的一切健康化、美化、诗意化。晚年的汪曾祺,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而又明净的世界观,看待事物的方式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感伤的过去,希望除净其中或矛盾、或冷嘲的底色,转变为和谐之美。汪曾祺在后期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和谐美,实际上对于“京派”、对于他自身而言,都是一种超越:这是“从‘有意为之’转入‘自然流露’的境界……是彻头彻尾的和谐,是由内及外的和谐,是人文一致的和谐”[20]。因而从美学感情的意义上来看,汪曾祺在《星期天》中的上海书写,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不再仅仅是为了追寻那个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而是如同其在这一阶段写高邮、昆明等地一样,都是通过和谐化的美学改造,来表达他作为“通俗抒情诗人”所独有的个人气质和文化意识。在这里,我们不再去追究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书写是否符合过去的真实,而是要在当代意识与美学需要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他是如何通过构建过去来抵达和谐的境界。
(三)“回到民族现实主义”:多重资源的娴熟融合
20世纪80年代末,黄子平曾撰文指出,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具有“中介”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他承接了由鲁迅、废名等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开创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另一方面他将40年代的新文学、现代派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21]罗岗则在此基础上撰文强调,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三十年并非是毫无意义的空白,他通过阐释汪曾祺从“现代主义”到“民间文艺”的转向,来说明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思想文化(甚至包括延安文艺)同样是沉潜于其20世纪80年代创作中的内在动力,从而打通了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创作上的断裂[22]。同样是讨论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前者发现了其对于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现代派文学传统的承接,后者则是强调不应忽略20世纪50到60年代民间文艺传统对其深远影响,可以说两者都是从传统文学资源的吸收与继承上去谈及这一创作阶段的文学史渊源。
但是问题也紧接而至,纵观汪曾祺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创作及观念,似乎与任何一个文学传统脉络,无论是现代派也好,还是民间文艺也好,都无法做到完完全全的匹配:有人认为汪曾祺这一阶段属于现代派的脉络,他却一再强调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有人认为他这一阶段属于民间文艺的脉络,但他在1994年提出的城市文学理念却是如此的现代。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为何汪曾祺对于城市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在其强调民间文化重要性的时段,又加入现代派的角度。
这一问题自然还是要返回新时期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上来谈。自1983年开始兴起的城市文学,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是从题材角度去理解的,反映和针对的始终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文学(有些批评家开始改称为“都市文学”)则渐渐受到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强烈渗透,转向有意识地展现“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强调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城市文学要以现代意识为内核,并且应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形式。此时的城市文学的概念,早已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其讨论的焦点是要剔除与传统观念紧密联系的“市井小说”,并将城市文学逐渐纳入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轨道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对于城市文学来说是热闹非凡的一年,当代文学迎来“新”字号的高潮,各个刊物都鲜明地竖起了“新”的旗帜,展现出它们“新”的理想与追求,以适应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比如《上海文学》的“新市民小说”、《当代文坛》的“新都市小说”、《钟山》的“新状态小说”等,而这一切的“新”都是围绕着城市文学紧密开展的。对于这番当代文坛的“新”景象,汪曾祺则认为,“关于方法,我觉得有一个现实主义、一个浪漫主义,顶多再有一个现代主义,就够了。有人提出‘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花样翻新,使人眼花缭乱。我觉得写小说首先得把文章写通。文字不通,疙里疙瘩,总是使人不舒服。搞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让人觉得是在那里蒙事,或者如北京人所说‘耍花活’,不足取。”[1]196由此观之,汪曾祺虽不赞成各式各样的“新”,但倾向于以现代主义来概括城市文学,究其缘由,一方面在于他个人对于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在于城市文学发展现状对其创作理念的深刻影响。
20世纪80到90年代的汪曾祺在创作上“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路子应当更宽一些”[23]。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民间文艺,在汪曾祺这里,并非如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路径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或者是断裂与承接的关系,而是体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化与融合,尤其是他对于多种文学因素的交互运用,已并非是简单的现代主义转向所能概括。总而言之,此时的汪曾祺已经能够在“民族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将不同的文学传统以及迥异的创作手法娴熟地运用与融合,能够与其个人气质和文化意识融为一体而未见丝毫的生硬与突兀。
五、结语
显而易见,汪曾祺的上海书写在不同年代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与创作风格,探究其缘由,则发现个中意味: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通过“冷嘲”的方式所呈现的处于矛盾感觉之中的上海,属于无法规避的现代性体验的产物,是其最为及时、也是最为真实的情感反映与书写方式;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通过“回忆”的方式所呈现的和谐的上海,则是其有意识地融合“当代意识”和“美学感情”,将过去进行重塑的结果,是最能够显示其后期个人气质和文化意识的书写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汪曾祺的上海书写,尤其是其后期的上海书写,只有被放置在其对于传统文学资源的吸收与继承上,放置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才能彰显其意义,作为一个能够将各种传统文学资源娴熟融合的创作大家,汪曾祺无疑具有了典范意义,从而也能够为更多学者关于跨越现当代作家的转向轨迹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