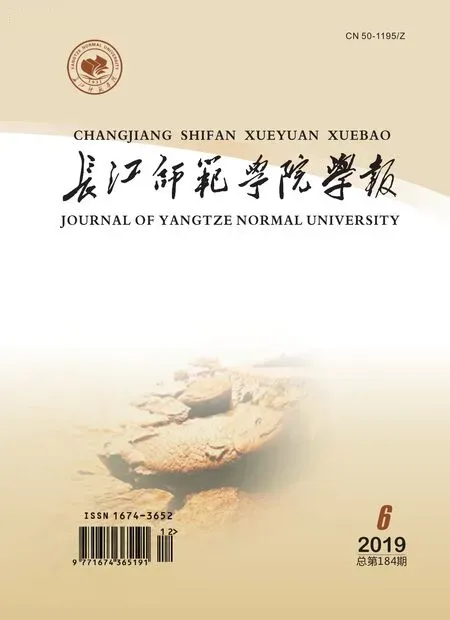胡适与他的“不争主义”思想
韦黄丹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子通主编的《胡适评说八十年》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他人眼中的胡适:有朋友们的怀念,有论敌的批评、“围剿”,还有对胡适生平事迹的考证与历史评价。对于胡适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及评价,众人各执一词,但对他的为人品行,鲜有异词。季羡林说胡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1]56。温源宁说:“在大多数人眼中,他(胡适)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1]22梁实秋认为“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学,更令人钦佩”[1]92。连政见立场相反的千家驹也赞胡适“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1]71。因而胡适在早年拥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美誉,受到人们的敬重与爱戴。其实,胡适之所以拥有磁铁一般吸引人的品格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不争主义”思想。
一
胡适虽然早年失怙,但是,其父对他思想的启蒙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影响贯穿胡适的一生。胡适读到的第一本书是他父亲手抄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2]15,诗的开头四句: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科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胡适从父亲的教导中明白,学会做人,努力成为“圣人”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学识是否渊博在其次,养成良好的品性才是首要问题。这诗的最后三句直接写出做人的方法与道理:
为人之道,非有他求: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胡适的父亲告诫他,学习知识、实践运用、勤勉守道相互补充配合,知行合一才能立身为人。如果说父亲在大方向上培养了胡适塑造高尚人格的自觉性,那么母亲冯顺弟则通过言传身教为他指明了一条温和“不争”的处世法则。
胡适自小在孤儿寡母受人欺负的环境中长大,眼睁睁看着母亲受苦却无能为力,他心疼母亲,更佩服母亲经受苦难的能力。胡适在自传中曾说:“我母亲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2]25母亲从不与家人争执,有委屈全都忍着,实在忍不住便躲在房里哭,使“闹气”的嫂子们自觉有愧,反过来劝慰母亲,家里又恢复“太平清静”。胡适在母亲身上看到一种柔弱而坚不可摧的力量,那便是“容忍”与“不争”。母亲因为从来“不争”,所以她能独自一人化解人事的纷争,保全自己,也保全了家人。正因如此,胡适欣然地、感恩地接过母亲传授给他的“不争”衣钵,在《四十自述》中提道: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2]26
其实,胡适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宽恕”正是“不争主义”在伦理上的重要体现。陶东风在总结哲学家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宽恕”观点时写道,“宽恕是一种志愿的道德选择行为”,“不是不分是非,也不是简单地遗忘过去”,而是“一种态度和情感的改变和升华:不再被仇恨心和报复欲所控制”[3]。可见,胡适的早年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宽恕”的“不争主义”思想,使他在日后应对来自各方的攻击时,可以摆脱“仇恨心和报复欲”的控制,获得心灵与思想的自由。这种“宽恕”使胡适养成了以己度人、为他人考虑的伦理观,他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4]535宽恕他人便是宽恕自己;不与人争,放过他人,也就是放过自己,这是胡适的慈悲,也是他的美德。
除了父母的影响外,胡适的“不争”思想还源自他少年时代所接触到的中西文化教育,此后,“不争主义”逐渐由一种无意识的遵循演变为有意识的恪守。在晚年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专门谈到自己的“不争主义”(“不抵抗主义”),其思想渊源有两个:一是老子思想,二是耶稣基督。胡适曾说:“老子对我的影响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张‘不争’(不抵抗)。‘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一直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老子总是拿水做比喻来解释他的不抵抗哲学。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5]57为此胡适还特意写了一首“咏柳”诗,赞扬寒冬中的柳枝能以柔软来维持生命的智慧。这应该是胡适第一次从思想上认识到“不争”的力量。留美之后,在基督《圣经》中发现“人家打你们右颊,你把左颊再转过去让他打的原理”与老子思想相通[5]58,更加深了对“不争主义”的认识。于是,“不争”思想成为胡适的“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从而塑造出“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6]。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不争主义”并不是“不疑”。胡适说:“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1]11他的一生受到杜威“实验主义精神”影响很大,而实验主义则是对“传统‘律例’的怀疑主义”[7]。因此,胡适最有名的格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即主张于不疑处有疑,并通过实验找到可靠的证据。换而言之,胡适的“不争”不等于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质疑中求真辨伪,与人争不是目的,求真证实才是胡适一生的追求。于是,在怀疑精神的帮助下,胡适虽然不与人争,但也非被他人牵着鼻子走,反而形成对待真理小心谨慎的态度。
胡适的“不争”思想还与“人道主义精神”有关,他尊重个体的人格独立与自由,待人平等,“父权”“夫权”等有违人道的伦理都是他所不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宗法礼教与争取人的解放是时代主题,譬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控诉宗法制度的四大弊端以主张个人本位主义,周作人写《人的文学》宣扬以人为本的精神,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父权与强调子女的人权与独立品格。胡适也作新诗《我的儿子》回应这一时代思潮: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8]104-105
可见,胡适的“不争”不是一种消积与被动的价值选择,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主动追求。
总而言之,父母的言传身教与求学过程中所受到的中西文化的教育,终于让“不争主义”深扎于胡适的思想中,让他能在众多的考验面前泰然自若。因此,他在人生和社会的舞台上皆能进退得宜,可以说,“不争主义”为他的人生旅程铺下了一条坦途。
二
季羡林称胡适的微笑为“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1]56,这种与世无争的“笑容”正是“不争主义”思想的外化体现,帮助胡适化解生活、学术、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在家庭生活中,胡适以“不争主义”维护母慈子孝、夫妻和睦的模范家庭,不恤人言,毅然听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胡适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对父母竭尽“为人的容忍”[4]538。尤其在婚姻方面,胡适恪守这种不与母争、也不与妻争的原则。胡适曾在致老友的信中写道:“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9]为了顺从母意,胡适接受了旧式的包办婚姻,于1917年与不大识字的传统女性江冬秀完婚,“‘胡适博士娶小脚太太’被传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10]。此外,胡适默然接受这份旧式婚姻,还体现了他对女子的宽容与慈悲。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11]江冬秀常年替胡适照顾母亲,胡适不忍心看到对他有恩的江冬秀的生命之光被吹熄。他在192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2]正是这个“不争”与“不忍”成全了这段特殊的姻缘与包括胡适在内的几个人的幸福。
众人都为此婚事鸣不平,而胡适却能小心经营,夫妻之间由最初“名分之情”演变为真挚的感情。夏志清在《胡适的婚姻与爱情》中写道:“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1]271并把胡适的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视为他俩夫妻不合的印证: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1]273
夏志清认为这首诗写出胡适夫妇“精神上毫无默契”与夫妻不和的忧愁。其实,这首情诗中的“干涉”“恼”“闹”“吵嘴”这类看似令人不悦的词汇反而流露出博士与小脚太太特殊的相处方式,其中包含着对彼此的关爱与深情。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所以不争取恋爱自由,是因为他看到传统婚姻中合乎人情的一面。在1914年1月27日的留学日记中,胡适为旧式婚俗辩护道:“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己之术……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4]262这正是大博士胡适能与小脚江冬秀相守一生的思想根源。然而,江冬秀的脾气并不好,有一回还当着外人的面对丈夫发火,胡适当场并未与妻子争吵,忍了十天之后才给江冬秀写信道:“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录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媒,我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听了这话,只装作没有听见,我面不改色,把别的话岔开去。但我心里很不好过。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决不同你吵的。但我这回出远门,要走几万里路,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像走呢?我不愿把这件事长记在心里,所以现在对你说开了,就算完了。你不怪我说这话吗?”[13]492-493另外,胡适的“不争主义”并不意味着要百依百顺、不辨是非地事事迁就,而是在保证不会产生冲突的前提下以鼓励或建议的方式去感化江冬秀,帮助她改掉一些旧习。比如鼓励妻子看书识字,这是胡适与妻子早期的通信中最常提及的事情[13]30;又如建议江冬秀放足,早在江冬秀未嫁入胡家之前,胡适便写信给她说:“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大,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不久终当禁绝。贤姊为胡适之之妇,正宜为一乡首倡。”[13]61胡适还会很客气地提醒太太不要沉溺于打牌娱乐而疏忽家庭职责与个人修养的提升,他在1938年5月5日致妻子的信中说:“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是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14]364总而言之,胡适的“不争主义”思想弥补了他与江冬秀之间的种种差距,在无法自主的婚姻中获得另一种自由——“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4]535。胡适在《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所写道: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8]60-61
实际上,胡适对婚姻的“不争”是履行家庭责任之后的心安理得,是以“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为心理自足。
在学术上,胡适的“不争”表现为不偏激,不压制人,而是以理服人。“五四”时期同样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革命”,具有“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强硬感,表现出与守旧文人一争到底的决心;而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来主张“文学改良”,所谓“刍议”则含有容许他人就此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意思。徐即在《念人忆事》通过陈独秀与胡适对新文学态度上的不同,说明胡适性格上的“矛盾与妥协”的一面。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胡适的这种“妥协”正是不以争执来决定真理的。新事物在形成之初本来就比较幼稚,如果每个人都像陈独秀那般不倾听他人的评议的话,新事物便很难摆脱稚嫩走向成熟。胡适提出新文学的“八不主义”正使众人的讨论更加完善。胡适很擅长发现问题,但不少问题连他自己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谨慎的他对没有把握的难题往往存而不论。换言之,他有时只抛出问题自己并不解答,而是激发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来讨论,自己退而不争,却充分地听取他人的论争,在必要时才参与讨论。他的这种“不争”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言:“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毕竟,我们都在孜孜以求的是客观真理。”[15]梁漱溟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信中质疑胡适的改革方案,直言若胡适找不到中国社会的改革方案,便大可闭嘴莫再谈论革命问题。胡适没有直接与梁氏争执,而是先进行自我反思,在他没有办法明确指出中国应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依旧只抛出问题来引起众人的重视,并通过众人的智慧一齐寻找解决途径。由此胡适形成“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处事之道,而这种“不为师”的“不争主义”反而能起到激发学生潜能与思考能力的巨大功效。
在道家思想中,“不争”是一种“术”,它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端赖使用此术者的存心、目的与良知[16]。胡适与周作人都曾主张过“不争主义”,但因为二人的民族节气不一样,所以“不争”的结果也不一样。显然,前者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而后者则是自私的投降主义。胡适在《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中写道: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14]400
此诗是胡适劝周作人不要投降当汉奸的诗,也体现了胡适遵循“智者识得重与轻”的高尚情操。
三
胡适尤为推崇老子的“不争主义”,常以“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自勉。老子常以“水”来喻“不争”,《老子》六十六章有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7]175又《老子》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7]22江河为万物提供生命的条件,却从不争上游而自愿流向人人所厌恶的下流之域,也正因其谦卑不争,所以才能容纳百川,成为百谷之王。胡适恪守其父的教诲,“黾勉于学,守道勿失”“以期作圣”,在国乱当头之际能沉心静气地学习新知。他学识渊博,却从不摆教授高高在上的架子,从不与人争一官半职,却多次受众人信赖委以重任。留美时被推举为“世界学生会”主席,归国后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而后任驻美国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以“水”的谦卑“不争”自居,换来“百谷之王”的美誉。胡适不仅争得了众人的爱戴与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也使他挺住了一切横逆。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各式各样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胡适很少与人争论,但无论争辩之声有多高,都无法掩没他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声音。面对保守派的攻击,胡适从中西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找证据、摆历史、明事理,从不作无理的争辩。最后逼得林琴南无理可争,不得不通过写小说来讽刺谩骂一通,反对的攻势在理亏辞穷下不攻自破。这是胡适的高明之处,自己不争,任凭对方在争辩中自露破绽。思想争论一旦失控便极易变为人身攻击的辱骂,胡适很理性,他从不参与这类论争。故鲁迅与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的“笔战”开展得如火如荼时,胡适非但不参与,还写信劝鲁迅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论之中。他于1926年5月24日在致鲁迅、周作人与陈源的信中写道:“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我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19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13]486-487从胡适的“劝架”中可以看出他拥有稳固的自我认同,因为一个人如果“缺乏一种稳固的自我认同”,那么“他的存在意义只在于不断地颠覆他人”[18]。
胡适的“不争主义”思想让他具有一种自我控制的美德,从而获得非凡的抗压力量。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宽宏大量这种崇高的美德,毫无疑问需要更高程度的自我控制,它远非凡人的菲薄力量所能做到。”[19]
总之,随着时代的推进,当胡适的弟子(唐德刚、罗尔纲等)、朋友(陈寅恪等)以及后世的学者(余时英、沈卫威等)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胡适时,胡适的精神与思想价值受到应有的重视。胡适的“不争主义”使他成为自我现实的人,“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20]。在婚姻选择上,胡适为了尽孝不与母争,接受旧式的包办婚姻;在家庭生活中,他不与妻争,包容谅解,于是得以白头偕老;在学术交流中,他不与人争,在容许他人合理匡正的过程中寻找真理;面对批判,他不公开辩解,相信时间会替他讨回公道,这正是对“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最好诠释。胡适的“不争主义”思想使他能在“无地自由”[21]的时代里获得心灵的自由,才有如今《胡适全集》四十四卷巨著问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滋润后人。但是,对于胡适的“不争主义”思想必须一分为二的加以看待。其“不争主义”虽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缺陷和不足,这是必须要加以指出的。